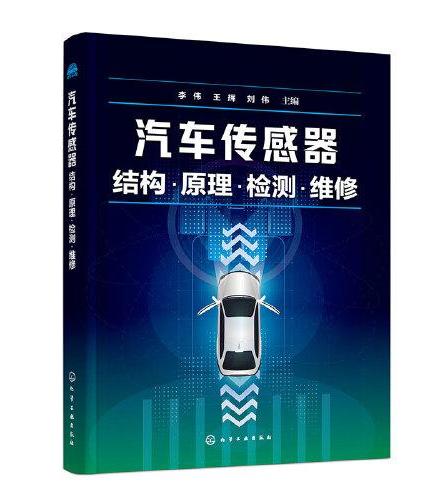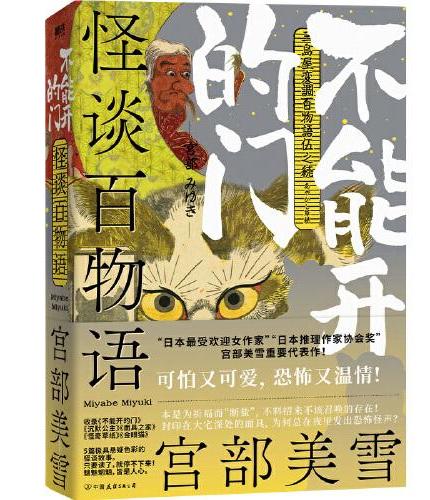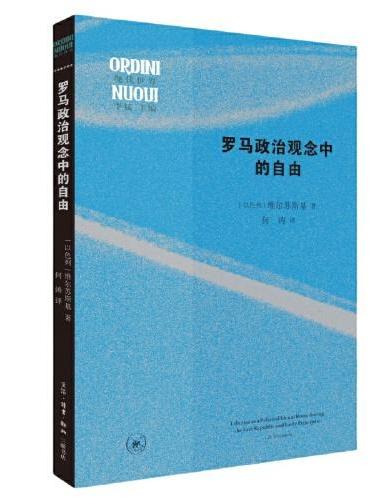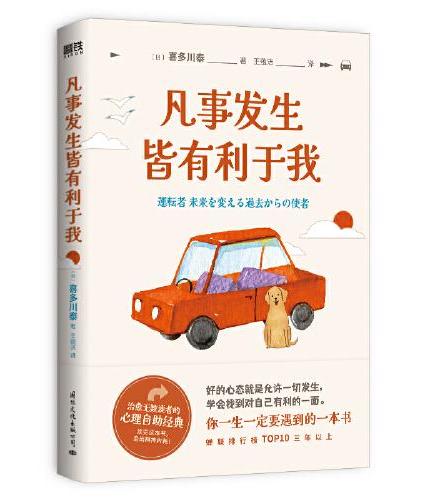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HK$
69.4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09.8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5.0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0.4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1.6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4.6
編輯推薦:
正如弗洛伊德自己喜欢强调的那样,精神分析是他的创造。精神分析是一项伟大成就,同样它还有其缺陷,这都表明了创立者的个性特征。精神分析的起源无疑应该到弗洛伊德的个性中去寻找。
內容簡介: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揭开了无意识的面纱,发明了精神分析,但他发明的这种方法却没能帮助他更好地恢复本我,持理性主义的弗洛伊德依然要让理性主宰一切,而忽略了一个本来便存在于世上的东西——爱。
關於作者:
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190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192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纳粹上台后,他于1934年赴美,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于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讲学,井先后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高校。1980年,弗洛姆病逝于瑞士洛伽诺。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他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作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包括:《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占有还是存在》《人心:善恶天性》等。
目錄
再版絮语
內容試閱
第三章 弗洛伊德和女人的关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