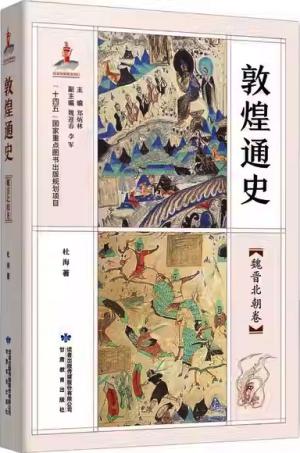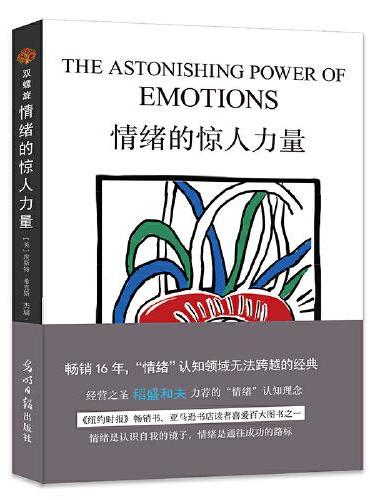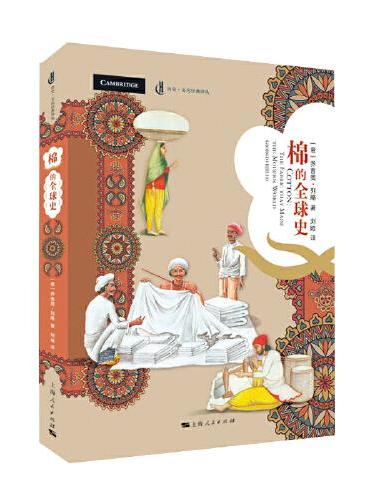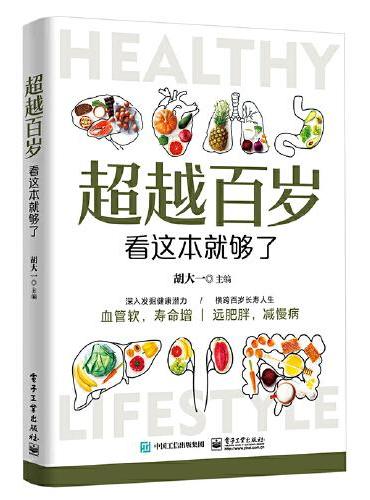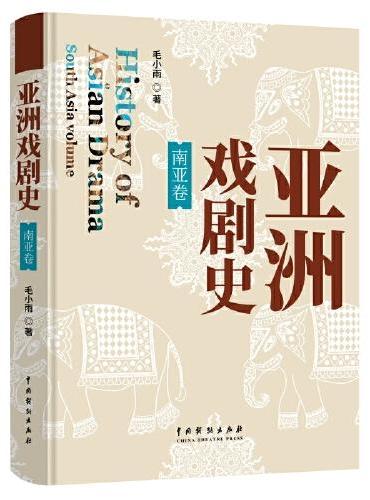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真谛全集(共6册)
》
售價:HK$
1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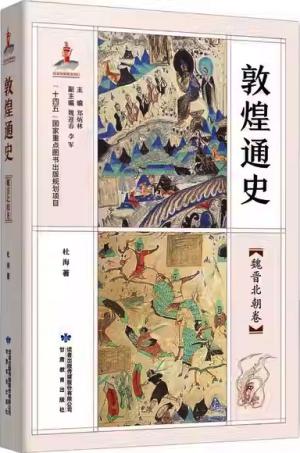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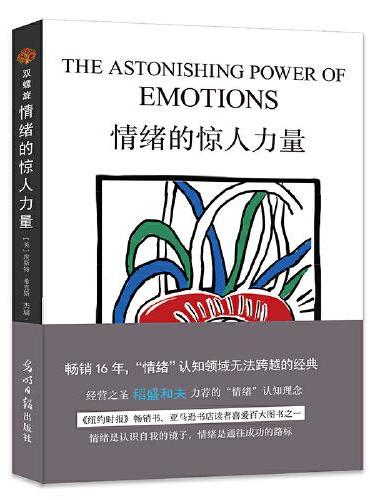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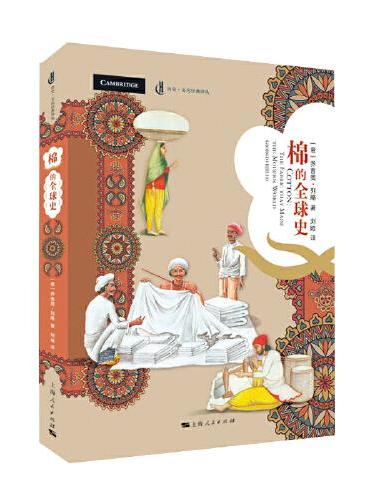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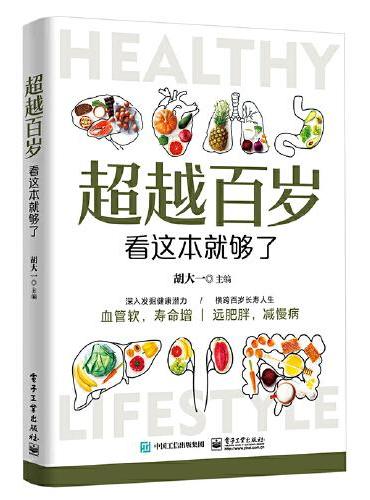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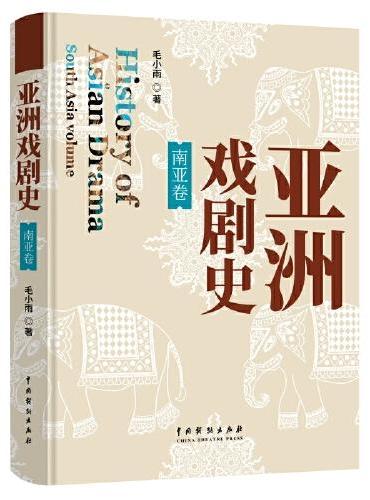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7.2
|
| 編輯推薦: |
《个人主义的孤岛》,讲了什么故事?
故事发生在九十年前,穿行于海格路环龙路霞飞路以及湖州乡下等场景,展现革命党元老遗孀明玉的身世命运。故事由一个惊悚离奇的雨夜开始,小格林受伤被丢弃在海格路公寓门口,从此中英混血儿小格林和已故生母金玉的鬼魂再也没有离开过故事主线。
明玉生于破败的江南水乡,12岁时就面临被卖入火坑的厄运;幼小的生命不甘沦落,被迫出逃,在上海街头由戏班收留。在戏班主的皮鞭和斥骂下,纤纤的弱女子阅遍世间眼色,终于出落得声色婉转地立于戏台上,端起人生个饭碗。
生命就此开始转折。这株16岁的江南弱柳被命运之手连根拔起,放置在处于“大正民主”年代的东瀛;作为国民党元老赵某的姨太太,明玉从此有了社会地位和家庭保护。她被丈夫送进日本学校念书,丈夫成了明玉的天,她服侍丈夫,满怀感恩地服侍。略读诗书崇尚日本明治维新的她,身处丈夫恩威并施下,过往经历形成她心里那口深井,根本看不透!明玉的出现带来她身边的一拨人物。丈夫赵鸿庆,早年跟随国父孙逸仙,积极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在家里却暴躁专横;虽赴日本学习明治维新,但封建根基纹丝未改。明玉是他中意的女人,将她从戏班子赎买出来娶回家,却一
|
| 內容簡介: |
|
《个人主义的孤岛》是作家唐颖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在《收获》长篇小说2020秋卷。这部小说以个人命运为线索,贯穿着历史维度,经纬交错,密密织就,再现了上海90年前形态各异、散发着声响和温度的立体生活图景。可以从中瞥见上海城市文化基因内相互缠绕的前世图谱:中国传统的江南,西欧,东欧,犹太,日本;旧封建专制和共和国,古代和现代,科学民主文明和愚昧黑暗暴力……丰满生动的细节再塑了历史的真实,消逝在过往时光中的一切又重新被打捞出来,再现于读者面前。
|
| 關於作者: |
|
唐颖,以书写上海题材小说闻名,被认为是对上海都市生活“写得准确的作家之一” 。著有长篇小说《上东城晚宴》《家肴》等,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随波逐流》,中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糜烂》《红颜》《无力岁月》《不属于我的日子》《纯色的沙拉》。
|
| 內容試閱:
|
这是早出现在上海的公寓楼,坐落在西区海格路,入口对着马路,四周无楼房,宛若孤岛,浓密的攀援植物几乎盖住了公寓外墙。
租客中有外侨、演员、金领、身份难辨的民国男女,单身,出生地不明,独门独户,自由来去……
一
193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海格路几无行人,一辆小汽车疾驰而来,停在转角的公寓楼门口。
马路对面躺着乞丐,见到小汽车一骨碌爬起身。
此时,明玉打开公寓门,从里面出来。
小汽车停在她的黄包车后面,车夫阿海斜倚在车杠上,半梦半醒之间。
车门打开,小汽车里掉出一条腿,然后,一个男人的身子从车里滚出来。
走出公寓大门的明玉,脚步停了一秒。
这是一辆美国奥尔兹车,驾驶座上坐着化了浓妆的金发女子,正欲踩离合器,眼角瞥见明玉。
“娜佳?”明玉吃惊,“怎么回事?”
金发女子朝明玉耸耸肩膀。
“他……在夜总会,喝多了……被打了,我……送他回来,还要去演出。”金发女子说着带东北口音的汉语,朝明玉摇摇手,车子又疾驰而去。
此时十点不到,海格路这一段静得如同深夜。
小汽车里滚出的男子挣扎着试图从地上起身。
明玉走下公寓台阶,乞丐迎面捧上洋铁罐,她扔了几枚角子,眼睛在看地上男子。
男子很年轻,发色略浅,他的目光与她撞上,眸子褐色,眼梢细长上斜,她一愣,目光旋即落在他的左手,他的左手下意识地握着。
他试着坐起身,但身体不听使唤。
明玉从他身边经过,酒气扑鼻。她径直走到黄包车旁,拍醒阿海,让他去扶倒地男子。
“那个人需要我们帮助。”
阿海看看明玉,眼中有疑虑,“那个人”是谁?
明玉冷静冷淡,一贯的神情,阿海是她的雇工,他不会直接问“为什么?”
阿海蹲下身帮着挣扎的男子起身,青年男子用上海话向车夫道谢,彬彬有礼。他躲开明玉目光,努力起身,可是身体不争气,沉重无力,动一动便被疼痛遏止,痛得龇牙咧嘴。
在身体瘦小力气却不小的车夫帮助下,男子终于起身,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呻吟。
明玉去挡住公寓门,她跟他们一起进楼。
在狭小的电梯间,青年男子无法躲避明玉的注视,他向明玉伸出手,介绍自己:
“我姓格林,戴维·格林。”
“是的,戴维·格林。”
她像在自语。
金玉突然出现在侧,含血丝的眸子怔怔地看着明玉,明玉一个冷战,伸手欲推开金玉似的,奇怪的动作让阿海一愣。姓格林的年轻人已经垂下手,眼皮跟着垂下,似睡非睡。
四楼的小套房,很久不通风,房间里烟气酒气和隔夜气,气味刺鼻。四墙空白,没有照片和任何装饰,辜负了大楼外观的精雕细琢。
小套房外间只有一张双人沙发,孤零零的,没有配上茶几,歪向一边,好像被随意扔置。
沙发旁的地上,放了几个空酒瓶和烟缸,烟缸里塞满了烟头,一房间的潦倒。
青年欲扑倒在沙发上,被明玉止住。
“去平躺在床上!”她用近乎严厉的口吻命令,倒是让阿海吃了一惊。
男子躺到床上嘴里嘀咕着谢谢,眼睛已经闭上。
明玉放了一张名片在他枕边。
“明天我带医生过来,戴维·格林!”
她强调地叫着他的名字似要唤醒他。金玉的面孔又出现在侧,她的眸子被泪花遮住,明玉的身体一闪,似乎要躲开金玉的面孔,她撞到阿海,金玉消失了,阿海却在向她道歉。
明玉出门时看了一眼房门的号码。
在一楼门厅有整齐排放的信箱,她瞄了一眼这间公寓的信箱,信箱外贴着一个中国名字:周飞飞。
什么怪名字?明玉皱起眉头。
回家路上,阿海忍不住嘀咕:“以为是外国人,再一看像中国人。”
“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
“那就是杂种!”
“难听吗?杂种是骂人的话。”明玉训斥道。
“人家就是这么叫的。”阿海嘀咕着为自己申辩。拉着明玉回家路上,他心里还在吃惊今天雇主的“多管闲事”超出她平时为人处世的界限。超出太多,而且是为一个“杂种”。
戴维·格林,前上海大班、英国人格林先生和金玉的儿子,一个混血儿。
明玉暗暗摇头,社会上的人对混血儿有着莫名的恐惧和偏见,连车夫也跟着鄙视。她蹙紧眉尖,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
那双眼梢细长的单眼皮眼睑活脱遗传了金玉。金玉怀孕时的恐惧还历历在目。
明玉去探望她,金玉发出歇斯底里的怪笑声。
“我会生出一个浑身长毛的怪胎!”
金玉拿出一张小报,报上刊登一幅漫画:神情恐惧的中国女人看着接生婆抱着的婴儿,那婴儿身上汗毛像动物毛,屁股后面有根小尾巴,一个小妖怪般的婴儿。长着一管大鼻子的洋人爸爸害怕地缩在角落,半只眼珠使劲斜向另一边,不敢直视自己的孩子。
明玉在想,公寓楼是否阴气太重?竟然看见金玉了!她去世四年整,从来没有出现过,哪怕在梦里。
她不会无缘无故出现!
她在回想那个瞬间,当她念着小格林的名字时,金玉兀然出现!含血丝的眸子,然后被泪水遮住……
金玉生前,明玉没有见过她流泪,倔强强悍的女人。
她是看到了将要发生的灾难?小格林又撞魔窟运了?明玉一个冷战。
他不是应该在英国读书?什么时候回了上海?怎么会住进这栋公寓?
天开始下雨。阿海加快脚步。
已经进入十一月下旬,气温还停留在初秋似的。气候反常,这两天温度上升,格外闷热潮湿,上午出一会儿太阳,中午以后便被云挡住,云下沉一般,天变低了,连着好几天,夜里都会下一阵雨。
雨水太多了,蔬菜烂在地里,菜场的绿叶菜卖成猪肉价。明玉家的佣人阿小每天和菜贩子讨价还价,有时还会争吵,回家来向明玉抱怨。
阿小粗嘎的嗓音给明玉安全感,她喜欢听阿小说话,阿小带来市井的纷扰,没有她,家里会少了很多活力。
丈夫去世后,家里仿佛少了一半人口。丈夫脾气暴躁,经常发怒,但他是干大事的人,他把外面的世界带进家里,让明玉产生错觉,仿佛,她也在参与这世道的变化。
从湖州搬回上海市中心,她反而觉得更冷清。她自己就是个看起来冷清的人。
这是一场中雨,落在梧桐叶上,“哗哗哗”的,有大雨的声势。气温迟迟不下来,梧桐叶还未掉落,才会有雨落树叶的喧哗声。
这一路少见行人,连乞丐都消失了,他们躲进弄堂过街楼下。
这“过街楼”是建在弄堂口上方的房子,楼上住人,楼下通行,可以避风雨。每每雨天,路过有“过街楼”的弄堂,看见满地躺着的乞丐,明玉便会叹息,这城市亏得有“过街楼”。
奇怪的是,今天经过的“过街楼”空无乞丐。街道好像一张绘到一半的画,只有房子和树,还未添上人。是的,街上空寂得古怪,空寂得让她心里发怵。
眼前的一切好像渐渐成了平面:雨,只有声音,并未模糊视线,尽管路灯是黯淡的,房子却格外清晰,清晰得失去立体感,却又不那么确定。
明玉慌张了,她睁大双眼,死死盯着双手拉着车杠、步履不停朝前奔跑的车夫背影,有些瞬间,她几乎以为他也会消失。
明玉相信,关于鬼魂,阿小肯定懂得比她多。
可是阿小晚上回自己房间,她住在隔壁弄堂口搭出的一间只能放一床一桌的棚屋。
经过阿小的棚屋时,明玉很想敲门进去坐一下,却又忍住了。阿小三十不到,小小的个子,为人泼辣,却忠于明玉。她从浙江农村到上海帮佣,除了不会做菜,家务活一把好手,让明玉回到有秩序的生活。
明玉重回上海三年有余。她和阿小相处也已经超过三年,阿小几乎是明玉在上海的半个亲人。
明玉自己住的弄堂没有“过街楼”,弄口有镂空大铁门。白天大铁门打开,夜晚关上,镶嵌在铁门上的一扇小门开着,夜深时上锁。
已经十一点半,大铁门关上了,黄包车只能停在弄堂外。
今天晚上,因为小格林的耽搁,阿海比平时晚了一两个小时回家。明玉给他小费补偿,心里却在暗暗奇怪:她次走出海格路的公寓门时看过表,当时九点三刻;送小格林上楼顶多耽搁十多分钟,可她第二次走出公寓时再看表,时间已经流走一小时。明玉像被击打了一下,她是被时间的莫名流逝给惊到了。
她跨进铁铸大门镶嵌的小门,弄口地上的马赛克被雨水冲刷得闪闪发亮,亮得像上了一层玻璃漆。她从来没有发现夜晚的马赛克这么刺眼过,她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在梦里。今晚金玉的出现,让眼前一切都变得异常。
二
明玉走进弄堂,唱机高分贝音乐声和鼎沸人声一起制造的噪音,让整条弄堂变得热哄哄的。声音是从她住的楼房传出,明玉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六。周末晚上,是一楼的白俄人玛莎和马克家的派对夜,他们喝酒跳舞,然后打架结束。
明玉居住的这栋楼房,单独屹立在弄堂右侧,前后左右没有挨着房子。玛莎和马克的派对夜,只骚扰到同楼人家,尤其是二楼。
二楼的前楼房间住着白俄契卡,周末夜晚他必定逗留在外,直到凌晨才回家。
明玉住二楼的后楼和亭子间,夹在白俄人中间。
这条弄堂的居民,以白俄人为主,夹杂一两户英国人和海外回来的年轻夫妇。
明玉当初搬进这条弄堂,就是想隔离本地邻居小市民的流言。
她生活态度端庄,言行谨慎,不会给人留下话柄。但戏子出身这件事,成了她一生的心理障碍。
与外国人同住的好处是,有语言隔阂。这是一道阻隔闲言碎语的墙。
其实,白俄邻居不会在意她的出身,即使知道了又如何?他们自顾不暇,为了讨生存,白俄女人不也都纷纷入了风月场?出身好家庭的白俄们,流离失所漂泊他乡,他们的价值观已被现实改变。
明玉的住房面积有点紧,和白俄做邻居也有诸多不便和困扰。楼下玛莎家放纵的周末派对,也许会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不过,大女儿朵朵很听话,周末总是关起门看书。她担心的是鸿鸿。
鸿鸿这孩子才四岁,已经会说几句俄语。玛莎家经常发生失控事件,她家周末派对夜,醉醺醺的客人们大叫大嚷时破口而出的、酒气浓郁的俄语粗话,只要重复过几次,鸿鸿就能说了。好在他不太明白俄语的中文意思,也没有机会和俄国人对话。
明玉考虑搬家,所以才顶下海格路的公寓房,但希望再延宕几年。她现在的生活很需要阿小,阿小不方便跟着明玉搬迁移动,弄堂口的棚屋是她安身之处,此外,阿小还在玛莎家和环龙路其他一两户人家做小时工。再说,朵朵的钢琴老师就在同楼。三楼的白俄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夫妇是音乐家,妻子薇拉和丈夫伊万,在上海教钢琴谋生。女儿每星期上钢琴课不用她陪伴,对于惜时如金的明玉很重要。额外的好处是有音乐环境:楼上的琴声,楼梯对面的琴声,弄堂里的琴声,住到这里,她算领略了俄国人对音乐的热爱。
此时,穿越整条弄堂的喧闹,并未让明玉烦恼,甚至成了一种需求。她今晚受惊于金玉的鬼魂、奇异的街景,她需要人世间的噪音,渴望旺盛的人气,让自己回到现实世界。
走过一楼敞开的房门,透过烟雾,看得到翻倒在地的椅子,有人躺在地上,但并不影响搂着跳舞的男男女女。房间拥挤,他们只能在原地踩舞步,借着舞步接吻抚摸。常常因为吻了、摸了别人的老婆或情侣,便开始打架。
她瞥见玛莎被搂在陌生男子怀里,却没有看见马克。马克身高一米九零,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近,明玉很少见到他。
这天晚上,明玉次羡慕起白俄邻居,这些被上海本地人称为“罗宋人”的白俄,他们流落他乡潦倒后,仍然有能力抓紧时间寻欢作乐。
明玉未在一楼停留,急着上楼进浴室洗沐换衣。弄堂短短一程,她手上撑伞,裙摆和鞋袜仍被雨水溅湿。奇怪的是,头发不过飘到了雨,却也不至于湿成滴水,难道伞不是首先遮住头颅?她几乎怀疑自己刚才没有把伞撑开来。
她进不了浴间,门从里面锁上。浴间灯亮着,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可看出里面的模糊身影。
这间二楼浴室,是她和契卡两家合用。
前楼的灯暗着,契卡没在家,周末夜晚,他去夜店消磨,不可能在家。
她推开后楼房间门,朵朵半卧在她的小钢丝床上看书,她是个书迷,总是三番五次催着才肯睡。明玉进屋时,朵朵头也不抬,表明她在生气。
儿子鸿鸿已经入睡,七歪八扭地横躺在她和鸿鸿睡的四尺半的棕绷床上,脸上还留着泪痕。
“弟弟又闹了?”
明玉这一问,是让朵朵明白,她已经看出朵朵惩罚过鸿鸿了。
朵朵不响。
朵朵虚岁十二,像个小大人。明玉不在家时,她帮着照看弟弟。她性子急躁,弟弟要是不听话,教训起弟弟疾言厉色一点不心软;把她惹急了,还会动手打弟弟。当然弟弟也不会买账,会还手,于是便有几个来回。后,弟弟还是要讨饶的。
明玉并不阻止朵朵代替自己惩罚老二,为了自己在家时间太少,得放一些权力给老大管住老二。她告诉朵朵,弟弟太闹可以打几下屁股,但不能打脸。她告诉朵朵,打脸是非常可怕的侮辱。母亲的话让朵朵记起往事,她看到过父亲扇母亲耳光。她因此向母亲保证,不会打弟弟耳光。
但是,明玉很忧虑朵朵的坏脾气。她性情更像父亲,或者说受了父亲坏脾气影响。在她幼年时,经常看到父亲对着母亲发脾气,动辄怒吼摔东西,打母亲的情景更是深深刻印在她记忆中。朵朵因此有点恨父亲,却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坏脾气。而弟弟又特别缠人,他一岁不到父亲去世,母亲和姐姐都在小心呵护他,鸿鸿是在娇生惯养的氛围中成长的,格外敏感脆弱,别说打,即使骂他几句,也会哭闹不已。
明玉不想斥责朵朵,她知道,斥责只会让朵朵更加叛逆。这孩子吃软不吃硬,她唯有找各种机会跟女儿讲道理,让她明白,人挨打不仅肉体痛,心里更痛。
此时,明玉没有再说话,顺手理着姐弟俩扔在房间各处的衣服,她几乎忘了还在滴水的头发,事实上,她的头发莫名其妙地干了。
朵朵偷偷瞥了明玉两眼,忍不住发起牢骚。
“今天我给他唱了两小时歌,我会唱的歌都唱完了,他还不睡,我不理他,他就哭,哭了一会儿自己就睡着了。妈,你不在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家这个讨债鬼(沪语发音:jū)有多烦人。”
“讨债鬼”三个字让明玉忍俊不禁,这是以前朵朵吵闹时她说的话。朵朵做了七年独生女,被妈妈捧在手心,小时候比弟弟还难缠。
明玉现在没有心情和朵朵聊弟弟的事,她急着洗澡换衣服,可是浴间有人。显然,楼下玛莎家的客人又来占用二楼浴间。
“你又忘记给浴间上锁?楼下乱七八糟的人上来用马桶,多不卫生!”明玉责备朵朵。
“我刚刚上过厕所,上了锁呢!”朵朵指指门后挂着的一串钥匙。
“浴室里面怎么会有人?”
“是契卡吗?”
“好像是个女人,契卡的房间灯暗着。今天周末,他要到早晨才回来。”
朵朵从床上跳起来,打开房门,冲到走廊门外,她站在楼梯口,几格楼梯下便是浴间。
“妈,你来看,浴间明明上了锁了!”
“是锁着,从里面上锁。”
“你来看,锁明明挂在门上。”
明玉走到楼梯口,她看到浴间门关着,门上挂锁镀着克罗米(铬)的锁柄,在走廊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亮。
明玉一惊!
“太奇怪了,刚才明明看到里面开着灯,有个人影……”她嘀咕着,又戛然而止,不想吓着朵朵。她边催朵朵上床睡觉,边去拿煮水的大铜吊准备到浴间灌自来水。
老实说,这一刻进浴间她得有些勇气。
“我陪你去,”朵朵觉得母亲的神情有些奇怪,“我正想上厕所呢!”
说着,朵朵已经走下楼梯进了浴间。
明玉把灌满水的大铜吊放在煤气灶上煮着,煤气灶就安在房间门口的走廊上,她从煤气灶旁的料理台上提了两只热水瓶去浴间,先给自己洗头。
朵朵要陪明玉洗头,她等着用脸盆里的温水帮妈妈冲洗头上的肥皂泡沫,平时,这件事由阿小来做。
洗头时明玉询问朵朵练琴的事,朵朵就没好气了。
“你不如直接上三楼问薇拉。”
朵朵烦母亲问练琴的事,她不太喜欢三楼的钢琴老师。薇拉神情严厉,朵朵能看懂她眸子里一抹不以为然。“你以为练练琴就能成为钢琴家?”早熟的朵朵几乎能听见薇拉神情里无声的责问。
朵朵跟着母亲从湖州的大宅搬进上海弄堂的小房子,家里变得非常局促。母亲整天忙饭店挣生活费,却还要为她付学琴费。她想赶快长大,帮着妈妈一起经营饭店,童言无忌直接说出“等妈妈死了,我就可以当老板娘”的话。明玉大发雷霆,不是因为朵朵说了忌讳的话,而是生气朵朵没有志向,辜负她的期望。她告诉朵朵:自己辛苦成这样,是为了给女儿创造条件,以后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即使当不了演奏家,也可以当钢琴老师,这个社会,给女孩子就业机会很少,等等等等。朵朵次看到明玉失控,忽然就有了压力。学琴这件事变得自觉了,但她就是不喜欢钢琴老师薇拉。
“如果你要我好好学琴,我要换老师。你又不懂薇拉,她根本看不起我们,她心里很傲慢。”
明玉一惊,撩起湿淋淋的头发看住朵朵,朵朵的神情让明玉明白她不是随口说的。
“我会考虑,给我一点时间。”
朵朵点点头放松地笑了,让明玉放了心。
明玉洗完头,煤气灶上大铜吊里的水也沸腾了。这只大铜吊,至少可以灌满三只热水瓶还多。
明玉用去污粉飞快地擦洗一遍浴缸,给浴缸塞上塞子,一边放冷水同时把铜吊的开水倒进浴缸。蒸汽弥漫在浴缸上,很快就会消失。
明玉此时坐在浴缸温水里,觉得生活好像又回到正常轨道,没有任何异样。
二十五支光的电灯泡照得浴间亮堂堂的,白瓷灯罩和墙上的白瓷砖被阿小擦得雪白。暖色调的灯光里,浴间像一曲明亮的生活颂,是给予明玉快乐的空间。她对墙上的白瓷砖、对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喜爱,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
她在日本见识到日常生活的文明设施。从日本回来,她曾跟随丈夫回他老家湖州的小镇住了一阵。虽是一个丝绸业发达的富庶小镇,生活设施传统落后,生煤炉倒马桶,终究不方便也不卫生,她那时像害思乡病一样思念日本。
她对自己的这种“思念”有罪恶感,年幼时温饱都无法满足,听到父母商量着要把自己卖去花船,她逃出苏州来上海,遇上了戏班子……她的人生是一次次地逃离,终于逃离她的底层。
记得自己在丈夫家乡用木桶给三岁不到的女儿洗澡,引来家里女佣围观,女佣把邻居也叫来了。邻居家的婴儿身体痒哭闹不止,她便为邻居示范如何为刚出生的婴儿洗澡。哭闹不已的婴儿,洗过澡便安静了。但是给婴儿洗澡这件事并不容易,明玉每天被邻居恳请去为婴儿洗澡,直到婴儿满月。那一阵子,邻居家有头疼脑热也会来咨询明玉。
明玉在小镇受欢迎,便有阴风吹来,邻里间突然传言她曾做过戏子。在他们的流言里,戏子似和卖身等同。但丈夫并不在意,他是从戏班子将她赎买出来。她视他为恩人,他即使没有给过她幸福,至少将她解救于贫穷。她也没有辜负他,她一路帮衬他,日常生活中没完没了的麻烦,是她在解决。以后,在他虚弱的时候,她是他的拐杖。
给朵朵换个钢琴老师算什么事?朵朵觉得有人看不起她是好事,这是让她不甘心的动力。
可是……可是,薇拉凭什么看不起朵朵?明玉胸口涌动怒火:她可以受尽窝囊气,却见不得女儿受委屈,尤其是被人轻视。朵朵在温室里长大,没有漂泊没有流亡,从小读书学钢琴……你们不过是以前有点钱,咱家朵朵的父亲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那又怎么样,他周围那些曾经的有钱人衰败潦倒时,样子也一样难看,也许更难看。明玉在心里骂着粗话,她在农村长大,又在戏班子混过,她不是不会撒野。在陌生的地方,比方说公交车上,要是有人动手动脚,她会武力反击,一点都不会示弱。然而,在一个笼罩着所谓文明气氛的小社会,她也会收敛成一位淑女。
她心爱的朵朵,脾性和容貌都更接近她父亲,眉宇间的刚毅,有几分男孩子气。儿子鸿鸿却太秀气,朵朵是有点嫉妒鸿鸿女孩般的精致。但是,朵朵弹琴有力度,初学钢琴时老师就赞扬过。那时是一位英国老太太做她的钢琴老师,也是就近找,在同一条弄堂,他们当时住在环龙路的另一头。明玉好像和环龙路有缘似的,连饭店都开在环龙路。
朵朵会有出息的,不一定在音乐方面。明玉现在已经不像前几年,执着地要让朵朵在钢琴演奏上有出息。随着社会更加开放,女孩子的职业机会也越来越广,比方,朵朵也可以去学医。自从朵朵生了一场大病,她便有了让女儿去学医的念头。当然,她会尽快帮朵朵换钢琴老师,绝不能让女儿内心有那么一丝自卑,因为她自己,全身上下浸透了自卑。
明玉擦干身子穿上睡衣吹干头发,心情已经恢复平静。女儿那番抱怨,让她一时忘记海格路的遭遇,潜意识里,是想放在明天再仔细思量。她感到极度疲倦,闭上眼睛的同时已经沉入梦乡。
夜深浓,有人在哭,金玉在哭!不,金玉不会哭,她从来不哭!她在心里自问自答。
然后她听见自己的鼾声,她责备自己,你就是心硬!有人在哭,你睡得打鼾!
接着她发现家里的窗子有破洞,有人从破洞钻进屋,就像黄鳝从泥洞里钻出。她骇得坐起身,听到金玉的声音:
“明玉,你忘记了,你忘恩负义!”被怨恨包裹的声音。
金玉站在床边,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明玉害怕得闭住双眼。
明玉心里想,金玉说话总是这么生硬,她演小生,戏里的男人说话却温柔。嘴里在回答金玉:“我明天还会去看小格林,不晓得他遇上什么麻烦!你看得比我清楚,给我一点暗示吧!”
金玉的嘴在动,她听不见,一急便醒了,打开灯,窗帘拉得密密实实,刚才是个梦。
她盯视浅绿底色白色花纹的四墙,才能肯定自己睡在上海某一条弄堂自己的房间。
她在半醒之间常常以为自己睡在马路上,睡马路的噩梦跟随她很多年。她因此不让白天的自己停歇下来,所有的努力是不让自己和孩子们回到睡马路的日子。
她看钟,才两点,没了睡意。
楼下的派对已到尾声,梦里听到的哭声是从楼下传来,玛莎在哭,马克在说话,玛莎的声音越哭越响。平时他俩偶尔也会吵,通常是玛莎在斥责,很少听到她哭。明玉坐起身披上衣服打算下楼去劝。
以明玉的处世原则,玛莎家或者说邻居家的吵闹她是不会管的,尤其是夫妻之间吵架。然而今夜,她走出房门走下楼梯进入别人家的纠纷中,更像是为了冲破裹卷住自身的梦魇。邻居生命力旺盛的冲突,驱赶了令她窒息的阴暗。
马克近经常夜晚出门,今天连自己家的派对都缺席,这是玛莎发火的缘由。
马克说,他有重要的事情,不是玛莎怀疑的与其他女人苟且。马克的中文述说能力差,连他的辩解都是由玛莎转译给明玉的。到底是什么重要事情?现在还不能说!玛莎一边与他吵,一边还要翻译,虽然她的中文也是歪歪扭扭,还带着点东北口音。这一边争执一边翻译的过程,让明玉觉得有几分荒唐竟笑了,玛莎也渐渐平静。
玛莎年轻时是个美女,如今四十出头,身材已经发胖。她五官端正如雕像,高高的颧骨,两颊微陷,脸型骨感,有着古典的贵气。旁边的马克,高而瘦,留着络腮胡,几分落魄相。他俩站在一起,不是很般配,是马克配不上玛莎。当然,看起来般配的,未必能成一对,明玉此时想起她的“他”,心里有些感慨。
深更半夜,邻居下楼劝架,玛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哭叫声影响了别人,于是暂时休声。
明玉的心情也转换了,世俗噪音令她暗暗相信驱赶了鬼魂,突然有了踏实感。
她再上床却难以入眠。此时,小提琴声替代了刚才的哭声,是隔壁弄堂的女人在拉琴,女人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她家二楼楼梯窗口。女人总是深夜才开始拉琴,背对着关闭的窗口,看不到她的脸。窗口的女人,总是戴着帽沿上有蕾丝装饰的黑色呢绒帽。对面房间墙壁漆成浓郁的紫蓝色,从来不拉窗帘。
阿小说,对面窗口的女人是罗宋人,是神经病。阿小不会追究这个罗宋人为何得神经病。阿小在不同人家做小时工,收集了不少八卦。她上午和傍晚在明玉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照顾明玉的孩子。
明玉搬来上海经营饭店时,金玉已经离世。
她们曾经是戏班子的结拜姐妹。金玉唱《薛仁贵征东》里的薛仁贵时才十八岁,是戏班子的台柱子。
明玉被戏班子收留,才十二岁。她是家中长女,年纪尚幼已具美人坯,母亲原本抱有希望,让她读私塾认字,以后有资本嫁好人家。
她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十一岁时母亲带她和弟弟改嫁打渔的鳏夫,搬到了船上。明玉十二岁那年,母亲突然和继父商量,准备把她卖去花船,她嗓音好,爱唱歌,又识字,可以多卖几个钱。明玉在水上生活的一年里,目睹花船上的糜烂,她逃走了。
明玉在戏班子做小群演,有天分,格外努力,也会看人脸色,她乖巧得像跟屁虫一样地跟着戏班子红的金玉,很得金玉欢心。“明玉”是金玉给她取的艺名,明玉拜金玉做干姐姐,是点香磕头,有仪式的。
那时,金玉已经是格林先生的相好。金玉做歌女时和格林先生认识并成了他的情人。那时的格林还是一名海关小职员,但很快从低薪海关下层职员发展成做外贸的商人。金玉是个有主见的女人,一心要进戏班子为自己挣前途。她和格林先生同居后,不再卖唱,让格林先生为她付费拜师学戏曲,从歌女转身成为戏曲演员,如愿以偿唱上了主角,让英国情人为她骄傲。
金玉唱主角,又有个英国男朋友,在戏班子里气焰胜过班主,或者说,班主也要讨好她。
明玉在戏班子讨生活,有强烈的危机感。她害怕被抛回漆黑的街上,学艺刻苦。即使如此还是挨了不少打,班主打,金玉也会打,班主是急于让她上台赚钱,金玉是要她成材。
后来唱《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扮司马相如的金玉让明玉唱卓文君,那年她才十六岁。
在金玉严厉的指导下,她扮演的角色才有了光彩,渐渐坐稳旦角的位子。这出戏让她赢得与金玉并肩的“双玉”美誉。出去唱堂会时,金玉点名让她做搭档。
有一天她和金玉去饭馆唱堂会,遇到赵鸿庆,她的命运因此发生巨变。
赵鸿庆是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他们当时为躲避袁世凯迫害暂居日本。堂会相遇那次,是赵鸿庆回上海参加一个会议,那天是去饭馆和同仁商讨会议议题,便遇上金玉和明玉搭档唱折子戏。
赵鸿庆中意明玉,他给了班主一笔钱,把她从戏班子赎出来。
明玉跟随赵鸿庆去日本定居。她离开上海之前去金玉家道别,金玉向明玉抱怨,和格林先生的关系,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连你都去了大户人家,我怎么可以比你差?”
金玉就是这么说的。是她成就了明玉,她对明玉讲话不用顾忌。
戏班子的姐妹们都很羡慕金玉,虽然她的外国男朋友不肯和她结婚。是的,他们好了至少五年,看起来没有婚姻前途,但也没有生存忧患,假如戏班子解散,格林先生会资助她。金玉的人生很容易激发身边小姐妹的野心,明玉也是暗暗把金玉当作自己的人生标杆。
现在,却是明玉先离开戏班子,她对金玉有内疚。
金玉倒是觉得正常。人往高处走,是金玉的座右铭,但她还是没好气地扔给明玉一句话:
“有本事让他娶你。”
那时,金玉已经有了两岁的儿子小格林。
赵鸿庆带着明玉返回日本,在日本报上登了一条结婚告示,请同仁们来家里吃了一顿饭,让明玉作为主妇亮相一下,明玉便成了赵太太。她很快又知道,她是姨太太,赵鸿庆在湖州有个明媒正娶的太太。明玉当然不会计较,她觉得对于自己,已是高攀了。
她没有把“结婚”的消息告诉金玉,怕引起金玉的嫉妒或者嘲笑。金玉棱角尖利的个性,让明玉畏惧。
明玉此时回想,她生命中的两个恩人都很难相处,另一位是她亡夫赵鸿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