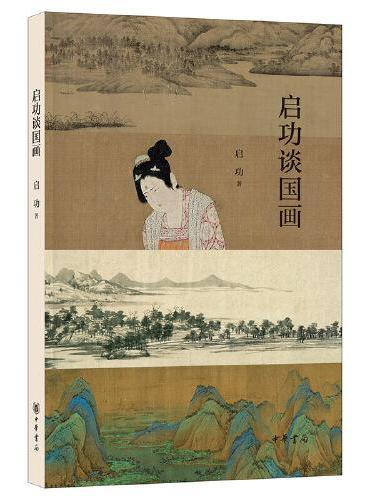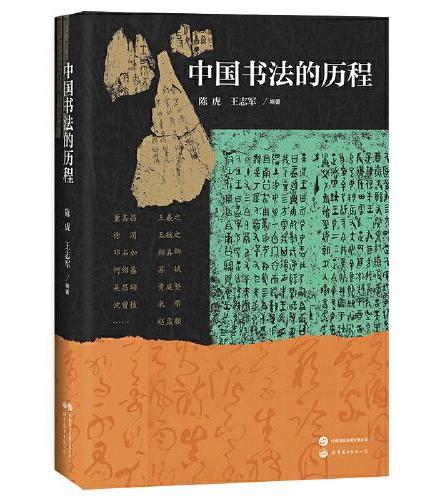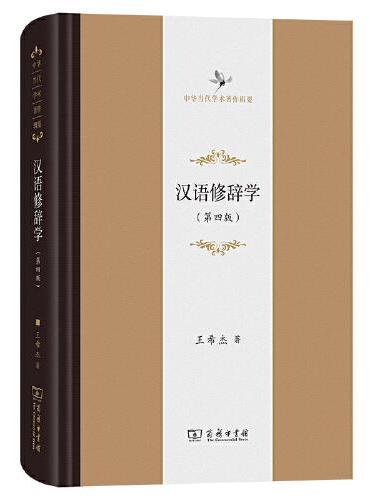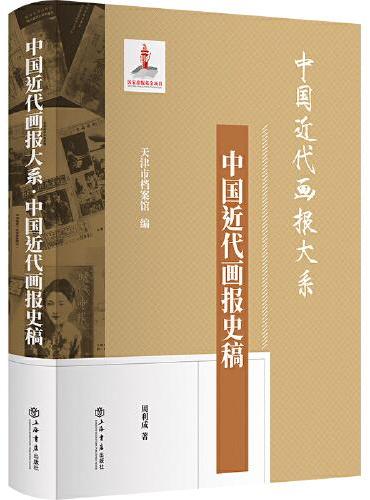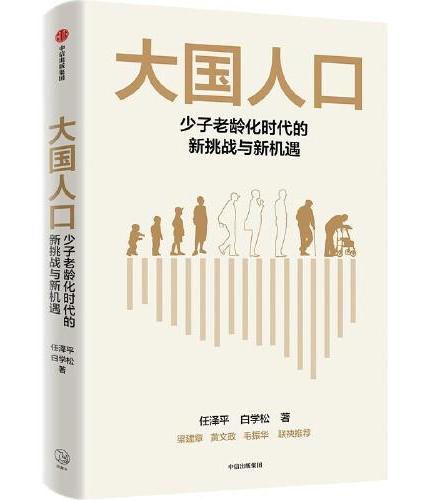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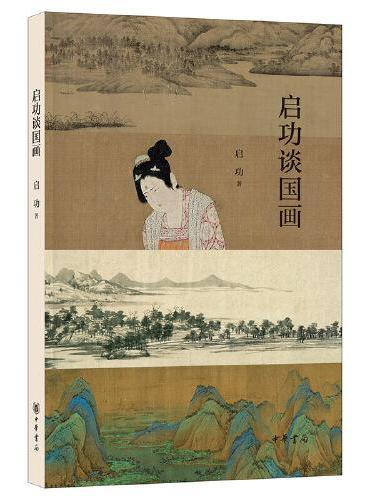
《
启功谈国画(启功著,中华书局出版)
》
售價:HK$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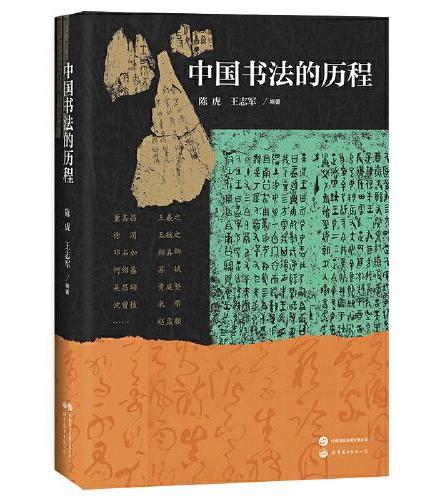
《
中国书法的历程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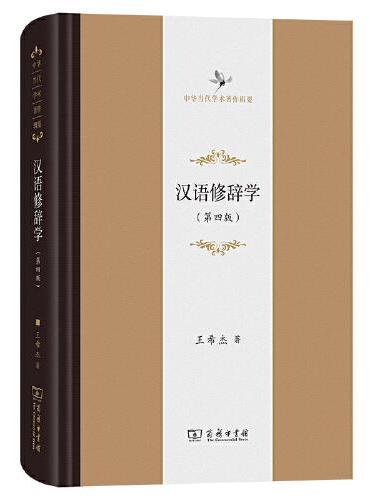
《
汉语修辞学(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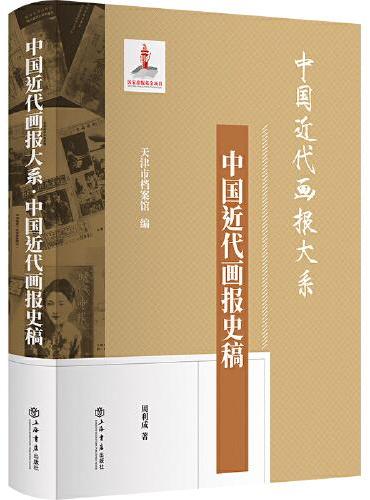
《
中国近代画报大系·中国近代画报史稿
》
售價:HK$
181.7

《
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艺文志·日本思想)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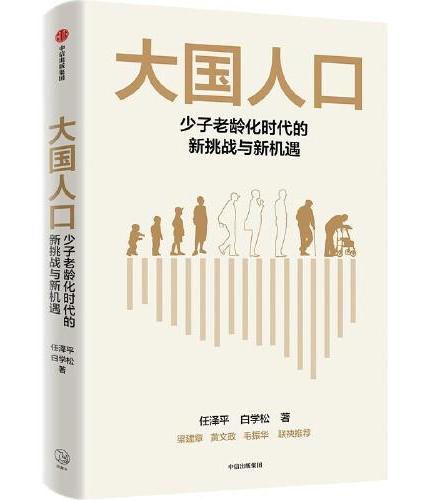
《
大国人口
》
售價:HK$
90.9

《
何以中国·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
售價:HK$
112.7

《
文明的故事(全11卷-2024版)
》
售價:HK$
2631.2
|
| 編輯推薦: |
*以宋代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的“锦毛鼠”白玉堂为原型人物加以创新的系列历史小说
*耳菜点评犀利、戏谑,亦庄亦谐,以今探古
*塑造了一个英俊帅气、风度翩翩、智慧超群、潇洒不羁、崇尚自由又心怀天下苍生的侠客白玉堂形象
*悬疑 推理,作者以高超的叙事技巧、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步步谜团、处处机关中寻出蛛丝马迹,挖掘真相,令人脑路大开
|
| 內容簡介: |
|
本案说行走江湖的白玉堂被结义大哥找来帮助开封府破案,刚到就发生系列离奇事情,玉玺被偷,开封府3个捕快、他的3个结拜兄弟突然失踪,他不得已杀掉最好的朋友,却发现朋友的一家都卷入了太子之争,幕后的操作者正是失踪的四皇子。离奇曲折的告诉情节、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出人意表。
|
| 關於作者: |
|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龙烟铁矿,作家、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与何申、关仁山并称文坛“三驾马车”。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发表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千余篇,计有1500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奖、《小说选刊》奖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日等文字。
|
| 目錄:
|
楔子 ………… 〇一
壹 ………… 一〇
贰 ………… 一八
叁 ………… 二九
肆 ………… 三三
伍 ………… 三七
陆 ………… 四七
柒 ………… 五五
捌 ………… 五七
玖 ………… 六三
拾 ………… 六九
壹壹 ………… 七五
壹贰 ………… 七九
壹叁 ………… 八二
壹肆 ………… 九四
壹伍 ………… 一〇二
壹陆 ………… 一一二
壹柒 ………… 一二四
壹捌 ………… 一二八
壹玖 ………… 一三五
贰拾 ………… 一四一
贰壹 ………… 一五〇
贰贰 ………… 一五三
贰叁 ………… 一六四
贰肆 ………… 一七〇
贰伍 ………… 一七四
四种势力 ………… 一八〇
六皇子的故事 ………… 一八七
皇子之谜 ………… 二〇五
云中英 ………… 二二三
尾声 ………… 二二七
|
| 內容試閱:
|
楔
子
宋仁宗赵祯皇祐二年初冬,瑞雪飘飘的季节里,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情。皇上要册封的四皇子突然失踪了,据说这个四皇子是得了疯癫病,一天夜里,疯跑出宫去,寒风凛冽的夜里,竟不知道四皇子去了什么地方。皇上派出去许多大内高手,四处寻访,但没有寻到四皇子的下落。皇宫里的太子和公主很多,历朝历代,总是难免有一些性格奇奇怪怪的太子或者公主的。如此说来,失踪了一个性格奇怪的皇子,不是什么大事情。
皇宫里的事情从来都是与民间的事情不相干的。皇宫里的心情当然也不会影响民间的娱乐的。民间向来是不关注朝廷里的是是非非的。如此说来,礼不下庶人的确是一件好事。老百姓本不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本不应该知道那么多让人头疼的皇宫中的事情。于是,才有了民间世俗的欢乐。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疯癫的四皇子的失踪,竟引发了后来的一场惊动朝野的动乱。
这是白玉堂的另一个故事。耳菜请读者注意,这一个故事,也同样不同于石玉昆先生笔下的白玉堂。耳菜请读者耐住性子看下去。我相信您已经看完了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现在,让我给你们讲白玉堂的第三个故事。
转眼已经到了第二年秋天,四皇子失踪的事情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秋高气爽的秋天,东京城内的菊花处处盛开,东京城外的庄稼已经是金黄一片了。此时是农民们的收获季节,也应该是达官贵人们秋游出行的当令。此时,更应该是一个饮酒的季节。赏菊饮酒,自古至今都是一件美事。其实,赏菊饮酒只是酒徒们的一个美好的借口,只要是好饮酒的人,哪一个季节不是当饮的好季节呢。有道是,好酒知时节,当喝乃发生。从古至今的酒徒们概莫能外。所以酒楼是没有淡季和旺季的。一年四季,酒楼的生意总是好的。
东京城外十里铺上的“得意酒楼”的生意当然更好。也有人说,得意酒楼的生意好,是因为它开在了寸土寸金的东京城外的十里铺。这是进入东京的必经之路。人们在这里送客,或者在这里迎客,都必须在十里铺歇一歇脚的。当然最好的歇脚处也就自然会选在这得意酒楼了。
十里铺是东京城外的十里铺。如果把十里铺放在别处,得意酒楼的生意恐怕不会这样兴隆了。得意酒楼沾了十里铺的光,十里铺沾了东京的光。京城永远是经济中心,是商家眼中的黄金宝地。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谁也说不清楚这座得意酒楼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但都知道这店至少是一个百年以上的老店了。店前的门匾,传说是唐朝颜真卿先生的真迹。世人传说颜老先生曾经外出游历,到处歇脚,得知亲侄颜季明被安禄山杀害,悲愤交加,在这里大醉了三天,才有了后来传世的《祭侄文稿》,颜体才得以发扬光大,流传于世。传说,这家老店最早是颜氏家族的人所开。但是,这家百年以上的老店的老板几十年却一直姓张,而现在却又姓了冯。人们现在议论的故事是这样的:姓张的老板因为嗜赌,才把这老店输给了姓冯的老板。而酒客们是不注意这些的。酒客们只会记住酒楼中的飘香的美酒,没有人会记住酒楼的老板。店老板姓冯还是姓张,不关他们的事情。更无人记得什么颜真卿先生了。
得意酒楼门前的幌子在秋风中摇摇摆摆,仿佛在撩拨着人们胃里的馋酒虫子,丝丝痒痒地爬上人们的喉咙。酒香从楼里弥散出来,满街飘荡。酒楼门前,人们进进出出,进去的人一个个如饥似渴,出来的人一个个红光满面,有的已经失态,醉步踉跄。店家小二笑容满面,迎来送往。
得意酒楼果然是好生意。
今天中午,一个长须汉子走进了开封府的得意酒楼,汉子器宇轩昂,身着华丽的服装,看得出是一个腰缠重金的角色。商家永远是看人下菜碟的货色。站在店门前接客的店小二看到长须汉子走了进来,目光登时一亮,高高的一声“客官里边请”的欢叫,就惊动了正在店前柜里坐着的店老板。店小二这一声欢欢的叫声,大概是本店的暗语,大凡有重要的客人光顾,店小二才这样喊的。店老板慌忙起身,笑嘻嘻地迎进了长须汉子,喜气地说:“这位爷,请上楼,老地方。”
长须汉子点点头,打量了一下老板,微微一笑,先是仰头看看酒店匾额上的“得意酒楼”四个大字,然后就抬脚上楼,楼板踩得颤颤响。只有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人才会有这种满不在乎的踩法。店老板屁颠颠地跟在汉子身后,嘴里尖声叫着:“小二,贵客来了,看座。”
这几天里,长须汉子已经成了这得意酒楼里的明星,每天在这里挥金如土。他每天在这里开销一两银子的酒钱,却总是掏出一锭银子扔到柜上,从不找零,便扬长而去。如此出手宽绰的主顾,似乎他腰袋里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或者是天上飞来的?弄得店家瞠目结舌。据说这个长须汉子是一个书法狂客,他到这里吃饭,只是为了每天看一看“得意酒楼”这四个颜体大字。管他是不是书法狂客呢,他只要走进店来,便是一个食客。对于这样一个出手慷慨的食客,哪一家酒店不欢迎呢?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几乎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趋炎附势,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君若不信酒席看,杯杯先敬有钱人。看到此处,耳菜大为感慨。
楼上临窗的一张桌子,是酒店这些日子专门给长须汉子留的。长须汉子已经以每天十两银子的惊人价格定下了这个位置。小二手脚麻利地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菜端上了桌子。长须汉子微微笑笑,就坐下畅饮起来。长须汉子饮得很慢,仿佛在品酒。
长须汉子已经饮了两个时辰。已经到了他平日要走的时候了。
可是今天长须汉子饮罢酒却不走,低头在桌子下边寻找什么。这样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会寻找什么呢?什么会使他细心寻找呢?长须汉子已经把眉头紧紧皱起了。似乎真是发愁了。什么事情会让这个挥金如土的汉子发愁呢?
眼尖的小二已经悄悄告诉了老板,老板慌慌地跑上楼来,拱手问:“敢问大爷有什么事情,可说与小店,小店一定尽力。”老板的声音十分小心,他唯恐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得罪了这位挥金如土的顾客。
长须汉子闷闷地说一声:“你帮不上的。我丢失了一块玉佩。”
店老板心里火烫般地一惊,暗想这位大爷是不是要讹上了。店老板的脸就白了,眼睛僵僵地看着长须汉子。
长须汉子一看老板脸色,便知道店老板误会了,忙笑道:“此事与你无关,或者我遗失到别的什么地方了。我只是记不起了。”
店老板大大松了一口气:“敢问大爷,是一件什么样的玉佩?”
长须汉子长叹一声:“倒不是一块什么值钱的玉佩,只是祖上几辈传下来的,便显得宝贵些了。若送到当铺,或者说值十两银子,或者也不值这么多,但是祖上留下的,便是不好丢失了。”说罢,一脸的沮丧。
店老板笑道:“我与大爷留意些,如打听到谁捡到了,便让他给大爷送去。”
长须汉子摇头苦笑:“怕是不容易,如果被哪一个爱小的捡到,便不容易璧还了。”
店老板一时闷住,不知道如何开导这位大爷,看长须汉子的表情,真是犯愁了。世上的物件所值,本无定价。你看上去不值,到了张三手上,连城也是它。如果放到李四手上,一文钱便也是不取的。一块普通的玉佩,或许真是长须汉子的传家之物。
长须汉子想了想:“店家,请把笔墨纸砚拿来一用。”
店老板不知汉子有何用,也不敢多问,就喊小二取文房四宝上楼。小二端着笔墨纸砚飞快地上楼来了。
汉子喃喃道:“我还是留下一张文告的好。凡捡到者,某愿出一万两银子。重赏之下,或许有望。”说着,一挥而就,写了文告。
店老板真是呆若木鸡般了:何等物件,如此值一万两银子。呆呆地看汉子写毕,老板忙双手接过文告。只听汉子吩咐道:“贴到店门前便是了。”
这张文告便贴到了得意酒楼的门前。
长须汉子扬长去了,他身后是一片惊得目瞪口呆的酒客,围定文告呆看。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群酒客中,有一个年轻漂亮的书生,他正在用一种诧异的目光盯着远去的长须汉子。年轻的书生,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年轻漂亮的书生让人注目,他的微笑则意味深长。
第二天,长须汉子又来饮酒,问店家有无消息。店家说还没有。又隔一日,汉子又来看过,仍无有消息。长须汉子说要去东京办事,留下一百两银子给了店老板作为感谢,请老板帮助留心。
长须汉子愁眉不展地告辞走了。
那个年轻的书生似笑非笑地望着长须汉子的背影。
这一日中午,得意酒楼大步进来了一个中年汉子。汉子七尺身高,一脸浓密的胡须,两眼精光暴射,吵吵嚷嚷进了店里,也不饮酒,直奔了柜台,大声寻问贴文告的汉子在哪里。
店老板听到,便迎上来,施一礼问道:“客官找哪个?”
这汉子打量了一眼老板,鼻子里哼一声:“我只是要找这贴文告的。”
店老板问:“你找他做什么?”
这时,已经围上来一群酒客观看。
中年汉子说:“我捡到了那值一万两银子的玉佩。”说罢,就掏出一块玉佩放在柜上,目光亮亮地看着老板。
老板拿起,细细地验过,果然是一个写着如意百年的玉佩,如同长须汉说的那块玉佩特征一样,毫无二致。老板心中大喜,脸上却不动声色地讲:“客官有所不知,那遗失玉佩的大爷不在,需要等上几日才行。”
那中年汉子不耐烦地说:“如何这般麻烦,不给了。我还要赶路。”说罢,抄起桌上的玉佩便要走。
老板惊得心慌,忙上前一把扯住汉子:“莫急,莫急。这位兄长,咱们细细商量一下如何?”又转身喊小二上茶。
中年汉子与老板在一张桌前相对坐下。
中年汉子想了想,对老板说:“不如你先给我些银子,你再送还给他吧。”
老板皱眉,似乎有些犹豫。
这时,酒客中那些看热闹的就开始议论。那个年轻漂亮的书生从中走出来,朝中年男子笑道:“不如这样,我给你些金银,这块玉佩我收下了。”
中年汉子一怔,看看这年轻的书生:“你?”
书生笑道:“你莫要轻看我。”就掏出一沓银票举在空中。
酒客们发出惊呼,书生手中的银票至少也有上千两。
中年汉子笑道:“这位小爷肯出多少?”
书生莞尔一笑:“你肯要多少?”
中年汉子笑道:“你不怕我奇货已居,便会漫天索价?”
书生摇头一笑:“即使你开出天价,我也可就地还钱。”
中年汉子点头:“好说,你我不妨商量商量。”
书生笑道:“好说。”也坐在了中年汉子的旁边。
老板已经听得心焦,他忙对书生和中年汉子道:“二位有所不知,这件事情是那客官托付于我的,自然要由我来处置。”说罢,就朝中年汉子拱手道:“这块玉佩,我暂且替那客官收下。不知道这位爷要多少钱?”
中年汉子笑道:“我还识得几个字,那文告上写得清楚,一万两银子嘛!”
老板忙赔笑道:“小店并没有那么许多。还望少收一些。”
中年汉子摇头:“不可。那文告上写得可是真切,分文少不得的。”
老板道:“你急着赶路,本店又无许多,还望少收。”
中年汉子的目光似乎犹豫,但嘴上却硬:“如何少收,我定是不能吃亏的。”
于是,二人讨价还价,老板花掉了五千两银子,几乎用掉了所有的积蓄买下这块玉佩。中年汉子很不情愿地拿着五千两银子的银票走了。
酒客们也哄地四下散了。有人忌妒地说:“恁地这老板真是走了财运,直是掉进了黄金洞里了。”
店老板安心等那个长须汉子。老板心里很是快乐,他一厢情愿地相信,这只玉佩将会换回来一万两银子。
老板当然是上当了,这一当上得极惨,他至少要关张了店铺,还要搭上一些钱财。长须汉子再也没有露面。望眼欲穿的老板,几乎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据说这个老板极是精明,从没有吃过哑巴亏,何况是这样大的一个哑巴亏呢。从来都是老板算计酒客,怎么会让酒客算计了老板呢?但是,事情总有例外,有时酒客会盯上老板的。
看到这里,耳菜想起一句老话,叫作天上掉馅饼。其实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天上常常掉陷阱,而人们常常把陷阱当作馅饼。于是,一厢情愿,总会有人上当。
自古至今,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里上当,当事人所犯下的错误永远只有一个字:贪。
壹
也许就在店老板惊呼上当、捶胸顿足之时,长须汉子已经走在了东京城里的玉石街上,他走进了玉石街的一家名叫万兴客栈的店,长须汉子进了客栈,径直进了他的房间,他一进门便摘掉了假须。分明是一个年轻英俊的武生。
他是白玉堂。
房间里摆着一张酒桌,桌上有几碟小菜和一坛已经打开的酒,满屋子里飘动着酒香。那个捡到玉佩的中年汉子正在饮酒。白玉堂微笑着看看中年汉子,便在对面坐下,自取一只酒杯,倒满了。他没有说话,先自饮了一杯。
中年汉子笑嘻嘻看着白玉堂。这人名叫秦子林,是白玉堂当年做杀手时交下的生死朋友。他与白玉堂联袂演这一出捡玉佩的戏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玉堂笑道:“子林兄,你如何知道这样一家客栈?果然环境幽雅,你若不讲,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客栈呢。”
秦子林笑道:“这是一个朋友介绍来此的。我过去也不知道。”
白玉堂笑道:“我已经几年不来东京,想不到东京变得如此繁华了,我还听说东京城里出了许多富豪,有一个叫田仿晓的是大大的有名,据说他家在东京城里开了许多买卖。”
秦子林一笑:“现在大宋与辽国已经停战,国泰民安,东京城里自然是一派繁华。出几个富豪便也在情理之中。你刚刚说的那个田仿晓,当属东京城里第一富豪。”
白玉堂笑道:“有钱是一件好事。钱会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秦子林也笑道:“像你这样挥金如土自然也是一件好事,也会给你带来许多快乐。”
店家推门进来,他又端进一坛酒和几碟小菜。这是白玉堂刚刚进店时让上的。店家躬身退出。秦子林举起一杯酒,笑道:“玉堂弟,得意酒楼那个贪财的老板,现在必是肉痛得捶胸顿足呢。我这一杯酒姑且算作是伤心酒,替他饮了吧。”他仰头饮了,然后哈哈笑了。
白玉堂鄙弃地一笑:“这等人物,活该是如此了。他设赌局抢人家张姓的酒楼,这一次要赔一个底掉了。”也饮了一杯。
秦子林点头:“直是活该了。”说罢,又斟了一杯。
白玉堂笑道:“不过,我看过几日,真是有些喜欢上‘得意酒楼’那四个颜体字了。也许真是颜真卿的墨宝啊。”
秦子林笑道:“玉堂弟,你可算得上江湖上罕见的才子了,诗琴字画,样样了得啊。我是一个粗人,与你结为兄弟,直是有些高攀了。”
白玉堂哈哈笑了:“子林兄,你何必如此取笑玉堂呢。”他起身出门喊店家,“店家,喊那张姓的老者进来。”
店家在门外答应一声便去了,不一刻,便引来一个布衣老者。那老者见了白玉堂,倒身便要跪下,白玉堂忙将他搀住。他便是得意酒楼原来的老板,因为嗜赌,入了人家的套子,将酒店输与姓冯的了。
老者长叹道:“多谢二位恩公,如若不是二位相助,那酒楼必是姓他冯家的姓了,我将如何去见祖宗啊?”
秦子林取出那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递与那老者,叮嘱道:“日后切莫再赌了。财大者,气不可太粗,得意时,形不可忘记。”
老者连声道:“记下了,真是记下了。”话说着,却不接那五千两银票。
白玉堂愣住:“老丈何意?”
老者道:“此店夺回,我已经感激不尽,只是这酒店本也不值这许多银子。我想二位留下一半,也算小老儿孝敬……”
白玉堂突然冷笑:“你以为我们是贪财的人吗?”他的目光里已经露出了凶气。
老者呆住。
屋中的空气立时十分紧张了。
秦子林淡然笑道:“张老板,你快些走吧。这位先生如若贪财,这银票岂能给你。”
老者长叹一声,重重地看了白玉堂一眼,目光十分复杂。他深深揖了一礼,出门走了。白玉堂目送老者出门,心念一动,目光有些怅然失落。
秦子林感慨道:“玉堂弟,你果然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这五千两银子,竟是不动心。”
白玉堂摇头笑了:“钱这东西,可成人之美,锦上添花是它。惹事的根苗,万恶之源也是它。想我……”他突然不再说,他想起了韩彰和张子扬的事情,心中有了些旧日的伤痛。他转开话题,问道:“子林兄,你已经很少在江湖上露面,如何重现江湖了呢?”
秦子林淡淡一笑:“我只是隐身时间长了,情绪沉闷得很,出来走走,散散心而已。”
白玉堂笑道:“你来东京就应该去竹子街住宿,如何住起客栈来了,岂不怪事?”竹子街有秦子林的住宅,秦子林不回家,反而住店,当然让白玉堂不解。
秦子林摆手笑道:“小女秦莲刚刚完婚,与我那爱婿季明扬正是情意浓深之时,我岂能去打扰人家的欢乐呢?孩子们当面不会说些什么,背后要说我不长眼力了。”
白玉堂点头,突然问道:“兄长,可否听说过一个叫归景东的英雄好汉?”
秦子林一愣,笑道:“此人你也听说了。”
白玉堂点头:“现在江湖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传说此人武功已经出神入化。即使南北二侠联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不曾想到,江湖会出现这等英雄人物,我只是无缘得见。”
秦子林道:“我也听说此人武功深不可测。传说此人是当年归景西的同胞兄弟。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白玉堂怔道:“归景西的胞弟?”
秦子林道:“江湖上都是这样传说,详情我也不大清楚。”
白玉堂点点头,哦了一声:“是吗?想不到归景西会有这样一个兄弟。”
归景西是十几年前横行江湖的一位英雄。他出山之时,正值黄河四魔横行江湖,滥杀无辜。南北二侠联手去战黄河四魔,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而已。黄河四魔由此更加横行无忌。归景西与这四个魔头这一战极为惨烈,归景西终将黄河四魔杀死。归景西此战被江湖中人激赏至极。后归景西不知所终。归景西如日中天之时,白玉堂尚未出道。白玉堂知道的归景西,也只限于这些材料,他从未听说过归景西有一个名叫归景东的胞弟。
白玉堂又问:“子林兄,近日我在街中闲走,听人传言,这个归景东现在投到了六皇子门下?”
秦子林摇摇头:“我从未听说。”
白玉堂哦了一声,沉默下来。
秦子林转开了话题,问道:“贤弟此次到东京来做甚?莫非与这个归景东有关系?”
白玉堂摇头一笑:“并无关系,我只是随口问问罢了。”说罢,又皱眉道:“我此次来东京,是大哥卢方飞鸽传书,让我来帮他们捉一个名叫飞天蜈蚣的江洋大盗。”
秦子林点头:“是有飞天蜈蚣这样一个人物,听说最近在东京闹得声势很大,皇上已经下令缉拿此人了。玉堂弟,你人在江湖,心却还是在公门啊。想不到你还能千里迢迢跑来,为朝廷分忧啊。”秦子林的语调里有了些许讥讽之意。
白玉堂摇摇头:“子林兄,你错怪小弟了,玉堂从不过问公门之事。我只是却不开卢大哥的情面。”
秦子林笑了:“我一句玩笑,你何必当真呢?我只是羡慕卢方有你这样一个好兄弟啊。你见到卢方了?”
白玉堂苦笑一声:“这正是我奇怪之处,卢大哥催我快快来东京,我来东京之后,他却又不见我。我已经在这家客栈里闲住了十几天了。这才有了得意酒楼的这一个闲笔。顺手帮了那张老板一回。”
秦子林点头:“卢方此举,确有些奇怪。”
白玉堂道:“我大哥从不是这般迟疑的人。如此说来,其中必有隐情了。我想这次传书有假。”
秦子林一怔:“你是说这书并不是卢义士所传。”
“是的。”
“那又是何人所为呢?”
“我现在还不知晓,我去了他家两次,他只是一味让我快快离开东京。我问他如何传书给我,他支吾搪塞,也解释不清。看他那惊慌的神色,的确让人奇怪。卢大哥从不是怕事之人啊。”
秦子林疑道:“哦?此事倒是有些奇怪了。”他看着白玉堂,似乎等着白玉堂再说些什么。
白玉堂却突然打一个长长的哈欠,他笑道:“子林兄,我真是有些困倦了。”
秦子林奇怪地看着白玉堂,刚刚要说什么,白玉堂却给他使了个眼色。秦子林突然明白了,白玉堂已经感觉到窗外有人。
秦子林挺身站起,刚刚要说话,忽听窗外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二位演的好戏。一块玉佩,莫非定要人家店主赔尽钱财倾家荡产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店家纵有千般不是,二位也过于歹毒了一些。”
秦子林看了一眼白玉堂,他有些脸红,不承想自己跟白玉堂的所作所为,竟被人识破。秦子林有些懊丧。
白玉堂突然笑了,大声道:“何方朋友,何不进屋来坐。房门并没有上锁。”
窗外那人笑道:“秋高气爽,二位何不出来说话。”那人明显不想进来。
白玉堂看看秦子林。秦子林点点头,二人开门走出去。他们已经听出窗外就一个人。依他二人的身手,是不会在乎任何一个人的。
窗外,月光如清水般泼了满地。在得意酒楼遇到的那个年轻漂亮的书生正站在窗下。书生手持一把扇子,这扇子在这秋天已经不合时宜。书生这扇子似乎只是一个装饰,使这个书生平添了不少文气。但白玉堂和秦子林都看出,这扇子其实是一件杀人的武器。
文质彬彬的一把扇子,竟是隐藏了可怕的杀机。
秦子林认出这书生正是在得意酒楼里那个年轻漂亮的书生,不禁笑了:“我刚刚已经听出是你了。不知道阁下来此何干?”
书生也笑道:“若不是我帮腔作势,恐怕那个老板也不会轻易出手那五千两银子。”他的扇子护在胸前。
秦子林拱手笑道:“那就多谢了。”
书生笑道:“谢倒不必,只是我猜想那笔银子落入你二人之手,岂不是要独吞了不成。按照江湖中的道理,应该是另有一个说法。”
白玉堂盯住书生,稳稳地问一句:“依你之见,又该如何一个说法?”
书生笑道:“我们三人应该是三一三十一才合情理。”
秦子林哈哈笑了:“原来是黑吃黑啊?”
白玉堂冷笑一声:“主意不错,不过,如果我们不答应呢?你岂不是一厢情愿?”他的脸上已经有了杀气。
书生微微笑了:“那我只好作罢。”
秦子林和白玉堂相视一愣,没有想到这书生竟会说出软话。
书生笑道:“因为你们是两个人。”
秦子林摆手道:“这个你倒不必担心,我们不会以多欺少,你可以跟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单打独斗。”
书生笑道:“那我也胜算不多。”
秦子林和白玉堂静静地看着这个奇怪的书生,他们不知道这个书生想做什么。
书生笑道:“我若跟大侠秦子林或者锦毛鼠白玉堂争夺他们已经到手的银子,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在下还不肯做这样无望的事情。”
白玉堂和秦子林心中一凛,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名字会被这个书生点破。
书生很是得意地看着这二人。
白玉堂突然笑了,说了一句:“我们也不好出手。”
书生微笑道:“为什么?”
白玉堂笑了:“因为我们两个人谁也不会对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出手。”
书生大窘,用扇子一指白玉堂:“你如何这样说?”
白玉堂笑道:“因为现在确实如此。”
书生显得十分沮丧:“你是如何看出的?”
未及白玉堂答话,书生却猛地转身纵出院子,无影无踪了。
白玉堂禁不住赞一句:“端的好轻功啊。”
秦子林愣了一下,转身问白玉堂:“玉堂,你是如何看出她竟是女扮男装?”
白玉堂笑道:“其实,她刚刚说话时,我就已经看出了。她一直用扇子遮住咽喉,这是其一;其二,她说话时拿腔作调。”
秦子林笑了:“精明过人的白玉堂啊。”
白玉堂叹气:“其实你也早看破了,只是你不说,把一个聪明的关子卖给了我。子林兄,你才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啊。”
秦子林一下子窘住。忽又笑了:“玉堂啊,你果然是一个鬼精啊。”
白玉堂突然问道:“子林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刚刚此人来历。”
秦子林道:“我还可说出她的姓名。”
白玉堂惊疑地看着秦子林:“哦?”
秦子林突然笑了:“算了,其实你早已经猜出她是谁了?”
行文至此,耳菜希望读者要注意一下秦子林这个人。谈歌后边还要写到他,精明无比的秦子林,的确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白玉堂爽然笑了。
贰
秋风阵阵,万里无云。今日是一个极好的天气,耀眼的太阳高高地悬在天上。东京城里的石板路都被秋阳烤得酥酥的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人们的心情应该是舒畅的。
现在,有四个便装的汉子在暖酥酥的石板路上走着。他们的目光却冰冷,冰冷得像饿鹰寻找猎物一般四下盯看着,他们虽然身着便装,却不是寻常百姓,他们是开封府里四个声名显赫的捕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只是他们现在的心情并不舒畅,或者说,他们已经不舒畅了很多日子了。有句俗话,只看官差威风,不见官差头痛。其实做官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司的白眼、训斥,甚至责罚,你都要领受。稍不留意,你可能就被上司砸了饭碗。
四个声名赫赫的捕快走在秋风习习的东京街道上。他们并不是闲逛,或者说,他们这一行当是没有闲逛的时间的。他们是奉了新任开封府尹梁月理大人的命令前去缉拿两个江洋大盗:飞天蜈蚣和散花仙女。他们的心中涌动着杀机。自古以来,捕快是一个时刻充满了危险的职业。捕快的对手,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匪盗。捕快们随时都面临着两种可能,即或者捕获到对手,或者被对手夺去性命。这是一种生死一线高度危险的职业。
经营了开封府十几年的知府包拯去年已经离任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是官场中人的无奈。现在换作了梁月理做开封知府。梁月理原是南阳太守,后调兵部参事。调任开封府是包拯的举荐。包大人举荐梁月理来做开封知府,看似为朝廷重用,直却是把梁月理推到了一个火炉上来烤了。梁月理上任三个月来,就遇到了飞天蜈蚣和散花仙女这两个案子。也许梁月理已经后悔了,他在南阳太守的位置上,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在兵部参事的位置上,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清闲而且自在。而开封府里,竟是整天在乱糟糟的案件中绞尽脑汁。
包拯去任了,也许现在已经无官一身轻的包拯正在家乡的田野里闲闲地散步呢。
公孙策先生也走了,也许除却能与包拯共事,旁人他是不愿意侍候的。也许现在仍旧心高气傲的公孙策先生正在江湖上云游呢。
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在开封府当差。
展昭、卢方、徐庆、蒋平也还在开封府当差。
这一干差人也像忠诚于包大人一样,忠于梁大人。
或者说,不管是包大人还是梁大人做开封知府,捕快们都要忠于职守,因为开封府永远是一个麻烦事情层出不穷的地方。不认真工作,或者不肯付出辛苦的人,绝对做不好开封府的事情。开封府是一个需要认真工作,不许可有一点疏漏的地方。生死一线之间,谁敢稍有怠慢?
现在,梁月理大人已经感觉自己有些心神疲惫不堪了。差人们都看到了,还不到十几天的时间,梁大人已经连连几次被皇上召进宫去密谈。每次梁月理从皇上那里回来,都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显然,皇上总是交给他一些不好处理的难题。但是梁大人从来不说,捕快们也不便问。也许他们都知道,他们现在还不能与梁大人交心。或者说,梁大人还不愿意与他们交心。
昨天下午,梁大人从皇上那里回来,就通红着两眼立刻升堂,看得出这些日子梁大人一定经常失眠。梁大人派展昭、卢方、徐庆、蒋平等人,立刻缉拿飞天蜈蚣的同党、一个名叫散花仙女的大盗。此盗闯进皇宫作下一起大案,盗走了皇上一把宝剑。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宝剑,而是当年太祖传下来的一把宝剑。这起案子,闹得庄严肃穆的皇宫竟似鸡飞狗跳,简直像一个热闹的集市了。
这个散花仙女真正是猖狂至极。更为嚣张的是,此人作案之后,竟敢在皇宫留下姓名。一个飞天蜈蚣已经很热闹了,如何又加上一个散花仙女呢?展昭们已经感觉到了身心的疲惫。梁大人告诉捕快们,皇上已经怒气冲天了,一个江湖盗贼,竟然闯宫如履平地。这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皇上限开封府五天之内拿住这个大盗、缴回丢失的宝剑。皇上还出动了禁军太尉陆晨明大人统领千余名禁军在城中日夜巡查。
当然,护卫们和捕快们知道的就是这些情况。一定还有许多护卫们和捕快们不知道的情况,梁大人是不便讲的。梁大人只要他们尽快缉拿飞天蜈蚣和散花仙女归案。
缉拿飞天蜈蚣,梁月理大人命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负责。
缉拿散花仙女,由展昭、卢方、徐庆、蒋平负责。
今天一早,有眼线通报,今日午前飞天蜈蚣将出现在紫石街上,与某人接头。这某人很有可能就是散花仙女。这眼线是开封府使用多年的一个名叫张大的市井泼皮,此人在东京居住多年,耳目灵通得很,总有一些重要消息报来,此番看来也不会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便化装到了紫石街。展昭、卢方、徐庆、蒋平紧随其后。此事现在是绝密,不敢走露半点风声,四名捕快内心已经是十分紧张了。
街上的贩子们叫卖声此起彼伏。各家商号店铺都大开着门板,赔着一张永远生动的笑脸,候着主顾们的到来。赚钱,永远是东京市民的第一目标。如果没有钱可赚,东京市民是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应该说,是东京市民们赚钱的冲动,促成了东京城的繁荣。繁荣的背后,是金钱源源地滚动。金钱的背后,却常常是罪恶的发生。
四个名捕已经转了两个时辰,线人张大还没有露面。临近中午,捕快们的肚子开始饿了。前边就是得月楼。这是一个饭菜都做得十分可口的酒楼。闲暇时,开封府的捕快们常常来这里吃酒。王朝笑道:“今日上得月楼吃一席,我来请客。”
马汉看一眼得月楼,苦笑道:“王朝兄,公务当急,却是吃不得酒的。”
张龙笑道:“马兄今日如何这般怯了。那是包大人定下的规矩。今日开封府是梁大人做主,不必萧规曹随了。”
赵虎似乎也饿得急了,也匆匆道:“张兄讲得极是。上楼上楼。”他第一个进了得月楼。
马汉不好再说什么,也跟着赵虎进去了。
四个化了装的捕快走上了得月楼,线人张大还没有出现。
得月楼是东京城里一家豪华的酒店,它是东京城里最大的富商田仿晓开的生意。田仿晓到底有多少钱,东京城里没有人知道,但是,田仿晓与当今圣上的交情,却是人人皆知的。田仿晓与开封府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开封府的差人便常常来这里吃酒。店家已经与开封府的捕头们熟稔得很了。
店小二笑脸迎上,把四个捕快引到一张桌前,四人坐下。王朝点了几道小菜和一坛老酒。几道小菜很快就端了上来,另有一个胖胖的店小二抱过一坛酒来。酒坛嘭地开封,酒香四溢出来,登时飘满了屋子。
马汉禁不住称赞了一声:“好酒。”
胖胖的店家小二抱起酒坛倒满了四只大碗。
王朝张龙赵虎端起酒碗饮了下去。王朝第一个叫起来:“果然好酒。”桌上却有一只碗没有动。王朝去看,看到马汉并不饮酒,他奇怪地看着马汉:“马兄,你为何不饮?”在王朝的印象中,马汉从来都是豪饮的。今天马汉有些反常。
马汉摆摆手:“我今日不想饮。”
张龙哈哈笑起来:“今日马兄真是怪了,这些酒果然是香,即使是毒酒,也禁不住让人饮。”
马汉摇头:“今日公务在身,我是不想饮的。”说罢,皱眉不再说话,似乎满腹心事。
张龙笑道:“我刚刚说过,你那是包大人的规矩。现在梁大人是不管这些的。再说,我们已经紧张忙碌了几日。今日无论如何也要痛饮一番。”
赵虎和王朝连声附和。
一坛酒顷刻被三人饮尽。
店小二又端上来一坛酒,马汉连连摆手道:“不饮了,不饮了。”
店小二的脸上堆满了笑:“是一位客官让我送给各位的。”
四个人一愣,转身去看。
一阵楼梯响,楼梯上已经走上来了一个中年汉子。此人大高的个子,青色短衫,脚蹬麻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汉子朝四人笑道:“酒是我送的。”
张龙似乎已经有了一些酒意,他骂道:“张大,你这混账,如何还没有见到疑犯的动静,莫非你哄骗我们不成?”
这汉子正是张大。张大笑道:“我哪里知道什么飞天蜈蚣和散花仙女,只是与开封府开了一个玩笑。饮酒,这酒直是不错。”
四人面面相觑,目光中露出杀气,王朝骂道:“张大,你敢戏弄我们?”
张大哈哈笑了:“你们一定奇怪散花仙女和飞天蜈蚣没有露面吧?”
马汉点头:“是的,我们的确很奇怪。”
张大说:“因为我张大就是飞天蜈蚣。”
四个捕快立刻站起身来,他们的手已经把腰里的刀剑拔了出来。邻桌的餐客们惊得起身散去了。
张大笑道:“莫慌,我既然来了,就是要随你们去投案的。咱们先喝几碗酒如何?”
张大坐下饮酒。一连三碗酒下去了,他仍然微笑着。
马汉和张龙拿出锁链,哗啦一声响,就往飞天蜈蚣的身上去套。
王朝的脸上突然起了异样的变化,他的脸色开始苍白,而且张龙赵虎的脸上也开始苍白,他们三个人互相看着,眼睛里都有了一种恐惧的神色。三人几乎是同时痛苦地叫了一声,就弯下腰去,跌倒在地上了。
张大也惊住了。他看看倒下去的三个捕快,他的脸色变了,他一指酒坛:“这……”说着,他也痛苦地变颜变色地跌倒了。
王朝从地上挣扎着抬头看看马汉,大声笑道:“真是……好酒……好……酒啊……”他就伏在了地上。
马汉吃惊地看着这几个人先后倒下去,自己也仿佛变得要跌倒了,这变化实在太可怕了。
楼梯一阵乱响,马汉醒过神来,抬头一看,竟是展昭、卢方、徐庆、蒋平冲上楼来。他们同样惊呆了,他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马汉,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有一把刀,直劈着马汉的心脏:马汉似乎没有什么悲伤的样子。王朝、张龙、赵虎都是他共事多年的朋友,他为什么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呢?
卢方走过去,弯腰看看躺倒的四个人。他盯住那个躺倒的张大,张大以微弱的声音说:“我是飞天蜈蚣。”
卢方大叫起来:“飞天蜈蚣?”上前一把撕去了张大的假面,这汉子竟是一个干瘦的青年人。
展昭、徐庆、蒋平过来看,展昭疑道:“他如何不是张大?他如何自称是飞天蜈蚣?”
卢方看着倒在地上的王朝、张龙、赵虎,皱眉问马汉:“他们是怎么回事?”
马汉道:“他们饮酒了。”
展昭问:“你没有饮酒?”
马汉摇头:“我滴酒未沾。”
徐庆冷笑道:“你一向豪饮的。我记忆中,你常常是逢酒必饮,逢饮必醉啊。”
蒋平皱眉问道:“马兄,我知道你一向饮酒爽快,而且常常独饮,为什么今天却不饮呢?我还知道,你们兄弟四人中,你的酒量最大。”
马汉点头:“你们说得都对。但是我今天的确不想饮酒。”
蒋平温和地问马汉:“你为什么没有饮呢?”
马汉不再回答,他呆呆地站着,目光空空茫茫地看着众人,他猛地转身,向楼下奔去,展昭一怔,旋即追下去,卢方、徐庆、蒋平也跟下去,展昭已经拦在了店门前。
而马汉却没有要逃走的意思,他夺路奔进了灶房。他呆住了,灶房里已经空无一人。刚刚上酒的胖胖的店小二已经倒在了地上。他胖胖的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
他当然不是醉倒的。
他是被人杀倒的,已经不会再说话。
他不再说话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死人自然是不会再说话了。
店小二胸前一把钢刀,几乎穿透了胸膛。好狠的手法,凶手一定是在店小二毫无防范中下杀手的。否则,店小二那一脸的笑容便不好解释。
众人全惊呆了。
马汉转过身来,他苍白的脸上沁出一层冷汗,缓缓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愕。
众人不说话,似乎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且只有一个答案,即马汉收买了店小二,店小二下毒毒死了王朝、张龙、赵虎和飞天蜈蚣,而店小二又被人杀掉灭口了。
展昭冷冷地问:“马汉,今天应该是你下的毒。”他说得很肯定。
众人把目光盯住马汉。
马汉道:“我没有下毒。”回答得也很肯定。
卢方问:“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喝酒?”
马汉皱眉道:“我今天实在不想喝酒。”他感觉自己这个理由说得确实软弱无力。因为,这实在不是理由。谁都知道马汉是逢酒必喝的人。他今天没有喝酒,当然要奇怪得让人生疑了。
突然,店外响起一阵笑声。这笑声有很大的劲道,众人听出这个发笑的人内力的深厚。众人只觉得耳膜被震得轰轰作响。那人笑道:“马汉,你若不走,更待何时?”话音刚落,寒光一片,门外打进无数暗器,暗器朝着展昭、卢方、徐庆、蒋平袭来。四人忙着躲避,马汉怔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猛然夺门而出,站在门口的卢方、蒋平慌地上前拦他,却不防马汉跑得凶猛,眼睁睁看马汉纵出店门。展昭飞身过来,门外却又击来一串飞镖。展昭忙闪身,一念之间,马汉已经冲出去了。
展昭冲出门去,只见马汉已经上了一匹快马,旋风般去了。那个刚刚发暗器的人也无影无踪了。
展昭回到店内,卢方艰难地一笑:“与马汉在开封府共事多年,不承想他有如此好的身手。”
展昭沮丧道:“只是枉送了王朝几个兄弟的性命。”
蒋平道:“不必着急。我刚刚已经看过,他们中的是屠龙毒。这种毒虽然说厉害,但并非无药可解。”
展昭疑道:“如何解得?”
蒋平笑道:“我相信卢大哥的身上肯定有解药。”
卢方点头道:“韩彰兄弟走时曾给了我许多解药,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种。”他从怀中掏出几个药瓶,交给了蒋平。蒋平接过看了,挑出一个。
蒋平、展昭、徐庆走上楼去,展昭突然上前锁了飞天蜈蚣。蒋平有些惊讶:展昭锁飞天蜈蚣为何?
飞天蜈蚣一动不动。
展昭为什么要锁飞天蜈蚣呢?他已经是一个中毒很深的人了。锁一个必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呢?众人看着展昭。
展昭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问,他冷声一笑:“他没有中毒。”
卢方也笑笑:“展护卫说得对,他的确没有中毒。”
展昭又说了一句:“他也不是飞天蜈蚣。”
众人呆住,这人不是飞天蜈蚣,为什么要冒充飞天蜈蚣呢?他为什么喝了几碗酒,而没有中毒呢?答案很清楚,他送进来的那坛酒是没有下毒的。但是他为什么也要装作中毒的样子呢?
徐庆性急地上前揪住这个人,怒声喝道:“你到底是谁?”
突然窗外有人影一闪,众人稍一分神,只听这个冒充的飞天蜈蚣大叫一声,当下毙命了。他当胸已经中了一支镖。
卢方大叫一声,也随声纵了出去。
“哪里逃?”蒋平也追了出去。
展昭对徐庆道:“你且看住他们几个。我去帮卢护卫和蒋护卫。”
展昭纵身蹿出酒店,到了门外,他却再也拔不动步子。
地上躺着卢方和蒋平。二人都已经负伤,都中了暗器,有鲜血从他们的胸前汩汩地流了出来。
卢方艰难地说:“是……”
是什么?卢方再也说不下去,头一歪,昏过去了。
展昭急忙喊徐庆过来搀扶卢方与蒋平。
街上一阵乱乱的脚步响,酒楼里已经冲进来了许多开封府的捕快。他们急忙把卢方和蒋平抬走了。又有几个捕快上楼去抬王朝、张龙、赵虎几个。展昭陷入了沉思,是马汉下的毒吗?问题现在不管是不是马汉下的毒,展昭已经认定是马汉所为了。所谓瓜田李下,马汉便是难脱干系了。
读到此处,耳菜慨然长叹。由此想到了世间许多冤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