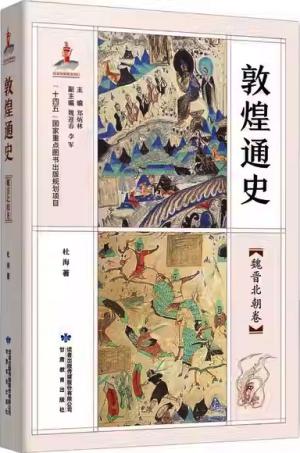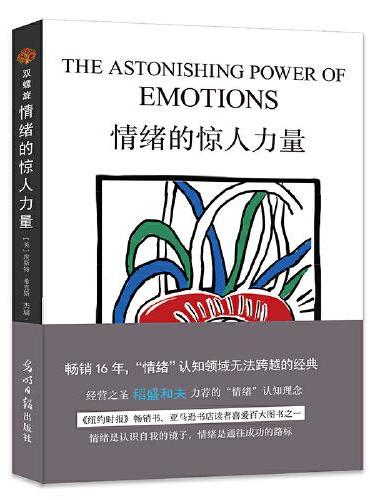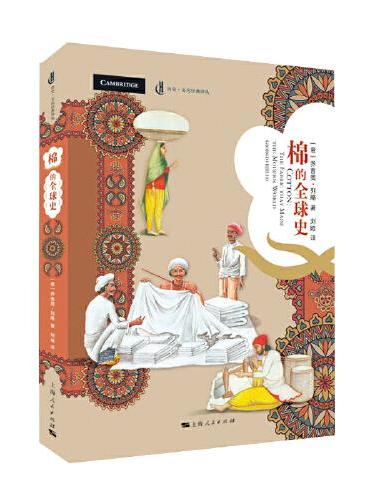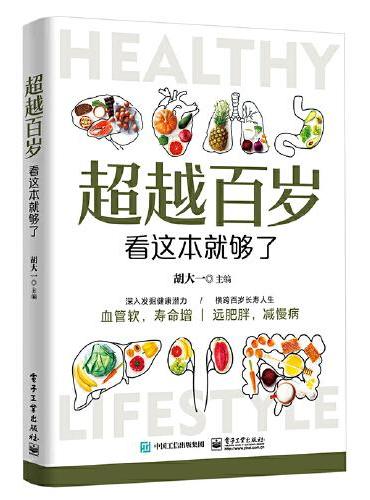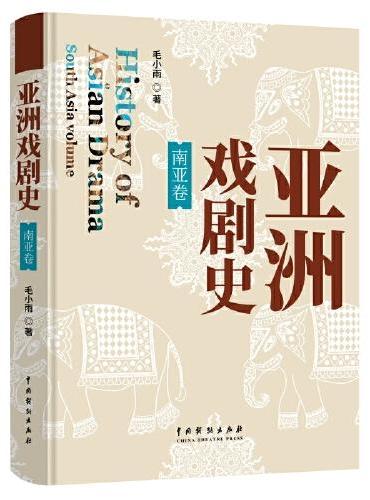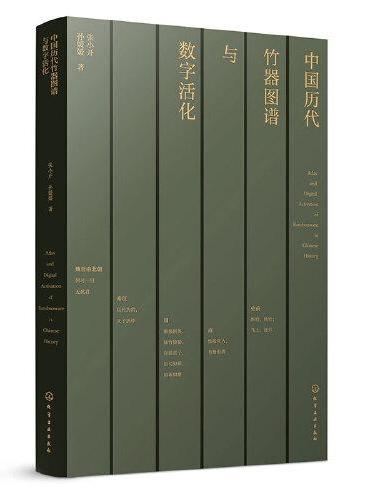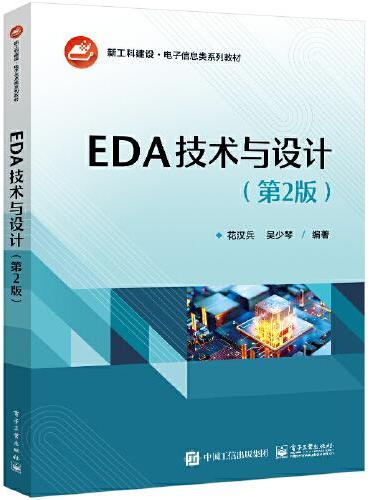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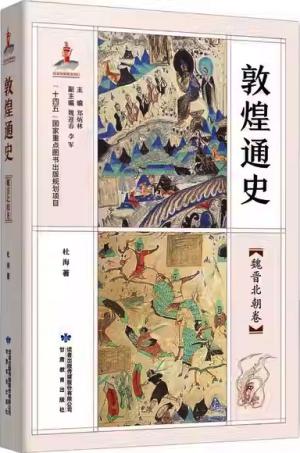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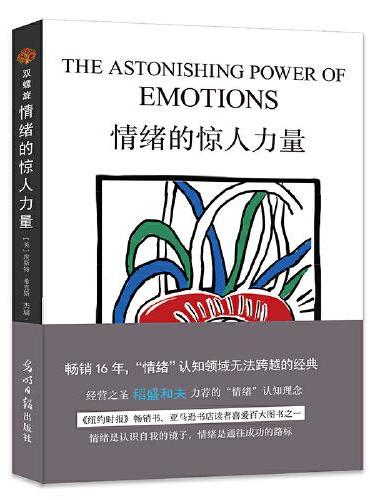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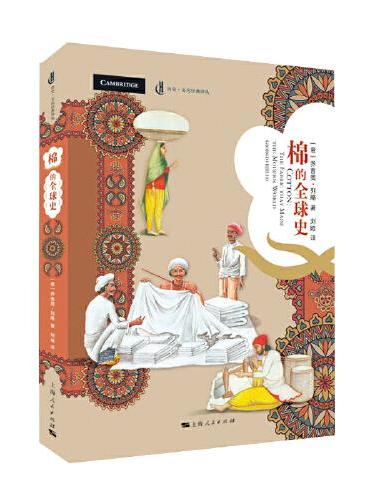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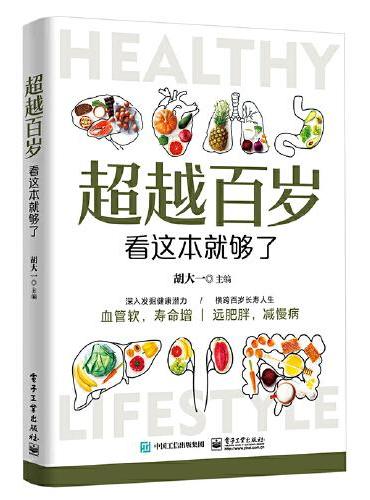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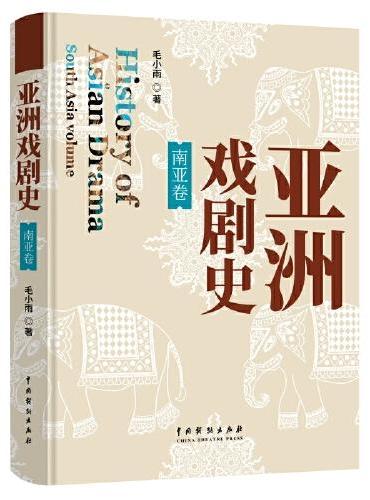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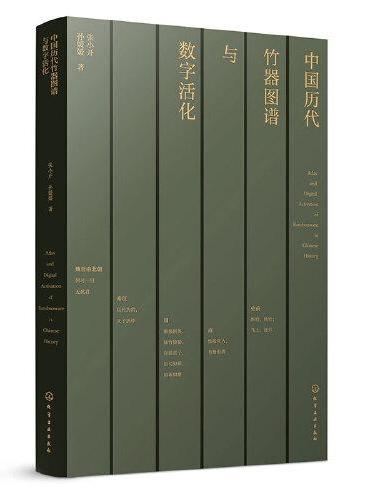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HK$
5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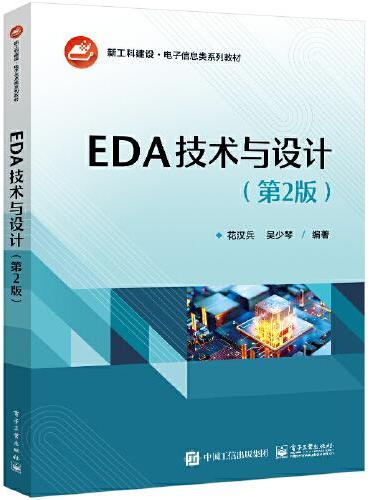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HK$
85.0
|
| 編輯推薦: |
当“设计”和“创意”成为时尚的时候,终于有人出来提醒“被设计”的“原罪”。从辨析Design
中译的含义到回应霍金《大设计》的思想超越。一位艺术史家逆流行价值的思考之作。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杭间作为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的总策展人,针对“设计的善意”这一主题所编集的一本个人文集。作为中国设计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本文集汇总了他自2006年以来最重要的有关于设计的文章,其中既有作为教育工作者对设计教育的思考和展望,也有作为充满情怀的学者对设计本来面目的追索与探讨;既有在全球化大格局下,设计作为创意文化产业龙头的责任意识,又有回归生活本真,怀抱理想主义的设计原乡情怀。“在设计界谈理想一直就是我的理想”,杭间,这位中国设计界最有情怀的学者,以设计的善意,向我们展现了设计的未来。
|
| 關於作者: |
|
杭间,艺术史学者,批评家,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展人。
|
| 目錄:
|
善意的
善意:反抗“被设计”
设计的民主精神
复杂设计的含义
手工艺的“新美学”释义
“烧包”美学
中国形相
另一种启蒙—— 30 年来的中国设计观察
关于国家视觉设计
中国的工艺史和设计史的区别
“中央工艺美院”消失了吗?
在清华的“美术学院”
“象山”的艺术乌托邦
中国设计与包豪斯—— 误读与自觉误读
从米兰开始的漫谈:中国有创意产业吗?
巴别塔
大设计—— 向霍金先生致意
“设计史”的本质—— 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设计的“公社”精神
全球化下的DESIGN 中译
芝加哥来信:关于艺术或设计的基础
大学、艺术和艺术史
有关陈丹青的误会
设计理论,怎样照进现实?
艺术的身后还有其他
|
| 內容試閱:
|
艺术的身后还有其他
《艺术时代》记者赵子龙、李国华专访
赵子龙(以下简称赵):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你就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你那时对当代艺术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当时的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价值是什么?
杭间(以下简称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85时期有着非常好的艺术环境。照相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等艺术风格进入中国最早的落脚点都在此处,加上吴冠中《形式美》的思想基础,整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80年代非常地活跃。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不少人投入到当代艺术创作中,最早在圆明园画家村做盲流艺术。如吴少湘、陈肖玉,以及最早进驻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华庆、高波、张大力。
而我最早接触当代艺术也是在85时期。当时有两份刊物比较活跃,一是《中国美术报》,一是《美术思潮》。1986年出于机缘,我写了两篇关于吴少湘现代雕塑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美术思潮》,借此机会我也开始接触一些现代主义艺术的书籍。后来我又受《中国美术报》的栗宪庭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工艺美术的评论文章。受《中国美术报》强硬文风及栗宪庭的影响,尽管文章并没有对工艺美术作全盘否定,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鸣,甚至受到很多老一辈艺术家的严厉指责。因为当时栗宪庭及《中国美术报》将工艺美术与设计作为整个现代艺术的一部分,并希望用现代设计这一新观念的提倡来否定传统的一些东西。如当年包豪斯是被作为一个现代艺术流派介绍到中国,康定斯基、克利等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策略,当时没有办法将这些人归入设计,只能作为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而在89艺术大展期间,我正好是《美术》执行编辑,除了编选作品,还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现代艺术展侧记”的文章。我选择了站在历史旁边描述的方式,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对“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看法。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我与同时代年轻人有着相同的激情,但我是学艺术史的,因此我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对当代艺术感兴趣。也正因如此,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察比较理性,不仅仅是从视觉或者观念的角度。我坚信在当时中国情况下,当代艺术的很多观念能够给中国的思想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推动力,虽然它有许多问题。直到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比如798艺术区,虽然我不喜欢它向商业性的侧重,但仅从视觉角度切入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多样性的拓展。
赵:那么后来为什么慢慢淡出当代艺术领域?
杭:因为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我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开始变得“暧昧”,让我不喜欢。尤其是到宋庄及798艺术区阶段,艺术家渐渐脱离了圆明园时单纯的理想主义,而进入到一种真实的、完全后殖民语境的商业状态。如何成名、如何与画商打交道成为重心,在创作上开始在原来的风格上停滞不前,他们已经不再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再加上我有学院教学这样一个稳定职业,于是我重新回到相对单纯的学院的生存环境,当然当时并没有像今天想得那么清楚。
赵:你的博士论文《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中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进行了研究,为什么会想到从“思想”层面进行切入?
杭:对我个人而言,我关注并极力追求的是事物的思想性,我希望能看到思想的各种可能性,这些思想性可以让我从容地面对各种挫折,或是颓废,或是不如意。比如做传统工艺研究时,我并不在意工艺美学史,而是强调它的思想史,强调其非物质部分的文化思想价值。在《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我最终的目的也不是讨论美学问题。我认为,手艺的新美学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样式,手工艺术是一种中介物,是大工业时代背景下探索人与社会、传统以及未来之间的关系的中介物。
我与邵大箴先生合编过一套《视觉革命》的丛书。现代艺术是视觉上的革命,而后现代艺术则是观念上的革命,观念革命最大贡献就是思想性。因此,二十世纪后半叶人文学科里,就思想而言,艺术的贡献是最大的。或许很多人反对后现代艺术里形形色色的思想,思想本身可以被批判,但至少这一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新的东西,它的产生某种意义上对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赵:在你看来,传统美术、工艺美术与你所关注的“当代艺术”是否有某种共同之处?
杭:无论从物质、技术,还是从视觉、形式角度,我认为传统美术、工艺美术和当代艺术都不应该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应该是为社会、生活而艺术。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等人艺术高度毫无疑问对社会有积极影响,但我更尊敬那些试图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的艺术家。比如庞薰琴和包豪斯,事实上他们都一脉相承地相信艺术可以被用来改造社会。我对北宋宋徽宗和他所处的时代的艺术也很感兴趣,因为在北宋时期,他的艺术与政治、社会以及文人之间的关系,以此为立足点,我觉得今天当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是不正常的,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在你看来今天的当代艺术家生存状态是不正常的,那么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杭:目前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外部问题。中国当代艺术要想真正处于一个正常状态,首先它的外部社会必须是一个正常状态。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很多制度还不明朗也不完善,这些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价值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艺术,无论是展览,艺术家创作,还是艺术市场都有很大问题。近些年,在资本的推动下,当代艺术仿佛呈现出非常繁荣的景象,并且接连出现一些高价作品,但它并不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正常。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好艺术家和差艺术家,我们不用去担心艺术家的问题,但是好的社会环境和坏环境会对这些艺术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李:那么面对当下中国这种状况,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应该如何做才能做到最好?
杭: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当代艺术家可以把自己悬置起来,但又不是孤零零的一动不动,这是现象学的一个概念,我很难把他说清楚。
当然,艺术家也需要回到应有的思考和职责上去。作为一名中国的艺术家,必须要对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去思考、创作。
赵:鉴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当代艺术诞生之初就带有反体制的基因。但在今天,在固有的体制之外,当代艺术似乎有形成自己新的体制,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杭:首先我要问,当代艺术新体制是什么?在哪里?是当代艺术院、798艺术区、宋庄,还是职业艺术家、博物馆、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由资本所建构的当代艺术体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而全世界都有。中国当代艺术的递进跟世界当代艺术的递进是一样的,因为资本总是一把双刃剑。当代艺术院现在仅仅还是一个空壳,我们暂时不用去警惕。在我看来,当下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特点还是非体制,活跃、自由与职业化。也只有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的体制才是当代艺术真正的体制。
当然,目前当代艺术也面临了一些问题。我曾在一次论坛上提出过国家公权力认为“前卫艺术无害论”这一概念。这个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一是前卫艺术的革命精神下降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观点、价值观的推动下逐渐地被资本化,已无法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构成批评;二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文化产业化,它已不是艺术的革命,而是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行为,它跟酒吧、广告公司、设计等等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与主流社会也许能够接受,但是否还是当代艺术,这就需要打一个问号。按照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当代艺术一旦被主流社会接受它肯定就不是当代艺术了。
赵:这里边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嫌疑。
杭:对,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旦为主流价值,或者主流体制辩护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天职永远都是批评,无论这个批评是对的,还是错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御史,御史如果不发表批评,它就不是御史了。当代艺术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与主流结合或者被招安,那么它就不存在了。
赵: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性”?
杭: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站在自己的角度,让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与世界的主流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对话过程的正常化。我在《新具象艺术——在现实和内心之间》这本书里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艺术的“现代性”探索。从古到今,尤其是整个二十世纪过程中,中国存在着很多非常特殊的情形:“五四运动”强调民主与科学,注重写实而贬低写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化思潮在美术界澎湃;五十年代以后,受苏联与新政权的影响,产生了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七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西方思想再次进入中国,中国人又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直到近两年,随着本土意识慢慢觉醒,中国人又开始回归到自己传统价值观。事实上,这个过程本身可以被概括成一个“现代性”。就艺术角度而言,“现代性”就是中国人试图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来探索中国艺术的生存问题。但是很可惜,中国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仅仅局限于艺术家的层面,而没有上升至整个社会的层面,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经济的现代性等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分离。
李:你师从庞薰琴先生,那你认为民国对“中国现代性”的启示是什么?
杭:我入学的时候,庞先生已经很老了,为了办一本学生刊物,我的老师王家树先生介绍我去见他,老人不因我是一个刚刚大一的学生而轻视,而是第一次见面就推心置腹的与我谈话,有很多意思我当时并不十分明白,但老人满头白发下那种仍然灼人的激情让我深受震撼。陈丹青在《新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提到,很多人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以前都是民国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正视民国的文化价值。从社会角度,民国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与建设期;从文化角度,民国时期是非常独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转换成近代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意识形态,无论是哲学、还是历史,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民国。在我看来,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个最初结果。
李:你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对当下中国文化、艺术的启示、价值是什么?
杭:改革开放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所谓重新整理国故是片面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检讨。我们希望从一个当代的角度重新延续文化传统,所以今天精英文化的回头就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文化,实际上我还是坚持一种生态、多元的概念,不要有太多的人为操纵。此消彼长都是内部产生的结果,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伟大人物去推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社会集团去推动。所以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生态,中国文化强不强,中国文化能不能跟西方的某种文化发生比较,这实际上很难说,大概只有上天知道。
赵:作为一位在“文革”之前出生的知识分子,可否谈一下你对文革历史的见解?
杭:对于“文革”,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虽然我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文革”时我六岁,还不能完全客观地认识“文革”,况且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中国“文革”是与“五四运动”一样的大命题。除了非常惨烈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根本摧毁外,对于文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群利益集团的概念,代表着一种人;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它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军事的和社会的,而是一场“文化的”革命;第三个关键词是“革命”,革命在中国有其特定的含义。基于此,对于许多“文革”事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的封建社会没有太大的革命性变化。而新中国政权建立后,按照阶级成分划分,社会形态和价值观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角度来说,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端的延续。“文革”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且持久,比如“文革”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格局等、文化的后遗症,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彻底回避。
赵:结合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你认为文化建设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杭:近现代的精英知识分子,无论是蔡元培,还是陶行知,最初他们都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然后就到西方寻找真理,进而发现文明的结果包括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两部分,西方的传统文化显然无法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又相对处于落后状态。最后,教育成为众人之选择,成为兴邦救国之良药。这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所走的一条路,最后都回到教育问题。所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尽管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不一样,但解决或者超越它的根本方式却往往只有一个。对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君权高于民权的权利分配不均问题。但我们现在流行的民主概念来自西方,不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里。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是有一个“明君”,还是一个多数服从少数的体制,当然这个“多数”在今天是通过集团的利益来体现的,但因为这个集团的利益有了一个“明君”概念存在,故而就不需要有另外一个集团来制衡,这是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厉害之处。
事实上,要改变中国还是要回到改变观念的问题,要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归根结底的办法就是教育,所以自梁漱溟、陶行知以来众多知识分子最终都选择了教育事业。但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教育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教育问题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赵:如何在延续传统和文化民族主义之间斟酌?
杭:晚清以来破多于立,破就是革命,立就是建设,而破立问题本身都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对中国主流意识而言,肯定是破多于立,但从当代艺术视觉本身来说,立还是不少的,至少构成了九十年代一个非常丰富的当代艺术图像景观。事实上,最终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三个词是要分开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民族问题会逐渐淡化。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族群里长时间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应该予以保留,因为它是世界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民族主义则是这个族群中的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持集团利益而虚构出来的一种功利性的理念,所以它是我们要警惕和不可取的。
赵:中国当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当代文人的责任?
杭:人类可能很难超越时代的束缚,包括我自己在内。目前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只有少数的几个。在我看来,“当代文人”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他可以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当下,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举止,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往往都透露着内心的浮躁与庸俗,其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摆脱体制而独立自由地生存。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需要内外兼修,但今天已经不再被社会所强调。
赵:中国文化体系中能为今天世界贡献出的核心价值有哪些?最为糟粕的因素又有哪些?
杭:仅仅是以自我体悟的方式,我认为中国文化体系能够向世界输出的就是遵循生态过程中生生不息和生态之间要遵循的伦理,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糟粕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中国的农耕文化太注重经验,天生偏向于保守。对于一种文化,与西方那种截然另起炉灶的方式不同,我们不会系统地去否定,而是习惯于不断地作注、修正,而这也令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了活力。
赵:你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杭:对于文化,随着人的年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体悟。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我认识到了儒家的入世的可贵,但我在现实面前碰壁时,又会想到老庄的超越。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在根本上东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中国的文化并没有被很好地推广,也许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让西方人真正地去尊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实现。因为在中国,大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文化启蒙。
李:那么你认为真正的启蒙是什么?如果今天中国开始文化复兴,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杭: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希望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内核的情况下,尽可能客观、正确地反思中国文化。启蒙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发现,文化现实已经客观存在,而发现是文化复兴最重要的一步。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复兴的内容及方向是什么?是不是明代、清代、民国,亦或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时我不愿意提文化复兴这个词,因为这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存在很大的危险。中国历史上的形态和今天的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复兴的具体方向与内容,更何况这一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变化,社会形态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即便今天的文化内核没有改变,但文化越来越精致化、丰富化的变化趋势,已经注定了不可能恢复到三千年前那种简单的社会形态。即使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成分也并不一定能适应今天的中国,中国的文化发展还需要进行艰难的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