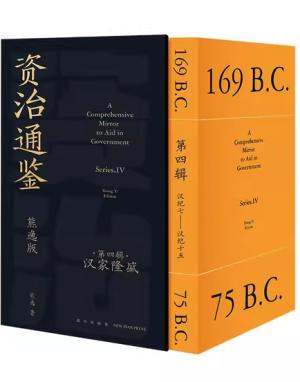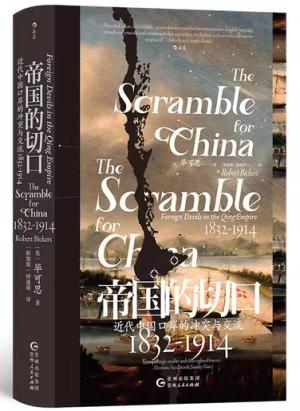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59.8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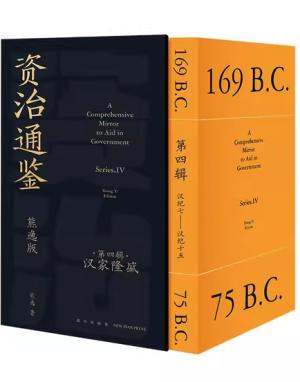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58.9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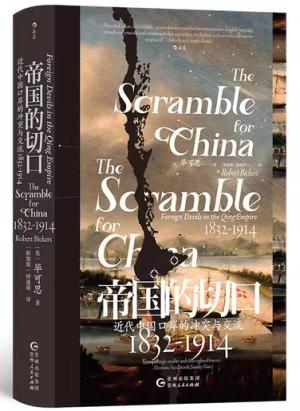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4.2
|
| 編輯推薦: |
虐恋王牌作家 短发夏天 倾城回归,
再续《北极星下落不明》飙泪经典!
这世上那么多爱情,
没有一种能抵达,她笔下的浓烈决绝。
一场误枪意外,三人命运逆转。
她是爱中困兽,怎样在他的怀笼里逃出生天?
初以为生命是一场华美盛宴,走至尽头,才发觉无法到达。
史上最悲怆的青春“犄角”成长录
给每个曾在大大蓝天下,单薄对抗世界的小小身影!
|
| 內容簡介: |
十年前的枪声响起,划破了暮鼓的沉静。叶明媚和叶晴朗,这一对双胞胎从此成了孤儿,却不得不要跟杀害母亲的凶手生活在一起。十三岁到十九岁,在这兵荒马乱的青春期里,叶明媚如同是斗士一般本能地保护着自己,以及弟弟叶晴朗。傍晚的冷风如同匕首一般刺穿了他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再也没有办法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然而唐诺的出现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整片的光明与温暖。爱与恨,离别与相见,误会与芥蒂,殊不知爱情是亦是百上加千,令她寸步难行。
这个时候,明媚亲生父亲的出现又将她推入了深渊:他带来了她难堪的身世,和母亲不可告人的过去。而她仇恨敌对了多年的弑母凶手,却另有真相……
在坠落的刹那,她仿佛看到了最美的时刻:在生命初始,人人都以为人生会是一场盛宴,待走到了尽头,才知不过如此。当我们回望来时的路,均是几许欢笑几滴泪,我们却已无法抵达。
|
| 關於作者: |
|
短发夏天,知名青春作家,出版畅销作品《北极星下落不明》《听说每颗星球都会哭泣》等
|
| 目錄:
|
第一部分:雨
大朵大朵的积雨云从东面飘了过来,天空黑压压一片。
傍晚的风如同匕首一样刺穿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露出铮铮白骨、血淋淋的肉。色
彩褪去,每一个人都面目可憎。
我拉着晴朗的手,像是走在地狱尽头。
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第二部分 多云
贫穷像虫子一样折磨着我,啃噬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想迟早有一天,我要过上很棒的生活,让每个人都羡慕我、嫉妒我。
我和晴朗身处其中,再也不会过辛苦的日子。
那一天迟早都会来的,我相信。
第三部分 晴
爱情出现得猝不及防,让我毫无招架之力。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即使是走在最平淡无奇的路上,也会遇到电闪雷鸣一般的感情。
很久以后当我轻念“love”这个词,脑海中满是那些温柔的细节:寂静的午后,冬日的阳光穿过树枝在地面留下斑驳的影子。
我与唐诺两两相对,却几乎一句话都不用说。
不用说,彼此却都明白。
那0.01秒,足够我珍视半生。
第四部分 风
曾几何时我们都幻想会有一双大手将我们从泥潭中拉出,清洗我们的凌乱和不堪
带我们去遥远的地方。
路途也许并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没关系。
只要我们都足够坚信,就一定能到达丰沛之地。
在那里我们再也不会悲苦,亦不会落泪。
第五部分 雨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唐诺的誓言就成了我的信仰。
它指引着我走向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确信的方向,
遇到困难时我就想,这是我通往极乐的必经之路。
唯有经历这样的磨难,我们才可以抵达终点。
只是我希望
那终点不要太远。
第六部分 沙尘
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待你多好、愿意为你付出多少时间与精力,你都没办法爱他们。而另外有一些人,
你甚至不明白自己在他们的生命中算什么,
却也没有办法讲他们从你的脑海中抹去。
他们就像是用钉子嵌在你的心里一般,你再用力也拔不掉。
也许不久之后,那些钉子脱落了,你终于可以解脱,
却发现他们曾经存在的位置上有许多的洞
你再也没有办法填满。
第七部分 雪
细小的雪花,轻飘飘、晃悠悠地落下来。
我第一次看到雪,那洁净的小羽毛,如同天使一样亲吻大地。
我看呆了,眼角还挂着眼泪,就那样痴痴地靠着窗户望着外面。
一片、两片、三片……
世界变得格外寂静,所有的声音都褪去,困难和不幸也褪去。
时间静止,这一刻仿佛永恒,
一切都不存在,没有过去,也不会有未来。
第八部分 风
外面是北京的春日,风呼啸着从小巷中窜过,如同猛兽一般。
这样的风声会让人欠缺安全感,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带去陌生的地方,
独自一人面对那些不知道的东西。
送走了韩放之后我去找晴朗,我们两个人在校园里散着步,
晴朗紧紧挨着我,
这一年他已经比我高了,但还是很瘦,头发短短的,依然是青葱年少的模样。
第九部分 雨
忽然下起雨来,是春天的第一场雨
北京的雨,不是那么干净,夹杂着泥土的味道
一滴两滴,干燥的大地如饥似渴地吸收着。
我看着前方,这是清晨的北京,宽阔的街道,
几只脚慢慢地走了过来,有人蹲下来望着我,轻声地说着什么,
但我什么都听不到。
|
| 內容試閱:
|
第一部分
大朵大朵的积雨云从东面飘了过来,天空黑压压一片。
傍晚的风如同匕首一样刺穿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露出铮铮白骨、血淋淋的肉。色
彩褪去,每一个人都面目可憎。
我拉着晴朗的手,像是走在地狱尽头。
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1
我们的母亲在我们八岁那一年去世。
我们——我,叶明媚,以及我的弟弟叶晴朗,一对双胞胎。二十一年前我们从同一个子宫内相继爬出来,降临人世。晴朗比我晚了一分钟,但更为顺利一些,据说是因为我在他之前,已经将道路铺顺了的缘故。晴朗自出生时就很乖,不哭不闹,护士担心他有什么问题,用力拍了一巴掌他才发出声音来。
那一天下着大雨,六月,南方小镇已然是酷暑,难产和身体的虚弱狠狠地折磨了我母亲,她一个人爬到医院里来,一个人面对生命的诞生,事后又一个人去交医药费、一个人带着我们离开。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那一年她不过十九岁,理应还是个孩子,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将我们生了下来。
未婚生子,在那个时代还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小镇是没办法待下去了,于是她带我们来到了城市,在城郊租了一间很旧的房子安顿下来,同时做点小生意维生。供养两个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还是有办法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回忆童年,固然我们过得很穷,然而并非不幸福。我母亲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最简单的菜也可以做得很可口,家里也总是干干净净,同时她知书达理,会讲故事给我们听、教会我们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她尽量让我们生活得体面,逢到节日,即使欠着房租我们也会有新衣服穿;本城开第一家麦当劳时,她便带着我们去吃。如今已经沦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厕所的麦记,在那一年多少人将之视为一顿豪华午餐,店铺门口停着不少好车,穿着簇新的小朋友挤成一团,我的母亲左手牵着我,右手牵着晴朗,不卑不亢地从人群中走过。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裙摆像伞一样打开,镜子里她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扎着两条辫子,尾部蓬松地搭在胸前,甚是好看。
“呦,这是你弟妹吗?好漂亮的双胞胎!”有妇人打量着我们看,在路上,我们常常收获这样的评价。但我母亲回答:“不,他们是我的孩子。”
那妇人愣了一下,很快又恢复那种恭维的神色:“您保养真好,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母亲淡淡一笑,带着我们离开。
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母亲,对我和晴朗来说,有没有父亲便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到了入学的年纪,我们母亲将我们送去附近的学校念书,自己则整天忙来忙去。她身兼数职,每天很早起床去市场进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卖,中午回家做饭,同时接了一些缝补衣服的活来做,傍晚又是一个销售高峰,一大群妇女坐在桥头叫卖,我母亲不,但她会把蔬菜洗干净,整齐地摆放在席子上,引得过路人来看。她卖菜都比别人有姿态,一到六点准时收工,无论有没有赚回本钱,都要确保我和晴朗能准时吃饭。穿堂风从巷子里呼啸而过,我和晴朗坐在旧沙发上看动画片,她在厨房里洗洗切切。那是我一旦回忆,就会立刻平静的好时光,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简单温暖,从未缺过什么,也从未抱怨过什么。
然而命运并不怜悯我们,它就像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看到哪里平静,就伸手拨弄一下。之于它这如同游戏,之于我们却是摧枯拉朽式的灾难。1998年10月23日,它带走了我们的母亲。那一天是霜降,但南方依然闷热躁动,天上的云纹丝不动,时间定格,枪声响起。
从此世界崩塌,巨厦轰然倒地。
2
1998年10月23日,晴天。傍晚的天空被夕阳染成霞紫,如同幻觉般瑰玮。下课铃声响起后我和晴朗整理书包,一起走出学校。我们所在的学校离家不到一千米,很近。刚入学那年我母亲同其他人一样,每天站在学校门口来接我们,但没几个月我们就认得路了,开始自己回家。母亲总是嘱咐我:“照顾好晴朗,路上不要乱跑,知道吗?”
因为那一分钟的时间差,我当然要照顾晴朗,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说,其实我是个路痴,记得路的是晴朗,他总是用很小的声音说:“这里要拐弯了姐姐。”
八岁那年我们一样高,但走在路上我还是习惯在前面一点。我们总是手拉着手,我一直觉得晴朗的手比我的好看,手指白白的、细细的,柔若无骨似地。小时候晴朗有点呆滞,反应也慢,但比我乖巧很多。他有一双异常好看的眼睛,漆黑、硕大,犹如一个小宇宙,里面干装载着星尘与光。假使我与晴朗留同样的发型,我想我们两个不会有任何不同,唯独那双眼,是晴朗最具辨认率的地方,他的眼睛比我大,也更圆一些。
我们去母亲常去摆摊的地方,这一天却没有看到她,问旁边的阿姨,她说:“你们妈妈好像去银行了。”
去银行干什么?我们没问,只是致了谢,转去银行的方向。西街有一间不算太大的银行,我们走到哪里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那里,附近停着几辆警车。我和晴朗一愣,费力地钻进人群,这时便看到了我们的母亲。
她站在银行门口,表情有些奇怪,侧对着我们,后半身被柱子挡着,只能看到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人群里面围着一圈刑警,正奋力阻挡看热闹的人群,而远处几个刑警正握着枪,或蹲或站地对准银行大门。我愣在那里,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时晴朗大叫:“妈妈!”
同一时间,枪声响起,我看到我们的母亲眉毛皱了一下,接着身体朝前倒去。
后来的这些年里,我总是一再地、一再地回忆起那一幕:尖叫着散开的人群,暮色的天空,凌厉的枪声。我和晴朗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看着我们的母亲倒了下去。只不过是一秒钟的事情,在记忆里却被无限地延长,那一秒变得无比缓慢、寂静。临终前她一定是听到了晴朗的叫声,她朝我们转过头来,眼睛里是无限的温柔和幸福,她费力地动了动嘴角,像是抽搐,又像是微笑。接着她眼里的光开始暗淡,没多久就像一小团火苗一样彻底熄灭。
多少年过去后,这个画面在记忆里已经褪去了所有色彩,变得灰暗而陈旧,声音也不复存在,如同一张老照片,充满了颗粒状的哀伤。我望着它、望着幼年的自己与晴朗,始终没办法忘记。
一双双脚从她身上跨过,将她留给我们最后的容颜分割成了碎片。再向上一点,她的额头上,鲜血正从一个黑乎乎的小洞里涌出来。
“妈妈!”我和晴朗一起向前跑去,却被一双大手突然抱起,一个警察粗鲁地说:“你们不许过去!”
“你放开我,我要去找我妈妈!”我用力地踢他。
“现在不许去!”他费力地阻拦我们,很明显,他很清楚我们的母亲是谁。那边警察和劫匪已经展开激烈的交锋,这边他抱着我们快步地走向警车里,将我们放下,说:“你们不要乱动,在这里等一下。”
他的眼神机敏且严肃,像某种野生动物,令人畏惧。说完他便把车门关上,那是辆专门押送囚犯的警车,驾驶座与后面隔开,只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外面。我们爬在车窗上看到他渐渐走远,而我们的母亲与我们隔着至少五十米的距离,行动已经接近尾声,警察很快制止了犯人,医护人员在我的母亲周围跑来跑去,没多久,她被他们抬走了。
这便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
3
那天夜里天开始下雨。绵绵的小雨如同细针一样洒落下来,警局里人来人往,我们被关在其中一间小屋子里,听着外面繁忙的脚步声。我和晴朗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但我们两个都在发抖。晴朗被吓坏了,目光呆滞,一直盯着前方的一片空白区域看。我小声唤他:“晴朗,晴朗。”
他半晌才转过头来:“嗯?”
看到他的表情我简直想哭,但我知道我不能哭,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
不久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推开门来,她穿着警服,十分娇小,长发扎成一个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她将一纸袋的食物放到桌上,问:“你们饿了吗?来,吃一点东西。”
她从纸袋里拿出汉堡和可乐,但我跟晴朗都没有接,我们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她,她愣愣的,解释说:“你们妈妈是人质……也不完全是人质,她不该出现在那里……开枪的人一开始不是要打她的……”
她有点慌张,说到这里拿出可乐兀自喝了起来,晴朗忽然小声问:“她死了吗?”
“什么?”她转过头来。
“她死了对吗?”晴朗的声音越发微弱。
她没有回答,但在那个时刻对我们来说,沉默就已经是答案。我紧紧地抓住晴朗,转过身去抱住他,生怕一不小心就哭出来,晴朗却依然身体僵硬,面无表情。
这时另一个刑警推门走进来,那是韩放,1998年的十月,他开枪打死了我的母亲。四年后我十二岁,第一次与韩放吵架,一遍一遍而又声嘶力竭地冲他尖叫:“是你杀了她!是你杀的她!”
他颓丧地站在那里,低着头,不看我。那时他已经略显老态,才三十岁的年纪,看起来如同四十。但1998年他还是年轻的,穿着合身的制服,因为刚进行完激烈的行动,衣服有点皱。他像所有的警察那样留着平头,有一双严肃而敏锐的眼睛,他看着我们,很久都不说一句话。旁边的女刑警跟他说:“他们都不肯吃东西。”
“你先出去吧。”韩放对她说。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出去。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他拉出椅子坐了下来,酝酿了很久才说:“你们妈妈做了坏事……”
他当我们是三岁小孩,我问:“什么坏事?”
“抢劫银行,有她的份。”他沉吟道,停了一会儿,又说:“她只是负责把风,不是什么大罪,不过……”
“那个阿姨说有人开错了枪。”我说。
他抬头看着我们,如果说之前他的眼睛里还有杀气,到了这一刻也只剩下脆弱。我怔怔地望着他,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
“是你开的枪。”我说。
他没有回答。
沉默降临在这个房间,如同石块一样巨大而厚重的沉默,盘旋在房间的上空,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我看着韩放,但他并不看我,只是低着头,用手撑着脑袋,显出一种很无力的状态来。我看着他,喉咙里有无数话想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紧紧地咬着嘴唇,克制着自己不去骂他。还有太多的问题我没有搞清楚,比如,我母亲为什么会出现在哪里?比如,她为什么会参与抢劫银行这种事?比如,她计划了多久?难道不明白这其中的后果吗?
比如,她究竟该不该死?
就在气氛如同凝结的冰块一样冷漠而压抑的时候,晴朗忽然发出很小的一声呻吟,接着倒了下去。我尖叫:“晴朗!晴朗!”
韩放连忙走过来蹲下去,拍了拍晴朗的脸,又翻了翻晴朗的眼皮,然后拉开门朝外面叫:“卢梦瑶!”
先前的女刑警跑了进来,看到这一幕时愣了一下。
“你去备车,我们去医院。对了,绕开那些记者,我们从后门走。”他吩咐她说。
叫卢梦瑶的女人跑了出去,韩放走过来抱起晴朗,但我不肯松开他的手。他看着我,说:“先带你兄弟去医院好不好?他大概是吓到了。”
我不说话,他看了我半天,才说:“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们母亲,对不起,但她犯罪在先,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你想打我、骂我,都可以,但不是现在,现在你兄弟的身体最要紧。”
很奇怪他会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仿佛在他心目中我根本不是个孩子。
后来我才明白,他并不只是这样对我们,他对每一个人几乎都这么冷冰冰,根本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但他讲了那一番话后我忽然觉得他是对的,当下还是晴朗最要紧,所以我松开了晴朗的手。他抱着晴朗朝外走,又回头对我说:“你跟在我后面,无论谁叫你都不要理他们,知道吗?”——他指的是守在门外的记者。
我点点头,跟在他后面向前走着。
4
我盯着韩放的背影看,他很专注地开着车,卢梦瑶坐在副驾座上,偶尔问他一些警局的事。这起事件带给她的影响不亚于我们,那一年她还是个新刑警,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也吓坏了。韩放偶尔会安抚她的情绪,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不动声色。
晴朗躺在我的旁边,我握着他绵软的手,偶尔他会叫我:“姐姐。”
“我在这里。”我说。
“我想回家。”
“一会儿我们就回去。”我把脸贴到他的额头上,韩放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卢梦瑶忽然说:“原来你是大的那一个啊,他叫晴朗,你叫什么?”
“明媚。”我说。
“真是一对好名字,简单好记,是你们爸爸取的吗?”
“我们没有爸爸。”
卢梦瑶怔了一下,又问:“那……其他亲戚呢?”
“也没有。”我说。
卢梦瑶发出一声轻叹,随即就不再说话了。终于到了医院,韩放将晴朗抱了出来,卢梦瑶则去挂号。因为穿着警服,所有人都让路给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警察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优待,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讨厌这个职业,讨厌一切他们所受尊敬和优待。
可能在心底深处我已经明白,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被推倒了“恶”的那一边。
我要如何接受,“我母亲是银行抢劫犯”这个事实?
好在晴朗没有什么问题,医生说他只是受到了刺激,挂点葡萄糖,睡一觉就好了。
我在病床前陪着晴朗,而韩放和卢梦瑶则陪着我。中途我趴在晴朗的床边睡着了,忽然被压抑的争吵声吵醒。我听到卢梦瑶说:“什么?这可不是件小事情,这两个孩子才八岁,你养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再说现在养个孩子又不是养只猫那么简单,你才二十六岁……”
“我已经想了一路了,我还有点积蓄,拿去做点小生意,省着点过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是韩放的声音。
“做点小生意是什么意思?你要离开警局?为什么?”卢梦瑶的声音尖锐起来。
我听到韩放叹了口气,轻声说:“早就想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十九岁入职至今,我亲手击毙过三个人,加上今天这个,是第四个。每天晚上我都梦到这三个人,他们变成厉鬼,来向我索命。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三个人的面孔,他们跟普通人的长相没什么区别,没有那么凶残,也不是一看就令人讨厌的类型。如果不是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他们也许会拥有虽不那么顺畅,却能勉强能过得去的人生。甚至如果他们能活下去的话,也许就交了好运呢?但是我摧毁了这一切,让那些可能性都变成了零……”
“但你是警察,这是你的职责!”
“杀人就是杀人。”韩放说。
好久后卢梦瑶才说:“好吧,如果你真的决定了,那加我一个,我家里还算阔绰,大钱没有,小钱还是不缺的……”
忽然有护士来查房,他们的话题就此终止,我闭上眼睛,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