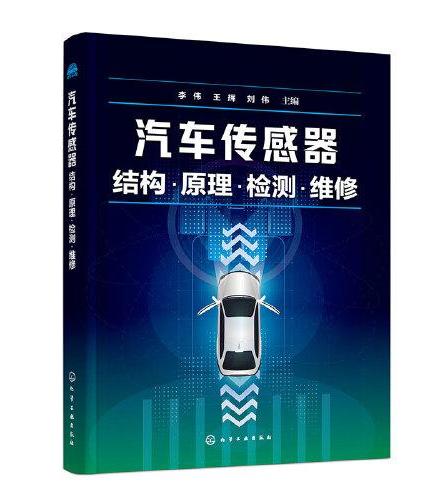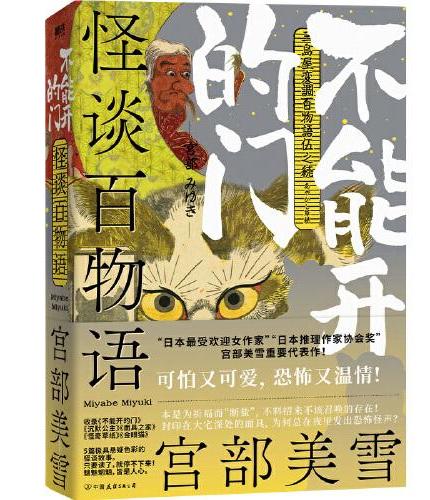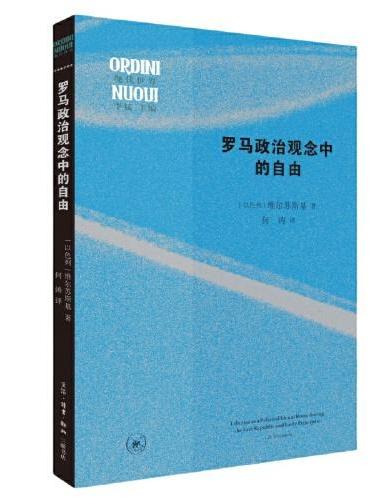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单元教学设计20讲
》
售價:HK$
76.2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HK$
69.4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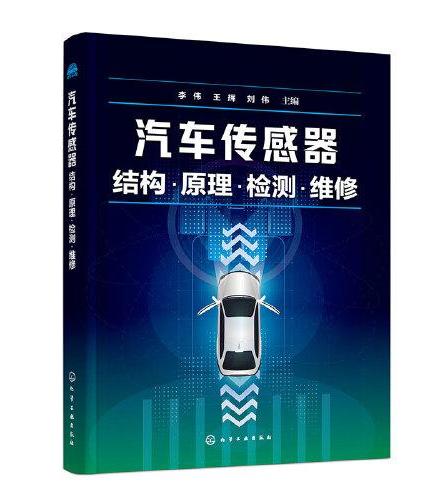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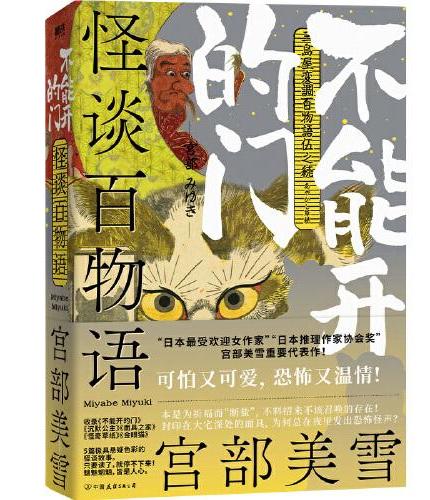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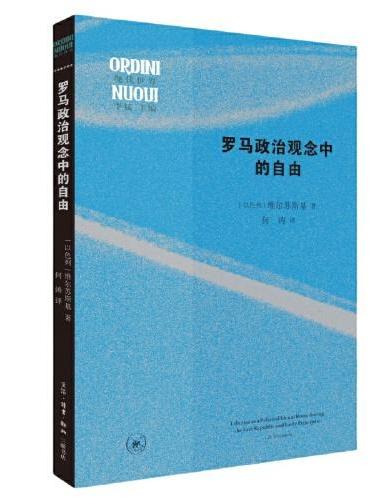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0.4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
有高宝军的《四季陕北》,则陕北之一切皆有情、有神。这本书写陕北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举凡清晨和夜晚、山川和风雨、农事和习俗、歌声和人情,一篇一事,从年头到年尾,六十篇短文,便是似水流年,天长地久。
|
| 內容簡介: |
《四季陕北》是作者高宝军结集出版的第四本小书,书名为《四季陕北》,是因为书中的章节以四季划分。收入书中的六十篇小文,写的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往事。
相信,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离开了那片土地的人们,读这些文字时眼里会含着泪水。
|
| 關於作者: |
|
高宝军汉族,1973年8月生,陕西吴起入,研究生学历,现就职于延安市委政策研究室。作品多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读者》《人民文学》《十月》等,获第四届、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一届、第二届西部散文奖等多个奖项。主要著作有《乡村漫步》《吴起古城寨堡初考》《大美陕北》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陕西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
| 目錄:
|
序
春
春日老黄风
细雨润早春
山村春暮声
陕北二月天
崖畔上的春色
冰雪上传来春消息
秧歌场跑驴
开门炮
正月初一吃饺子
陕北道情
穿新衣的烦恼
家家门前挂红灯
搭火龙
喊山
清明节的坟地
夏
亮红晌午
送饭婆姨
夏日收麦人
大雨前后的庄户人
西瓜庵子
捡麦穗的孩子们
初夏剪羊毛
揪苜蓿
暴雨中的山头
农活四记
夏夜里浇地
水菜园子
夏季锄地人
在洪水中游泳
打麦场趣事
秋
秋月下的山村
深秋霜叶图
露水地里的女人
秋日农家饭
秋天的庄稼
秋暮野望
老南瓜压塌地圪塄
金秋农家一幅画
连阴雨天编筐忙
刨红薯洋芋
陕北的大豆
手把利刃收高粱
收玉米
陕北麻子
高原秋声
冬
阳崖根晒太阳的老汉
清晨扫雪人
红白事上管事人
陕北道路
风雪夜里看病人
冬日放羊人
陕北窑洞
冬季砍柴人
生儿育女陕北人
冬日里的牲口市
冬晨挑水人
陕北说媒人
贴对联
做年茶饭
冬闲陕北看喝酒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春日老黄风 冬春更替时,阴阳大轮回,陕北不时刮大风。这风,学名沙尘暴,俗称
“老黄风”。在陕北方言中,“老”是大中大,强中强,猛中猛。一个“ 老” 字,说尽这黄风的阵势大、来头猛、危害重。
老黄风到来之前,会出现许多奇怪的预兆。本来好好的烟囱突然不冒烟了,柴烟从灶口往出喷,用大锅盖也扇不进去。扇得慢了它照样喷,扇得快了它在炕缝里墙缝里甚至锅台上往出冒。冒出来的烟不往上升,只擦着地面漫。
像舞台上施放的干冰。原本很老实的母猪突然噙开了柴草,把整捆的柴火往窝里拉,挡也挡不住。挡得慢了它不理,挡得紧了它还想咬人。眼睛红巴巴的,牙齿白厉厉的,细长的小尾巴来回甩。正推磨的毛驴突然不听话了,时不时就停下来竖起耳朵听,棒打也不动。打得轻了它不理,打得重了它往磨台上爬。
鼻子口里三股气,四个蹄子就地刨,浑身抖得格颤颤的。平时爱唠叨的老汉老婆突然不说话了,不但不说话了,连出气也不顺畅了,直催着孙子给他们捶背。这背就是个难捶,捶得重了他嫌疼,捶得轻了又嫌不顶用。嘴唇憋得乌黑,脖子胀得通红,翻来覆去把闷气生。本来很懂事的娃娃突然不听话了,一个劲地哭闹,不停点地翻腾。喂奶他不吮,儿歌他不听,大人稍一呵斥,他就用头在炕沿上碰。河面上的变化最为明显,水朝下游流,纹向上面涌,两者在反方向运行。大水潭更是古怪,无缘无故就自己“格涌”起来,像一碗没端稳的香油。
这时天低了,山愣了,空气好像不动了。气温闷楚楚的热,光线怪拉拉的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呛烘烘的土腥味,熏得人眼睛睁不开,心里生烦躁。
就在这时,老黄风远远地来了——天边生出一圪塄云,格涌涌地推过来。
这云瞬息万变、随步移形。先是平的,后是立的;先如锅底黑,后似铜锈红;乍看像雾霭,再看是黄尘。到此时,它已经完全变成一堵风墙了,顶上连着天,脚下扫着地,两边喷出无数黄絮子,像土坝决口时喷出的烟尘、大火突起时蹿出的火舌。它一股一股往出冒,一下一下向前舔;一冒就翻一道梁,一舔就越一条沟。过梁时像一只大手兜头捋,捋得小树伏了地,捋得大树折了枝,不大不小“半搭子”树,仰起来又伏下,伏下了又仰起。过沟时总是顺着沟底钻,一边钻一边朝两面山坡上卷,上去又下来,下来再上去,把藏在犄角旮旯里的隔年落叶,统统卷出来抛在河面上。河面立刻就被这些枯枝败叶罩住了,像洪水中的河柴,河水只能在下面委屈地流。
由于大山遮挡了视线,劳作的人们发现风时,风头子已经到了人们面前。
砍柴人没办法收柴,压住这一束,飞了那一束,好不容易收了一捆却背不回来。顺风走的,柴捆子成了降落伞,直把人往空中提,明明前面是崖畔,自己却收不住脚。逆风走的,不要说前进了,后退得慢了也不行,轻的吹人一个仰面朝天,重的会连人带柴扔出老远。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拦羊人了,大风一到羊群立即分化,山羊像疯了似的在坡洼上奔,拦也拦不住;绵羊头插在圪塄下嗅,拽也拽不出来。拦羊人只能在大风中操先人,先操羊的先人,再操自己的先人。可惜没人能听见,骂声早被风撕成了碎片,东山上一句,西山上一片!
山里的风大得惊人,村里的风却邪得出怪。迎风处扬黄尘,背风处卷杂物,半阳半背的山圪□里,风像漏斗就地旋、就地转。码在硷畔上的柴火垛子被旋到了河壕里,挂在墙壁上的羊皮被旋上垴畔山。直旋得门环铛铛响,门扇咣咣掼,窑檐上的黄土像大雨时的屋檐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下泻;窗户纸像吹鼓手的腮帮子一般,胀起又瘪下,瘪下又胀起。喜鹊窝散了,柴枝子在空中乱翻翻地舞;燕子巢满了,雏鸟在尘土里格哇哇地嚎。鸡娃子钻进猫道里,狗娃子躲到驴槽下;驴驹子靠在大树上,老母猪逃进萝卜窖。
这时候,天成了黑沉沉的天,地成了雾腾腾的地,光线暗得像黑夜一样。
划着火柴寻不见灯,两口子见面认不出人;窗棂子咯吱吱地响,窗玻璃咔嚓嚓地摇;裱在墙上的炕纸一闪一闪地往起皱,窑洞里的空气一搐一搐地往外抽。
直吓得老婆拉住了老汉的手,老汉抱住孙子的腰。当家的男女则忙成了一团,移来案板顶门扇,揭起毛毡遮窗户,切菜刀插在门闩上,破被子塞进窗窟窿。
做完这一切,一家人才缩在炕头喘粗气,瞪大眼睛听风声。
那风声就是个惊人,粗一股、细一股,紧一阵、慢一阵,高一声、低一声,长一下、短一下。一阵和一阵不一样,一声和一声有区别。粗起来好像天出气,细起来又像鬼拉琴;紧起来好像火上房,慢起来又像虫呻吟。一阵价
“唔儿一唔儿”地叫,好像儿马追骒马;一阵价“轰隆一轰隆”地吼,好像大炮轰雷霆。风到拐弯处盘旋时,那声音是“吱儿——吱儿”往出挤,像卡了挡的车轮、离了卯的轴;风在硷畔上横扫时,那声音是“哨儿——哨儿”
往出吹,好像二胡松了弦、竹笛破了腔。如果门外边有电线杆或白杨树,那风声就越发古怪了:一会儿像雪夜荒村弹棉花,一会儿像山寺禅房奏古筝,一会儿像女角暗夜吟京戏,一会儿又像碗碴瓦片擦锅帮。听得人哭笑皆不敢,胆战又心惊。
风终于小了,人们侧着身子出门,看到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景象。太阳像戴上茶色墨镜,万物都在这茶色中发晕。远山显重影,近山镶金边;旮旯里满是柴草,石盖上积了沙尘;大树只剩下骨架,小树只留了游魂;磨道里堆着沙蓬,窑檐上悬着头巾;麦秸堆揭了顶,碌碡上缠芦根;小河里飘着锅盖,石崖上挂着粪筐;老公鸡提爪巍巍立,碎猪娃竖耳静静听……
P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