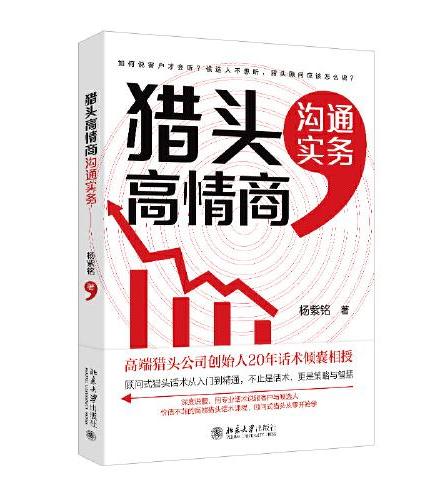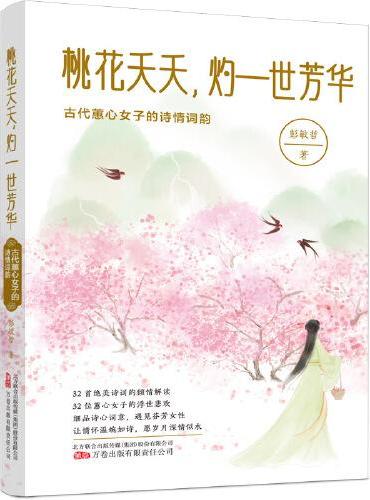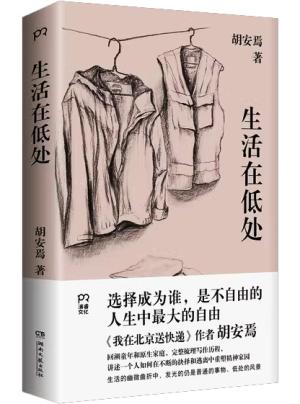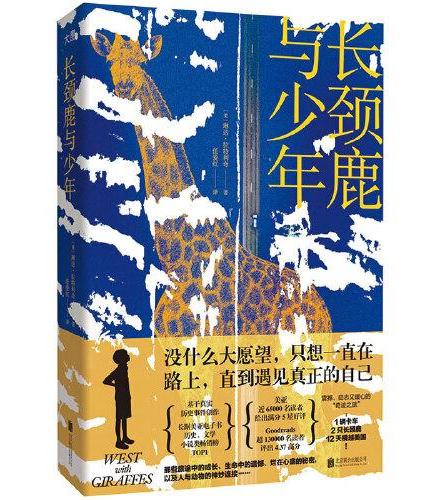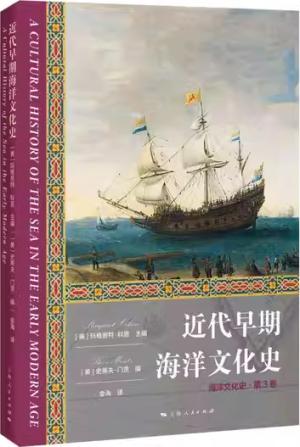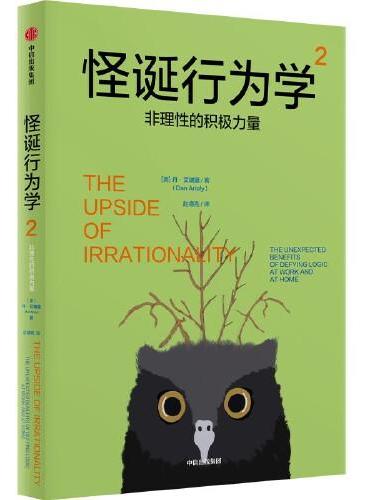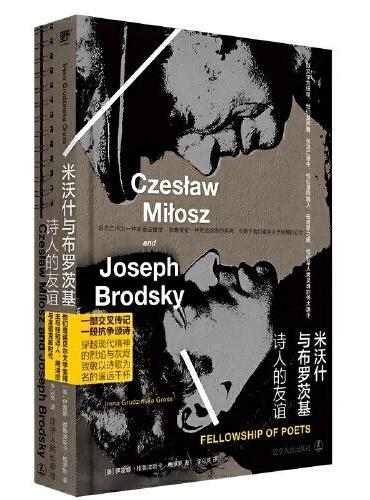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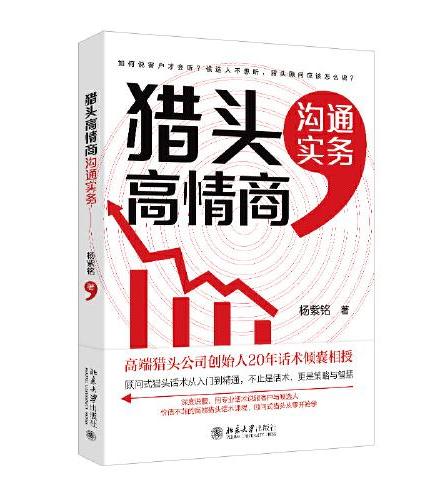
《
猎头高情商沟通实务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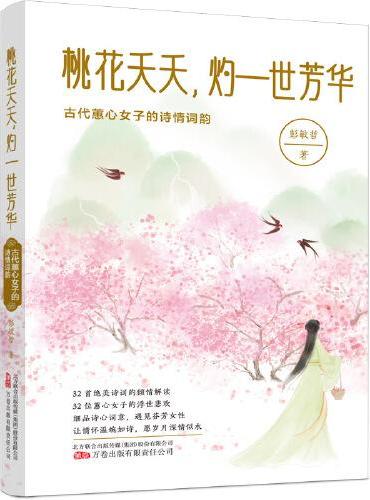
《
桃花夭夭,灼一世芳华:古代蕙心女子的诗情词韵
》
售價:HK$
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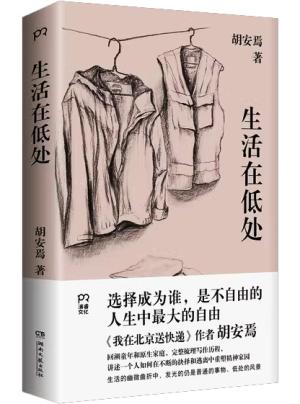
《
生活在低处
》
售價:HK$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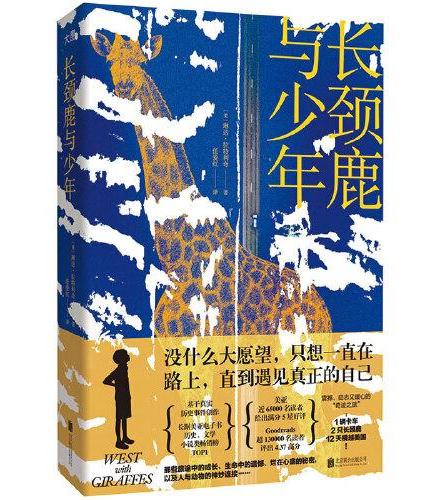
《
长颈鹿与少年(全球销量超过50万册。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
》
售價:HK$
5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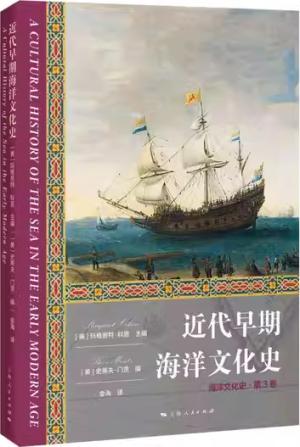
《
近代早期海洋文化史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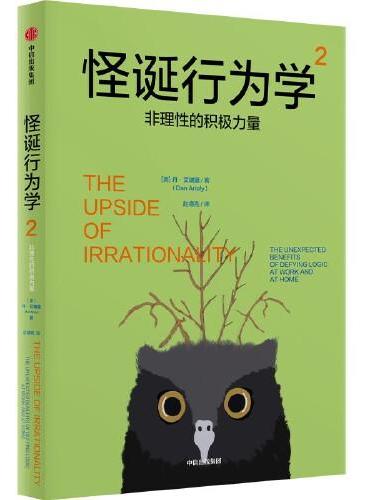
《
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
售價:HK$
78.2

《
锦衣玉令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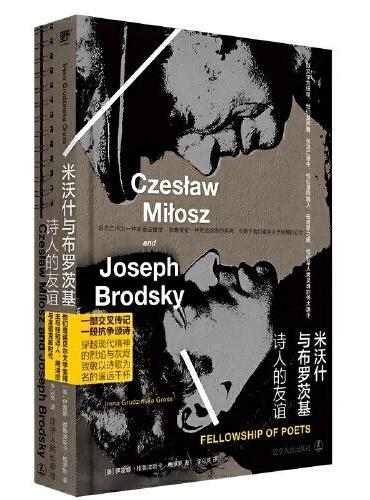
《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
》
售價:HK$
89.7
|
| 編輯推薦: |
欧美诸国各大书店热血推荐!百家出版机构主编连夜读完!
人生有很多抉择,最终考验你的不是你能得到什么,而是你愿意舍弃什么?!
认命、惜命、搏命——人生,你要哪种“命”?
又是哪种“命”可以成全你的漂亮人生?
柏林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法国读者评审团特别奖
毛姆文学奖得主 国际畅销书作家克里斯?克里夫新作!
一对姐妹花的人生PK 一场满载感动与启迪的幸福思辨
|
| 內容簡介: |
人生就像一个看不见的赛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制造的选手。
残酷的PK从爸妈孕育你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然后,你之后的每一天都处在竞赛的状态——似乎没有人想要一个比别人更逊的人生。
小说的主人公柔依和凯特,一个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择手段,一个遇事不争善解人意。
她们从十九岁相遇的那天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正面交锋——同为职业运动员,她们必须要一决胜负。甚至,在情场上。
如果人生有一天,必须为了最爱的人牺牲,放弃自己原本认为最重要的事,她们各自的选择会是什么?
最终,除了金牌一无所有的柔依,和为了家庭不断牺牲的凯特,到底谁才是人生的赢家?
这一次,请您做裁判!
|
| 關於作者: |
克里斯·克里夫Chris Cleave
二○○五年出版小说处女作《燃烧弹Incendiary》,即获得极大好评,不但荣获“毛姆文学奖”与“不列颠国协作家奖”提名,还被改编拍成电影。
三年后推出第二本小说《不能说的名字The Other
Hand》,一上市就造成轰动的阅读热潮!连续入围“柯斯达小说奖”、“不列颠国协作家奖”、“都柏林文学奖”,以及年度十大选书等。
备受各界期待的第三本小说《漂亮人生Gold》,克里夫以两位情同姐妹的奥运自行车选手为主人公,将她们放进最极端的情况中,让她们做出最困难的抉择,一如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处境,从而引起读者最大的共鸣。匠心独运的构思加上优雅的文笔势必再次俘获所有读者的心。
|
| 內容試閱:
|
柔伊瞪着下方的车道。凯特和杰克在笑。弧光灯照着他们。杰克仰头大笑,凯特玩笑似的握拳捶他的肩膀。灯光在她的头发上闪动,也在他的眼中闪烁。他们两人都他妈的在发光,好像他们是中空的,里面有十亿烛光的探照灯往外照,光亮穿透了随风飘浮的云朵,金银闪光盈满了普通人应该有肝肺肠的他们的体腔。
柔伊大皱眉头,“他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喜欢上对方,就这样?”她说,还弹了一下手指。
“啊,那叫化学作用。教练当久了,这种事也看多了。地球上最容易恋爱的人就是速度飞快的年轻人。”
柔伊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及时打住。
“有话就说啊。”汤姆说。
“好。”柔伊说,“你恋爱过吗?”
他笑了出来,“大概一天只恋个二三十次吧。到了我这年纪早就不去计算了。青蛙只要接上电还是会踢腿的,其实它早就跟星期二早晨的迪斯科舞厅一样,死透了。”
“不是啦。”她恼怒地说,“我是说真的恋爱。”
汤姆叹气。“恋爱?”他说,“有啊,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是什么感觉?”
“你问错人了。我说过,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柔伊仍盯着凯特和杰克,说:“我只是觉得心里有点没精打采,大部分的时候。有点像死了。其他时候,我又超级生气的。”
“这让你很害怕吗?”
她想了想,“对。”
汤姆点头,颇像医生同意自己的诊断。
“怎样?”她说。
“没怎样。我只是觉得这样子不叫做没有问题。”
“我只是诚实说出自己的感觉。”
“你才十九岁,柔伊。事情会越来越容易。”
她做了个嘴巴飞走的手势。
汤姆微笑,“真的。身为你的教练,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知道,你没见识过的东西还多着呢。”
“而你都见识过了,是吗?”
“我只是说,光阴总是向前进的。将来你也会找到喜欢的人。”
她瞪了他一眼,“我不怕一个人。你怕吗?”
“天喔,你疯了吗?我怕都怕死了。”
两人在上面坐了一两分钟,看着凯特和杰克,没有交谈。最后,柔伊把色拉盘递给汤姆,汤姆拿了颗葡萄。
他说:“谢谢。”
她说:“不会有下次了。”
汤姆哈哈笑,柔伊可没笑。
“我想跟杰克比赛。”她说。
“你在说笑?”
“不是,我对他很生气。让我试试能不能打败他。”
汤姆怀疑地看着柔伊,柔伊强迫自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她看着他的眼睛,两人间竟浮现了某种悲哀。让柔伊感觉痛,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是她自己的脆弱吧。她突然怀疑她当真能比日子更强壮,也怀疑她可能是个固定的物体,而时间有如风洞里的烟,无痕无迹地从她的身边绕了过去。
汤姆说:“我是自行车教练,又不是媒婆。我是说,要是你喜欢杰克,何不干脆下去跟他讲话。”
柔伊居然脸红了,“我才没有喜欢他。”
“那就放手吧。”
她轻蔑地甩甩头,“放他妈个鬼。”
汤姆仔细地观察她。
“怎样?”她说。
他曲起手掌,衡量两块隐形的物体,“你将来要不是上台领奖,就是装进尸袋里。我正在掂量会是哪一种。”
柔伊冷哼,“你不可能真的关心。”
“我领薪水来关心你们,好吗?这是我的工作。我深信你找对了教练,你会是个惊人的冠军。”
“我不需要教练,我只需要比赛。”
“那我跟你谈个交易,好吗?如果我让你跟杰克比赛,你就让我训练你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你还是觉得不需要我,我就把你野放。说不定在你身上装个追踪器什么的,将来警察找你的尸体也方便一些。”
她咧嘴而笑,“好。”
汤姆拍了拍她的肩膀,“乖孩子。好,你想跟杰克怎么比?如果是争先赛,你一点机会也没有,对不对?”
她俯视杰克所站之处,他仍然在车道边和凯特说笑。以车手来说,他很巨大,六英尺高,浑身肌肉,体脂肪是零,只有长长的骨头上铺展开四头肌、臀肌、腹肌,有如一张解剖图。柔伊上上下下打量他,看不出有软弱的地方。
“距离吗?”
汤姆点头,“我看也是。让他骑个几圈,他可能会慢下来。有没有比过追逐赛?”
柔伊点头。个人追逐赛是最简单的比赛。两名车手各据车道的一侧,以逆时针方向前进,追上对手。一开始就要使尽全力,谁追上了对手谁就是赢家。要是两人都没有追上,就看谁先骑完全程。
“那好吧。”汤姆说,“十四圈?”
“好。”
两人下了台阶到走道上,汤姆召集学员,大声宣布比赛规则。柔伊紧紧盯着杰克,而他则觉得有趣地回看她。他那一双眼睛似乎有魔力。柔伊摸索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安全帽扣紧。她躲进镜面护目镜后面,喃喃说着:“来啊、来啊。”她开始控制呼吸。
她紧闭眼睛,任由所有深埋的愤怒浮上表面。她感觉到心底深处有股狂怒,怒气开始上升,越来越快,最后她知道如果她不立刻跨上自行车,让车子动起来,她会放声尖叫,而害自己被带离这个团体。
“开始吧。”她说,眼睛闭着,“来吧、来吧,开始吧……”
她任由自己被带到起始线。不知是谁推来她的自行车。她的身体因肾上腺素而发抖。她独自在起始线。其他学员聚集在车道另一侧杰克的四周,他们都希望杰克赢。柔伊无所谓。可是没有人帮她扶着自行车。汤姆号召自愿者,谁也不愿意。最后还是汤姆自己过来帮她扶着。
他握着柔伊的手臂,可是被她甩开了。
“得了,柔伊。”他悄声说,“我们现在实际一点。先尽量别让他在十圈内追上你,如果你能拖到最后四圈,你跟我就认为我们赢了,好吗?”
她设法开口,说:“好、好吧。”
汤姆大声要车手准备倒数,女生都兴奋地站在车道另一边,大喊:“加油,杰克!痛宰她,杰克!”红光满面地拍着大腿。柔伊看着赛场的中央,杰克回头看她,还笑嘻嘻的,笑得很假。
她硬把目光拉开。汤姆大声倒数。
还有十秒。柔伊瞪着前轮车道上的线。这窄窄的黑线会把你拉回来。她用力呼吸,把氧吸入血液里。专心。她顺着弯曲的黑线看过去,重力绕着她的愤怒轨迹在弯曲,召唤了她所有的恶魔,结合在一起,在她的核心凝聚为无边无界的能量热点。那力道令她打颤。她努力压抑,但也在爆发边缘。倒数即将结束。再压抑几秒,她将因这份绝对的愤怒而死。她拼命克制。速度想要破蛹而出。最后三秒,看似要失控了,但她还是克制住,专心想着比赛与真实的世界,只待信号一响,就要率先冲出。她的嘴在动:她在祈祷哨声快响。
说时迟那时快,“哔”的一声,她都能感觉到尖锐的哨音冲下了脊椎骨。这一声结合了她凝聚出的一个报复的白热光点。哨音释放了光点的生命。她的脑子还没听见哨音,脚已经先蹬下了。直冲出了二十码才有知觉。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有条理的想法冒出来:喔,看看,我在比赛了。
技巧自动恢复。她的身体所受过的训练开始接手。通过第一圈弯道,她放松坐上坐垫。两手放掉了把手宽的部分,手肘使力,摆出了空气动能姿势。她的脑子胡言乱语。说:“干干干,我要输了。”说:“鞋子,我需要一双新鞋。”说:“她的名字是里欧,而且在沙上跳舞。”这时她的心跳是每分钟一四〇下,消化系统也停止了,以便节省能量。愤怒转化为肌肉燃烧。肌肉燃烧又化为速度。她的脑子说:“铟锡锑碲。”她的脑子说:“我见过你们这些人不相信的事情。”骑到第二个弯道,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心跳已经是一五〇下,心智麻痹,视线周边开始模糊。是她的身体在截断非必要系统的供血。她的脑子说了最后一句,随即陷入死寂。“大伯恩罕树林。弹跳!弹跳!”她的心跳一七〇。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哀鸣。到第六圈,心跳一九〇。她不能思考,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也快失明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
一种极为缓慢的平静将她笼罩起来。每一焦耳酸苦的愤怒都化为速度。她整个人放空了。没有痛苦。风呼呼从耳畔吹过。她专注谛听,唯有沉默,是宇宙在表现它的大慈大悲。终于,她谁也不是。
这是绝无仅有的时刻。
可是紧接着就不对了。先是像窃窃私语,慢慢地想否认也不可得,杰克的轮子在她后面呼啸,还有他参差的呼吸声。还有八圈,他已经要追上她了。她使尽了全力,他也是。杰克就是比她快,她也无可奈何。
被另一个人追逐,是非常亲密的事情。她从来没有被追到过。她听见了杰克的每一次急喘,她听见他的踏板转到最高点要往下蹬时呼吸一顿;也知道他的身体俯得更低,贴着自行车,她能听见他四周的嘶嘶气流改变了音高。她的视线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光圈,光圈里有一条鲜绿色的隧道,仿佛她是戴着有色的头灯在骑车。竞速的黑暗边缘后只有她的呼吸以及杰克的,越追越近。外围传出别的人类唱诵杰克名字的声音。黑暗布满了幻影,她看见高大的桦树掠过,她看见绿色斑驳的树荫,还有条柏油路在前方向左拐。她听见在呼啸的气流中有个小孩子吃吃笑,她更用力蹬,希望自己的心脏会迸破,就不用再听了。
就在这个时候,杰克对她说了什么。他用不着拉高嗓门,因为他逼得极近。他说:“抱歉了,柔伊。”
他真的抱歉。她知道唯有这种抱歉是有意义的。他们两人每分钟的心跳二百下,筋疲力尽下的宁静席卷而来,她能体会他费了多大的力气才说出这几个字。她深知简单的一句话他得付出多少代价。
她大可就此接受。她大可全身一松,缓慢骑上几圈,随他去吧。她很想要。可也不知是什么愚昧的愤怒使然,怕是岁月的沉积,她的四肢自动上紧发条,让她拼命到快昏迷的程度。她使出了全力,即将失去意识。忽然她的把手一抖一歪。
“砰”的一声。
起初她不知道是她撞车了,还是杰克。
她的视线开始清晰,颜色恢复了。她仍在动,仍直立在自行车上。
稍后,汤姆向她解释事情经过,他说他从没见过有人那么用力撞上内侧的栏杆。杰克显然是卡住了她的后轮。值班医护人员只看了一眼,立刻在车道上帮他打针,让他昏迷。然后才把他抬上担架,移出场外。
事后的调查他们询问柔伊为什么不停下来。她跟他们说她一定是太过震惊。真的,她不要别人看见她的脸。她想要戴着头盔,因为护目镜可以遮住眼睛,而且她需要继续骑,让自己恢复正常。要是她能够一直骑下去,骑到地老天荒,那她真的会骑下去。可是她只慢慢骑了二十圈,尽量不去看杰克昏迷不醒躺在地上。等他们终于把他抬走,她才在赛场中央下车,用那里的固定训练器做缓和运动。
她专注地把心搏率降下来,想从一六〇降到八十,以一分钟降十下的速度,每蹬一下都用上两分钟。她降到了一四〇。有些女生走过来,没有一个给她好脸色看。她只耸肩以对,因为她又没有怎么样,她只是拼命地骑车。接着凯特过来了,眼里泪光闪动,而且全身颤抖。
“我不想这么说,柔伊,可是你很可能会害死他。”
她降到了每分钟一三〇下。
“我没有骑歪,我骑得很直。”
“不,是你斜插到他的前面,他怕撞到你只好急转弯,他一点机会也没有。”
“我又没有要撞他,我只是不想输。”
凯特瞪着她,竟然呜咽了一声──只有一声,声音尖锐。
“见鬼了!也不过就是一场自行车赛,柔伊。”
柔伊不敢看她的眼睛。悲凉的锐利边缘又硬插了回来,把比赛赐予她的平静硬生生掰开了。她极力抗拒,可是混乱仍然跑回来。她看着地面,缓缓摇头,“我知道。对不起,凯特。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凯特盯着她看了好久,接着走过来,碰她的手臂。
“也许你应该找个人谈一谈。你知道吗?找个医生。”
“嗯。”
“有没有人能带你去?”
“嗯。我是说当然有啦。”
凯特捏了捏她的手臂,“谁?”
她低头看着心跳监控器。
“一大票人。”
“其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
别承认。这是柔伊第一个想法。别让她看见弱点。往后的几年你会跟这个女生竞赛,可别给她抓到了小辫子。随便编个家人,随便编个伙伴,扯出北京人也没关系,就是别告诉她你只有一个人。
她说:“嘿,你是好人,我不是。这样总行了吧。”
“拜托。”凯特说,“我的意思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个人谈一谈。我是说,我们以后经常要一起比赛,不是吗?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做朋友。”
十三年后,在她四十六楼的公寓里,柔伊煮第三杯双倍浓缩咖啡,努力让手不要发抖。
你应该找个人谈一谈。关心你的人都会这么说。
快乐的人会相信某个人。她和凯特的差别就在于此。像凯特这样的人总是谨慎地走在同伴的附近,准备随时陪伴。即使是在最消沉的时刻,他们也能想象出有个人可以投靠。某个有魔法的人,能够用言语把他们再黏合起来。这个某人需要是个善于倾听的人,而且需要非常了解你,而且你也不必在十岁的时候杀了他们。
柔伊喝掉咖啡,冲洗杯子,进浴室去做今天早晨第二次的淋浴。她任由水把实习医生冲洗掉,把经纪人冲洗掉,把和杰克撞车的回忆冲洗掉。一切都冲洗掉之后,她又是孤独一个人,她哭了。没什么大不了。感觉很制式:纯粹是压力累积,接着泪水就涌了上来。几乎是无声的,唯有泪水混合着淋浴的水。一切都流了出来。为了淹没身体的痛,她练习伦敦奥运得奖感言。你知道,我只是很高兴我那天全力以赴,没有让队友失望;我得说各界人士以及我的粉丝给我的支持实在是太神奇了,而且,哇,好多的英国国旗。谢谢各位。
东曼彻斯特,克雷顿市贝灵顿街二〇三号
杰克抬起苏菲,要抱她下楼,动作很小心,怕压到了希克曼导管。到了她的卧室门槛,杰克停下。
“你确定我没办法哄你把衣服穿上吗,小把戏?”
苏菲格格笑,两脚乱踢,“不要!”
“那你这一辈子都要穿这套睡衣吗?”
杰克感觉到苏菲抵着他的肩膀点头,只是看不到。
“睡衣?真的吗?连回学校上课也不换吗?连结婚那天也不换?”
苏菲又点头。
“连你踏上奥运颁奖台听他们播放《天佑女王》也不换?”
“我没有要当运动员,你忘了吗?我要当绝地武士。”
“喔,我忘了,对不起。”
“你会后悔。”
“你在威胁我吗?”
“这是保证。”
杰克哈哈笑,可是苏菲对准他的太阳穴打了一拳,痛得他一缩。
“嘿!”他说,“你不是应该是可怜兮兮的男人婆吗?”
他捏捏女儿,力道不重,只是让她格格笑与扭动,并不会刺激到她的白血球又作出任何帮倒忙的反应。轻重该如何拿捏,你自会体会得到。
他抱着苏菲下楼,把她放在厨房餐椅上。凯特早就下楼了,拿褐色釉彩大茶壶泡茶,她搅拌过后才端上餐桌,覆上国协旗图案的茶壶暖罩。蒸汽从壶嘴冒出来,轻轻卷绕,穿过四月的薄光。凯特穿着扎口短裤和白色T恤,她探过身来要把茶壶放好,T恤下摆就往上跑,露出了屁股。杰克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怎么了?”她问。
“你是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只有你到现在还在用茶壶暖罩。”
她把他的手拍掉,“你们这些苏格兰佬,一点也不知道满足。”
“还不是因为你太好欺负了。”
她压低声音叫他住手,扭动着挣脱他的魔掌。
杰克吻她的颈子,放开了她,还朝苏菲眨眼睛。他把手机插进了音响,播放“宣告者”The
Proclaimers的《五百哩》,因为这是苏菲最爱的歌曲,还有什么歌曲更适合揭开一天的序幕呢?艰苦的训练尚未展开,清新的旭日颜色就像孩子的承诺。
苏菲跟着唱了起来。杰克喜欢苏菲对“宣告者”的喜爱,这两个来自利斯的精力旺盛的小鬼头,上半身穿着最好的星期日衬衫,塞进廉价牛仔裤里,眼镜和头发都丑不拉叽的。如果他们还公开表演,说不定他会带苏菲去看,等她好一点时,那她就可以亲眼看看他们如何站在舞台上。一个弹着原声吉他,另一个就空手站在台上,大声唱出这首歌,活像是把钢弹射进恶魔的内脏里。副歌的部分来了,杰克把苏菲抱起来,在厨房里转动。
一声啊会走五百哩远!一声啊会再走五百哩!做那个走一千哩倒在你门前的人!苏菲大声唱,杰克的胸臆间忽然充满了对女儿的爱。这是叛逆的呐喊,这首歌的精神所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凯特和苏菲都知道她会好转。内心深处,杰克很肯定他们可以赢过这个白血病,只要他们像个苏格兰人。
歌唱完了之后,该把苏菲的化疗药物从各种褐色药瓶里倒出来,装好一天的分量。苏菲抱着他的腿,跳舞跳累了。
“来,苏菲,坐下来好不好?我在弄你的药。”
糟糕,他数到哪儿了。六颗黄色小胶囊。四颗蓝白胶囊。六颗红绿胶囊。装进旧银杯里,银杯把手上绑着黄缎带,写着“冠军”。女儿知道服药的顺序,他们也印了一张单子贴在冰箱上,用漫画的无衬线字,还有美工图库的小太阳。幸好,化疗是这么的欢天喜地,真的,否则的话杰克可能会觉得很可怕。
小手又在拉他的腿,“爸爸?”
“干吗?”杰克说,声音很大,赶紧又放柔,“怎么了?”
“尿尿。”
“怎样,那就去厕所啊。”
“可是我累了。”
“什么,你连走到厕所都嫌累?”
她微笑,“对。”
他咧嘴而笑,尽量若无其事。她是真的太累了走不动,或只想缠着他胡闹?有时候实在是很难分辨。
杰克朝苏菲摇手指,“不要现在又变成娇滴滴的英国小姐了。”
凯特从隔壁房间跳进来,把手机放在餐桌上,抱起了苏菲,让女儿坐在她一边髋骨上。
“没关系,”她说,“我来带她。”
苏菲微笑,两手抱住妈妈,小脸埋在她的颈窝里。凯特俯身亲吻杰克,嘴唇分开,而且相当不急不缓,空着的那只手伸进T恤里摸他的后腰。
“你……”她低声说。就这样,他的恐惧过去了。
杰克坐在餐桌后,看着她完美的屁股渐渐消失,心里纳闷人生究竟是用了哪一种的算法,才让他娶到这样的好女人。说不定人生只是刚好分了心,把药丸倒出瓶子的时候算错了。
东曼彻斯特,克雷顿市贝灵顿街二〇三号,楼下厕所
凯特抱着苏菲到厕所,为她拉绳点灯。她摘掉了女儿的星球大战棒球帽,因为女儿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帽舌会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等着苏菲尿尿。有时裤子还没脱,就喷了出来,有时候你可以像这样站上一分钟,她还没动静。有时候只是虚惊一场,而你庄重沉默地等待着,一直到似乎安全了,母女俩可以稍息了。化疗就是这样子,每件事都受到影响。
她想着刚刚收到的短信。
“我跟柔伊下午训练完了以后要去找汤姆,”她大声跟杰克说,“可能有什么状况。你今天能不能再多照顾苏菲一会儿?”
“没问题。”她听见杰克也喊回来,“反正我可能会带她去看你们训练。”
凯特站着,观察女儿的大腿绷紧又放松,努力想尿出来。
“你要不要来看妈咪和柔伊训练?赛车场里可能会很冷喔。”
她半希望苏菲说不,可是女儿说:好。还是没有要尿尿的迹象。
利用等待的时间,凯特修正了下午训练的后勤准备。既然杰克要带苏菲去看,他们就得带着鼓鼓一大包的装备袋子到赛车场去。他们会需要氧气筒、希克曼导管,以及值班医师名单。也会需要苏菲的应急注射、她的吸入器,以及一整套的星球大战公仔。他们还需要那十几个不知为什么埋到急救袋最底下的东西,东西的功能你都忘了,可是你知道你不会忘了把东西挖出来使用的第二天。因为以他们家来说,后果会不堪设想。他们不能让苏菲因为爸爸妈妈把她的输氧管误接上某个快废弃不用的脚踏车打气筒,而枉送性命。
另一方面,柔伊却只需要把一把钥匙塞进牛仔裤后口袋里,就能出门。为了到赛车场,凯特和杰克必须把苏菲安置到安全椅上,检查所有的细节,再安全谨慎驶过十几个广告牌,每一个都有柔伊的脸。她的绿眼、她的绿发、她的绿唇膏,贴着泛出水珠的绿玻璃瓶。沛绿雅:冰凉后风味更佳。等到阿尔果一家子抵达车场,柔伊已经热身一个小时了。凯特拿什么跟人家比?柔伊一个人住在曼彻斯特最高的大楼上,而凯特却住在下面的人间,和家人在一起。
“放弃吗?”她轻声问。
苏菲叹气,“嗯。”
她帮女儿拉上牛仔裤,抱了抱她。她知道今天下午的一对一训练她会满脑子想着苏菲,而汤姆的哨子会冷不防吹响,那时她才会从恍惚状态回到现实,而柔伊已经超前十分之一秒。自由使得柔伊更快更哀愁,就算凯特有选择,她也不会跟她换。虽然如此,有时她仍得很费力才不感觉愤慨。即使知道是什么在鞭策柔伊,即使了解她的弟弟出了什么事,也很难忘记在两人成为朋友之前的争斗。不过,再想一想,说不定人人都有这种感觉。说不定人人都在和记性独有的缺点抗争,你越是想遗忘什么插曲,记性就越是贮存得牢。说不定等你长到三十二岁这个年纪,若是能够完全原谅朋友,就可以说是奇迹了。
凯特打个哆嗦,硬把这想法赶走。
她低头对苏菲微笑,想将女儿额头一绺稀疏的头发拨开,岂料头发却黏在手指上,连根从苏菲的头皮上脱落。这是她最后的一束头发了。苏菲并未注意到。
凯特拿起棒球帽帮女儿戴上。
“好,去跟爸爸玩吧。”她活泼地说。
苏菲一走,凯特放下马桶盖,有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屁股坐下。她瞪着手指上女儿的头发,小小的黄色发根在黑色发束的末梢颤抖,恍如裸露的电灯泡。她将头发举到唇边,吻了一下,感觉到发丝的柔软,吸入了微微的化疗及灰尘味。接着她站起来,掀开马桶盖,把头发丢进去冲掉。没道理大惊小怪。如有必要,杰克自己就会发现出了什么事;否则,略去不提比较好。说欺瞒就太严重了。她觉得自己做的就像舞台上的魔术师表演:玩个巧妙的手法,把噩兆的时刻收进掌心里,将家人的目光导向比较健康的迹象。这只是个小技巧。一个家庭是否生病,全看你怎么做。
凯特看着水由水箱如瀑布冲下。
苏菲的头发第一次长到可以剪的时候是两岁,凯特亲手帮她剪发。她把剪下来的第一绺头发收进相簿里,用胶带把黑色鬈发黏住,以最工整的笔迹写上苏菲的名字和日期。为此,她还特地跑到街角商店去买了一支钢笔,而不是一般的原子笔。
而眼前是她女儿最后一束头发,浮在马桶里。她再按一次冲水,可是头发就是冲不下去。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冲不走。
杰克在精英展望计划撞车之后,凯特不知所措。汤姆向其他学员宣布杰克被送进了北曼彻斯特综合医院加护病房,至少有些骨头断了。计划也就此结束,比预定时间提早两个小时。震惊之余,脑中的思绪有如雾中声音一般模糊,凯特冲了澡,从赛车场走路到火车站,装备袋沉重地压着肩膀,头发也还没干。
行走在寒冷的空气中,她记起了杰克按着她的手臂,两人在比赛间的长谈,他还玩闹似的摸她的脸。她现在就看见他的十指,骨折浮肿,骨头穿刺而出。还是手臂?腿?脊椎?不同的画面掠过心里。她怎会就这样走开?她不会用渴望或吸引来形容,那不是她的风格。她只是有所领悟,她在乎他究竟是断了什么骨头──她需要知道。
然而去医院的想法让她不安。去干吗?坐在他床边,检查他的手,如果不是断得太厉害,就握住他的手吗?她凭什么?她也不过才跟杰克认识三天。可是毫无行动,感觉也不对;搭火车回家仿佛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这样也不行。难道这只是自然反应,不愿意离开现场,只因为跟男生的交谈不该这样子结束,不应该是男生注射了镇静剂,一动不动,被戴手套穿工作服的医护人员放上担架抬出谈话现场。以她想来,计划中的每一个女生都跟她有同样的想法。杰克不也都对她们微笑了?她不会是唯一心跳加速的女生吧?说不定她的感觉很平常,只是一个稚嫩的普通北方女生错把下雨当成了彩虹。
凯特蓦地在街上停住,行人略一踌躇就修正弹道,从她的两侧流过。
她抬头,努力思索。承平时代并没有现成的礼仪规范,可以让你由轻松的调笑一跃而至严肃的探病,还能为这么突兀的一步找出圆滑的托词。没有情感上的法理学;有的只是怀疑,怀疑她对杰克的感情是否真到了让她需要为他产生感觉。倘使她真的对自己诚实,她现在确实是想坐在他的病床边,双手抱住他的手,说不定还小哭一场。对了,就是这样──她想哭。是陪他一起哭,或是为他而哭,她也说不上来。
如果她在街上看见有人这样凄惨地抬着头,她可能会基于礼貌而移开视线。这样正常吗?别的女人也有这样半疯狂的感觉吗?或者这样的左右为难是她独有的,与她所选择的激烈生活有关?说不定她并没有反应过度,说不定这是她真正的感情,只是太过锐利,乍然涌出所以才承受不住,被十三年来的艰苦训练压抑住,而如今像智齿一般割伤牙龈。
她呻吟了。难怪没有人要参加自行车赛,难怪没有人要一天训练七小时,难怪别人要喝酒、累积体脂肪、晚上和朋友放轻松,才不用像新生儿一样处理这么棘手的感情。她的心跳加速,脑子乱成一团。她蜷起手指握成拳,挫败地闭紧眼睛。
白昼的明亮日光被午后的云遮住了,这时第一阵雨点落在路面上,其他行人纷纷加快脚步。新雨赫然带来了清新的水汽,渗透了城市交通的乌烟瘴气。她看着人群四散,不禁纳闷是哪件事比较可怕:她也跟大家一样,或是她跟大家不一样。假使他们也有和她一样的感觉,那怎会有人活得下去?要如何承受那么多撕裂割扯?那么多裂解,而你的每一层黏附着彼此,却由你的核心完全剥离?如果她让自己恋爱,很快她会一无所有。只剩她在做鸟兽散的人群里踽踽独行。
她应该回家。她明天早晨五点又要恢复训练。她在LA健康中心担任私人教练,还在大学修课,两年后就能成为物理治疗师。她有需要她的人。
凯特迈步又走,向火车站而去。她很自觉地导航,悒悒然知觉到每一步都是不祥的预兆,都带着她远离杰克,回到自己的生活。她自觉太渺小,无法思索这么宏大的问题。她看着运动鞋又在潮湿的石板路慢下来,她对脚下的纹理与踩到的每样东西都极敏感。这是合成鞋底和濡湿的烟蒂,以及一坨坨硬掉的口香糖的重要对话。
要是她现在转身朝他而去,她会失掉重心。她原本计划在精英展望计划结束后离开赛车场,直接搭火车回家,再等着看英国自行车协会是否跟她联络。计划很好,可是偏又出了这件事。她的心既是日落又是日出──明晃晃,却又半昏暗的一团混乱。既是她一生中最刺激的时刻,又是极端痛苦沮丧的时刻。
她十九岁。走到车站的半途中猛然打住,方向一变就朝医院飞奔而去。
她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加护病房外的宽敞走廊。两边墙壁排满了可堆栈的褐色塑胶椅。护士说不出个所以然,要她等。她坐了一个小时,读着有关死亡与死因的传单,还是没有消息。今天的比赛让她累坏了,所以她躺在三张椅子上,用大衣当被子盖上。
她梦到杰克,醒来时双腿间湿润,胸口如小鹿乱撞。外头一片漆黑,医院走廊亮着长灯管,死苍蝇困在霜状表面的亚克力罩壳里。这是她看见的第一样东西,然后才是一张中年人的脸俯视她。她坐了起来,两眼眨个不停。男人的脸很像杰克,却是半死不活的。她一手捂住嘴,硬把尖叫吞了下去。
男人身边还有个女人,握着他的胳臂。
女人低声说:“你吓到她了。”
凯特的心智在梦境和难以理解的现实间打哈欠。
男人一脸好奇,也可能是敌意,也可能两者兼具,“你是来看杰克的?”
凯特坐起来,拥着大衣,“嗯,对。”
“你也骑自行车?”
“对,我是凯特。”
男人瞪着她。他的脸和杰克的脸全混在一起了。她吓死了,用力眨眼,驱走睡意,膝盖紧紧靠拢,突然又羞又慌。梦里的影像逐渐散了,不知道她在睡眠中有没有发出声音。
“你就是那个害我们家小子撞伤的疯女孩?”
天啊──这是杰克的父母。
她摇头。
“那你跑来干吗?”
凯特这才发觉自己脸红了。
“哎呀,别烦这个小姑娘了。”女人说。
“我是罗伯?阿尔果。”男人说,“这是我太太席拉。”
席拉穿牛仔裤、蓝T恤、米色麂皮靴,脚踝内侧的麂皮磨得发亮。她大约四十岁,骨瘦如柴,肤色苍白,头发干燥,蓝眼睛,还有两个黑眼圈,不像是挨过打,倒像是服毒所致。剂量极小,不动声色地服食多年。看她的皮肤,微泛蜡黄。还真可以想象出她溜到楼梯下的柜子,把鞋油盒打开,迅速地嗅一下舔一下,再匆匆回到厨房,帮罗伯泡茶。罗伯那副样子……凯特说不上来。就像是那种会把你逼到去吃鞋油的家伙。
席拉抬头对她短促一笑,又低头看着双手,摆弄着一件折起来的蓝色丹宁布外套。
罗伯比儿子矮小,也比较瘦,秃头,脸上带着病容。五官确实有点像杰克,可是抽烟腐蚀了他的生命。他的皮肤蜡黄,粗如皮革。凯特的脑筋转不过来,怎么可能杰克那么健美,他的父母却是一副中毒已深的德性?杰克简直是腌蛋里孵出来的天堂鸟。
罗伯和席拉在走廊对面坐下,面对凯特。两人之间留了一个空位,罗伯把汽车钥匙放在上面,还有一份折起来的报纸,是那种在第一页就有乳房可是乳头以小星星覆盖,以免有人觉得伤风败俗的小报。他又在钥匙旁放了蓝色迷你打火机,一包十支装的班森海吉香烟。他穿棕色皮外套,有垫肩。散发出烟和牛的气味,有些冲鼻。他没看凯特,而是瞪着她头上的墙。
“我们儿子是来这里出人头地的,不是来给小妞追的。所以别动歪脑筋。”他的视线一直往下掉,最后直直看着凯特,“对吧?”
就连他的眼白都是黄色的,虹膜混浊。
席拉脸红了,两手挤压外套。不看凯特,却对她说:“对不起,凯特,真的很对不起。可是你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这是能让他脱身的唯一机会。”
她摇了好几次头,动作很快,强调她的话。
罗伯拿起了打火机,只转动了摩擦轮几次,动作也很快,但并没有打燃瓦斯。
他说:“医院打电话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了,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席拉说:“不知道。”
“我们走M6公路来的,汽油一升一镑,可是谁叫他是我们的儿子呢。”
席拉说:“我们的儿子。”
凯特听见自己说:“对不起。”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这句话,她也搞糊涂了。突然从跟杰克有关的春梦中被叫醒,就撞上了他的父母亲,这样的现实太沉重了。她急忙告辞,拎起装备袋,匆匆沿走廊离开。
如今她明白了,她误判情况,错得离谱。她也真是的,怎会天真得以为杰克的调笑有更深刻的含意。他当然会跟女生甜言蜜语。而她毫无免疫力。这些年来别的女生陆陆续续累积经验,已经打过许多预防针,而她只懂得绕着圈子越骑越快,现在可好,她被内在的各种力道压得不成人形了。
她羞愧得无地自容,趿着湿透的运动鞋,背着沉重的袋子,在夜色及雨幕中走向曼彻斯特皮卡迪利车站,及时搭上开往格兰吉杉兹的末班车。搭出租车回家后,深更半夜无法成眠,只看着窗外黑色的海浪轻拍沙滩,然后她又骑着训练自行车回车站,又买了一张到曼彻斯特的票。她太疲惫了,一丝丝诧异也没有。她搭上了南下第一班火车,温驯地坐在角落,车厢很快挤满了乘客。她根本也不是勇敢。她两手交握,摆在腿上,小脸抬起来看着雨,高速的气流吹得雨珠横飞,打在车窗上,她等待着,清楚地知道等着她的只有羞辱。
从曼彻斯特皮卡迪利走回医院,她是个毫无希望的囚犯。她爬上楼到加护病房,脚步沉重,等到了走廊上,就听见护士说杰克已经转到一般病房了。饥饿再加上一夜无眠,她的头嗡嗡响,但她仍勉强循着明亮的三原色标线在走廊上寻找,最后找到了杰克的病房。她一掌平贴着沉重的自动门,不知道杰克看见她会有何反应。可能是难以置信吧,而后是尴尬,再来就是怜悯。她的脑袋嗡嗡响,觉得视界变小,好似快要晕倒。
她一把推开门。半空的病房对面一半的地方,杰克躺在病床上。他躺在绿床单上,颈子装了护套,一条骨折的腿吊着。床边有人坐在褐色塑胶椅子上,剃了大光头,穿着黑色羽绒外套,也是一副自从意外发生就没阖过眼的模样,是柔伊。她用双手握着杰克一只手,柔情款款。
凯特走进病房,柔伊抬起头,两人视线交会。当时柔伊的眼神──恐惧、挑衅、凄凉兼而有之──凯特永远也忘不了,即使是这么多年后、柔伊已经是她的朋友的现在。
凯特扯了两张卫生纸,沿着孔眼折成一张,小心把纸平放在马桶里,盖住苏菲仅存的头发。水箱又装满了水──时间自动更新──凯特再按一次冲水柄,把头发和卫生纸一起冲走。等到确定都冲掉了,她才把盖子放下来,坐在上面,在光秃秃的灯泡下。坐下后,她轻拂电灯的拉绳,看着她的旧国协金牌吊在灰色磨损的拉绳尾端,来回摆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