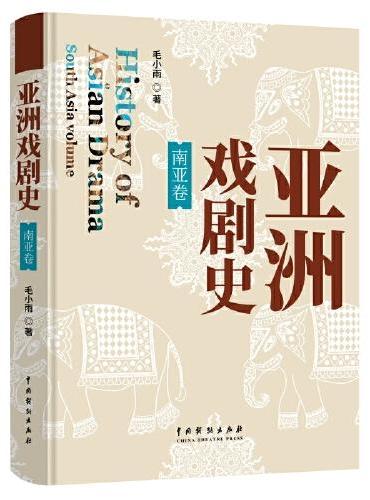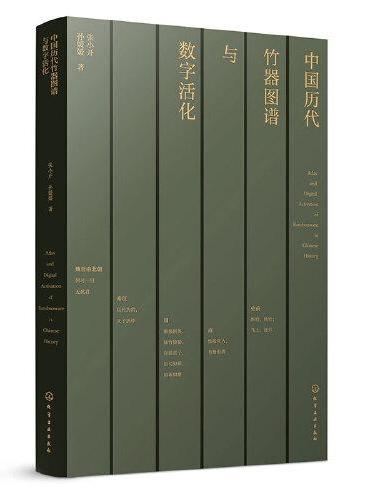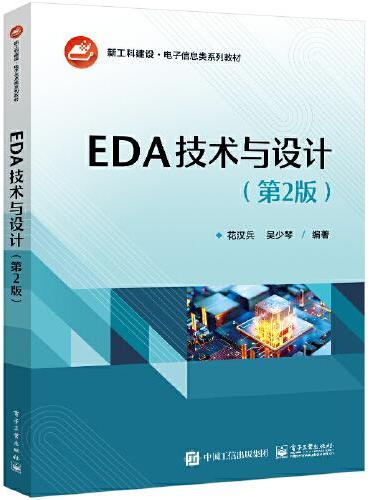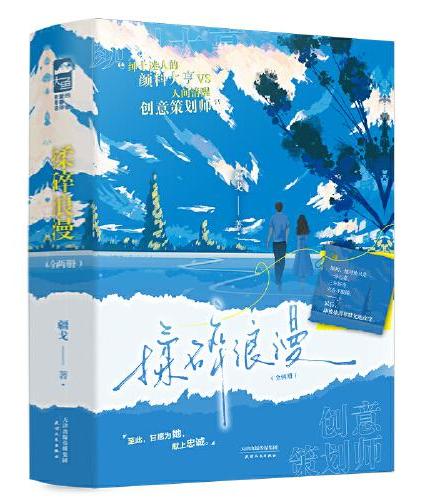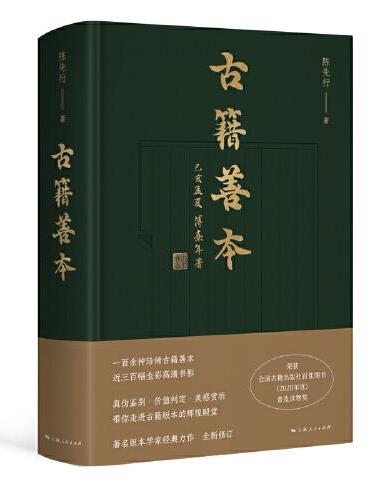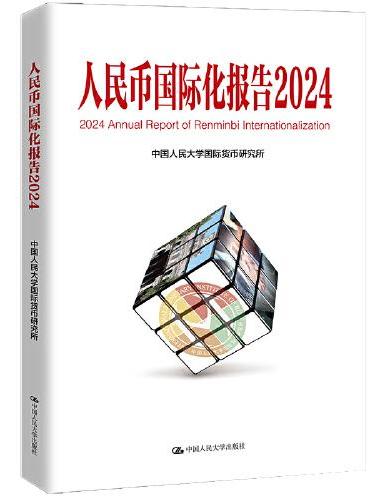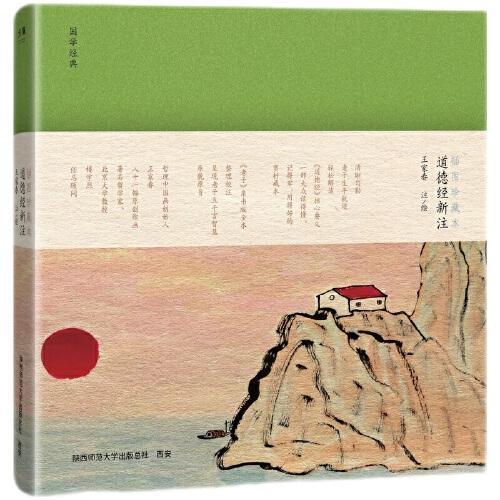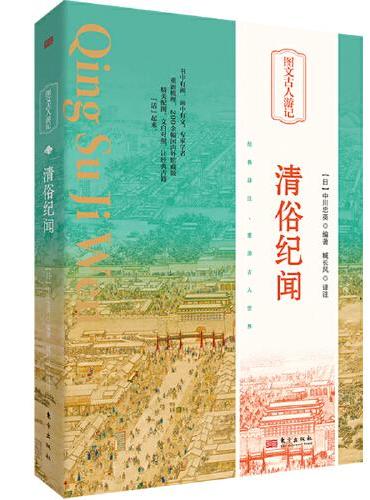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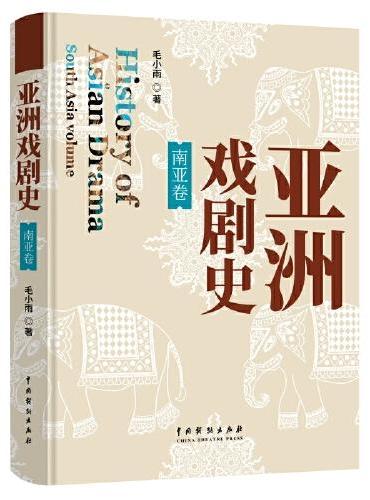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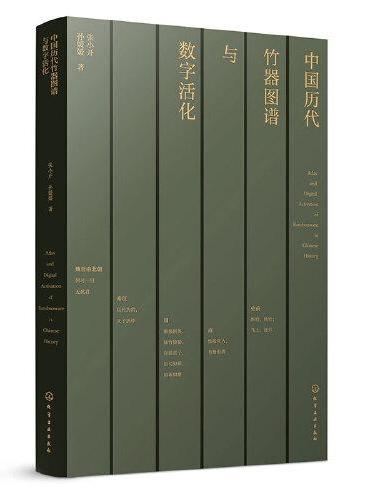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HK$
5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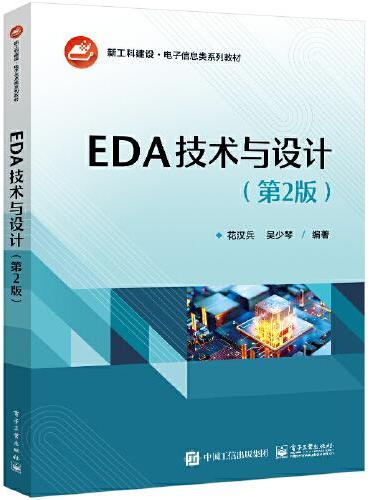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HK$
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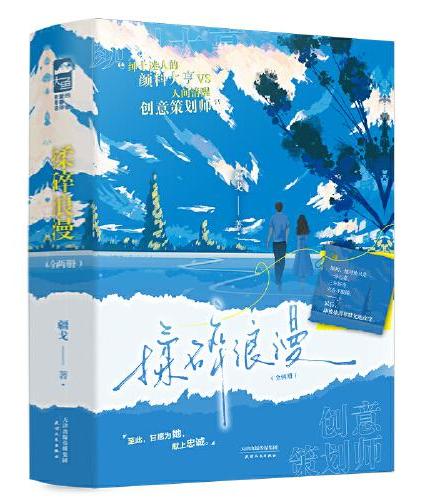
《
揉碎浪漫(全两册)
》
售價:HK$
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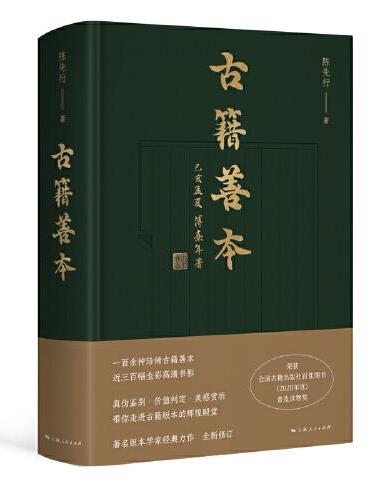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HK$
5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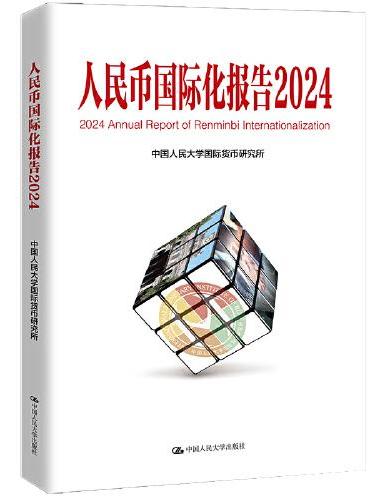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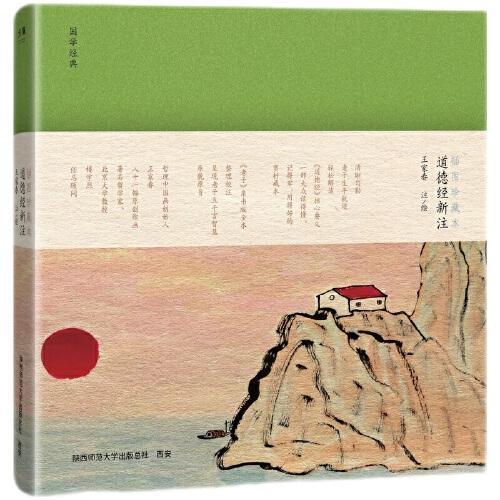
《
道德经新注 81幅作者亲绘哲理中国画,图文解读道德经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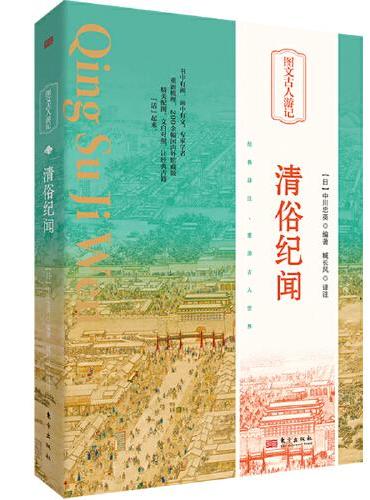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 編輯推薦: |
|
没读过土屋隆夫,对日本推理小说的认识,永远少一块,很小很小(因为土屋隆夫的作品那么稀少),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块。——杨照(台湾知名作家)
|
| 內容簡介: |
什么样的秘密必须死守,什么样的仇敌必须拿命来偿?
文艺评论家去长野(又见长野)取材,却在小诸车站神秘失踪,后来其上衣被人发现丢弃在草丛里,上衣口袋里还放着一截断指,和写有“我就像是那只盲眼乌鸦”的碎纸片。后来,又有一名年轻的男子突然死在路旁,临死前说了“白色乌鸦”。再后来,一名美貌女子选在寒冬自杀,在调查过程中还出现了《陶制乌鸦》这首诗……
这三条平行的生命是如何走上了死亡的路途?埋藏在遥远过去的黑暗过往,造成了现在的连续杀人事件,原本一切可以避免,到底是怎样的情爱纠葛,造就了今天的置人于死地的仇恨?
|
| 關於作者: |
|
孤高寡作的推理大师。他自1949年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却直到1958年才推出第一部长篇作品《天狗面具》,1963年以《影子的控诉》(千草检察官系列首作)摘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此后总要隔两三年甚至七八年才有新作印行,可谓寡作之至,但部部均是足以传世的佳作,其“千草检察官系列”更有日本推理小说史上最成功系列作品之誉。土屋隆夫性格怪僻,久居山间农村,晴耕雨写,几乎不跟东京的文坛往来,却深受文坛和读者敬重,2001年被授予日本推理界唯一的功劳奖——日本推理文学大奖。
|
| 內容試閱:
|
野狐忌——想必有读者会问,这是哪门子忌日啊?我一向与狩猎无缘,从没亲手了结过野生狐狸的性命,自然不存在为野狐祈福的问题。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的忌日常会演变成俳句的季语,“野狐忌”算是其中之一。但它不同于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忌”
和太宰治的“樱桃忌”,并无他人知晓。这也难怪,因为“野狐忌”是我命名的忌日,换言之,它不过是铭刻在我心中的岁时记之一罢了。
十一月三日。大多数岁时记中将这一天——“文化之日”
视作冬季的季语。但我的野狐忌和它并无干系。
对我而言,“野狐忌”就是个顾名思义的忌日。那是一个不为世人所容的作家亲手了结无赖人生的日子;也是侧耳倾听他那被人疏远鄙视的作品中传来的恸哭与罪人祈祷一般的苦恼,在追慕与回想中度过的一天。
这位作家,正是田中英光。
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田中英光来到三鹰市下连雀地区的禅林寺,在他无比敬慕的文学导师太宰治墓前自杀。“野狐忌”便是取自他的作品《野狐》。
然而,我之所以将那天命名为“野狐忌”,将它牢记在心灵岁时记中,并不光是因为我对他的作品心怀哀惜,因为那一天对我的人生也有重要的意义。
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是年六岁的我,其实就在田中英光的自杀现场。我就站在他背后四五米开外的地方,目睹了他自杀的全过程。
当年的报纸如此报道这起案件:
“当天田中英光前往新潮社拜访野平健一,却得知他不在公司,便赶往三鹰造访龟井胜一郎与户石泰一,但这两位也不在家。傍晚五点半左右,他带着酒和安眠药来到禅林寺的太宰治墓前,服药后用安全剃须刀割开左腕动脉。在周围玩耍的孩子发现异常后报警。急救人员立刻将其送往井头医院,但他仍因出血过多,于当晚九点四十分去世。临终时并无血亲在场,很是孤独。他在随身携带的文学全集封面上写下疑似遗书的文字:觉悟赴死,勿让尸首再受屈辱……”
各大报刊的内容大同小异,发现者都是“附近的孩子”。
但“孩子”不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我正是其中之一。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了。记忆已然远去。在场的孩子们——就连在禅林寺里玩耍的玩伴叫什么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然而,在茫然的过往中,唯有一张脸浮出水面。
那个女孩名叫“早苗”。
早苗和母亲住。她家的房子好像是用农户的杂物间或仓库改造而成,面朝马路的窗口总拉着花朵图案的窗帘。我好像进过她家一次。屋里飘荡着油漆的味道,中间放着张大床,而早苗就静静坐在床上。
那日的光景,至今历历在目。
短裙下那双洁白纤细的双腿。
看上去凉凉的、披散肩头的长发。
小小的嘴巴里,嚼着口香糖……
她朝我挥挥手,让我坐在她旁边,突然搂住我的肩膀,倒在床上说:“妈妈和叔叔们都是这么睡的。”
早苗凑在我耳边发出魅惑的声音,热热的气息扑鼻而来。
秀发顺滑的触感。
早苗的衣服是什么时候脱下的?记不清了。但她的裸身如照片般烙印在我的眼底。她雪白的肌肤如白瓷一般,那炫目的美丽令年幼的我喘不过气来。我将手伸向那娇小的乳头,仿佛那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一样。“不行,好痒啊……”早苗扭过身子,甩开了我的手。长发在胸口摇晃——
我那时岂能理解闪过全身的甘美战栗代表着什么。日后我上了初中,又进了高中,曾无数次回忆着那天的早苗自慰。
那空想中的少女,就是我的恋人。
扯远了。总而言之,目击到田中英光自杀现场的不光有我,还有早苗。这一点绝对没错。我上小学时,她与她的母亲已销声匿迹。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又去了何方。
日后,我曾跟两三个人打听过她们的下落,但没人知道。
“好像是有过这么个姑娘……她妈妈是做美军生意的妓女吧。要是她还活着,八成走了她妈的老路。” 兴许他说得没错。我只得作罢。
事已至此,再也没人能为我的所见所闻作证。
但早苗要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定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
她会想起那个肩膀很宽的彪形大汉。
她会想起那人抱着墓碑,与墓碑说话时的哭声。
她会想起男子手上飙出的鲜血打湿了墓碑,形成一摊一摊的血池,然后被发白的土壤吸收的光景。
她会想起她突然哭着揪住我的双臂。
她会想起男子听见她的哭声,回过头来,露出被鲜血染红的双颊。
她会想起男子大手一挥,仿佛在赶人一样,随即露出半哭半笑的悲凉表情……
早苗定会记得那些光景的碎片。
我们曾肩并着肩,目睹那一切。年幼时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投下长长的阴影。后来,我之所以在大学专攻心理学,并不断进行自杀作家的研究,兴许原因就在于此。
被田中英光奉为导师的太宰治的作品至今广受欢迎。他就像生前的太宰治那样,时而昂然扬起眉头,时而像街头艺人般哈哈大笑,在现代的年轻人中漫步。然而会提起田中英光的人少之又少。
我仍会不时地想起,他将染着血污的半张脸转向我和早苗,露出那温柔的表情。还有那双少年般清澈的双眸。
他自比落入水沟的野狐。人称无轨道、无赖、颓废派的男人在他荒废的生活中,悄悄点亮了心灵的明灯。而这盏明灯永远在我心中摇曳。
只属于我的野狐忌。就是明天,十一月三日。
一合美酒冷,野狐忌之夜。
摘自K大学新闻学艺栏“一人一话” P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