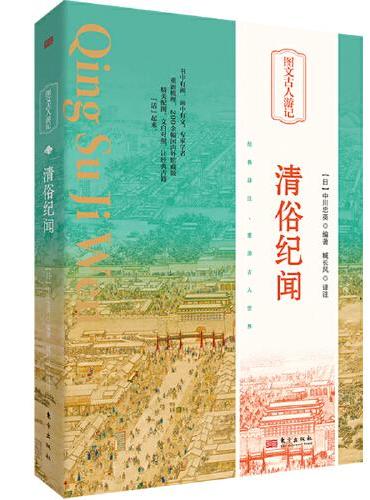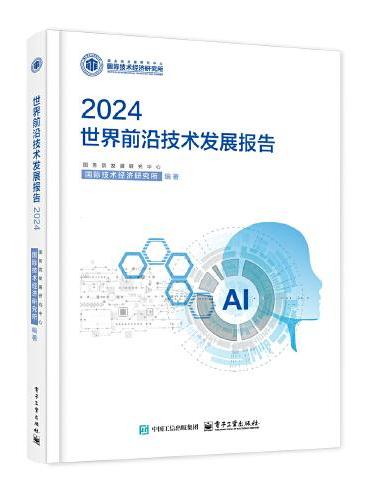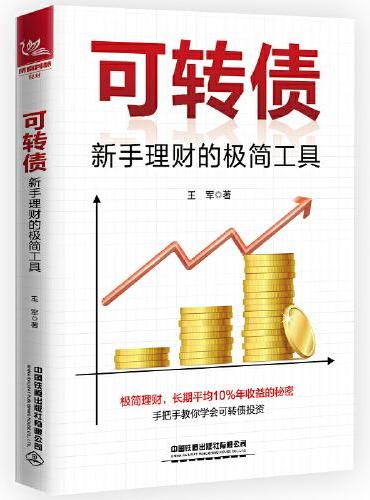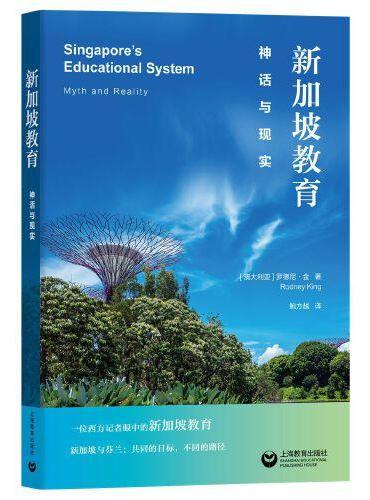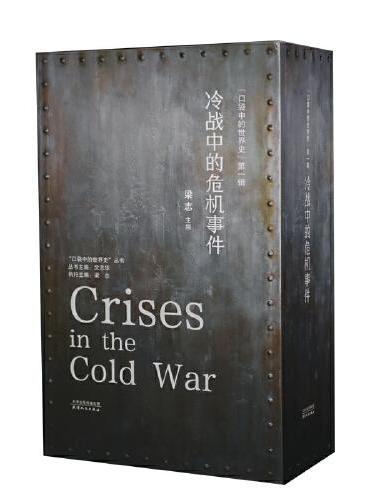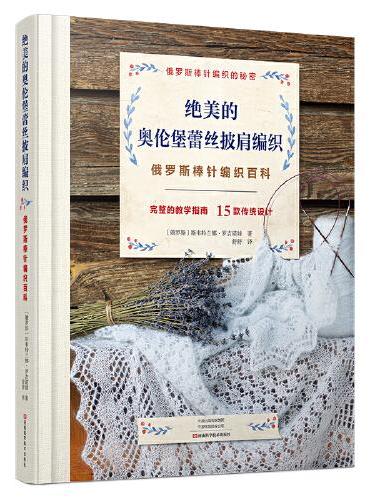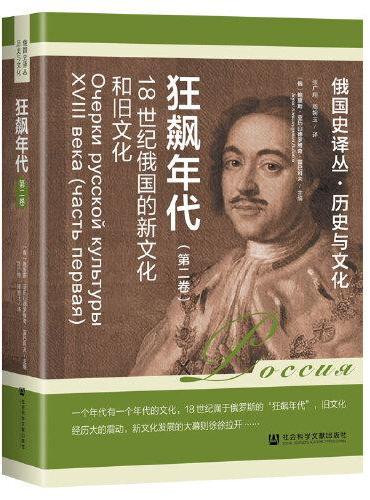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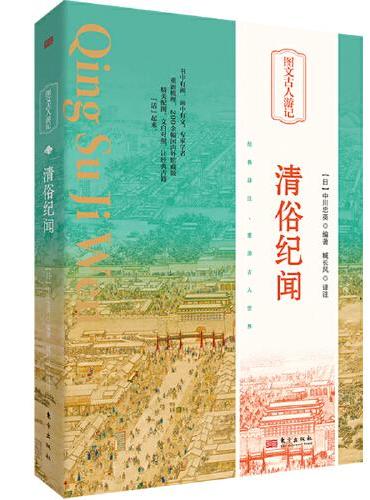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镜中的星期天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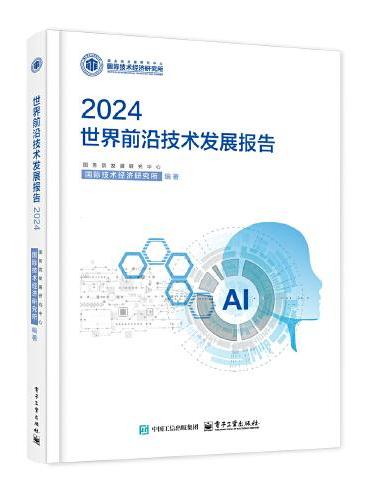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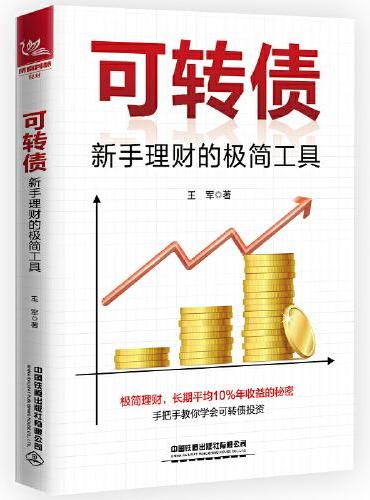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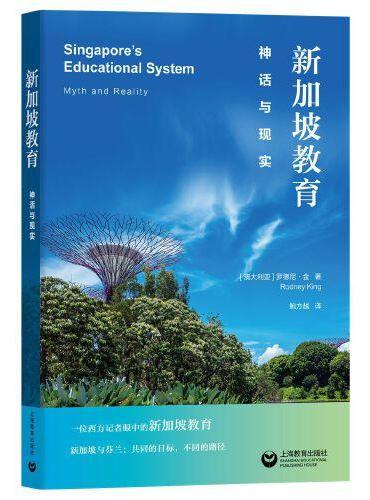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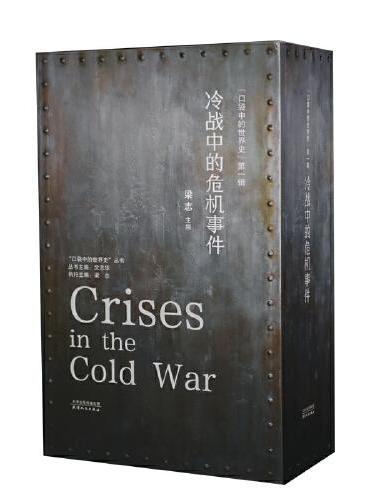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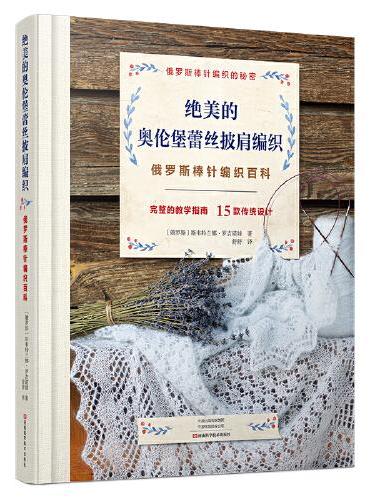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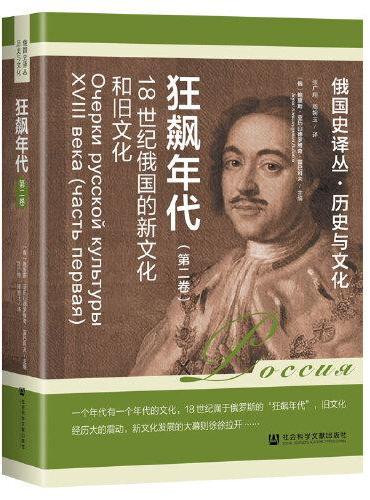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
| 編輯推薦: |
幸福,就是相信自己;
幸福,就是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
幸福,就是不盲目攀比;
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
幸福,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幸福,就是让自己活着有意义!
曾经,有人断言他活不到三十岁,结果,他已经活到了五十四。
曾经,他想找一个漂亮、健康、有文化的女孩做妻子,结果,他如愿了。曾经,许多人担心他的婚姻走不长,结果,他已经走过了二十六个年头。
曾经,他只想让女儿读个大学,结果,身高一米七二的女儿被澳洲一所大学录取。
曾经,他只想坐在大学梯形教室里,听听教授们上课。结果,他自己也站在这样的讲台上,面对台下数百位学员讲课。
曾经,他总希望扔掉自己走路的拐杖,结果,他成了无数人心理的拐杖。
曾经,他只想在蓝色的大海边听听涛声,结果,他今天住在了北纬十八度的海边。
|
| 內容簡介: |
幸福是什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当你生来就有缺陷,你又如何去面对生活?
作者在这本自传中,以另一种姿态,平实地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书中主人公江自立,自幼残疾,但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顽强而幸福地活着。大半生中他辗转新疆、上海、海南,远离父母之爱走过了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了少年,青年时遭遇了两次爱情的失败,30多岁被下岗再一次冲击……这期间他迷茫过,彷徨过,但心中一直充满希望,充满对幸福的向往,最终,也收获了生命中的幸福时光。
让我们静下心来,在平实的文字中,感受那份对生活的希望、对幸福的向往。
|
| 關於作者: |
唐海东。
职业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杂志特约作者,上海市心理学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工作室特聘婚姻咨询师。
擅长处理各类婚恋问题,在多家报刊情感倾诉专栏担任特约专家点评、专栏点评,发表情感、婚姻、心理等各类分析、点评、随笔达400余篇。
现居住、工作于海南。
博客:http:blog.sina.com.cnhaidong6
微博:@婚姻心理咨询专家唐海东
|
| 目錄:
|
第01章 我不是废人;
第02章 活着,必须有意以;
第03章 接纳不完整的自己;
第04章 做被需要的人;
第05章 大学梦;
第06章 不算美好的初恋;
第07章 是火柴,就要燃烧;
第08章 被绞杀的第二次恋爱;
第09章 谢谢你,真爱;
第10章 结婚;
第11章 下岗的日子;
第12章 站起来,再站起来;
第13章 才妻是我的骄傲;
第14章 做自己喜欢的事;
第15章 向着太阳,幸福一生
|
| 內容試閱:
|
第01 章
我不是废人
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孩子拖着两条又细又软的腿在地上爬着。他昂着头,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向前高举,一边爬一边大声地哭喊:“我不是废人,我不是废人,我不是废人……”一声接着一声,一遍接着一遍。突然,我被这叫喊声惊醒,才发觉是个梦。然而,醒来的我已是满眼泪水。
后来,这个情境竟然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的名字叫江自立,可户口本上记录的是我的曾用名:江州齐。父亲说,当初起这个名是因为母亲在兰州怀上了我,而生我时已经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了。
我对出生地乌鲁木齐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在我开始懂事的那天,忽然发现自己走路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要依靠一只小木椅才能站起来,要靠左右摆动小椅子来移动身体。我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其他小孩走路不用小椅子?”父亲没有回答我。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三岁时,也就是在1962年,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在昏睡了三天三夜之后,虽然有幸保住了命,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至今,我的个子依然不到一米四,两条腿均肌肉萎缩,左脚比右脚短十厘米,脊背畸形,走路依靠拐杖,体重也只有一百斤。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待在上海,而要去新疆?否则我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了。”父亲告诉我,在他刚刚读完小学不久的几年中,我的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没有了父母照料,他经常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那年刚好铁路上招工,说好是流动性工作,年轻的他无牵无挂,便报名了。由于父亲曾读完高小,还算是个文化人,在起初的铁路建设大军中,他便成了一名很派得上用场的技术员。在离开上海前,父亲和母亲已经相恋。由于母亲这时也已经没有了父母,便辞去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也转到了铁路系统,穿上铁路制服,和父亲一起随着铁路建设大军,由上海一路北上,把铁轨一直铺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小时候的我,特别羡慕父母衣服上带有铁路路徽的纽扣,尤其是那身呢子服上的金黄色路徽纽扣。父亲现在还留有一张穿着这种制服的照片,简直是帅爆了,难怪老妈会放弃那么好的工作跟着老爸去喝西北风。
我一直想了解小时候得病时的情况,但父母总是回避我。父亲只告诉我,在我得病以后,他们是如何着急地把我送进医院,我是如何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好几次医生都说我没指望了,因为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治我这种病的急救药,父亲苦苦地哀求着医生。幸亏我的邻床是一个部队的团长,他也得了什么导致昏迷不醒的病,部队上特意为他送来了三支针剂,打完第二针时,他醒了。看着我这个小小的生命昏迷不醒,他了解情况后,要求医生把剩下的那一针给我打。他对父亲说:“就看这小生命的运气了。”于是,医生把这最后一针注入了我的体内。有幸,几小时后,我醒了。父亲也不知道这团长姓什么叫什么,但我却记住了他是一位解放军团长。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我总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军人情结。比如,我喜欢看军人的小说、电视、电影,甚至还渴望自己是一位将军。这种情结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记不清什么时候,反正有那么一次,在我的梦中突然出现了幼年在乌鲁木齐生活的零星片断。
我住的地方似乎是一排土木结构的低矮的房子,后来证实是父母单位的宿舍。我家有两间屋子,屋子外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个很深的坑。当冬天到来前,坑里会放许多吃的东西,比如土豆、白菜、南瓜和红薯什么的。当然,这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主要食物。我出生的年月正值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新疆这个地方更是物资极其匮乏。父亲曾说过,那时可以配给婴儿的是每个月二斤面粉,大米基本是没有的。父母每天都要上班,工作很重。我每天就被放在床上,关在屋内,中午休息时,他们回来给我弄点吃的。我常常一个人在床上饿得哇哇大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依稀记得,我双下肢残障以后,父亲在卧室的墙角用水泥砌过一个浴缸,每天烧满热水让我在里面泡澡暖脚。父亲希望我的腿能够通过锻炼变得有力,可以自己站立起来,但显然这种原始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五岁以后我离开了乌鲁木齐,被送到了上海。我一直没弄明白父母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好多年以后有一次和父亲提起,他说新疆那地方冬天时间长,冰天雪地,缺医少吃,像我这样的情况很难成长和发展,所以才把我送到了上海。虽然这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心头总有个疑虑,我感觉父母看到了我这样的身体后,是想甩掉包袱不管我了。
总之,在离开乌鲁木齐这个出生的故乡之后,我就没有再踏上过那片土地。
为了不让这段伤心的记忆伴随我一生,回到上海后,父亲替我改了名字:江自立。
他希望我能够自立起来。
刚来上海的头一年多,我被寄养在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家。
这是一个大家庭,父亲让我管一位年龄比他稍长的男人叫大伯,女的叫大大妈。大伯和大大妈有六个孩子,我去的时候,最大的哥哥刚刚开始工作,最小的姐姐也刚刚开始读书,其他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分别读小学、初中或高中。最大的姐姐似乎当年就要考大学,在所有的大姐姐大哥哥中,就她一个人从没和我玩过。很不幸的是,听说后来她没考上大学,人变得有点不正常了。反正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她在家跳高要摸屋顶,一边跳还一边叫,跳的时候手都能碰到房子上粗粗的木头。在这个家里,大大妈没有工作,每天给一大家子人做饭、洗衣服。白天,我和大大妈在家。在这个家我最小,大伯和大大妈以及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虽然说不上喜欢我,但确实没有一个人打过我、骂过我或欺负过我。我喜欢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家里尤其热闹。
大伯家有个哥哥,大家都叫他老三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家中老三。那年他在读中学,估计他读书不太好,因为大大妈老是骂他只会吃饭不好好读书。他确实很能吃饭,一吃就是三大碗,所以他个子也长得高大。有一次,我俩去弄堂里玩,他让我坐在一边,看他和一群人“斗鸡”。所谓斗鸡,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一条腿曲起来,用双手捧住,凭借另一条腿的力量边跳边把对方的守军一个一个撞倒,然后跳到对方的阵营中把放在地上一块象征军旗的石子夺回来放在自己阵营中,谁先夺得谁就是胜者。比赛一开始,我就看见老三弟冲锋在前,他一阵单腿奔跳就冲过了半场,进入了对方阵地。对方有点害怕,有几个主力队员赶紧过来阻止老三弟的进攻。这时候,老三弟部下里的小个子快跳手迅速地绕过对方几名主力对手,直插营部,弯身夺得石子,回身就逃。此刻,老三弟另几位部下也顾不上看家护石,全部跳出去增援夺得对方阵营石子的队友回来,被老三弟吸引的几个对方主力一看上当,马上转身阻止,但已经慢了半拍,老三弟的队友很快拿下一城。
我坐在一旁,第一次看到如此激烈精彩的对决,控制不住大声地为老三弟这边叫阵。叫着叫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已经站了起来,虽然是靠在那面墙上。
有一次,老三弟让我看了一回真正的斗鸡。那天,大大妈不在家,他抱出了一直养在自家后院里那只漂亮的大公鸡。我摇摆着小木凳跟着他来到了他家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大院里,那家也有个和老三弟差不多大的男孩,也抱出自己家的大公鸡,准备开斗。
老三弟抱着的那只鸡头小冠平,颈粗而长,腿壮而高,全身羽毛黑中带绿,富有光泽,尾部有三四根黑白相间的长镰羽。而对方的是只白鸡,躯体昂直,头小颈粗,眼小而有神,嘴壳为黑色,全身羽毛洁白油亮,显得干净利索。两只鸡的个头大小差不多。
此刻,闻讯而来的小孩子们已经围成了一圈,老三弟把我安排在他的身边,所以没有人敢挡在我的前面。
斗鸡正式开始。只见双方蹲下身子放出了各自抱着的公鸡,才一脱手,两只公鸡飞腾扑打到了一起。双方一开始就拼命地撕咬着对方,以至于它们身上的羽毛都不断地被啄掉,那真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景象。
突然,白鸡凌空高高跃起,以铁爪拍打老三弟的鸡,同时飞快地咬住了它的鸡冠狠狠地转了一圈。老三弟的黑白鸡一边挣脱,一边躲避着。我看着都急得想哭,老三弟也在一边闷不作声,围着观战的人群开始为白鸡喝彩。
白鸡继续追逐着老三弟的鸡,老三弟的鸡把头低到地面上躲避着,白鸡的头也渐渐地跟着在地面上转。猛然间,老三弟的鸡找到了一次机会,向对方进行了反击,只见它向白鸡的颈部连续啄了几口,被啄处突然呈现红色,那场面真是十分惨烈,不一会儿,白鸡忽然倒下,两爪向天。对方那个男孩赶紧过去抱起白鸡,给它吹气,可是已经无力回天了。白鸡颈下的血越来越多,还没等人散开,就死了。
老三弟也抱起自家那只脖子被啄得没毛的获胜的大公鸡回家了,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结局,他似乎也没有了凯旋的得意。
后来听说白鸡的主人没有舍得杀了鸡吃肉,而是把白鸡整个地埋在了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下。自这件事以后,这两家的大人和小孩子再也没有说过话。
这以后,我每天都会去后院探望那只勇猛异常的大公鸡。直到我离开大伯家的时候,这只大公鸡的脖颈上依然没有长出毛来,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如此真实、如此紧张激烈精彩壮观的斗鸡场面。
夏天的时候,老三弟还带我观看过他和别人斗蟋蟀,但那场面和斗鸡比起来,就没什么精彩可言了。
至今我仍保留着爱吃鱼头的习惯,而这恰恰就是在这个大家庭里养成的。大伯全家八口人,他们家里有一张红色的八仙桌,吃饭时八个人刚好两个人一面坐满。我人小只能在下面拿一个大人们坐的方木凳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吃。他们会给我夹一些桌子上的菜,但我知道有一样菜他们通常不会给我吃,那就是鱼。这主要可能还是怕鱼刺卡住我的喉咙,其实我吃鱼确实是经常卡住喉咙的。那时,我知道上面他们在吃鱼,很想吃又不敢要,就说自己爱吃鱼头,于是他们会挑鱼鳃处的肉给我吃,慢慢地他们也会把大鱼头的部分给我吃。结果,长大以后,我还真的养成了爱吃鱼头的习惯。更没想到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菜市场里鱼头的价格比鱼肉还要贵,原来爱吃鱼头的人竟然还会有这么多。
也就在大伯家,我听到了一句有关我的非常重要的话。
大伯家有个邻居,是一对夫妻,不知什么原因,结婚多年依然没有小孩。据说,他们是上海一所大医院的主治医生,平时也总有人来向他们求助或咨询。一个夏天的晚上,大人们都坐在院子里乘凉聊天,而我和大伯在屋子里。大伯平时很少出去与人聊天,他每天吃完饭洗完澡总是半躺在一张躺椅上,喝着茶摇着扇子看报,我则坐在他的一旁。院子里邻居们说话聊天的声音,如果不注意,似乎也听不见;如果注意了,那每一句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至少当时我就是这样。
当时话题不知怎么地转到了我的身上,一番东点西评后,那医生突然说话了。他说像我这样的残废人,活不到三十岁肯定会死,因为……因为什么我没记清,反正是很专业的话。我当时还没有学过数数,对“三十”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句话记得很牢。直到读书以后学了数学,我才知道三十是一个多么小的数;后来我又知道人通常可以活到七十多岁,三十连它的一半都不到。不过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小,对死也没有什么概念,想着自己才八岁,这一天一天过,到三十岁还远着呢。于是,我就把这句话抛在脑后了,直到我三十一岁那年,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根根某天晚上突发心肌梗塞死去。根根的身体状况一直很棒,而他去世的那年刚好三十岁,在开完他的追悼会时,我才猛地想起儿时邻居医生的那句话。但当时我只把那句话看成了扯淡,因为我确确实实过了三十还好好地活着呢。
以后每每想起那句话时,我反而非常开心,因为打那以后每过去一年,我就当自己是白赚了一年。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我已经多活了××年了,有什么比能多活一年更重要的呢?
不过,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做了本章开头的那个梦。
小时候,那些我不认识的大人们都称我为残废。在稍大点以后,我对“残废”这两个字很是排斥。而现在,人们对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归之为“残疾”或“残障”。也许是那个梦的缘故吧,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废人”,我最排斥的是有人称我为“残废”。我内心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不是废人,我是个对家里有用的人,我是个对他人有用的人,我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几乎成了我的信念,我人生中执着追求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