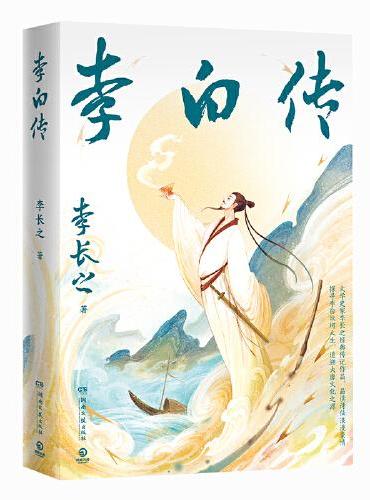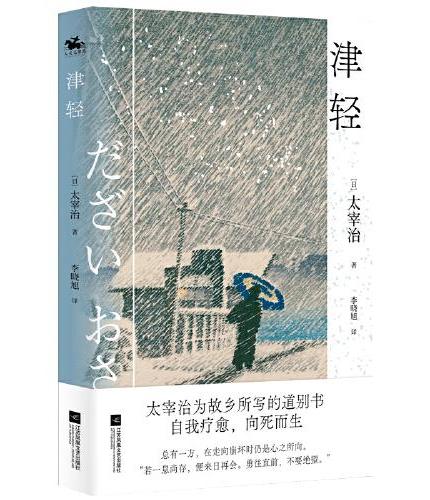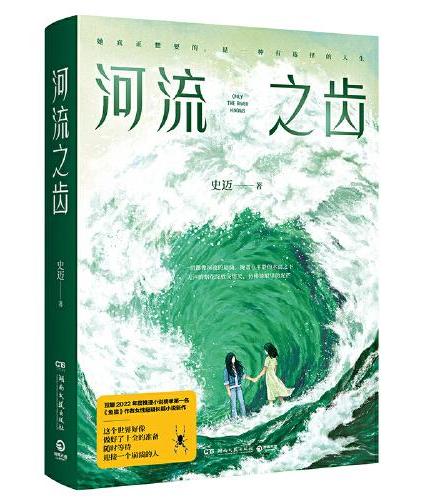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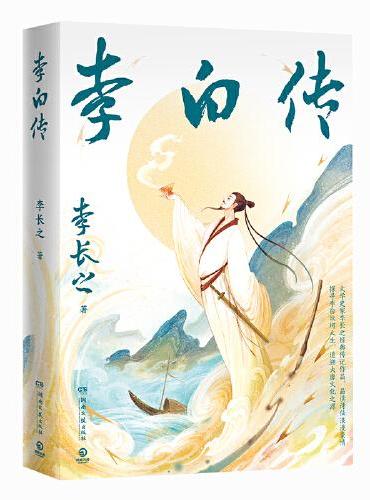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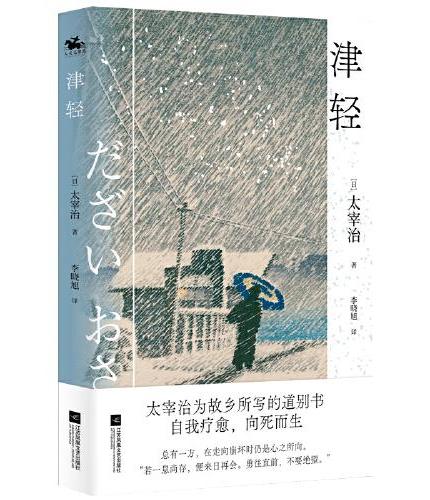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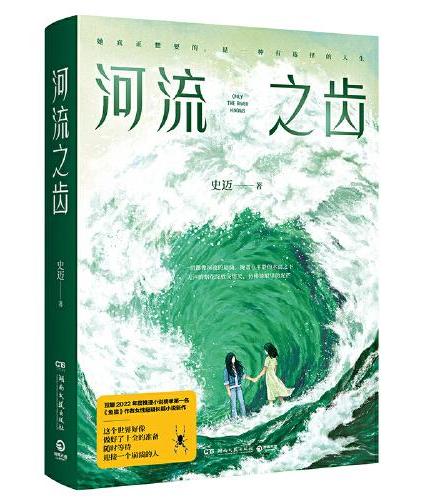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 編輯推薦: |
《民国的忧伤》:民国的宪政探索是当下民主实践的一面镜子。
学者作家祝勇以新散文代表作家的笔力和学者的知识结构,把民国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重构。让我们清晰理性地知道,清末的积重难返,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建立了多党政治的平台,却不等于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一个对话的、调和的、服从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根本意义。
|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宪政那段历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乱局面中为实现宪政梦想而努力挣扎的人们,领会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和纠结。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只是在以革命为主导的历史叙述,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地位。
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
| 關於作者: |
祝勇
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中央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非虚构历史著作《纸天堂》、《辛亥年》,“文革学”著作《反阅读》等。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任《我爱你,中国》、《辛亥》、《岩中花树》等纪录片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
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 届、第26
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香港无线电视台(TVB)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
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
| 目錄:
|
自序 滴血的宪政
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举手投足,都可以耳闻目见。或者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所有际遇与抉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传奇一 迷宫,1911-1912
有人向袁世凯进言说,唐绍仪与孙中山是同乡,他们勾结紧密。每当唐绍仪进出总统府的时候,他们会指着唐的背影低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传奇二 子弹,1913-1914
宋教仁死前多日,谭人凤、陈其美和《民立报》记者徐血儿等人曾向他提醒了有关暗杀的消息,甚至准确地说出了杀人者的名字——青帮大佬应桂馨。
传奇三 天命,1914-1916
那天晚上,很少饮酒的袁世凯可能喝醉了。宴会后,有人听见他在大唱“孤王酒醉桃花宫”。但另一人说,他唱的是大登殿,声音最高朗的一句是——“我薛平贵也有今日一天!”
传奇四 残局,1916-1917
这两个在战场上通过望远镜对望的人,已经循着各自的来路进入民国,在民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棋盘上狭路相逢。在中华民国的第一届政府内,他们分别担任副元首和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
传奇五 歧路,1917-1918
我们无法知道梁启超看到公布的选举结果的时候的心情——他是会哭,还是会笑?只能从他的书信里查到,八九月间,他生了一次病,医生诊断为肋膜炎,微带肺炎。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
传奇六 呐喊,1917-1920
唯有绍兴会馆的周氏兄弟,对惨淡的现实没有抱丝毫的幻想,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周氏兄弟的判断。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所有的希望再度化作绝望与悲愤,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了血书。
传奇未完 选票,1923-1949
蒋介石兴犹未尽,再请胡适吃饭。席间,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淮南王书》,希望蒋介石能留意《淮南王书》中“无为主义的精义”,做一个能开放视听、尊重民意的“虚君”。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唐绍仪决定出走。
作出这个决定以后,唐绍仪没有犹豫。他干净利索地换上便装,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两三个随从,走出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
胡同仿佛麻线,把他的心紧紧缠住。他的心里很闷,想摆脱那些麻线的纠缠。车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来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人力车从一条胡同折向另一条胡同,像在迷宫里穿行,接踵而至的粗重的墙总是令他感到恐惧,但车夫总是能够敏捷地避开它们,像一条鱼,在墙的围困中游来游去,慢慢地,他才适应人力车的速度。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兜风的布篷似乎成了一只风筝,带着他,忽忽悠悠地飘了起来。
民国元年,北京城密如蛛网的胡同里,这是无数辆人力车中的一辆。没有人注意,车上坐着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总理。
对于这个新生的民国来说,没有人比唐绍仪更能胜任国务总理这一职务了。唐绍仪每天5点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谒见袁世凯。唐德刚先生说:“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对此,袁世凯是默许的,按照民国报人陶菊隐的说法,因为他需要唐绍仪成为“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
武昌起义以后,唐绍仪是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孙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进行谈判的。正是这场谈判,终结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把袁世凯送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在复杂的局势中,他能敏锐地找到被荒草覆盖的捷径。帝制结束了,小皇帝退缩到宫殿的一隅,粗砺坚固的城墙不再守卫帝制的威严。革命也结束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里,安静地签署各种命令,卸职后的孙中山回到了他的故乡,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大榕树下,与老人们放声地高谈阔论。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回到了它应有的轨道上,一道难解的方程,终于被化繁为简,求出了最大公约数。几乎同时,所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曾说:“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袁、唐之间的冲突,需要追溯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修改——武昌起义之后,由各省代表团(1912年1月28日改为临时参议院)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些革命党中,形成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宋教仁,这个30
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由于孙中山在革命党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这个新政权最终效仿美国宪法,采用了总统制。但是,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没有想到,他们不闹了,但总统与总理两制之争却会一直闹下去。府院(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一再周期性地上演,使民国的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以枪炮来收拾。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总揽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职权,府院之间才偃旗息鼓。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参议院急匆匆地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为的是减少和制约总统的权力。所谓内阁制,实际上就是把总统当成摆设,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政府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总理对国会负责。总统权力,如任免官员、发布法律命令等,必须经由内阁副署,才能产生效力。时人说:“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10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早在1912年1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了国会采取两院制。到8月10日,以总统名义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
举法。
这种因人而异的制度设计,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刚在中国着陆时的水土不服。他们从不掩饰对袁世凯的公开怀疑,而对于袁世凯这个深谙官场之道的旧官僚而言,南方所设的种种牵绊,显然不是一种真诚的合作态度。他们虽有让贤的诚意,却缺乏合作的诚意。并且,他们过分低估了北洋系的实力尤其是忍耐力,为未来埋下无穷的祸患。这个为袁世凯精心设计的纸手铐,注定会被袁世凯撕得粉碎。
唐德刚说:“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亲历过清末改革、见多识广的袁世凯一眼便可以看穿。但他深知政治的火候。在他心里,真正的大事业,都需要文火慢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孙中山那样火烧火燎的,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并组成内阁,30岁的宋教仁出任内阁农林总长。政府成员中既有前清官僚和北洋军人,也不乏革命党。这些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在奏折、书信上势不两立,在战场上拔刀相向,现在却心情复杂地站在同一个队伍里,见证中国的华盛顿的诞生。
从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会的选举。随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的政党政治也空前活跃起来。自武昌起义到1913年底,新成立的党派有682个,这些党派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经过复杂的斗争、较量、分化、组合后,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4个较大的政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是1912年8月25日,借孙中山到达北京之机,在北京湖广会馆,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5政党合并组成的。国民党以革命派为主,积极推行与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相比之下,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则以清末立宪派为主。在他们看来,中国虽有四万万人口,但80%是文盲,其余20%虽然粗通文字,但对民主、选举这些事情,则所知了了,所以,他们力主政治渐进主义,与国民党相对抗。选举揭晓,国民党在两院议员共占392
席,占绝大多数,从而以第一大党的地位控制了国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三党联合起来仅占223席。那一天,袁世凯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得到的仅仅是一个虚位,不要说宋教仁,就连曾经长期作为袁世凯的僚属、对袁唯命是从的唐绍仪,在袁世凯这位老上级面前也突然铁面起来。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袁世凯的讲话稿,须经过唐绍仪的删改才能最后定稿。对总统府的决定,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就立即驳回,不给袁世凯留一点面子。他的目的是捍卫《临时约法》,捍卫内阁制。这令习惯了居高临下的袁世凯十分不适,以至于袁的左右都对唐绍仪的“忘恩负义”抱有微词。
袁世凯向杨度暗暗道出了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诚如顾维钧所说,谁也没有料到,“唐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
有人向袁世凯进言说,唐绍仪与孙中山是同乡,他们勾结紧密,“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每当唐绍仪进出总统府的时候,他们会指着唐的背影低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有一天,袁世凯对唐绍仪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袁世凯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和,波澜不惊,甚至还透着老朋友的宽厚与大度,挑不出一点毛病。但唐绍仪听出了这句话里的警告意味,它的真实意思是:你在找死!
……
唐绍仪的首届内阁垮台后,袁世凯仍然希望宋教仁组成“混合内阁”,即只重人才不重党派,这是袁世凯拉拢宋教仁的目的所在。但袁的好意被宋教仁谢绝了。那时的宋教仁,手握国内最大政党,底气自然很足。他谁也不想求,谁也用不着求,一心想踢开各党,打造一个由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党内阁”。他目的明确,直奔主题,不会耍手段。固然光明磊落,但当时的民国政坛,尽管完成了制度转型,但制度内的人,还没有真正成为民主之人,传统的政治手段依然畅通无阻。日本明治维新经22年始行召集国会,而民国二年就成立国会,速度之快,已让人跌破眼镜。与其相比,人的现代化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制度的现代化未必同步。宋教仁低估了他所面对的现实,没有必要的对策,也不懂“韧的战斗”,他与许多国民党员一样,相信“制度万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然后,就赤膊上阵了。
然而,一粒子弹,只要一粒子弹,就可以打垮他的全部理想。
……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5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的发刊词。
蒋介石刚刚在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到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就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手里捏着电报,他沉默了很久,才对蒋经国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一路上,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不知走了多远,蒋介石说,去钓鱼吧。蒋经国就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一个人坐上船,划了出去。落山风直贯下来,吹透了他的青衫,使蒋介石的身影显得苍老孤单。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不知“人民”这个久违的词,是否就在那时跃入他的心里。读历史的人只是知道,不久之后,台湾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据说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关于“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诺言,但蒋介石还是给它取了一个“很共产党”的名字:
土改。
2010 年冬动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