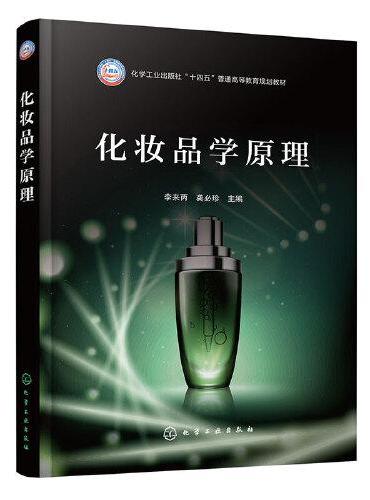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HK$
113.6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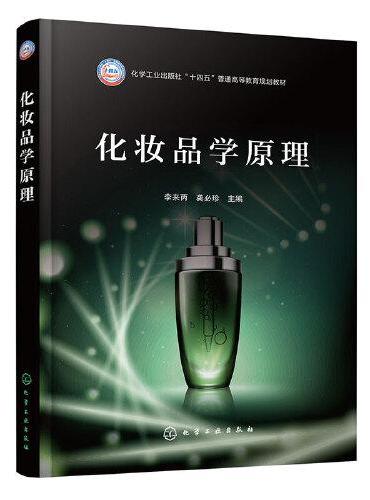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HK$
57.3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HK$
48.3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HK$
57.3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HK$
57.3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HK$
112.7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HK$
112.7
|
| 編輯推薦: |
《圣经旧约创世记》说:耶和华不愿世人建造通天之塔,遂去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
帕默尔所说:“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
梅希叶所说:“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们先推翻语言。”
布莱特说:“语言和社会在共变。”
作者郑也夫在《语镜子》中深入语言迷宫,反复咀嚼,在我们熟知不察乃至感知钝化的日常语言中,渐发现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富矿。
|
| 內容簡介: |
|
《语镜子》是一本语言文化类杂文集。作者郑也夫自如出入于语言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诸多学科,语言材料随手拈来,从法国大革命对语言的大规模清洗,到“文革”贻害至今的语言烙印;从官腔、黑话、国骂粗口,到长满荆棘的民谣、具有美学意味梦幻般的儿歌等,无远弗届,全书用语言现象折射社会万象,从习语改动窥见世代人心价值变迁,既具独特的学术底蕴,又不乏趣味畅读性,是一部有趣有益的语言新知佳作。
|
| 關於作者: |
|
郑也夫,1950年生于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获哲学硕士。1985至1986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终生绝缘于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常常得理不让人。
|
| 目錄:
|
序:语言,社会的舞动(阿城)
自序:我乃侏儒,它是富矿
编一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
语言,活着的历史
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
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
语言的强制力
语言,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
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
“好天气”可望发扬的遗俗
“谁?我!”封闭的社会
兄弟伯叔人伦之秩序
“哥儿们”关系之网
“先生”-“同志”-“师傅”鄙俗化过程
学术著作中的“先生”真理面前的不平等
“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
“张老”势利的恭维
“爱人”和“气管炎”称谓变革与妇女解放
“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
“爷”的变迁
“棒”性崇拜之痕迹
“他妈的”移情的心态
“撑的”饿人的文化
“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
“革命”现状的守护神
“红”与“黑”意识形态的社会
“砸烂狗头”“文革体”语言
“劳逸结合”为尊者讳
隐语大泛滥
民 谣
“沙发”、“干部”、“胡萝卜”外来文化的印记
编二 粗口俗话联语儿歌
商标与人名
仪式语言
沟通与误解语言是双刃剑
保护方言
关防暴客来
“牛逼”不是京骂
朗诵的用场
语言产生之猜想
语言是本能
“被”字声中听惊雷
“恪”字后面的俗人心理
谚语各说其理
儿歌玩之天性
联语礼之上品
参考书目
|
| 內容試閱:
|
赤橙黄绿青蓝紫,缺少了任何一种色调都构不成美妙的彩虹。世界是彩色的,每一种颜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红色在社会生活和语言中占据了其他色彩和词汇不可企及的神圣位置。我们从“文革”“红色”的巅峰期说起。
“文革”语言中含有大量带“红”的词汇: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人)、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以至那个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指当时把一切建筑涂成红颜色)。与之相对,当时的语言中也一下子增添了很多带“黑”的词汇:黑帮、黑帮分子、黑帮子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出身的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材料、黑线、黑修养。多彩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红黑两色。语言中“红与黑”(象征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泛滥,不过是现实中意识形态走向极端的反映。鲁迅的话正是这种时代的写照: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被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
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1927)
“红”的泛滥并不始于“文革”。相反,是“文革”前 20 余年的准备才把它推上“文革”的鼎盛时期。“文革”前文艺作品中“泛红”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歌曲《东方红》;文字作品《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戏剧《红灯记》、《红灯照》;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孩提时代的教育就是“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诗人们更在起劲地呐喊:
红色的历史一页一页用血写,
阳关大道老一辈一步一步踏出来。
(《接班人之歌》)
这里永远有不会退化的红色种子,
这里有永远不会中断的灿烂前程。
(《雷锋之歌》)
凡此种种使得中国在世人面前成了“红色”的同义词,遂使西方人将中国大陆称为“红色中国”。
然而,如果翻翻家底的话会发现:“红”在中国语言中是个“暴发户”,这一“族类”在传统语言中并不发达兴旺。不错,历史上有过“周尚赤”的说法,杜甫的诗篇中“朱门”成了富贵者的象征,婚丧在民间被称为红白喜事,结婚用红纸剪下喜字。但也仅此而已。
“红”在汉语语言中是个小户人家,在社会生活中也远不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甚至比之西方,当时“红色”在中国或许受到一点怠慢呢。西方天主教中的红衣主教的红色教袍已具有了十足的象征意味,以后的“红十字”再次将之变成一种象征。与“红的历史”相似,“黑”在传统中国的语言和社会生活中也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那么当代汉语中“红与黑”的象征意义来自何处呢?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俄国。陈原认为“黑帮”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最早出现于1938 年左右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联共党史》中提到,1905 年沙皇统治阶级“为了摧毁革命力量,又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性团体……这些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反动地主、商人、牧师和迹近盗匪的流氓分子,所以人民称之为黑帮”。显然“文革”中人们借用了“黑帮”与“黑帮分子”的词汇。(陈原,1980)对“红”的崇尚或许源出同处。当时红色几乎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特色,红军、红旗更成了俄国革命的象征。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张和象征它的红色一同送进了中国。中国第一代马列主义传人李大钊在1919年写出《赤色的世界》的小文:“一个消息,说某国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的旗子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们都叫作‘赤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以后他又说过:“未来之环球,必是赤旗之世界。”无独有偶,日本共产党也以《赤旗报》为其机关报定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以后也照搬了“红军”的名称。由此可见,这种特殊意义的“红”是俄国舶来品。甚至俄国民间文学中“红罂粟”的传说都铭记在生活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人心中。北岛写于 1978 年的那首感人肺腑的诗歌《走吧》的结尾词:
路呵路,飘满红罂粟。
怕是已难为今天的青年们理解。
像黄金成为天然货币一样,红色成为了革命的象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血与火的色彩是最能震撼人心的。
然而社会毕竟是“杂色”的,把革命时代两大营垒的格局推行到和平时代的社会中,必然显得滑稽。因为社会中多数人已既不要红色革命,也不要黑色反革命,他们要安居乐业,做普普通通的人。硬把无数人划分和涂抹成红黑两色,像一幅漫画,像一张脸谱,被涂成黑色的人固然可怜,被涂抹成红色的却更为可笑。
“红与黑”在五六十年代全是以道德判定的面貌出现的。“又红又专”更集中地体现出道德至上的判定原则。然而什么是“红”呢?即使人们可以清晰地定义它,也永远无法准确地检验一个人是否“红”。如此“道德治国”的结果必然是虚伪盛行。“红专与白专”的判定不禁使我们想起汉代察举中的“贤良方正”与“孝廉秀才”。已在历史筛选中淘汰掉的方式两千年后又被捡起,怎么可能不以失败告终呢?
大自然永远是多彩的,每一种色彩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社会是由千百万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棱角和闪光的思想。正是这无数个充满个性色彩的因子,构成了杂色的、斑斓的自然与社会。哪一天这个斑斓的社会一下子变成了两大色彩:黑与白,或是黑与红,便将意味着个性的丢失,自由的沦丧,思想的毁灭,人类的危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