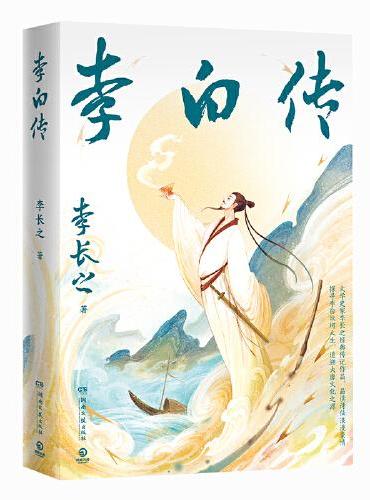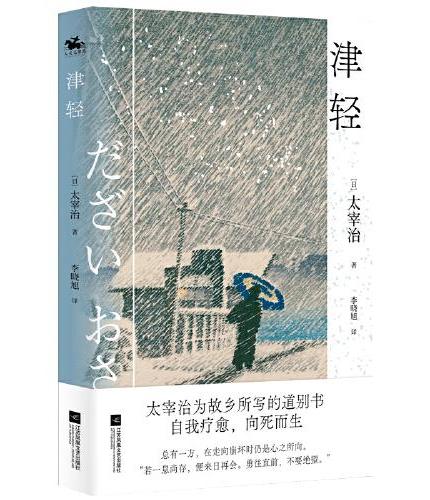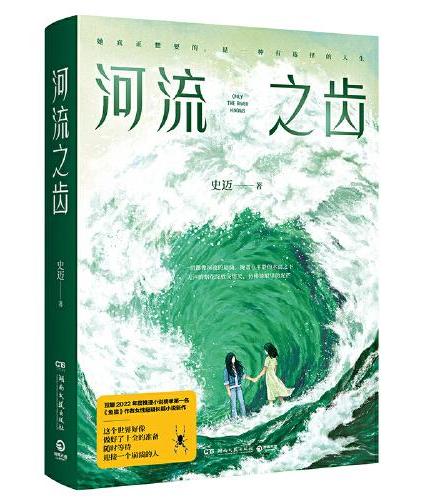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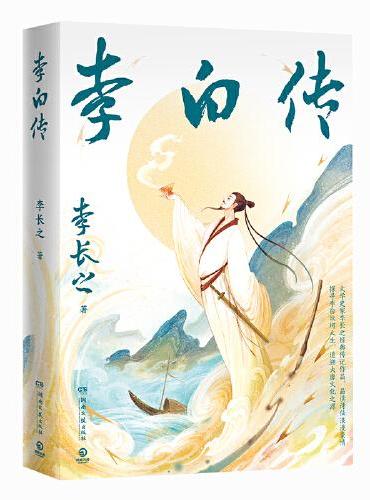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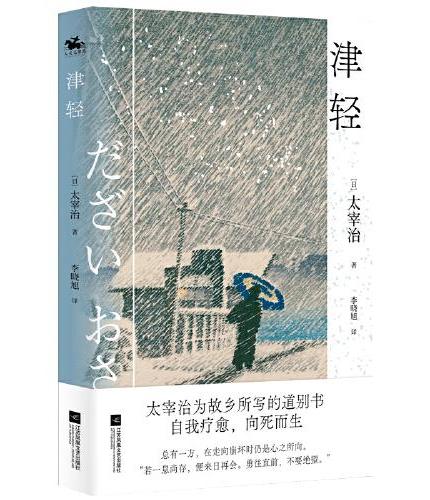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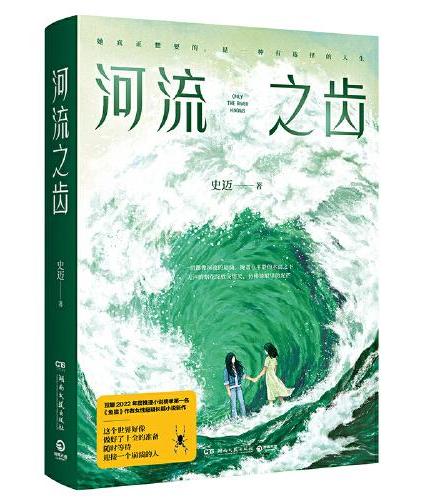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 編輯推薦: |
|
达尼伊尔格拉宁是我最敬爱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还在大三的俄语实践课上我就学习过他的短篇小说《第二方案》,当时便被蕴含其中的学术良知深深打动,随后我又先后读了他的小说《一幅画》《奇特的一生》《野牛》等作品。2012年底,老作家的最新力作《我的中尉》荣膺大书奖头奖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
| 內容簡介: |
|
1941年6月22日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年轻工程师达尼伊尔拒绝留守后方,告别了新婚的爱妻,毅然奔赴前线。他经历了战争的全部恐怖、残酷、血腥、艰难,见惯了炸弹、枪炮、饥饿、严寒、疾病所造成的大批死亡,人性在巨大的冲击下一分为二:一个是从其本体中分裂出去的中尉D,血气方刚,满怀必胜信念,而本体之我则不时陷入犹豫、动摇,质疑,反思。虽然主人公九死一生,熬过了战争,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但是战争带给他的噩梦并未终结,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久久无法愈合,本体之我和我的中尉之间的对话和争论仍在继续……
|
| 關於作者: |
|
达尼伊尔格拉宁,1919年1月1日出生于沃雷尼市一个林务官家庭。1940年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毕业后,进入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工作,并从工厂入伍,在坦克部队服役,直至战争结束。1949年,于业余时间开始写作生涯。素以科技题材和纪实小说见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探索者》1954,《迎着雷雨》1962,《逃亡俄罗斯》(1994),中篇小说《异城之雨》(1973),《奇特的一生》(1974)《同名者》(1975)等。作家一生笔耕不辍,曾荣获苏联国家奖文学艺术类大奖(1978),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文化与艺术类大奖(2001),大书奖(2012)等著名文学奖,并有多部作品被搬上舞台和拍摄成电影。
|
| 目錄:
|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达格拉宁和“他的中尉”
|
| 內容試閱:
|
第一次轰炸
真正的恐惧、人的恐惧,将我,一个愣头青,攫住,在战场上。那是第一次轰炸。我们的民兵梯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开赴前线。德军迅速逼近列宁格勒。两天之后梯队抵达巴捷茨基车站,距离列宁格勒约一百五十公里。民兵们开始下车,正在这时头顶掠过了德国飞机。一共有多少强击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整个天空都被飞机遮住了。原本晴朗、温暖的夏日天空开始轰鸣、颤动,声音越来越响。黑色的飞翔的影子将我们罩住。我从路堤上滚下来,扑到最近的灌木丛底下,把脑袋扎进灌木丛里。第一颗炸弹掉下来了,大地猛地一震,紧接着炸弹开始一连串地往下掉,爆炸声汇成一片,天摇地撼。飞机开始俯冲,一架接一架地瞄准目标。而目标就是我。它们都想要炸到我,贴着地面冲向我,螺旋桨卷起的热风搅动着我的头发。
飞机吼叫着。炸弹往下掉着,嚎叫得更加疯狂。它们的咆哮声直往我脑子里钻,直刺我的胸口、腹部,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搅翻了。飞坠的炮弹那凶恶的呼啸声充斥了整个空间,淹没了一切惨叫。呼啸声一直不断,把我的一切思想都拽出来,让我什么都不能想。恐惧整个儿将我吞噬。爆炸的巨响听起来反倒让人安心些。我紧紧地贴在地面上,以便炮弹碎片能从身体上面飞过去。是恐惧教会我这么做的。一旦有弹片飞过,我就有一秒钟的喘息时间。利用这一秒钟,我可以把发黏的汗水擦去一种特别的、恶心的、发臭而令人恐惧的汗水并且稍稍抬起头看看天。但是那晴朗宁静的蔚蓝天空重又发起新的、暂时还显得低沉颤抖的呼啸声。这一次飞机扔下的那黑色十字架刚好砸在我所在的灌木丛上。我努力地蜷起身子,尽量缩小自己的体表面积。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草地上是那么显眼,两条腿直挺挺地戳在绑腿里,背上的大衣卷像一座小山。炸起的泥土撒在头上。新一轮轰炸。飞机俯冲的轰响将我砸扁了,我生命的最后一瞬与这轰鸣融为一体。我开始祈祷。我其实连什么样子的祈祷词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信过上帝,因为我受过新式高等教育,懂得天文学,还知道神奇的物理法则这些知识告诉我根本不存在上帝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开始祷告。
天空将我出卖了,什么文凭和知识都不能救我的命。我一对一地面对着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死亡。我用烤焦的嘴唇咕哝着:上帝,行行好吧,救救我吧,别让我死,求你了,让死神放过我吧,别掉在我身上,上帝啊,救救我吧。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了这两个古老词语的意义上帝……保佑!……在我未知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启了,从里面像一股暖流一样涌出了很多词语,都是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说过的天哪,护佑我吧,求求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远处爆炸了,谁的身体被炸飞了,血肉模糊,其中一块肉血淋淋地掉在我身旁。高大的、被熏黑了的砖墙水塔慢慢地、悄无声息地、就像在梦中一样地歪下去,倒向铁路上的列车。一颗炸弹在蒸汽机车前爆炸,后者立刻被淹没在一片白色蒸汽中。道路被炸毁,枕木被炸飞,车厢被掀翻,车站的窗户被里面的火光映得通红。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远处,我尽量地不看这些,不往那边看,而是盯着绿色的草梗,看棕红色的蚂蚁在草地上爬,白胖的毛毛虫从细枝上垂下来。草地上是一如往常的夏日生活,从容、美丽,正是当时景致。上帝不可能住在天上那里充满了仇恨和死亡。上帝在这里,在花丛中,在虫飞草长之间……
飞机一次又一次地俯冲,像地狱的旋转木马无休无止。它想要毁灭整个世界。难道我注定不能死在战场上,而要像这样,屈辱地,什么都还没做,一枪还没开就死掉吗?我身上带着一个手榴弹,但总不能用它来炸向我俯冲过来的飞机吧?我被恐惧压倒了。我心里的这恐惧有多少啊!轰炸从我心中勾起一阵又一阵的恐惧可耻的、羞愧难当的、压倒一切的恐惧,我无法遏止。
几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死,却已经变成了一摊发抖的黏液。我已经不再是人了,而只是一个屈辱的、被恐惧攫住的动物。
……寂静慢慢地回来了。火舌噼啪作响。伤员们呻吟着。水塔坍塌了。弥漫着烧焦的味道,烟尘在无风的空气中沉淀下来。毫发无损的天空又恢复了它那冷漠的美好。鸟儿们又开始叽叽喳喳。大自然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它是不知道恐惧的。而我却好久没能缓过劲来。我在精神上受了重创,开始鄙视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个懦夫。
这次轰炸没白挨,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战士。不光是我,所有人都是。我们所体验到的恐惧使得体内发生了一些变化,接下来再遭遇轰炸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我突然发现,这些轰炸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它们首先是影响人的心理,实际上想要真正炸到士兵身上没那么容易。我开始相信自己有金刚护体,或者说,我可以免受弹伤。这是一种特殊的士兵情感,可以让我从容地寻找掩体,凭借炮弹的呼啸声来判断它的落点。这不是惶惶待死,而是积极战斗。
我们克服了恐惧,凭借我们的反抗、射击,给敌人造成了威胁。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头戴钢盔、身穿绿军装的德国士兵凭借自己的冲锋枪、坦克和空中霸权让人心生畏惧。他们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这种情绪。他们不仅有武器优势,而且还带着正规军的光环,而我们,民兵,看起来却可怜兮兮的:蓝色马裤,不是长筒靴,而是短靴加绑腿。身上是不合身的军大衣,头上是船形帽……
三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我们的炮弹和子弹也能消灭敌人,德国的伤兵也会哀嚎、死去。终于,我们看到德军开始退却。最初是一些局部的小型战斗,他们狼狈逃窜。这是个发现。从俘虏那里我们得知,原来我们这些民兵,穿着难看的马裤的民兵,也让他们感到害怕。民兵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和他们的一腔怒火将敌人猛烈的攻势遏止在卢加河边上。德军卡在了这个地方。最初令人晕头转向的打击所带来的压迫感已经消失了。我们不再害怕了。
在军事封锁期间,作战技巧变得不相上下。我们的战士们,饿着肚子,弹药不足,却坚守阵地整整九百天,他们凭借精神上的优势战胜了吃得饱饭、装备精良的敌人。
凭我自己的体验,或许在我们的其他战线也都发生着几乎同样的克服恐惧的过程。在战场上恐惧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就连久经沙场的老兵也会感到恐惧,他们知道应该害怕什么,该怎么做,他们知道,恐惧会夺去力量。
需要区分个体恐惧和群体恐惧。后者会导致恐慌情绪。比如被包围的恐惧,这种恐惧是自发的。德军冲锋枪在身后打响,有人大喊“被包围了!”其他人立刻就可能会开始逃窜。往后方跑,豕突狼奔,慌不择路,只求能突出包围圈。不可能坚守住阵地,也不可能阻止后退者。群体恐惧会麻痹思维。在战斗中,精神原本就高度紧张,这时候只要一声喊,只要有一个胆小鬼,就能引起普遍的恐慌。
被包围的恐惧出现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后来我们学会了从包围圈中安全撤退和突围,包围也就不再可怕了。
有一种东西和恐惧相互排斥,也许有些奇怪它是笑。恐惧时是笑不出来的。而一旦笑起来,恐惧就会过去。恐惧经不住笑,笑能将恐惧杀死、排斥、消灭,至少也能将其赶走一段时间。关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故事,是我从优秀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那里听来的。
在作家去世前不久,在“作家之家”为他举办了一场晚会。当时左琴科已被封杀,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也不允许他公开发言。晚会是秘密举行的。假托作家的创作汇报。受邀人员名单也极为有限。左琴科非常高兴,此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处于被隔离状态,哪儿也没去过,哪儿也不请他不敢请。
晚会开得非常喜庆,让人感动。左琴科介绍了他的工作情况。他正在构思一个短篇《我生命中最令人称奇的一百个故事》,他给我们讲述了其中的几个。他不是读的,因为他还没有手稿。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动笔。其中的一个故事和我们的话题有直接的关系。我试着凭记忆把它讲出来,遗憾的是,只能用我的语言,而不是用米哈伊尔左琴科那独一无二的神奇的语言。
这件事发生在战争中,在列宁格勒战线。我们的一队侦察员沿着丛林小路前进。时值深秋。落叶在脚下作响,影响了听觉。他们朝前走着,手中的冲锋枪随时准备开火。他们走了很久,逐渐放松了警惕。道路急剧地转了个弯,就在转弯处他们脸对脸地和德军遭遇了。对方也是一个侦察小组。双方都慌了。没有任何命令,德军自动地跳到了道路一侧的边沟里,我们的人也跳到边沟里,在路对面。而一个德国士兵忙中出错,跳到了苏军士兵这一侧的边沟里。他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他看到旁边士兵的船形帽和红五星时,立刻就傻了眼,一声惊叫,从边沟里蹿起来,一下子就“飞”到了对面的边沟。那一跳就像是巨人似的,把地面的落叶都扬起来了。恐惧赐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他当时很有可能破了跳远的纪录。
我们的战士们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起来,德军也笑了。两边的人面对面地坐到边沟里,取下冲锋枪,开怀大笑,打趣着这个可怜的兵伢子。
这么一来,再开枪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笑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将所有人结合起来。德军难为情地沿着边沟向一个方向匍匐前行,而我们的人向着另一个方向。就这样分开了,一枪也没开。
夏宫
分别前我们三个在彼得宫后面相聚,在一尊长着古罗马式臀部的大理石女神像的背后。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最爱。我们和自己的女友约会时也总选在这个地方。那里多荫又凉爽,太阳洒下的光斑在夏园那修剪齐整的草地上慵懒地摇晃。
本被分到高射炮部队,瓦吉姆则进了海防炮兵团。他们夸耀着各自的大炮,两个人都有尉官军衔,上大学的时候得到的,红色的方形领章在崭新军便服的襻儿上闪闪发光。军官制服让两个人大变样。瓦吉姆尤其显得帅气:头上的制帽,他管它叫大檐帽,大大咧咧地歪戴着,细蜂腰,扎着带红五星皮带扣的腰带。一切都锃光瓦亮。本显得有些笨拙,书生气还未完全褪去,他的忧伤就不像个军人样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临别前的忧伤。
我根本没法儿跟他们比:身上的军便服是退伍的,棉布料制成,脚上是不知被谁磨破了的低帮鞋,还有绑腿、贡斜纹的骑兵马裤。这就是我们民兵的装扮。很多年后,我找到了一张老得发黑的照片,那天照的。优秀的相片艺术家瓦列拉普罗特尼科夫用电脑奇迹般地将我们三个从最后一次见面的黑暗中拉到了上帝的光芒下,于是我又看到了穿着那身衣服的自己。瞧这模样,原来我就是这副装束奔赴前线的。我记得当时他们并没有嘲笑我,反倒是有些气愤:“难道说像我这样的,按照瓦吉姆的说法,志愿兵,就不配领套像样的衣服吗?”
他们愤愤不平地嘟囔着一句口号,这口号是当时所有集会都少不了的:“挺起胸膛保卫列宁格勒!”胸膛,难道说,除了胸膛之外,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吗?难道说要用胸膛去堵机关枪,撞坦克?真是扯淡,不过,从这衣沿的缭边来看,胸膛确实是首当其冲的!
我说,有这样的缭边就不错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申请下来脱去了装甲,调到民兵中的。
就是说当个小步兵?他们俩问道,你去当民兵干什么,那都是不经训练的炮灰。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本补充道。
他们的关心让我很感动。在我看来他们两个都是幸运女神的宠儿。大学里的老师们对瓦吉姆寄予厚望,包括福克院士本人,一位理论物理学的泰斗级人物。大家都认为瓦吉姆普什卡廖夫是为了重大发明而诞生的。而本则是一个数学尖子,备受卢里耶也是名人的青睐。他将来也许会是一个博士,没准儿还是个通讯院士呢。
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本来是没有人放在眼里的。跟他们在一起我永远像个丑小鸭,他们和我相比就是公子王孙,而我则从骨子里透着平民相。但是他们也因为我的一些品质而亲近我。
瓦吉姆从兜里掏出装着伏特加的军用水壶,他说这是他父亲用过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我们轮流着喝了一些,照了一张合影。本有一架小“莱卡”,叫一个路人帮忙拍了照。镜头闪亮的瞳孔定格在我们身上,从那里突然飘来一股凉意,一瞬间似乎微微启开了一道烟幕,显出未知的未来,等待着每个人。瓦吉姆脸色凝重,本抱着我们,坚定地说,我们一定会把敌人打个稀巴烂,只要等“闪电袭击”这一因素的影响过去,我们就会用猛烈的打击将他们消灭,因为……从泰加森林到不列颠海洋英勇的红军举世无双!我们分手了,相信不久就会重聚。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他们消灭掉的。
很快我们就失望了,接着失望变成了绝望,绝望又变成了愤恨,既是对德军的,也是对自己长官的,但心里还是隐藏着信心,压抑的、狂热的信心。
我们离开时走的是林荫大道,两旁的古罗马众神注视着我们。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曾经经历过的了战争、帝国的衰亡、灾难、崩溃。
十一月我接到了本从卡累利阿前线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当上了高射炮连连长,只在信的最后几行,看得出他是犹豫了半天,说瓦吉姆在奥拉宁鲍姆牺牲了,具体情况不详,是同团的校友告诉的。“但我不相信。”本最后说。那时我已经习惯了流血牺牲,但是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战争结束我都不信,甚至现在我都不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