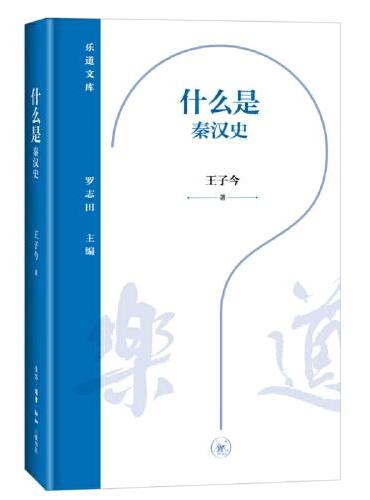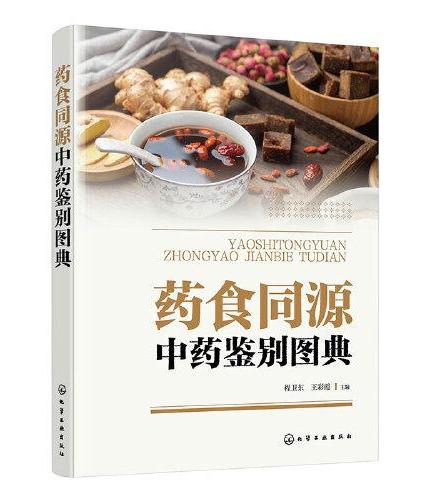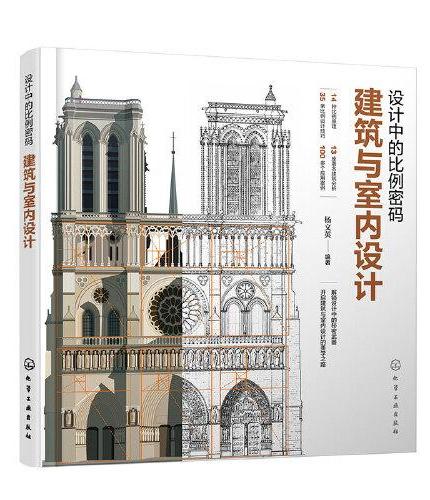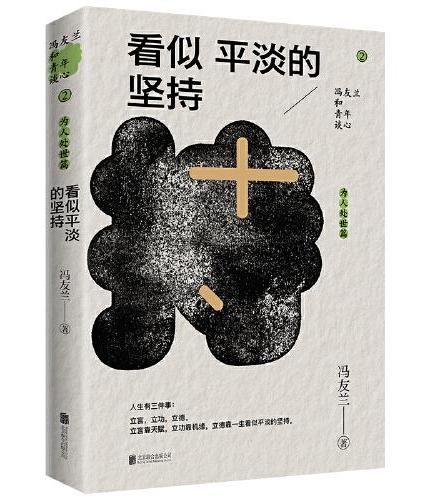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77.3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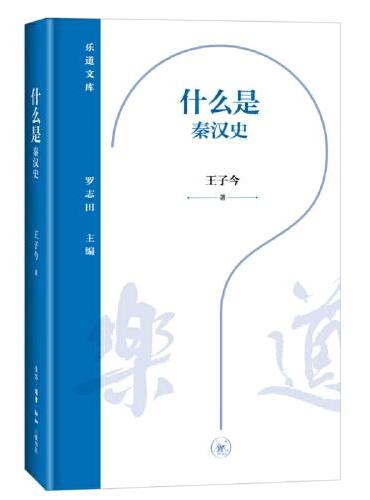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HK$
80.6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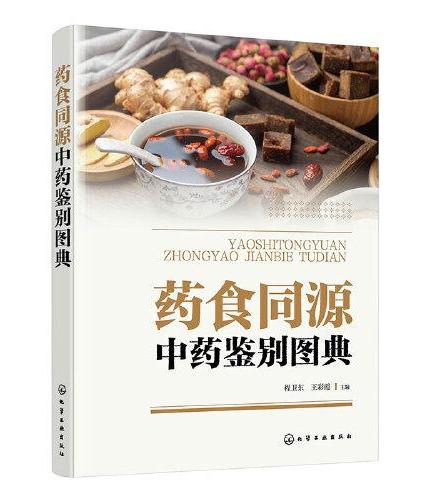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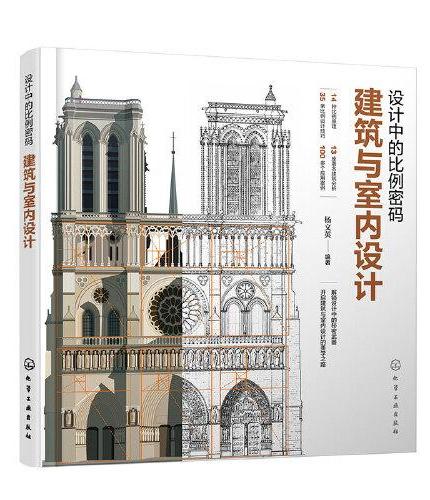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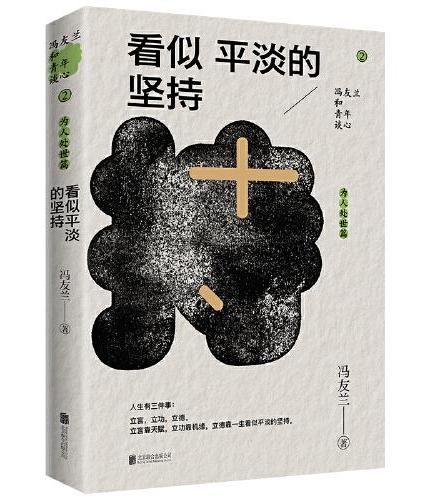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 編輯推薦: |
《暮光之城》出版方力捧新銳作家惊悚奇幻罗曼史《预言姐妹》
《预言姐妹》上市三周再版三次,銷售突破1000000册,版权已售15国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好书中的好书”(2009)
纽约公共图书馆 青少年推荐读物
《德州孤星》Texas Lone Star书单选书(2010)
《书目杂志》Booklist“青少年最佳读物”TOP 10
|
| 內容簡介: |
随着决战日的逼近,丽雅的信念却日益坚定。
为终结宿命般的预言,关闭界门,丽雅踏上了寻找剩余钥匙和失落书页的征途。她试图说服妹妹爱丽丝助她一臂之力——
否则,她将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拼死一搏。
丽雅身边还有深爱她的迪米提,爱丽丝则拥有了詹姆斯,
那个曾爱过丽雅,也许依然爱着她的男人。
詹姆斯还不知道姐妹间预言的真相,而爱丽丝打算永远对他隐瞒下去……
总有些事情即使姐妹间也无法分担,总有些秘密会将她们一齐毁灭。
|
| 關於作者: |
|
米歇尔·辛克(Michelle Zink),定居纽约,对古老的神话和传说非常着迷,《预言姐妹》是其处女作及成名作。她习惯于在阅读后提出种种假设。当所有假设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一个故事便诞生了。
|
| 內容試閱:
|
我坐在卧室桌前,手捧古书。书中的预言早已牢牢刻在我心中,如同手腕上的印记般清晰,不用看也能倒背如流。
话虽如此,但它是我父亲去世前收在藏书室里的,触摸那粗糙的封面能给我一种真实而安心的感觉。我翻开古老的封面,目光落在书页前面夹着的一张纸上。
索妮娅和我来到伦敦已经八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阅读预言成了我的睡前仪式。在这静谧的时刻,仆人和大屋都悄无声息,索妮娅在走廊另一头的卧室里面熟睡,米尔索普大宅处于最安宁的状态中。我,就在这种平和里继续努力解读由詹姆斯仔细翻译过来的预言,寻找任何也许能引领我找到失落书页的线索,寻找通往自由之路。
在这个夏夜,壁炉中的火苗发出轻轻的嘶嘶声。我低下头看着书页,再一次阅读这段把我和孪生妹妹牢牢束缚在一起却又水火不容的字句:
人类在试炼与和平之中煎熬,直到看护天使奉命下凡化作男子,娶人类女子为妻子和爱人,激发神的震怒。诞生于同一片摇荡海洋的两姐妹,一是戍卫,一是界门。一个守护和平,一个以魔易爱。当历代姐妹继续抗争时,从天堂堕落的天使将一直迷失,直到界门召唤他们的回归,或者混沌天使把钥匙带到深渊为止。魔军穿过界门大举进犯。魔王萨梅尔通过混沌天使入侵人世。混沌天使只有一层轻薄面纱做保护。从萨温节的第一丝微风中,在埃博的神秘石蟒阴影里,诞生四个印记、四把钥匙,结成火焰之环。若没有钥匙便打开混沌天使的界门,七灾将会降临人世,再无回头之日。
死亡饥荒血祸烈火黑暗干旱毁灭张开你的双臂吧,混沌女王,魔王浩劫将如洪水奔涌,因为七灾开始之日,就是一切失落之时。
曾几何时,这些文字对我来说近乎毫无意义,只不过是父亲去世前收在藏书室里的尘封古书中描述的一段传说,但那是不到一年之前的事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手腕上浮现巨蟒印记,并且遇到了索妮娅和路易莎。她们是四把钥匙中的两把。她们也有印记,只是图案跟我的稍有不同。
只有我的印记中间有“C”字。只有我是混沌天使,被迫担任界门,由身为戍卫的妹妹守护。这样的结果,并非由我们的本性决定,却是因出生次序的混乱导致。但是不论如何,唯有我可以选择永远驱逐萨梅尔。
又或者,召唤他,毁灭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
我合上古书,把书上的文字逐出脑海。时间已经太晚,别想世界末日,别想自己该怎样去阻止它了。这一切是如此沉重,压得我只想遁入单纯而平静的睡眠中。我在米尔索普大宅的睡床是一张四帷柱大床。我从桌前站起来,钻进被子里。
熄灭床头柜上的台灯之后,房间里只剩下火光。不过,这种点着炉火的房间里的单一黑暗,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令我害怕了。如今,是隐藏在熟悉的美丽地方的邪恶,让我心中滋生恐惧。
我已经很久没有试过混淆异次元魂游和单纯梦境了,不过这次入睡之后,我还是无法确认自己究竟身处哪一边。
我的四周是一片森林。直觉告诉我,这是环抱桦木庄园的那座森林。也许有人会说,所有的树看上去都是一个模样,不可能分辨得出哪是哪。但桦木庄园曾是我唯一的家,我在八个月前才离开它来到伦敦。从小我就在那片林子里玩耍,熟悉那里的地形,所以,我知道此刻的这片森林就是它。
太阳透过在我头顶高处摇曳的枝桠,投下模糊的光影,时间可能是早晨和傍晚之间的任何一刻。我开始琢磨,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现在的我,就连做梦也有目的。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丽—雅……来,丽雅……”
我转过身,好一会儿才看清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一个女孩的身影。她身材娇小,像座石像般一动不动,金色的鬈发在树林间暗淡斑驳的光照下仍然闪闪发亮。虽然上一次在纽约见到这个女孩已经是将近一年前了,但是,即便她化成灰我也能认出来。
“丽雅,我有东西要给你看。快来。”女孩的声音还是那么稚
嫩、那么甜美—正是她,第一次把那个跟我的手腕印记完全吻合的纹章交给我。从那时起,纹章与我如影随形。我等了一会儿。她伸出一只手,招呼我过去,脸上的微笑是那么狡黠,令人不快。“快点吧,丽雅。你不想错过她的。”小女孩转过身往前跑去,头上的鬈发弹跳着,消失在林中。
我跟上去,绕过树木和长满青苔的岩石,走向森林深处。虽然光着脚板,但我并不觉疼痛。小女孩的姿态像蝴蝶般优美而迅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白色裙子在身后飘扬,宛如鬼魅。我快步追赶。沿路的枝叶钩扯着我的睡裙,我边跑边拨开它们,生怕在林中失去女孩的踪影。可是,太迟了。过了一会儿她便无影无踪了。
我站在原地,转了一圈,扫视树林。所有的树木枝桠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就连太阳也被遮挡在外。我头晕目眩,失去了方向感,强忍心头涌起的恐慌,明白自己彻底迷路了。
过了一会儿,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纹丝不动,站着倾听。不会有错,她哼着的这曲子就是她在纽约蹦蹦跳跳地离开我时哼过的那首。
我循声而去。尽管穿着长袖睡裙,我的手臂上还是起了鸡皮疙瘩,颈后的汗毛也倒竖起来。然而,我不能转身离开。我在大大小小的树干之间曲折前进,朝着声音走去。然后,我听见河水的流动声。
我敢肯定,女孩就在那里。我走出最后的树丛,眼前出现一条河,往两边延伸。女孩再度出现,弯腰站在河的对面。我无法想象她是怎样渡过这条河的。她哼的曲子旋律优美,却隐含一种诡异的音调,听来毛骨悚然。我继续往前走,来到自己这边的河岸上。
她似乎没有看见我,只是继续唱着怪曲,手掌在水中划动,聚精会神地看着清澈的水面。可是,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稍后,她抬起眼睛,迎上了我的目光。看到我站在河对岸,她没有丝毫惊讶之色。
虽然她只是朝我微笑,但我知道,这笑容将让我不得安宁。“噢,很好,我很高兴你来了。”我摇摇头。“你为什么又来找我?”我的声音在宁静的森林里回荡,“你还想对我做什么?”
她低下头,手掌划着河水,仿佛没听到我的提问。
“不好意思,”我竭力装出强势的口吻,“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召唤我到森林里来?”“不用等很久,”她淡淡地说,“你就会知道。”她抬起头,蓝眼睛越过河面,与我四目相对。再次开口时,她
的面容开始摇晃。
“丽雅,你以为自己在睡眠中很安全吗?”裹在那颗细小头颅上的皮肤微微闪光,她的声调降低了一度,“你以为自己现在足够强大,没有人能碰你了?”
她的声音完全走调,面容再次颤动起来。我明白了。她露出微笑,但这时,她已经不是林中那个女孩。不再是了。她是我的妹妹,爱丽丝。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因为,我非常清楚那微笑里隐藏着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惊恐,丽雅?你知道我总是能找到你的。”
我不想对她泄露自己的畏惧,所以用了一点时间来镇静自己,之后才开口答道:“你想怎么样,爱丽丝?我们之间的话不是已经说完了吗?”
她扬起头。一如往常,这动作让我相信她可以看穿我的灵魂。“我一直以为你会学聪明些,丽雅。我以为你会意识到你为自己、朋友,还有仅剩的家人所带来的危险。”
听到她提及家人—我们的家人—我很想生气。把亨利推到河里的人,不正是她爱丽丝吗?害弟弟沉入河底淹死的人,不正是她吗?可是,她的口气似乎有点柔和,使我猜测,即使是她,也在为我们的弟弟哀悼。
我回答的语气刚硬如铁。“我们现在面对的危险,是我们为日后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日后?”她质问道,“那会是什么时候,丽雅?你甚至还没找到剩下的两把钥匙。靠着父亲那位老朽的侦探,你永远也找不到她们。”
听到她对菲利普的指责,我气得涨红了脸颊。父亲信任他,把寻找钥匙的任务交给他。即使到了现在,他依然不知疲倦地为我工作。当然了,如果没有找到《混沌之书》失落的书页,就算找到了另外两把钥匙也没多少用处,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对未来想得太远没有好处。只有此时。只有此地。
她像是听到了我的心声一般地再次开口说话。“还有那些书页呢?我们都知道,你还没找到它们。”她垂下双眼,平静地看着河水,一只手在水中划动,跟刚才小女孩的动作一模一样。“全盘考虑之下,根据你目前的状况,我会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相信萨梅尔。至少,他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保证你所爱之人的安全。
“除了安全,新的世界秩序建立之后,他还可以确保你的地位。新的世界,由他统治,由堕魂占领。它迟早都会降临,不论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们都一样。”
我本来以为自己对妹妹已经彻底死心,可是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更凉了。“爱丽丝,我看更有可能的是他会确保你在那个新世界秩序里的地位吧。这才是你的目的,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我们小时候起就跟堕魂合作了,对吧?”
她耸耸肩,看着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假装自己大公无私,丽雅。我只想尽职尽责,完成那本该属于我的任务,而不是那个预言在误导下强加给我的任务。”
“如果你还是这样想,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她又低下头看着河水。“这么看来,也许我不是劝说你的最佳人选吧。”
我以为自己今天不会再吃惊和害怕了,至少今天不会。然而,当爱丽丝抬起头来时,她的脸庞再一次幻变,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小女孩面孔的影子,但它又变回了爱丽丝。不过,这模样并没有持续多久。她的面容泛着波纹,套在一个奇形怪状的脑袋上,仿佛每一秒钟都在变化。我双脚生根般定在河边,满心惊恐却无法动弹。
“你仍然拒绝我吗,夫人?”这个声音曾经在索妮娅尝试联络我已故父亲的那一次,通过她传到房间中,我不可能认错。它是那么可怕,那么诡异,不属于任何世界。“你无处可藏,没有庇护,不得安生。”萨梅尔说。
河对面的他站起来,舒展身体。他的身高是普通男人的两倍,虎背熊腰。我真心相信,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纵身跃过河面,瞬间掐住我的喉咙。他身后的动静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双羽翼丰满的乌黑翅膀,收拢在背上。
此时此刻,除了恐惧,我的心里还有一种明白无误的渴望,一种牵扯,恨不能渡过河水扑进那双柔软蓬松的翅膀里。他的心跳声最初很轻,渐渐越来越响。扑通、扑通、扑通。我记起上一次在异次元遭遇萨梅尔的情景,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心跳也在变快,又一次跟他同频跳动。
我倒退一步。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叫我逃走,可我不敢转身,而是倒退着走了几步,眼睛紧紧盯着他那张变幻不定的面具脸。有几次,他变成人世间最英俊的男子,但很快,他再次变化,变成我所认识的模样。
萨梅尔。魔王。
“打开界门,夫人。这是你的职责,是你存在的理由。拒绝只能带来痛苦。”那深沉的喉音不仅从河对岸传来,还在我的头颅中响起,仿佛这是我自己说出的话。
我摇头。转身需要蓄积全身每一丝的力气,但我办到了。我转身奔跑,冲进河边的森林中,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他的笑声如有生命般在林间冲撞,仿佛在追逐我。
我试图把它隔绝,一边跑,一边用手推开往脸上扫来的树枝,一边祈祷从这个梦中醒来,逃离这次魂游。可我还没来得及想出办法,脚下便绊住一条树根,身体往前扑去,迅速而沉重地砸在地上,两眼顿时一阵发黑。我双手撑地,试图爬起身来。我以为,自己可以逃走,可以站起来继续跑。然而,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有一个嘶嘶的声音对我说:“打开界门。”
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忍住惊叫,脑后的头发全都被汗水浸湿。
我的呼吸急促,声音嘶哑;心脏在胸膛里狂敲,仿佛还在跟随他的心跳。就连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的光线也无法缓解梦境遗留下的恐惧。我等了好几分钟,告诉自己,那只是梦。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直到我相信为止。
直到我看见枕头上的血迹之前。
我抬起手,用手指轻触脸颊,拿开时,一切都了然于心。当然是的。指尖的红色血迹说明了一切真相。
我走到房间另一边,站在摆满面霜、香水、粉底的梳妆台前,几乎认不出镜里的女孩。她头发蓬乱,眼里是黑暗和恐惧。
脸颊上的刮伤不是很长,但十分显眼。我盯着脸上的血痕,想起刚才逃离萨梅尔时抽打在脸上的树枝。
我想否认自己这次被迫进行的独自魂游,因为索妮娅和我都同意,虽然我在异次元的法力越来越强,但是那样做并不明智。尽管如今我的能力已经超越索妮娅,可是这没有意义,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管我的能力如何迅速增长,也远远比不上堕魂—或者我妹妹—的意志和力量。
2
我拉开弓弦,停顿片刻,松手放箭。它破空而去,嗒的一声正中一百英尺外的靶心。
“你正中红心!”索妮娅欢呼,“离得这么远!”
我对她咧嘴微笑。我们雇用来自爱尔兰的弗兰尼甘先生教我们射箭的基本功。回想当初,就算有他帮忙,就算距离靶子只有二十五英尺,我也射不中靶心;如今呢,我身穿男式马裤,射箭轻松得好像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似的。想到这里,激动和自信同时涌上心头。
可是,我却发现自己无法因为掌握了这门技巧而真正高兴起来。毕竟,我的对手是妹妹,当弓箭派上用场时,箭头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她。也许,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应该很高兴看到她倒下。然而,面对爱丽丝,我无法把感情如此简单化。我心中混杂着百般滋味,有愤怒和悲伤,有苦涩和悔恨。
“你来。”我微笑着尽量用欢快的语气鼓励索妮娅上来射那个饱经考验的靶子。只是,我俩都知道,她很有可能脱靶。看来,索妮娅在与死者通灵和异次元魂游方面的天赋并没有延伸到射箭上。
她转转眼珠,把弓举起来,跟瘦削的肩膀平齐。这动作虽小,但我还是微笑了,因为,不久前的索妮娅还对这种善意的玩笑反应过度严肃呢。
她搭箭上弓,拉开弓弦,手臂因用力拉弓而微微颤抖。放手后,她的箭在空中摇晃了几下,默默落在距离靶子几英尺之外的草地上。
“啊!今天我受够挫折了,你说呢?”她不等我回答,“晚餐前,我们骑马去池塘边走走吧?”
“好,走吧。”我不假思索地答应。我可不急着放弃在惠特尼树林的自由自在,而去面对今晚那场正式晚宴的紧身胸衣束缚。
我把弓斜背在背上,把箭收在背包里。我们一起走过射箭场,来到马匹身边,上马越过原野,朝远处微微闪烁的蓝光地带走去。我的马名叫沙金特,我骑它的时间是那么长,简直是一种本能了。我一边骑马,一边欣赏四周铺展开的青翠田园。视野所及,没有其他生命。这种僻静使我又一次对惠特尼树林这个宁静的避难所感激不尽。
年轻女士穿着男式马裤骑马出来练习射箭和消遣,会被伦敦人视为失仪,但这里的平原往四面八方伸展,我和索妮娅得以避开旁人的眼光。惠特尼树林里还建有精致的别墅,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那儿换上马裤,偶尔也会去歇息喝茶。
“我跟你赛跑!”索妮娅回头对我喊着,说话间已催动马匹偷步。我并不介意。虽然只是一次友好的骑马赛跑,但是让索妮娅在马背上占点便宜会让我感觉我们依然处于同一地位。
我驱使沙金特往前跑,俯下身体贴在它脖子上。它迈开健壮的四蹄,大步飞奔,鬃毛如同乌黑的火焰,拂过我的脸庞。我不禁为他这身闪亮的皮毛和出色的速度而赞叹。很快我就赶上了索妮娅,但我稍微收了一下缰绳,保持在略略落后她那匹灰马的位置。
她领着我们冲过一条无形的终点线。我们的许多次赛跑都是以这条线作为终点的。马匹慢下脚步,她回头看我。
“我终于赢了!”
她在池塘边上停下。我微笑着,催马小跑上前到她身旁。“是的,好,这只是时间问题嘛。你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骑手了。”
她开心地灿烂一笑。我们下马,牵着他们走到水边,默默站着让它们饮水。索妮娅呼吸平缓。难以想象曾经的她连上马都害怕,更别提像现在这样每周至少三次骑马飞奔,翻越小山了。
马匹喝饱之后,我们牵着它们来到一棵长在水边的巨大栗树旁,拴在树身上,自己则在野草上坐下,手肘撑地,仰面半躺。骑马时穿的羊毛马裤裹着我的大腿,但我没有抱怨。能穿着它们已经是享受了;过不了几个小时,我就得束缚在丝质长裙里,参加灵异圈的晚宴。
“丽雅。”索妮娅的声音随着微风飘来。
“嗯?”
“我们什么时候去埃图斯?”
我扭头看她。“我不知道。我猜,要等阿比盖尔姨婆认为我已经做好旅行的准备,派人来接我的时候吧。怎么了?”
有那么一会儿,她那张通常很平静的脸蛋似乎因为烦乱而黯淡了下去。我知道,她正在想着我们寻找失落书页所面对的危险。
“我想,我只是希望能尽快了结此事罢了。有时候……”她扭过头去望向惠特尼树林的原野,“呃,有时候我们的这些准备仿佛毫无意义。与刚刚抵达伦敦那时相比,现在的我们与书页并没有靠近多少。”
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少见的尖锐。我突然心生歉意:我太沉迷于自己的困境和失落,从没想过去关心她身上的重担。
我垂下目光,望向缠绕在索妮娅手腕上的黑色天鹅绒手镯。纹章。我的纹章。虽然戴在她的手腕上是为了保护我,可我不由自主地想念那柔软而干燥的天鹅绒缎带和那冰凉的金色圆盘贴在皮肤上的感觉。它对我的这种奇异吸引力,既是我的负担,也是我的渴求。从它找到我那一刻开始就是如此。
我拉住她的手,露出微笑,却自觉脸上的笑容透着哀伤。“如果我对你为我分担忧虑没有表达足够的谢意,我向你道歉。索妮娅,如果没有了你的友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
她羞涩地笑笑,抽回手,满不在乎地朝我挥了挥。“别傻了,丽雅!你知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
她的话安抚了我心底的担忧。不论将来如何,不论有多少可怕的事、多少不可信任的人,我都知道,这份友谊属于我们,能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心灵安慰。
参与灵异圈晚宴的人跟任何其他宴会来宾一样风度翩翩。差异隐藏在表面之下,只有参与其中的人才能发现。
我们在人群中穿行,暂时放下先前的忧虑。虽然预言本身依然是我们—我和索妮娅—的秘密,但在这里,我最能做回自己。除了索妮娅之外,这个圈子里的人便是我的主要同伴,为此,我将永远感激维吉尼亚姨妈写的介绍信。
人群中,我发现了一颗整齐地戴着头巾的银发脑袋,于是碰碰索妮娅的手臂,说:“来,艾斯贝思在那儿。”
老妇人也看到我们了,她仪态优雅地在人流中穿行,来到我们跟前,脸带笑容。“丽雅!宝贝!真高兴你来了!还有你,亲爱的索妮娅!”艾斯贝思·舍尔顿靠过来,在我俩脸颊上轻轻一吻。
“为了全世界,我们绝对不会错过的!”身穿深红玫瑰色长裙的索妮娅回答,两颊泛起淡淡的红晕。这个圈子里的人,不仅拥有跟她一样的天赋,还各自拥有独特的能力。索妮娅在纽约受米尔班夫人约束多年,来到这里,受到众人的温暖关怀,自然光芒四射。
“我就知道!”艾斯贝思说,“难以置信,你们拿着维吉尼亚的信出现在咱们门口的那天才过去了八个月。有了你们两位的参与,我们的聚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过,我敢说,你们的姨妈期望我对你们的监护可远远不止这么一点。”她顽皮地挤了挤眼睛。我和索妮娅哈哈大笑。艾斯贝思也许把组织圈子活动和聚会视为己任,但她给我和索妮娅留出了充足的独立空间。“我得招呼其他人去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她朝一位老绅士走去。虽然那个人此时正在尝试表演隐身术,但我能看得见他,而且认出他是亚瑟·弗罗比舍。圈中传言,亚瑟的血脉可以追溯到许久以前的德鲁伊教大祭司。尽管如此,他的年纪削弱了他的咒术,那把灰胡子和皱马甲仿佛笼罩在雾中,能看到淡淡的轮廓。他正在跟一个年轻人说话,声音听得很清楚。
“如果维吉尼亚得知艾斯贝思给我们俩的监护只有这么一点点,肯定会歇斯底里发作的,你说是吧?”身旁的索妮娅笑嘻嘻地说。
“当然会的。不过,现在毕竟是1891 年了。再说,维吉尼亚姨妈怎么会得知这里的情况呢?”我对她咧嘴笑道。
“你不说,我也不说!”她大笑着,对房间里缓缓走动的人们摆摆头,“我们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扫视房间,寻找认识的人,发现一位年轻绅士站在雕刻精美的楼梯旁,顿时眼睛一亮。“来,拜伦在那儿。”
我们穿过房间。人们谈话的片段、烟斗飘出的烟雾,以及空气中浓重的熏香,都朝我们飘来。终于来到拜伦跟前,他闭着双眼,手臂垂在身侧,指挥着五个苹果在他身前以完美的间隔在空中轮圈。
“晚上好,丽雅和索妮娅。”拜伦向我们问好,没有睁开眼,苹果们仍继续跳着圆圈舞。他表演各种各样的娱乐把戏时,总是闭
着眼睛,却总是能知道我们来到他跟前;我早就已经放弃琢磨其中的门道了。“晚上好,拜伦。看来你的技术不错。”虽然他肯定看不见我的动作,我还是朝苹果点了点头。
“啊,对呀,这种把戏可以逗小孩子,当然还能让女士们开心。”他睁开双眼,直视索妮娅。苹果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他手中,个个都泛着深红色的光泽。他拿出一个,耍了个花势,递给索妮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