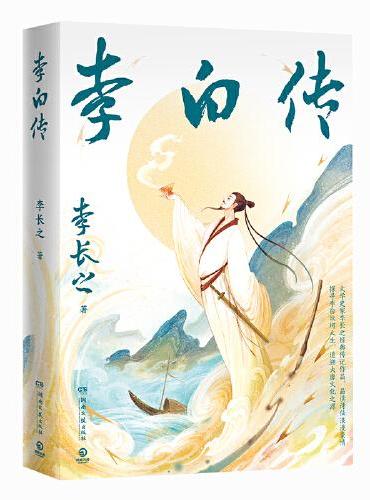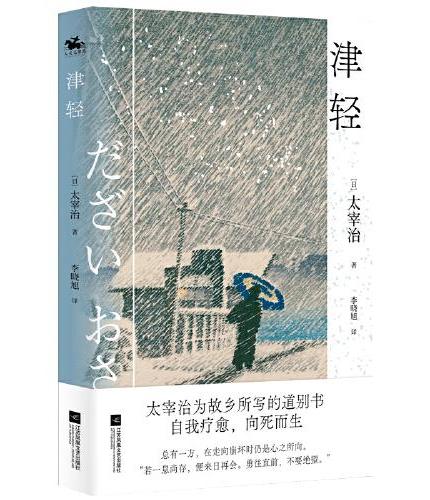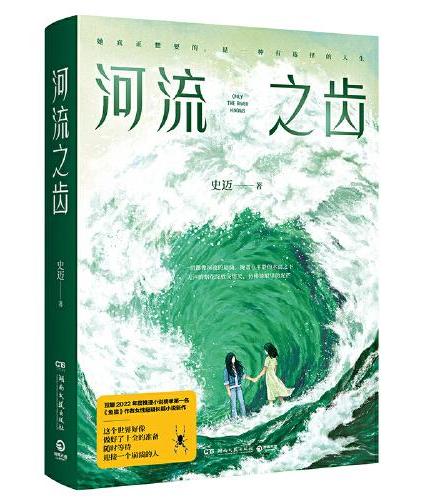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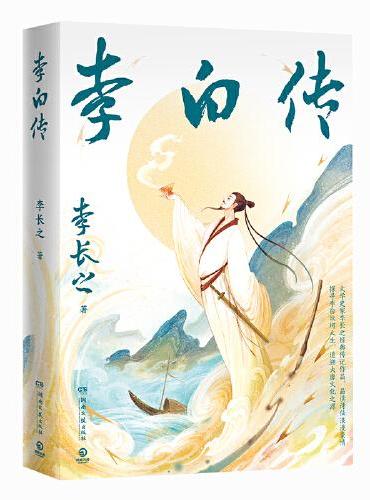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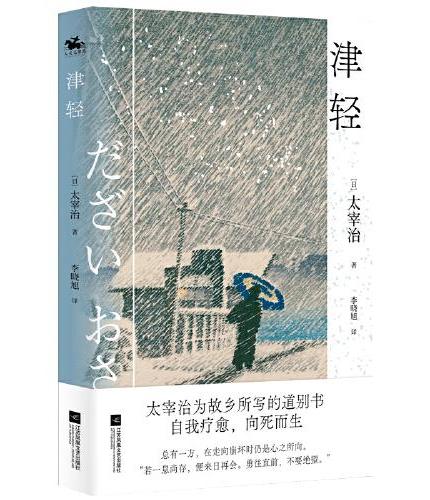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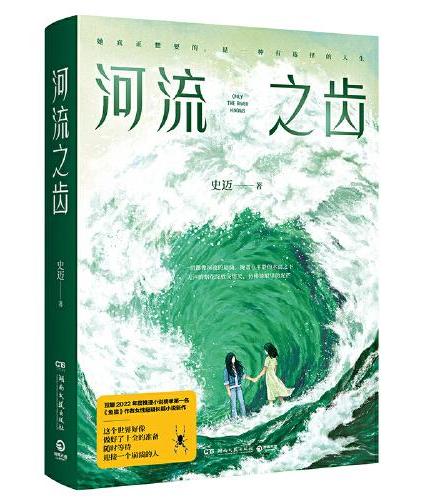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 編輯推薦: |
|
一个拥有吉普赛血统和经历的欧洲人,最爱的是日本文化,没有之一;一个神经质的诗人,将敏感的触角探到日本民族的灵魂深处,让它的思想一览无余。此书作者小泉八云是欧洲人,曾在英法美等国学习、工作,最后来到日本,加入日本国籍,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作者来自西方文明,又能体察并认同日本文明的种种独特之处,所以见解格外深刻。译者是民国时期知名学者胡山源。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小泉八云评论日本及日本人文章的选辑,从心理、哲学上剖析了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从日本人的内在和外表、历史和社会、心理学和伦理学各方面,描摹当时日本的国民特性。
|
| 關於作者: |
|
小泉八云(1850—1904),生于希腊,长于柏林,学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渡过了人生中最困苦的时期。1890年赴日,开始了在日本生活、写作的后半生,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讲授西洋文学。与日本女子小泉节子结婚,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从妻姓小泉,取名八云。他精通英、法、希腊、西班牙、拉丁、希伯来等多种语言,学识极为渊博,写过不少向西方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也是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
|
| 目錄:
|
译者自序
原编者序
第一章 日本文明的天性
第二章 柔术
第三章 远东的将来
第四章 一个守旧者
第五章 困难
第六章 奇异与魔力
第七章 忠义的宗教
第八章 关于永久的女性的
第九章 关于祖先崇拜的几个思想
第十章 灵魂先在的观念
小泉八云年表
曹聚仁笔下的小泉八云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日本文明的天性
引言
许多人以《心》为小泉八云著作中最有力量的杰构,这是确然不容怀疑的事情,本篇便是这书中的一篇。写成本篇的地点是神户,那时他是《神户年鉴》编辑部的一份子。那时他渐渐的不注意日本国内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专为“事物的中心”作说明。
“我想这是在神户,”威德摩夫人(MrsWetmore)写着说,“他达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的感觉敏锐中,他就写明了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里面充满着纽约城(New York City)可惊的描写,和东方世界难于捉摸的心灵上精微的观察。”
一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成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方面,全部变了颜色。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极大力量的发展,从来为国外所不知道的——是一种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学家都知道,所谓“西方文明的采取”,三十年来对于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脑筋中,素来所没有的,并没有加添什么。他也知道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并不能算作一种突然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转运来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较的慢些,必须要有数百年的光阴,才能产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学上的结果来。
就在这种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国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时代中,最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脑筋,竟能担任得下这样重大的一个震动。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事实固然是这样了,究竟在实际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无非将已有的思想之机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组罢了。在千万个勇敢的少年心思看来,便是死也不要紧。西方文明的采取,并不像一个没思想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这是很明白的,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因此,西方实业发明的应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显出了极好的成绩——根本着他们民族所熟习的种种技术,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许多年来,另是一种面目,格外的精巧。没有什么变化——至多不过是将旧能力改成了新能力,达到了较大的范围。种种科学的职业,也可见出同样的情形来。有几种科学,例如药学外科(世上没有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医生),化学,显微镜学,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适合的;在这些事上,成绩的惊人,世人早已有口皆碑了。战争时和国家有什么大事业时,他们更显出了奇妙的大能力;不过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最著名的,还是他们军事政治的大能力。然而外国的趋向,对于他们的民族性,并没有成功什么伟大之处。例如在西方音乐、西方艺术、西方文学这许多研究方面似乎不过浪费光阴罢了。(在某种有限制的意义上西方艺术已经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和戏剧;不过影响的性质,却证明了我所说的种族的差异。欧洲戏剧为了日本舞台改形了,欧洲小说为了日本读者改写了。文学的迻译是不很注意的;因为原来的事实、思想和情绪,对于普通的读者和观者,都得不到了解。情节是选取的;情感和事实就完全的改变了。“新马格大连”(New Magdalen)成了和一个“秽多”结婚的日本少女。嚣俄的《哀史》(Les Mirerables)成了一个日本内战的故事;而恩茄拉斯(Enjolras)便成了一个日本学生。出于例外的略有几种,其中有那《少年维特(Werther)之烦恼》照文字上翻译而得到显著成功。)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情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日本人的情绪生活却没有这样的重要。每一个切实的思想家,都知道个人的情绪,要用教育来转变是不可能的。想象那一个东方民族的情绪性格,会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转变的,那简直不合理。情绪生活,比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决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镜子的表面不为种种反映所改变一样。所有日本所以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绩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转变;那些想现在的日本在情绪上已比三十年前更和我们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学上确切不可移的事实。
同情是为理解所限制的。我们同情的程度,以我们的理解为标准。一个人可以想象他对日本人或中国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决不会超出普通情感生活中几点极简单的小范围——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几点。更复杂的东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个人的经验结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并没有真正显著的连带关系,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反过来说,日本人,虽然他们愿意,也不能给欧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终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绪(两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真面目,一方面他也始终要想象日本生活比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这固然是文雅,这固然含着极为珍贵,极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这又何等的渺小,比较起来,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为我们必须判断着可见可量的实物。这样判断起来,西方和东方的情感与理智方面,是怎样一个不同的对照呀!日本京都街上,无非是轻飘飘的木头建筑,而巴黎或伦敦的大道上,则到处非常的坚实,是常见的事。试将东方和西方对于它们的梦想、愿望和感触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加以比较——天主教大礼拜寺之与神道教庙宇,凡提(Verdi)的歌剧或华格纳(Wagner)的三幕剧之与艺妓的登场,欧洲叙事诗之与日本小诗——在情绪的卷帙、想象的能力、艺术的综合这种种方面,相差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真的,我们的音乐实在是近代的艺术;不过回顾着我们的已往历史,创作能力上的分别,不是不显明的——不一定是在有云母石的圆形剧场,和属地遍天下的伟大的罗马时代,也不一定是在雕刻达到神圣,文学达到绝顶的希腊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日本势力突进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实了。伊在生产方面和战争方面所显出来的那种伟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质的表征在哪里呢?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在伊的情绪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实业和商业生活上也找不出——伟大!土地还是和从前一般;它的表面上,因明治维新而增加起来的并不算多。小规模的铁道和电杆,桥梁和隧道,在那历古以来青葱满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没有谁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里,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分的外国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并列成行的绿树,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踪,也很令人难得。你可以作深入内地二百里的旅行,你决不能看见什么新文明的大发展。你也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出巨厦巍峨的大货栈,以示商业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数十亩,用着机器的大工业。一个日本城市,还和十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了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嚷——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愿意,你在东京城里也能享受到乡村的生活。这种使人看不见或听不见的新势力,现在正在威吓着西方的商业,改变着远东的地图,不禁令人发生着奇异,我甚至要说妖妄的感觉。当你跋涉了数里的寂寞长途,到了什么神道教的庵宇,而所见的只是空虚与孤零时,你差不多就要感觉到,只是一件渺小荒凉的木建筑,在千年的暗影中发着微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样,用不着什么巨大的物质宣示;它们的所在地,就是那不论哪一个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灵魂中”。
二
我默想起来,一个大城市的记忆,就回到了我的脑筋里——是一个壁垒耸天,闹声如海的城市。那种闹声的记忆先回转来,然后是看见的景象。一条深壑,那是一条街;嵌在群山之间,那是房屋。我倦了,因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峰峦中,已经走了许多里路,已经好久没有踏着一片土——只有石片,已经没有听到什么别的,只有暴乱的轰雷,在那极大的街面之下,我知道另有一个非常的空阔世界:组织重重,千头万绪,管理着水和汽和火。街的两边,有许多窗户层层的屋面高高的对峙着——这是遮住日光的建筑之悬崖。上面惨淡的一片青天,被密密的蛛网割得粉碎——这是数不清的电线网。右边那一区宅子中,住着九千个灵魂;房客们每年所付的租金是一百万元。稍远的一区所值的钱,总在七百万元以上,这样的区域,也不知有多少。钢铁梯和水泥梯,铜梯和石梯,装着最重的栏杆,扶摇直上,高至数十层,可是从来没有足迹踏到它们过。用着水力,用着汽,用着电,人人上下自如;对于肢体的应用,这些高度太眩人了,距离太大了。我的朋友,住在相近的一个巨宅十四层楼上,房金是五千元,从来没有踏过他的梯子。我因为好奇心的原故,就独自步行着;如果正经的讲,我是不应该步行的:空间太阔了,时间太宝贵了,对于这样慢慢的努力,人都是用汽力从这地到那地,从家到办公室的。高度太大了,声音传不到;命令的授受,都是藉着机器。藉着电气,远远的门户开放了;轻轻的一触发,百间屋里都亮起来热起来了。
所有这些巨大,都是艰难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这是达到坚固耐久的利用目的,应该用着科学力量的巨大。这些高楼大厦,商店工场,不论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都不是美丽,不过是不祥。谁感觉到这些创作它们的巨大生命,是没有同情的生命,这些发扬的浩漫力量,是没有怜惜的力量,谁也要感到沮丧的。它们是新实业时代建筑的宣示。车走如雷声,人足和马蹄如暴风,没有一些休止。问一句话,必须尽量的呼喊,被问者方才能听得见;在那样高压力的声浪传达中,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要有经验。不习惯的人,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风大浪,惊波怒涛中的感觉。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怪奇的街道,藉着石桥网桥,跳过了江河,跨过了海口。目力所极的地方,桅樯纷纷,绳索成网,将那石工造成如悬崖绝壁一般的岸边遮得密不通风。森林中的树木,树木的枝干,比了那样令人目眩心骇的长杆短橛,真显得贫薄,真显得稀疏。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三
总而言之,我们的建筑要耐久,而日本人则要无常。在日本普通用物中能有耐久观念的,实在没有多少。每次旅行的途程上,草屦破了又换了;身上的衣服,用几块布松松的一缝便可穿着,简单的一拆便可浣洗;旅邸中的新客人,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窗户上和墙壁上的糊纸,只顾目前之用,一年至少换两次;席子每年秋天换一次新的——所有种种这些事情,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无数小事物的略举一二,都可以显出他们的无常。
一个普通日本住所的故事是什么呢?早上,我离家走过那下一条街和我所住的街交叉处,我看见几个人在那边一块空地上,将竹竿竖了起来。五小时之后,我回来了,我看见那原地上,已有了一座二层楼房屋的骨骼。明天下午,我看见墙壁差不多要完工了——烂泥和芦笆。傍晚时光,屋顶已经完全盖好。又明天上午,我看见席子都已铺好,里面的粉饰也已完工。五天之内,这房子就完全造好。固然,这是一座便宜的宅子;比较优美些的,免不了还要多费些时间。不过日本的许多城市,大部分都是这种普通房屋组织成的。它们既便宜而又简单。
我第一次注意中国式屋顶弧形,犹存游牧时代篷帐的遗迹,我已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思想,常常缠扰在我的心中,自从我已忘却了所从找得的书本以后,我第一次在出云看见了神道教古庙的特殊建筑。在它的山墙和屋檐上,都有奇异的十字形的突出物体,这时候,我才突地记起了那书中所说来源恐非远古的话头。不过,在日本,除了许多原始建筑的传说以外,还有许多关于民族方面游牧祖先的传说。不论何时,不论何地,要找得我们所说的坚固,完全是不可能的;在日本人的外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似乎都留着无常的特性,除了农民的古服,和他们用具的式样,其中大多数已竟完全消灭了。看了这种事实,格外可以使我们大胆的说,每一个日本城市,在三十年之内是一定要重新建筑过的。有几处庙宇,和若干少数巨大的炮垒,可以作为例外;可是按着通例,日本城市即使不变更它的形式,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要变更它的实质。火灾、地震,和其他种种原因,固然是造成这种景象的一部分理由,然而主要的原因,便是所有房屋的建筑并非是传之久远的。平民都没有祖遗宅基。最宝贵的地点,不是出生的地方,乃是埋葬的地方;除了死人长眠之处,和古庙的残址以外,永久的地方是很少的。
土地的本身,就是无常的土地。河流时常变迁,海岸时常递嬗,而平原也时常起伏;火山的高峰,一会儿高,一会儿碎;石熔山崩,填满了幽谷;湖泊则忽隐忽现,甚至那举世无双的富士山,它那白雪皑皑的奇迹,为数世纪许多艺术家感兴的焦点,据说自从我到日本后,已经微微的变过样子了;至于在这短短时期中,完全变过形态的山岭,更不在少数。只有土地上一般的情形,自然界一般的状况,和时季的一般个性,还总算依然如故。就是风景的美丽,也往往变幻不定——是一个五光十色,烟笼雾摇的风景。在这群岛的历史中,只有熟习于美景的人,才能知道出岫的闲云,怎样的会将那已有的真正异象加以何种别的变态,预料着将来还有些什么别的幻景。
诸神确是存在着——依依于他们的山居,在林间的微光中,散布着幽幽的宗教威严,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形体的罢。他们的庙宇,像人类的居处一样,是不曾被人遗忘的。不过每一个神道教庙宇,在相当的时间中,必须要重新建筑一过;那最神圣的——伊势的庙宇——按着旧风俗,每二十年必须拆毁一次,将它的木料切成千百根小块,分给香客们,以为灵物。
佛教,带着它那博大精深的无常妙义,经过了中国,从亚利安印度来了。第一次在日本的佛庙建筑家——另一种族的建筑家——建作得很好,看了镰仓地方许多世纪以来还存留的中国式建筑,便可以证明,而那曾经围绕他们的大城,现在则要找寻一些残址遗迹,也不可得了。可是佛教的心灵上势力,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叫人类的心思喜爱着物质的稳固。它的教训,说宇宙是个幻妄,人生不过是无尽路上的略一驻足,人生事事物物所接触的,都充满着悲苦;只有将每个欲望——甚至是涅槃的欲望——压下去,人生才能达到永久的和平,的确是和那较古旧的种族情感相谐和的。虽然人民并不向着那外国信仰的精深哲学作多量的接受,而无常的教旨必定早就使民族性格受大影响了。它解释了,又安慰了;它恰与新力量,勇敢的去担任所有的事情;它将种族的癖性,忍耐,加以鼓励。甚至在日本的艺术——在佛教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倘然不是真正创造出来的——上,无常的教旨也留着它的痕迹。佛教的教训说,世界是梦幻泡影,是石火电光;不过它又教人怎样压伏那变化无定的梦幻印象,怎样将那些印象和那最高真理的关系,加以解释。他们学得很好。在那春花焕发的灿烂中,在那蝉声嘒嘒的去来中,在那秋叶的残红中,在那白雪的纯美中,在那风云的变幻中,他们看见了永久意义的古寓言。即使是他们的灾难——水、火、地震、瘟疫——也时常将那永久虚空的教旨宣示给他们。
“一切存在时间中的万物,都要灭亡。树林、山岭——一切这样存在的东西。一切有欲望的万物,都在时间中产生了。
日与月,帝释天自己,和他一切侍从之群,都须灭亡,没有例外;没有一个能够持久的。
起初万物都确定了;最后它们都分开了:不同的结合,引起了别种的材料;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永远一致的主义的。
一切形形色色的万物,必至老境;形形色色的万物都是无常的。甚至一粒胡麻子,也并不是那种永久的实物。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备具着分解的本性。
一切形形色色的万物,没有例外,都是无常的,不稳定的,无价值的,定要分开的,解散的;一切都是一霎那的海市蜃楼,幻象和泡沫。……即使所有陶工所制的土器,结果都要被打破,人的生命也要如此结束。
对于事物本身的信仰是记不起,说不出的——这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无论儿童和无知的人,都知道这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