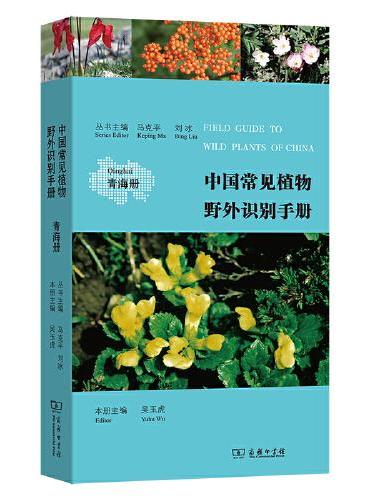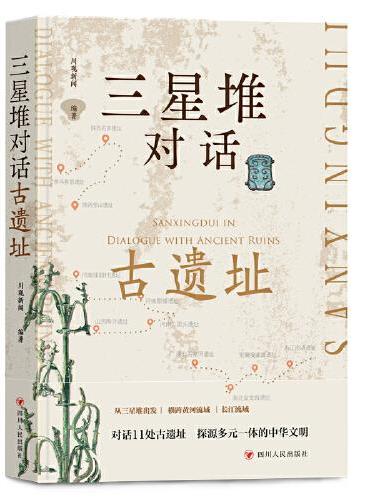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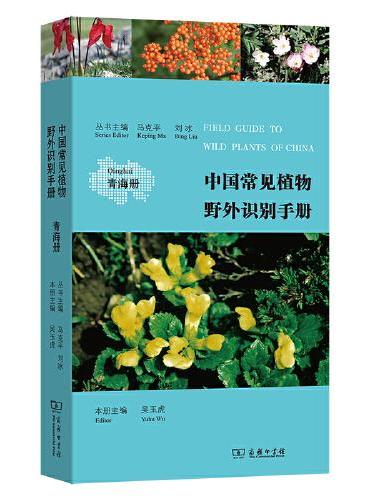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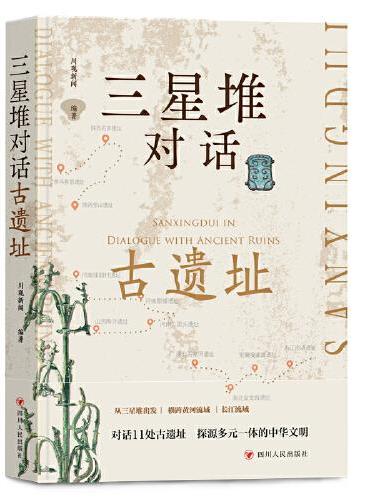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3.4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
卡特里娜(“同一颗星球”丛书)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
最受高中考学生欢迎的作文辅导书,开卷有益的青春文学阅读金库。 全新品质,文字优美,彩图精致,版式活泼。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2014年春节期间举办的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作品集,作为盛开的特色系列,本书均为90后的获奖者,他们用丰富细腻的情感和超强的文字,勾勒出了最独特的青春风貌和青春生活,是可读性非常强的作文学习辅导和课外阅读书籍。
|
| 關於作者: |
主编:方达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杂志主编。现居北京,湖南湘乡人。
|
| 目錄:
|
世事 吊线木偶
看不见的城市 朱聿欣
吊线木偶 黄明星
填涂 张恒立
小丑 徐敏乔
雨打 一城一少年
微光向晚 项若诗
绿皮火车 张子墨
一城一少年 白婷婷
阿奔的故事 琚峰
风若年少的回声 潘云贵
昨年 爸爸的自行车
夜行 谢金辉
爸爸的自行车 王宇昆
平安电台 刘坤
千吉与不死樱 潘嘉敏
老房子 姜羽桐
少年 昼若夜房间
昼若夜房间 徐岳林
你要的生活 程琛
场面中的性情 岳飞雨
逆海漂流 米天逸
我们都被这世界温柔爱着 徐美琳
颛童 亲爱的树小洞
流言 李荣琦
时间记 黄杰
去历险 许畅
亲爱的树小洞 柳敏
农夫的爱情 石梓元
过往 时光深处
背驰 黄萍
丹野的房子 杨欣雨
请在时光深处等我 林丽茹
花吃掉了那女孩 不日远游
|
| 內容試閱:
|
看不见的城市
文朱聿欣
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的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起程
我想我应该醒过来了。墙上钟表的整点报时声在空气中不安地跳动,指针冷漠地停在三十度角的午后,窗外阳光正好。
我看着自己空洞的身形,像一个发炎的腺体,萎靡不振。我能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但并不真切。头顶的天花板,似乎像这座城市的地面一样慢慢沉降,毫无时间概念地向我炫耀生命力。窗外的好阳光被厚重的窗帘肢解,破碎地坠倒在墙角,仿佛被灌进了一整个冬天的黑暗。
我起身,开始走出这一幢白色的建筑。没人发现我的离去,也许是因为我的脚步太过轻盈。离开时我特地回望了这幢白色的建筑,这让我想到卡夫卡笔下的那一座白色城堡。主人公K于深夜踏雪来到它面前,对自己的宿命早已洞若观火,那就是为进入它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陨。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想出去走走。
威尼斯
闹市区。
我的前边走着一个影子。她走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的双脚只能勉强踩中她的头部。
很快熙攘的人群开始拥袭而来,影子像块被殖民的领土,被红色的高跟鞋、白色的运动鞋、黑色的皮鞋占了个严严实实。
我伸出手想拉住她,却只抓到一片空白的酸楚。我张开嘴想叫住她,可声带仿佛粘着在一起,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任由空气分子嘲笑我的无能。
我如此焦虑,只因那个影子,像极了尼斯。
在我十九岁零五个月的那天,我下楼递给尼斯一把蓝色的雨伞,我们的命运就此开始交会。
那一天我看见一场飓风,它像棉被一样被一只巨手牢牢地捂住天空的呼吸,直到疲惫得动弹不得。天色暗得仿佛会一直熄灭下去。我在等待着一场一场迟迟不来的雨,将这个世界的喧嚣与浮躁冲刷殆尽。
“为什么给我伞?”她问。
“也许你需要。”说完这句话我突然觉悟过来,我嘲笑自己的愚蠢,因为在这样的坏天气出门的人不会需要一把伞,正如去投海自杀的人不会需要救生圈一样。
“谢谢,”她接过伞,“其实我在等待一场雨,可惜它迟迟不来,我毫无方向感地乱走,最终来到了这里。”
“我明白这种感觉。自己就像物体一样突然被一只大手拖拽到某个既定的时空,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比你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我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我会问你,为什么等雨。”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需要各种东西来麻痹自己。有的人选择摇滚,有的人选择诗歌,有的人选择毒品,更多的人选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喜欢雨,所以我选择等雨。这不是个好习惯,因为雨总会停,新一轮的等待在主观范畴里开始被无限拉长。你不能相信天气预报,因为它只会过分地关注一场台风、一场寒潮、一场大雪。如果你不想错过每一场雨,你就得学会等待。”她的瞳仁闪过一丝无奈。
我接过她的话把话题继续下去。
“然而,当你已经完全习惯等待时,你会发现任何一场大雨都不能再使你兴奋。漫长的等待已经耗尽了你的激情和梦想,你会自嘲——‘瞧,它终于下起来了,我没有白等!’这时你的关注点已经全都放在了等待本身,雨已经被遗忘在角落,作为客体去凸显等待的价值。是不是?”
她笑了:“你说得很对。我猜你和我一样。”
“哪方面?”
“至少在等雨方面。”
我们俩同时都笑了,不约而同地伸出手。
“我叫尼斯。”
“阿乔。”
我的全名叫马乔,阿乔是我道上的名字。为了生计,我加入了帮派,过了好几年在刀口上混饭的日子。我已经忘记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也从未考虑过要摆脱帮派,我更没幻想过天堂的模样,因为我被困在这个地狱里的时间太长了,长到足以让一只鸟已经习惯甚至离不开一个鸟笼。
那段日子过得很淡,真的很淡,像在云上。我在帮派的火拼中表现突出,光荣负伤,上头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我很满意,我不像别的混混一样渴望在刀光剑影中为自己争得荣耀。
在我闲着的日子里,尼斯每天下午都会出现在我家楼下,顺便给我捎一瓶她最爱的蓝色罐装汽水。然后我们开始交谈。话题时常在变,有时是电影,我喜欢的大卫?芬奇或她喜欢的诺兰;有时是诗歌,我们都喜欢的兰波或我们都不喜欢的顾城;更多的时候是瞎扯,关于人生,未来,还有梦想。
“你以后想做什么?”她有时会这么问我。
“没想好。”
“一辈子打打杀杀?”
“也许三年后我会收山,当个盗版书商人。”
“为什么?”
“身不由己。”
“什么叫‘身不由己’?”
“没办法,这就是我目前浅薄的水平所能设想出的最好的职业了。”
“政府文化部门的那些人很麻烦。”
“没办法,我就是喜欢挑战自我。”
“读者很挑剔,盗版不一定有市场。”
“没办法,以人为本是必须的。”
“盗版行业的人都是蝇营狗苟之辈。”
“没办法,我就当作是与狼共舞。”
“也许你会被其他行业的人看不起。”
“没办法,阶级斗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果你还没实现梦想之前你就死了呢?”
“没办法,到时你得继承我的遗志了。”
“能不能别总说‘没办法’?”
“没办法,人生总是有太多无奈。”
尼斯听完我的回答会笑,但她并不知道,我说了谎。
欺骗别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之一,因为在欺骗别人之前你必须欺骗自己。正如金融诈骗犯坚信自己非法敛财是为了振兴华尔街的股市,出轨的丈夫看着妻子的眼睛信誓旦旦地许下承诺一样,他们都首先欺骗了自己。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挣扎开道德的藩篱,活得更加潇洒,就算只是一时,但为了那一时,失去一世也在所不惜。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知道对于一个混混来说,成为盗版书商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我只是想让自己快乐。
“你的梦想是什么?”有时我会反过来问她。
“去威尼斯看雨。”
“自己?”
“和柏林。加上你也不错。”她的瞳仁里迸发出光彩。
蓝色的水城罩上一层朦胧的雨幕,雨幕下站着她和柏林。
蜿蜒的水巷,醉人的小雨,穿行而过的贡多拉里坐着她和柏林。
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雨水打在窗台发出游吟诗人般的低诉,屋子里坐着她和柏林。
而在我的所有的想象中,这些场景里是不会有我的。我从没主动问过她柏林是谁,说我天性淡漠也好,我只是坚信每个人的背上都会有一个沉重的故事,它们总是需要通过一种方式卸下,遗忘或死亡都是不错的方法。我很少向别人提起我的故事,我也从不对别人的故事发表任何看法。在这个人世,我们降临和离去的时候都是孑然一人,一个行人要让自己的步伐轻快只能卸掉自己的行囊,那些行囊就是回忆。
但人有时候是矛盾的。我时常会禁不住想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无须在那个夜晚热血沸腾地递给尼斯那一把伞……如果有结果,也不会有结果。
都柏林
当我正纠结于回忆中的问题时,一阵晃眼的白色车灯穿透了我。这种感觉很熟悉,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曝了光的底片。柏林每一次注视我时,我都会这种感觉,一次比一次更强烈。
遇见尼斯的两个月后,柏林和尼斯一起出现在我家楼下。他摘下白色的耳机,我能听出那是Radiohead 的high and dry。我永远都忘不了他打量我时的眼神,瞳仁里发出的光是警觉的,只一瞬,我似乎已被完全看透。
他跟我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如果说我的性格是外热内冷的话,那他的就是外冷内热,就像那座终年被灰蒙蒙的大雾和哥特式教堂遮蔽住天空却暗涌着反抗激情的城市都柏林。乔伊斯写过一本小说集叫《都柏林人》,我没看过,但我猜想里边的人就如同他一样,高贵而又自负,以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我以为有一些人永远都不会嫉妒,因为他们什么都有,太过于骄傲。
《追忆似水年华》里有这么一句话,当现实翻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自那一次见面后柏林就没有再出现过,但他的名字却频繁地出现在我和尼斯每天的对话中。他们为争论一首歌的歌词吵架,为喝不喝蓝山咖啡吵架,为卡尔维诺是意大利还是土耳其人吵架。尼斯清楚地记得与他吵架的次数,却早已忘记了两人一起去威尼斯的梦想。
我第二次见到柏林时是在一个阴郁的黄昏,夜的黑暗和夕阳特有的橘黄交织在一起,风敲击着玻璃窗像是乌鸦的呜咽。
“这是一座很奇怪的城市,大风阴天连连,却总是没有雨。是不是?”他问我。
“这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
“它太压抑,就像你和我。喜欢不能假装,讨厌不能隐藏,把感情埋得太深有时不是一件好事。”他冷峻的眼神仿佛要把我洞穿。
“你到底想说什么?”
“离开尼斯。”
“你在拍苦情剧吗?”
“我们吵架的根源其实是你。她把你当朋友,可也许你并不是。你只是一个在刀刃中混得一份温饱的人,终究会给她带来伤害。”
“不行,你这是职业歧视。”我笑了。
“如果我求你呢?”
“还是不行。爱情给人自由感,而不是囚禁感。如果你爱她,就不应干涉她交朋友。”
“那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消失?”
“怎么做都不行。”
然后我便转身走了,我怕我再多说一句就会完全暴露。他望着我的背影,满脸的惆怅与茫然,若有所思地停在原地,仿佛前方是都柏林茫茫的雾,已经无路可走。在爱情面前,他终究是骄傲不起来了。曾经有个兄弟对我说过,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失败,是因为他太过于爱她们。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始终没有告诉柏林,尼斯之于我就如同一块浮木之于一个落水的人,我之所以紧紧地抓住她,是因为我不想溺死。我曾在无数个午夜失眠,设想着向尼斯开启心门。当然,也永远只是设想。
我的十九岁属于风声,属于这座城市迟迟不至的雨季,找不到鸽子,找不到南方,找不到温暖。我没有家,只有一个还算健全的身体,也许我会在某次血拼之后丢失掉它,终究成为一个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
在我快要一无所有的时候,出现了尼斯,于是我紧紧地抓住她,像落水的人抓着一块浮木,像地衣附着着苔藓,像藤蔓攀缘着玫瑰花的窗台。
我需要她,或许,我是喜欢她,就像乌兰喜欢我那样。
乌兰巴托
我漫无目的地一边回忆一边行走,直到人群散去,暮色降临。我最终停在了一家便利店的门口,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行人撑开了五颜六色的伞,像一条条热带鱼在霓虹灯里穿梭。
曾经有个姑娘给我写过这样一首情诗,诗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我思念你在这个城市像飞鸟留恋灰蓝的天空像热带鱼思念霓虹的海洋。
以前我觉得这个句子平淡无奇,如今看到这个场景,我才觉得它好美。给我写这首诗的姑娘叫乌兰。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赢,但是我很清楚,从一开始,她就输了。
在我十九岁九个月的某一天,柏林留下一封诀别信,去了谁也不知道的远方。尼斯给的解释是,他们在一次大吵后分手了。我因为尼斯的消沉而情绪低落,在那段日子里,乌兰出现了。
我和她的相遇总让我想到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厘米(我在大街上扶住了快要摔倒的她),57个小时之后,她通过某种途径搬到了我隔壁的空房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开始她给我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我很少拆开来读,只是把它们都收好。爱情最大的缺点是它的自私,当你不爱一个人时,不爱就是不爱,是任何理由都解释不清楚的。况且对我这样一个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混混而言,爱情显得太过奢侈。我打算永远只和她做朋友,她明白我的想法,慢慢和我像朋友般相处。
乌兰是个热情的姑娘,她的名字总是让我想到中亚的一座城市。根据乌兰的说法,这个名字是她的父母为了纪念他们在乌兰巴托相识。我嘲笑她说,这城市名的开头跟你家的姓一样,你父母可真省心,我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以后我生女儿就叫马尼拉,生儿子就叫马德里,然后我要带我的孩子去马尼拉或马德里旅游,听无数的游客说,啊,马尼拉好漂亮,马德里好漂亮。
乌兰和尼斯通过我的关系熟了起来。我们三个人时常厮混在一起,这种关系很微妙,但说穿了无非就是爱与被爱的关于青春的陈词滥调。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我甚至开始尝试摆脱帮派去找份正经工作。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停在这里也许是最好不过了,但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苦。
在我二十岁那一天,我们三个在一家小饭馆里庆祝我的生日,突然间很多人都涌了进来,他们朝我走来。我意识到不妙,一把拉起尼斯和乌兰的手开始往后门冲,到门口的时候我把她们推了出去。
“快跑!”这就是我跟她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看到她们的瞳仁里充满了绝望,那是一种眼泪都不足以象征的悲哀。
我死死地守住这个门,昏黄的灯光反射在刀刃上晃到了我的眼,我在慌乱中竟忘记了反抗。透过围攻我的人墙,我看到一个眼神,那个眼神我一辈子忘不掉,是柏林的眼神。
小时候看《东方不败》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在倒地前,我看着柏林的眼神,那一刻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我永远都无法退出这个江湖;第二,嫉妒能把人的理智浇灭。
归途
小雨过后气温开始转凉,于是我走进便利店寻求温暖。走过自动贩卖机时,我看到玻璃门上没有我的影子。我试图向前台的售货员打听一个爱买蓝色汽水的女孩,可我依旧发不出任何声音。
因为我只是一具灵魂,慢慢虚弱慢慢消失的灵魂。
今天当我重新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一幢白色建筑里,我对它太过熟悉了,它的名字叫医院。医生和死神斗争了三天三夜,还是没能把我救回来。我青春的躯壳,永远地留在那个充斥福尔马林药水的地方,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送进的医院,饭店老板娘?围观的食客?我更愿意相信是柏林。我也不知道尼斯和乌兰去了哪儿,或许她们现在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我脱离危险的喜讯,或许她们以为我跑路了,或许她们已经知晓我死于非命。
有时候,爱上一部电影不是因为里面的主演,不是因为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有那么一句话,在主人公说出口后的片刻,击中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电影《蓝宇》里陈捍东说,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那时蓝宇反驳道,没完,留下的记忆还没完呢。
威尼斯、都柏林、乌兰巴托,在这些看不见的城市里,我以青春为筹码去交易了一段回忆。小王子的星球每天有四十三次日落,可我的青春只有一次,所以我只能交易一次。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赔了还是赚了,我只是我希望不久之后市面上会出现一本很畅销的盗版书,书的卷首语会写着——
我思念你
在这个城市
像飞鸟留恋灰蓝的天空
像热带鱼思念霓虹的海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