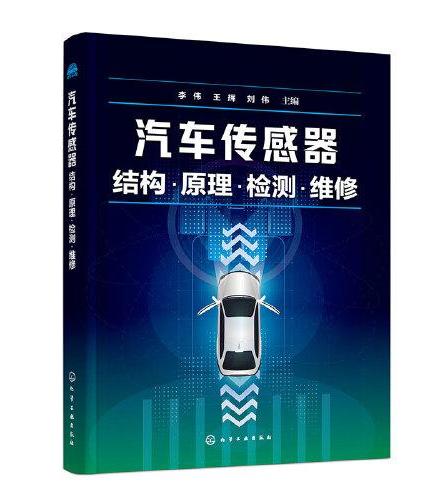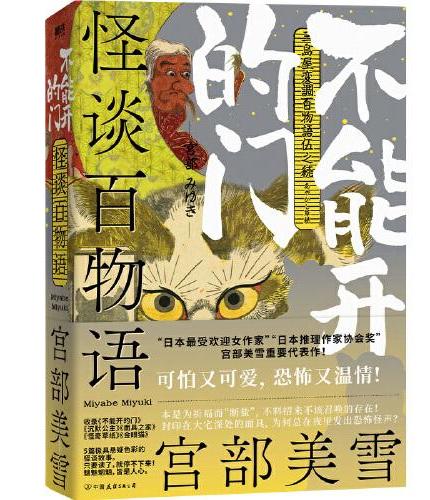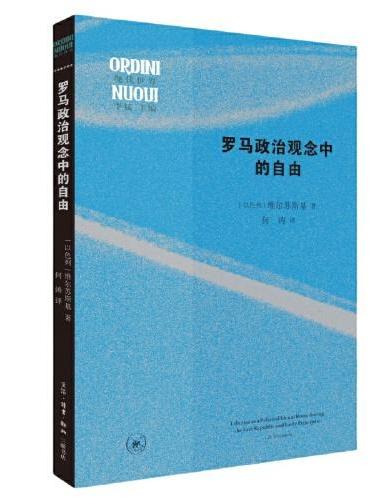沼泽大逃亡
月底的时候, 坦纳不再需要我, 我又被送回河口主人那里, 他正忙着制作轧棉机。 轧棉坊离大宅有一段距离, 是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我又开始为提贝茨干活,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得和他单独相处。我牢记查普林的叮嘱, 小心提防他找机会伤害我。 所以整日处于猜疑和恐惧之中。 我一边干活, 一边盯着主人。 我决心不给他任何借口找我麻烦, 更加勤奋地干活, 甚至比以前还要勤快; 只要他不伤害我, 我会谦卑地、 耐着性子忍受他对我的辱骂, 希望这样能缓和一些他对我的态度, 直到迎来我从他手中解脱的幸福时刻。
我回来后的第三天早上, 查普林出门去切尔维尼, 晚上才能回来。 碰巧那天早上提贝茨的坏脾气又发作了, 比往常更难伺候, 更加恶毒。大概上午九点钟, 我正忙着用刨子刨平一个板面。 提贝茨站在工作台旁边, 正在给一个凿子安装刚刚刻好的螺纹手柄。
“你刨得还不够平。”他说。
“刚好和线平行啊。”我回答说。
“你这个骗子。”他激动地大叫。
“哦, 好吧, 老爷, 我温和地说, “我会按照您说的继续刨平它,说着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还没等我刨完第一下, 他又开始大叫, 说我刨得太深, 板面这么轻薄, 我把整个板子都给刨坏了。
随后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我是完全按他的指示认真去做的, 却怎么也不能让这个蛮不讲理的人感到满意。 我沉默不语, 胆战心惊地站在板子旁边, 手里拿着刨子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又不敢什么都不干。他的怒火越烧越旺, 最后他大声诅咒我, 估计也只有提贝茨能骂出如此恶毒、 可怕的话。 他抓起工作台上的斧子朝我扑过来, 大骂着要砍掉我的脑袋。
这真是生死关头。 明亮锋利的斧刃在阳光下闪着光芒, 也许下一秒就劈进了我的脑袋, 就在那一秒———在如此惊恐的困境, 人的思维反应速度相当快———我心里盘算着, 要是站着不动, 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 要是我跑, 十有八九他手中飞出的斧子会不偏不倚地砍在我的后背上。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用尽全力跳了起来, 在斧子落下之前先一只手抓住了他举起的胳膊, 另一只手扣住他的喉咙。我们俩四目相对地站着, 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杀气。 我感觉脖子上有条毒蛇, 死死地盯着我, 只要我稍微放松, 就会立刻缠在我身上,越缠越紧, 直到把我勒死为止。 我想大声呼救, 希望有人能听到———但是查普林不在园中; 奴隶都去了田里干活儿; 没有人能看见或者听见我们。一直以来, 凭借机智的头脑, 我一次次从暴力手中逃脱; 这时我又急中生智, 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猛然用力一踢, 他惨叫一声,单膝跪倒在地, 我松开他的喉咙, 抓起斧子, 远远地扔出去。他气得发了疯, 抓起地上一根白橡树棍子。 那棍子大概有五英尺长, 一只手能握住那么粗。 他又一次冲向我, 我也迎上去, 因为我比他强壮, 我把他拦腰撂倒在地。 我趁势夺了棒子, 起身把它扔了出去。他也爬了起来, 跑到工作台去拿板斧。 不巧的是, 板斧上压着一块重木板, 这样他就没法一下子把它抽出来。 我纵身一跃, 跳到他身后, 把他紧紧压在木板上, 这样板斧就被压在原地, 纹丝不动。他的手紧紧抓住斧柄, 我试着掰开他的手却没有成功, 我们俩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
在我不幸的一生中,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 死亡是尘世忧愁的终结, 坟墓是倦体残躯的休憩之地。 但这些想法在危难关头就会消失不见。 没有哪个身强力壮的人能在死神这个“恐惧之王面前还能保持不卑不惧。 生命对每一个生物都是宝贵的; 即使是钻出泥土的蝼蚁也会努力生存下去。 在那一刻, 生命对我来说是可贵的, 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 哪怕是遭受这样的虐待。没能松开他的手, 我又一把锁住他的喉咙, 这时他虎钳般紧扣的手很快松开了。 他开始变得顺从, 也松懈下来。 刚才他的脸由于愤怒变得惨白, 现在因为窒息开始发青。 那两只像毒蛇一般喷射毒液的小眼睛里布满了恐惧———两只大大的白眼球快要被挤出眼眶!
我心底“潜伏的恶魔诱使我当场杀了这个恶人, 紧紧抓住那可憎的喉咙直到他一命呜呼! 可我不敢杀死他, 也不敢让他活下去。要是我杀了他, 我就得偿命; 要是让他活, 他迟早会报仇要了我的命。 心底的声音悄悄对我说, 逃吧! 哪怕成为一个沼泽游荡者, 一个漂泊逃亡的人, 也比现在的生活强得多。我很快下定决心, 把他从工作台拽倒在地上, 我越过附近的篱笆, 急忙穿过种植园, 穿过棉花地里干活的奴隶们。 跑了四分之一英里, 我来到了丛林牧场, 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穿过牧场。 爬上高高的篱笆墙, 我能看见轧棉坊、 大宅以及中间的空地。 这是一个显眼的位置, 整个种植园可以尽收眼底。 我看见提贝茨穿过田地回到大宅, 然后又拿着马鞍出来, 转眼间跳上马, 飞奔而去。
我感到孤独凄凉, 却又心怀感激。 感谢我的性命得以保全, 又为前途感到凄凉、 沮丧。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谁又能帮助我呢? 我应该逃到哪里? 哦, 上帝! 你给了我生命, 又在我的胸膛里注满对生命的热爱, 你用所有人同样的情感将它填满, 造物主, 请不要放弃我。 可怜可怜我这个奴隶吧———不要让我死去。 倘若你不保护我,我一定会迷失———迷失! 这些无声的恳求从心底升向上苍。 然而没有回应———没有甜美、 低柔的声音从天空降落, 悄悄地对我的灵魂低语, “我与你同在, 不要害怕。冶 看来, 我成了被上帝抛弃的人———受人鄙视和仇恨的人!
大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看见几个奴隶喊叫着, 做手势让我逃走。不一会儿, 我看到河口那里, 提贝茨和另外两个人骑在马上, 飞奔而来, 身后跟着一群狗, 大概有八到十只。 即使离得这么远, 我也知道这些狗的来历。 它们是邻家种植园主的狗群。 在贝夫河区域用来追捕奴隶的狗是一种猎狗, 但远比北方各州的猎狗更加凶残野蛮。它们会在主人的命令下攻击黑人, 紧紧咬住不放, 就像斗牛犬紧紧咬住其他四足动物一样。 在沼泽里常能听见狗吠声, 人们就会猜测逃跑的奴隶会在什么地方被猎狗追上———就像纽约狩猎者会停下来,听听猎狗在山坡上的叫声, 以此为依据向同伴预测哪里能打到狐狸。我从没听说过有奴隶能活着从贝夫河逃出去。 原因之一是奴隶被禁止学习游泳技能, 就连最小的溪流他们也无法穿过。 逃跑时, 不管往哪个方向跑, 跑不了多远就到了贝夫河边, 他们的命运就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被淹死, 要么被狗群赶上。 年轻时, 我曾在家乡的河流里练习游泳, 并锻炼成了游泳高手, 在河里我可是如鱼得水。我站在篱笆墙上看着狗群跑到轧棉坊。 一秒之后, 它们发出长长的嚎叫, 说明它们已经凭气味找到了我的足迹。 我跳下篱笆, 向沼泽跑去。 恐惧给了我力量, 让我发挥到了极致。 每隔几分钟我就能听到狗群的吠声。 它们快追上我了, 狗吠声离我越来越近。 我时刻感觉它们要跳起来扑到我背上———那长长的利牙深深咬入我的皮肉里。 狗群数量很大, 我知道它们会把我撕成碎片, 让我一命呜呼。我气喘吁吁, 断断续续地说出半句祷告, 祈求全能的上帝解救我———给我力量让我跑到宽阔的河口深处, 这样我就可以摆脱它们的追踪, 或者潜进水里。 一会儿, 我来到了一片茂密的蒲葵林。 我在里面穿梭, 发出了很大摩擦的声响, 但还是能听见狗吠声。我继续向南奔跑, 据我判断, 自己已经跑进一片没过鞋面的水域。 那时, 猎狗离我大概不出五杆远。 我能听到它们在蒲葵林里冲来撞去的声响, 整个沼泽回荡着它们激烈而高亢的叫声。 我跑到水边, 情势似乎好转, 给我带来了一些希望。 要是水更深一些, 狗群就闻不到我的气味, 一定会变得惊慌混乱, 我就可以趁机避开它们。幸运的是, 我越往前走, 水就越来越深———漫过我的脚踝———又漫过小腿肚———有时还能没过我的腰部, 但转眼间又变得很浅。 从我下水以后, 狗群就追不上我了。 很显然, 水流带走了气味, 它们迷失了追踪的方向。 现在它们疯狂的叫声离得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明白自己已经摆脱了它们。 最后, 我停下来侧耳倾听, 听见长长的狗吠声再一次冲上天空, 这说明我还没有彻底安全。 虽然河水冲淡了我的气味, 但是走过一个又一个泥塘, 猎狗还是能够跟上我的足迹。最终, 我来到了宽阔的河口, 这让我喜出望外。 我一头扎进河里,逆流缓缓而上, 游到对岸。 这样, 狗群一定会被搞糊涂的———水流带着那轻微、 神秘的气味顺流而下, 没有逃亡者的气息, 这些嗅觉灵敏的猎狗也无能为力。
穿越了河口, 水变得太深, 让我没法再往前跑。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自己身处佩克德里大沼泽之中。 这里长满各种树木———无花果树、 橡胶树、 木棉树和柏树, 而且据我所知, 沼泽一直延伸到卡尔克苏河。 我走了三四十英里地, 沼泽里人迹罕至, 只有野生动物———熊、 野猫、 老虎, 还有很多巨大、 黏滑的爬行动物。 早在我到达河口之前, 事实上, 从我来到水边直到后来从沼泽林里出来,这些爬行动物就一直在我周围。 我曾看到过几百条水栖蝮蛇。 每一棵树, 每一个泥塘, 每一截枯树的树干, 都爬满了这种蛇, 有时我不得不从这些地方走过或爬过。 当我靠近时, 它们就爬走了。 但有时我比较着急, 几乎用手或脚从它们身上爬过、 踩过。 它们是毒蛇———毒液甚至比响尾蛇还要致命。 除此以外, 我还跑丢了一只鞋,另一只鞋已经完全裂开, 只剩鞋帮吊在我的脚腕上。我还见到很多大大小小的鳄鱼, 有的躺在水里, 有的趴在浮木上。 它们常常被我的声响惊动, 之后便爬走或是跳进最深的水里。但有的时候, 因为没看见, 我也会冒失地撞上这些怪物。 这时候我会拔腿就往回跑, 绕着跑上一段路程, 这样就能避开它们。 它们会迅速地追赶一会儿, 但只是顺着直线追赶, 并不敢转弯。 作为能弯曲和下蹲的人类, 躲开它们并不是难事。大概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听见狗叫声。 它们很可能没能穿过河口。 我浑身湿透, 虚弱无力, 但是暂时脱离了险境。我继续向前走着, 却更加小心翼翼, 开始害怕之前见到的蛇和鳄鱼了。 现在, 在踏入泥塘之前, 我都会用棍子试探一下塘里的水。 要是水面有动静, 我就绕行; 要是水面静止不动, 我就冒险蹚水过去。太阳终于落山了, 夜幕渐渐笼罩了大沼泽地。 我继续蹒跚前行,时刻担心被腹蛇咬一口, 或者惊动鳄鱼被一口吞下。 这种恐惧几乎和对猎狗的畏惧不相上下。 过了一会儿, 月亮升起来了, 柔和的月光爬上四散的枝杈, 枝杈上悬着长长的苔藓。 我一直走到后半夜,一直希望能走进一片不那么荒凉、 危险的地域。 但是水越来越深,行走变得十分困难, 我觉得没法再往前走了, 更不知道要是顺利走到有人的地方, 我又会落入谁的手中。 我没有路条, 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逮捕我, 把我投进监狱, 直到我的主人“证明他的财产, 付清罚款, 然后把我带走。冶 我是走失的奴隶, 要是我不幸碰到一位守法的路易斯安那州公民, 他会认为马上把我投进监牢是为邻人尽义务。 天呐, 很难决定自己最该害怕什么———猎狗、 鳄鱼还是人!
午夜过后, 我停了下来。 眼前这瘆人的场面让人无法想象。 沼泽里回响着无数野鸭的叫声! 自从大地形成以来, 很可能人类的足迹还没有踏入这深深的沼泽腹地。 此时, 周围并不是一片沉寂———但黑夜里这些声音倒让人觉得压抑———就像是太阳当空照耀的白昼一般。 半夜里我的脚步声惊醒了鸭群, 成百上千的野鸭挤作一团,聚集在沼泽里, 不断发出杂乱的叫声———四处是拍打翅膀的声音———从我身边沉闷地跳入水中的声音———一时之间让我又惊又怕。各种飞禽, 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走兽似乎全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让这里充满了聒噪和喧哗。 并非只有人类的处所和拥挤的都市才会有生命的景象和声音。 哪怕是在阴沉的沼泽腹地, 上帝也为成千上万的生物提供了避难之所和栖居之地。
月亮已经升上了树梢, 我想到了新的计划。 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尽全力向南前进。 接下来, 我决定要转向西北方向, 目标是抵达福特老爷家附近的大松树林。 只要在他的庇护之下, 我会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我的衣服破烂不堪, 双手、 面颊和身上布满擦痕, 全被锋利的枯树枝、 灌木丛和浮木划伤了。 我光着脚走路, 脚上扎得到处是刺。我浑身上下都是污迹和烂泥, 还有死水上漂浮的绿色粘液———这几天我不分白天黑夜, 几次浸泡在漫到脖子的死水潭里, 所以沾上了这些东西。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我一直向西北方向跋涉, 早已疲惫不堪。 渐渐地, 水越来越浅, 脚下的土地也越来越坚实, 终于,我走到了佩克德里, 就是之前我在沼泽外面游过的那条宽阔的河流。我游了过去, 不一会儿好像听到一声鸡叫, 但是声音很微弱, 像是幻听。 随着我前进的步伐, 水也渐渐退去。 此刻我已经穿过了沼泽,站在干燥的地面上。 地形渐渐上升形成平原, 我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大松树林”。
天刚破晓, 我就来到一片开阔地———像是一个小的种植园———但是我以前从没见过。 在树林边缘, 我碰见两个男人———一个奴隶和他年轻的主人, 他们正在抓捕野猪。 我知道白人会要求我出示路条, 要是我拿不出, 他一定会把我抓住。 我当时太累了根本跑不动,而且坚决不愿被抓到, 因此, 我想出了一个成功的计策, 而且事实证明相当奏效。 我装出一副凶狠的表情, 径直朝他走去, 死死地盯着他。 看着我走上前, 他吓了一跳, 向后退了几步。 很显然, 他被我吓坏了———他惊恐地看着我, 就像看见刚从沼泽腹地爬出来的妖怪。
“威廉·福特住在哪儿?” 我粗声粗气地问他。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有七英里远。冶 他回答说。
“去他家怎么走?冶 我又问道, 装出比刚才还要凶狠的表情。
“看到那边的两棵松树了吗?”他边说边指着一英里外高高耸立的两棵松树, 它们远比其他松树高, 就像两个哨兵俯视着广袤的森林。
“我看见了。” 我说。
“在那两棵松树下,”他继续说, “就是德州公路。 向左转, 一直走就到威廉·福特家了。”
我没再继续说什么, 急忙向前赶路; 他也很开心, 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 走到德州公路, 我按照他的话左转, 路过一堆燃烧的原木。 我走过去, 想把衣服烘干; 但是清晨灰暗的光线很快就会消散, ———一些路过的白人可能会看到我; 此外, 篝火的温暖让我昏昏欲睡。 因此, 我没有停留, 继续上路。 终于, 在八点的时候, 走到了福特主人的宅子。奴隶全都离开住处下地干活了。 走到走廊上, 我敲了敲门。 很快, 福特太太开了门。 我当时完全变了样———衣衫褴褛、 狼狈不堪,她竟然没认出我来。 我问福特老爷是否在家, 还没等她回答, 善良的福特老爷就走了出来。 我告诉他逃亡的事情, 还有所有相关的细节。 他认真地听我讲着, 等我讲完后, 他还亲切怜悯地和我说话,又带我到厨房, 叫约翰为我准备食物。 自打昨天早上起, 我就没有吃过东西。约翰把早餐摆在我面前, 女主人又端来一碗牛奶和许多美味的点心, 这可是奴隶很少尝到的美味啊。 我又饿又累, 但食物和休憩都比不上那和蔼的声音和宽慰人心的话语, 哪怕一半也比不上。 对这个衣衫褴褛、 性命堪忧的奴隶来说, 这是大松树林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冶 倾注到他受伤的灵魂中的香油和美酒!他们把我留在木屋, 要我在那里休息。 安心地入睡! 梦境如期而至, 仿佛天空普降的甘露, 不管你是自由之身还是被缚之人。 很快, 它钻进我的胸膛, 赶走一切烦恼和忧愁, 带我来到那梦幻之境,在那里, 我再一次看见孩子们可爱的面庞, 聆听他们的声音。 唉,当我醒着的时候, 也许他们已经在另一个怀抱里熟睡, 而且永远不会被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