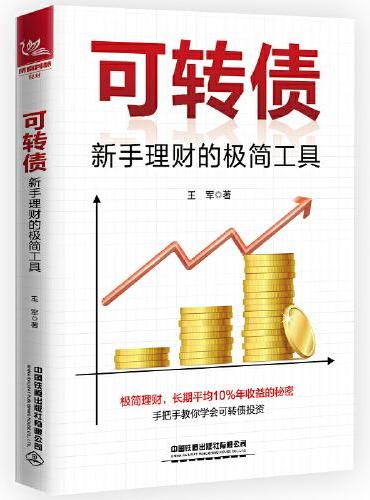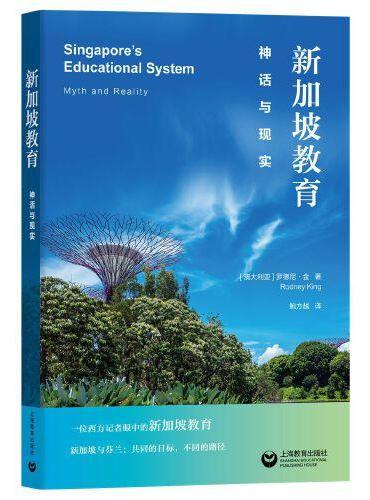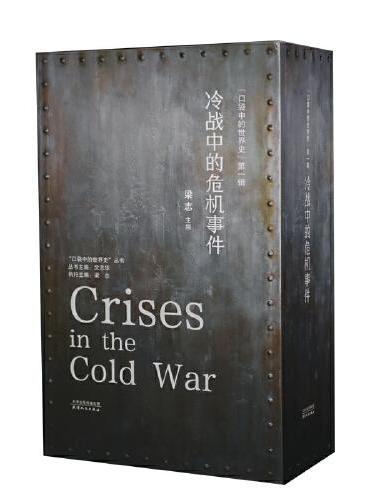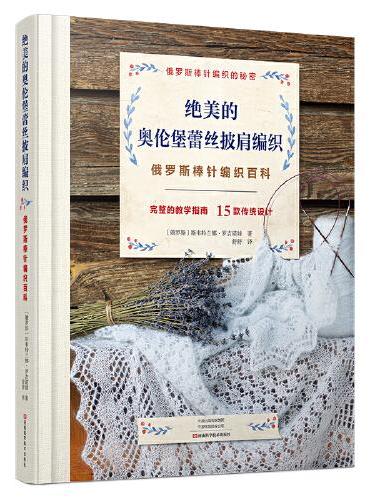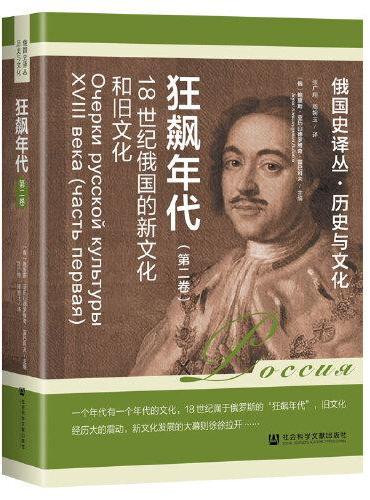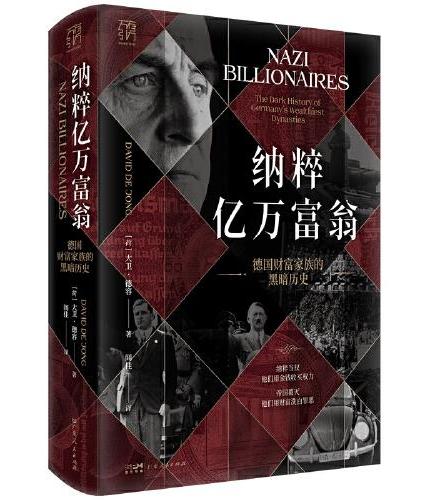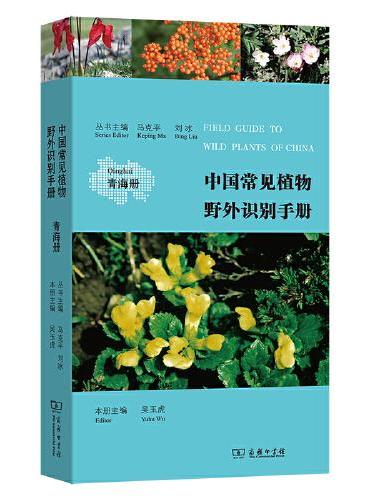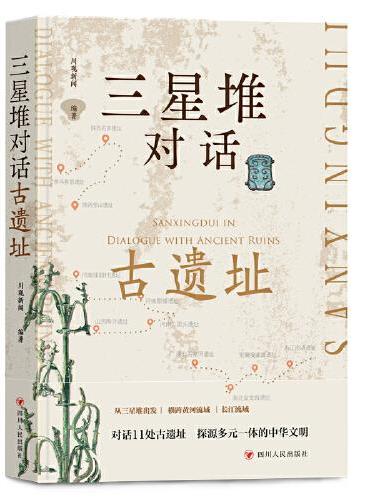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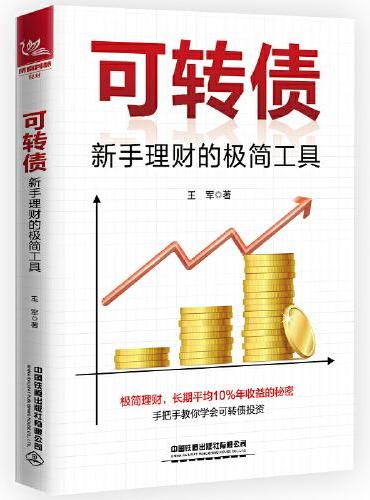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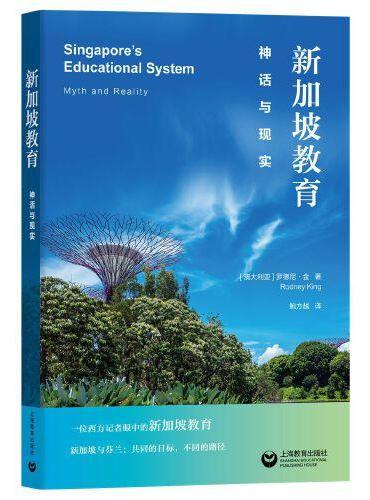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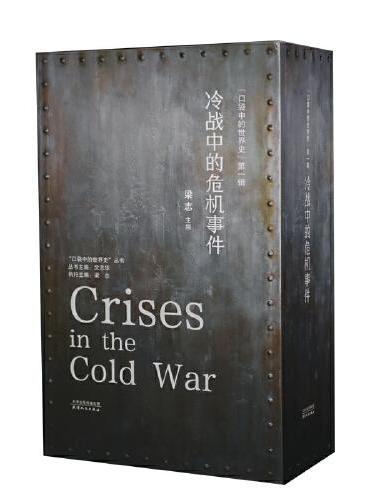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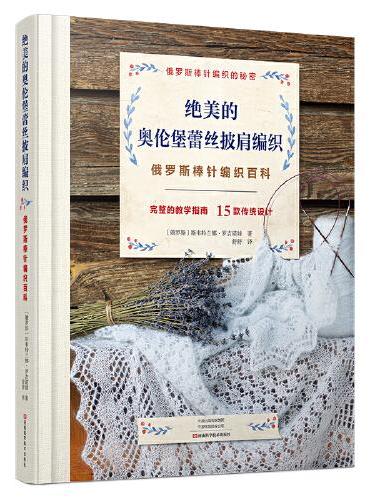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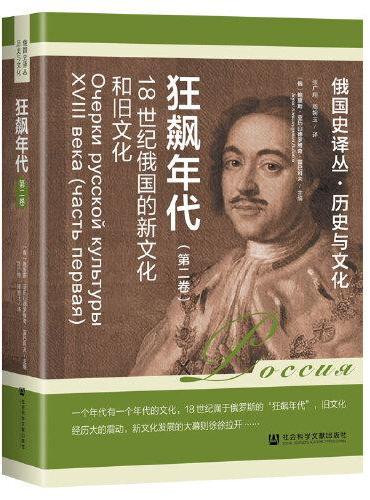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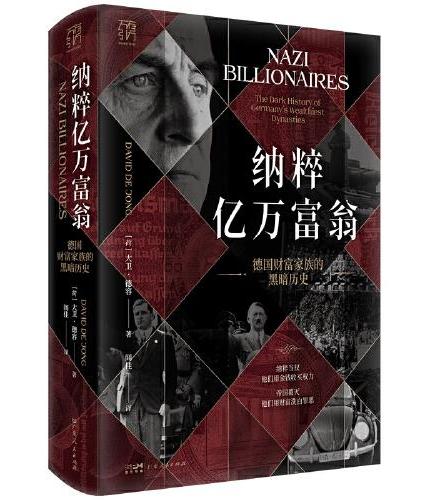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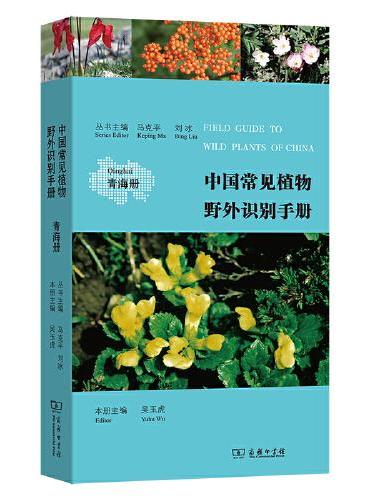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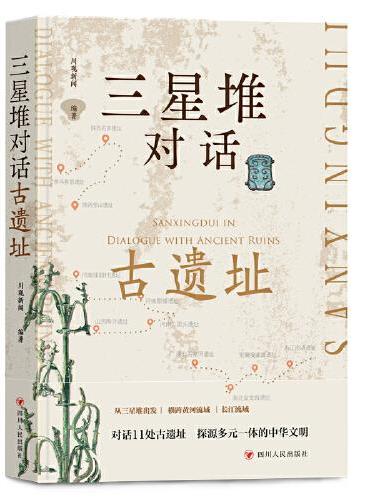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对中国学生而言,这是一场新的西学东渐。——姬十三,果壳网CEO
★ 全球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科教育不断滑坡,研究生学费节节攀升。与此同时,在线教育风起云涌,互联网技术令人眩目。
★ 在美国,140所高校提供MOOC课程;在中国,6700万学子走进数字课堂。国内外MOOC平台及公开课井喷式增长,拆掉“常春藤”的围墙,互联网重新定义学校和课堂。
★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威廉·G.鲍恩,凭借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和翔实的数据,探寻MOOC如何打破精英的知识垄断,治愈高等教育的痼疾,再掀一场学习的革命!
★ 姬十三作序推荐,一笔写透教育的未来!
★ 本书入围2013年美国专业与学术杰出出版奖(The PROSE Awards)。
|
| 內容簡介: |
《数字时代的大学》是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威廉·G.鲍恩对在线教育的一次深刻剖析。
在线教育迅猛扩张,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MOOC)颠覆课堂。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批量生产到个性定制。当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互联网,我们能否实现“有教无类”的理想?
威廉·G. 鲍恩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权威专家。在书中他立足美国精英学府,探讨互联网技术何以提高生产率,控制成本增长,同时保证教学质量,维护教育的核心价值。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坦纳人类价值讲座”的演讲稿,还包括四篇评述文,分别出自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尔德·加德纳,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以及Coursera联合创始人达芙妮·科勒。
数字时代的大学,激发每个人最大的学习潜能,拆掉常春藤的围墙。
|
| 關於作者: |
威廉·G.鲍恩(William
G. Bowen)是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前会长、非营利性学术组织ITHAKA创始人。著有多本畅销书:《河流的形状:高校招生时考虑种族背景将造成的长期影响》(获格文美尔教育奖)《跨越毕业线:从美国公立大学毕业》《历史的教训:一名大学校长的反思》
2012年,奥巴马总统亲自为鲍恩校长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
| 目錄:
|
推荐序 一场史无前例的“数字海啸”(尚俊杰,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
推荐序 一种新的西学东渐(姬十三,果壳网CEO)
前言
第一部分 高等教育的成本与生产率
成本趋势、成本病和高等教育的生产率
推高教育成本的其他因素
经济负担能力
问题严重吗
第二部分 通过在线教育解决问题的前景
背景
缺乏有力的证据
需要可订制、可持续的平台
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们必须保留什么
附录:在线教育现状
评述
致谢
|
| 內容試閱:
|
同样的话。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的评述
大约55年前,福特基金会就新技术改进高等教育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当时讨论的新技术是电视。它的潜力与今天互联网的潜力非常相似,“这种新技术,”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将让优秀教师的教育惠及更多的学生,”并将教授从“学期复学期的复述式机械教学”中解脱出来,从而“改善并提高教学质量”。换言之,这里的电视授课,是当前所谓“翻转课堂”的早期版本。它的理念是,由才华横溢的讲师通过电视广播传授入门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对老师来说重复乏味,却又是学生必需的——并将面授课堂留给高阶的教学活动。根据那份报告,这项新技术有望实现诸多前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它将把高校从呈螺旋式上升的成本增长循环中解救出来。20世纪60年代初,成本增长问题就已经很显著了。
现在,这些前景一个都没有兑现,原因显而易见:当时的技术根本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与我们现在的技术相比,电视太初级、太简单了。它无法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无法实现学生之间的对话——我喜欢将后者称为横向学习。今天,人们用一模一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早期用互联网来转变高等教育的尝试会惨遭失败。以我自己的学校为例,大约15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Fathom.com,希望这所网络公司能够盈利,以缩小我们与那些有更多捐赠收入的竞争者在财源上的差距。但在这次努力失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年轻女校友泰勒?沃尔什做了相关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作品《大门敞开:顶尖大学如何及为何开放本校课程》。她在这本书中引用了Fathom项目其中一位负责人的解释:“那时,我们没有宽带、视频、iPod等技术。”依我看,现在这种解释有点说不通,总有些东西是我们当下无法拥有的。今天真正的问题是,试了那么多次错,我们是否终于有能力实现这个被延迟了的梦想:通过技术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著名的鲍莫尔-鲍恩理论分析了成本病的根源,它拿教授和音乐家做了类比。他提醒我们,今天4名弦乐乐师完成贝多芬弦乐四重奏所需的时间,与这个作品19世纪刚诞生时4名弦乐乐师完成演奏所需的时间是一样的。与教学和学习一样,创作音乐也不是一个能清楚地解释效率或生产率提高的领域。我们并不清楚这样一种提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鲍恩的演讲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一位科学老师的预言,尽管当时是在1968年前后,是个敢于梦想的时代,但那个预言听来还是太异想天开、荒诞离奇了。那位老师说:“看着吧,不用多久,你们不需要亲自去卡内基音乐厅付钱买门票,就能听到某个未来的海菲茨或奥依斯特拉赫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计算机时代刚刚开始,没人听说过个人电脑这种东西,更别说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了。但他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种相对便宜的技术,能复制出最伟大音乐家用最棒的乐器演奏出的声音。大师现场表演这一概念会被淘汰,我们将在家中享受到卡内基音乐厅水准的音乐——减去了成本,也免去了旁边观众的咳嗽声。虽然我老师45年前的预言还未完全成真,但我们已非常接近了。
回到教育领域,且让我们假设,现在至少能够想象会有某种技术补救方案出现——我们将会拥有一种新的工具,即使无法根治,也能够缓解高成本、低效率这两个慢性病。这种未来虽并非近在咫尺,但我们也许已足够靠近,能够一瞥它将带来什么,它将意味着什么。亨尼斯校长告诉我们,它来临时,一定带着海啸般的威力。这是一个有趣的隐喻,因为据我所知,海啸的影响极具破坏性,该隐喻与在线运动倡导者,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说法一致,他称其为“破坏性创新”——这种说法源自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描述——资本主义是持续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从这些预测来看,似乎我们应该自问,什么将被破坏或摧毁,什么将被创立或创造?
就算无法彻底摧毁成本病,能够对其构成破坏也是极好的。我对许多教学人员的深度参与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在努力利用新技术实现目的。我还感觉到了他们真诚的信仰,坚信技术会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坚信技术不仅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经历,还能通过“混合”教育的形式改进传统教育方式。
与此同时,对亨尼斯校长的隐喻再做考虑,我们似乎应该明白,海啸并不完全因其选择性而出名。它们对于要冲走的事物不加选择。所以,除了成本病以外,我还想提另外两件也正处于被破坏或被摧毁的危险之中的事物。
第一件也许已极其明显了:教学人员正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率地谈论这一危险的严重性与急迫性。亨尼斯校长公正地断言,我们必须接受教学人员数量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下降这一事实。几个月之前,我在与此次研讨会有几分类似的一次聚会上听到了更直截了当的评价,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长保罗·勒布朗说,新技术给教学人员带来的恰恰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顺带一提,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已坚定地迈入了在线教育领域。
我认为他是对的。原因之一是,新技术很可能将严重扩大高校之间的分化以及高校内部教学人员的分化。教学人员也很有可能会加快向体制外的附属关系转移——该过程自19世纪末学科专业化时就已经开始,当时教学人员开始认为自己不是当地高校群体的成员,而是分布在不同地方的专业人士,首先忠于自身的学科。从许多方面来看,教员文化的这种发展是件好事。它减少了地方主义、半吊子作风和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的现象,但也播下了名师制度的种子。这一制度没有为“当地”教授创造机会,反而为经常往返于罗根机场、经常缺席的“罗根”教授们创造了机会。到20世纪中期,这一制度已经泛滥,克拉克·克尔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学人员描述为“因共同不满停车场地而聚集在一起的个体户”。到20世纪末,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多年的亨利·罗索夫斯基指责哈佛的教学人员“自制规章”,在教学工作量、校外商业活动、制定咨询与教学实践比例等问题上随心所欲。
我怀疑,新技术很可能会加大这样的离心力,让教学人员远离自己任职的高校。因为人们总愿意花钱与名人面对面,所以有网络知名度的明星教员将要求更多的演讲费,而越来越多的演讲费会刺激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实和虚拟的)路上。就在昨晚,大批布鲁克林区的人每人花350美元,只为亲眼看见芭芭拉·史翠珊,亲耳听到她的演唱,尽管她现在的现场唱功完全比不上30年前制作的CD。学术界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机会(或诱惑,就看你如何看待了),虽然与演唱会相比机会要少得多。举例来说,一日大学(One
Day University),一个技术含量较低的公司,我曾亲身参与其中,它向数百位想听大学教授演讲的成年人收取入场费,而相应地,教授的报酬也绝对不是个小数字。
我认为有一种预测是可靠的,即对某些教学人员来说,这种机会将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而增加,而另一些教学人员,虽然学术能力也许会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但明星效应却下降了,因为所教授的科目晦涩或困难,比较难吸引公众的兴趣,变成二等身价。还有一些人,如语言类教师,不仅地位可能会下降,还有可能被淘汰。iPhone上的法语版Siri,也许就是你未来的法语老师。如果我所说的这些趋势正确,那么我们不只应该担心学术界的名义,还应担心学术界的存续。
我们亟须重新思考学术管理结构,帮助高校抓住在线教育革命带来的所有可能。不过,目前为止,各大学还未曾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现实而重新定义利益冲突原则。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么学术机构本就脆弱的凝聚力将落入新的高压之下。另一方面,如果新定义限制过多,那么最吃香的教学人员将直接弃船,以网络名人兼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继续工作。其实这种情况已在发生了。不过目前,这些前景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未能在学术界内外激起多少讨论。也许我们最该问问,在未来的新环境下如何培训教师。追求学术意味着什么?教师花数年时间读研究生,是为了得到几个媒体明星助教的光辉头衔吗?
我们已经提过营利性“大学”加剧了学生的贷款问题,应当警惕逐利性可能给学术界造成的后果。不过,如我们所见,新兴科技开始在学术机构内外生根,许多聪明人都把赌注压在新技术的盈利潜力上。传统非营利性高校与新兴营利性部门之间将逐步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这一融合必然有失的风险,不过也有得的可能。
当然,新技术的前景或风险若要成为现实,必然需要大量的收入,但目前似乎没人知道收入将从何而来。也许能通过对证书收费,对附加的面授机会收费,为潜在雇主提供需付费的订制服务,或与教科书出版商立约,或多种策略结合使用。我担心,无论未来会如何,保持当前的互联网教育先驱所具有的崇高品格都不简单。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新技术给学生自身带来的前景或风险。我前面提到过一份20世纪中期的报告,该报告研究的是电视给教育界带来的前景,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电视教学的效果如何?”如今,技术已经改变,但关键问题不该改变。对于谁在学、学什么、学多少,还有许多疑问尚待解答,特别当学习的源头是不断激增的MOOC时。我们如何能将延期毕业率或毕业率这种传统衡量指标应用于这些新型教育的“输送系统”?如果做不到,我们又该如何评估其教育价值及产生收益的价值?
另外,对于“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如何”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我觉得在寻找新答案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这个问句的措辞提出异议。我的异议在于“教学”这个词,它让我想起了几周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一堂课。课上,我同本科生讨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著作。讲到某处时,我让他们注意爱默生1838年写给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班学生的一句话。“坦白说,”他对这些胸怀大志的牧师说,“这不是教学,而是来自另一个灵魂的激励。”
在我看来,爱默生的观点精准地牵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通常称为人文学科的领域中,在线教育是否能奏效,若能,要如何奏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对教学和激励之间的区别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种区别有多种表述方式:事实对认识;技术对智慧;纪律对灵感;信息对洞见。多个世纪以来,思虑周全的教育作家一直在探索这些区别。教学与激励断然不是全无交集,甚至不是相互对立的,但也非完全相同;我认为我们可以认同的一点是,无论任何领域——科学或人文,真正的教育必然是缺一不可的。另外,无论我们偏好哪种,认为美国教育(包括幼儿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最近正在向教学迈进,正离激励越来越远的观点似乎已不存在任何争议了。我认为,在线技术很可能推动教育向教学的方向更快地深入。
请让我再说得具体一点,虽然可能会显得有点感情用事。如果要我举例说明师生交流的意义,我想到的是自己刚上研究生时参加的一个研究美国早期文学的研讨班。在研讨班上,我们讨论了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预定论学说,而我非常幸运能遇到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察觉到了我对这一学说的抵触。我不喜欢爱德华兹的预定论,课程快结束时这位老师问我:“你具体不喜欢爱德华兹哪一点?是因为他对自欺行为的态度过分严厉吗?”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有位老师一直在注意我在研讨班上说了、想了、写了什么,他真的懂我是谁,或者换句俗话说,他真的懂我从何而来。他问我的问题自此后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也许未来有一天“翻转课堂”中也能保留这种经历。
很多人似乎也是这么想的。大卫·布鲁克斯不久前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技术将把教学搬上在线平台,提供更高效更实惠的教育,从而为这种意外相遇——激励——腾出更多空间。对此我并不确信。原因之一在于,我不认为将人文学科的教学分为“入门”和“高级”两类有何意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学科的学习是有顺序的(例如你必须先知道莎士比亚是谁,才能在麦尔维尔作品中读出莎士比亚的影子),但文科学位地位不如理科学位也确是事实。人文学科中,叙述往往等同于解释。不过,关键问题在于,人文学科不仅与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有关,还与价值观有关。10岁的杰夫·贝佐斯自豪地告诉祖母,她的吸烟行为给自己减了多少寿,而祖父对他说:“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可贵。”我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持住这样一种教育环境,让我们将善意和聪明都看作是教学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线教育能够孕育出这样的教学方式吗?但愿如此。
我的助教上周组织了一场有关爱默生的讨论会,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作家,会后他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想选取这封电邮的部分内容读给大家听:
嗨,我只是想让您知道,今晚的小组讨论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潦草地记了4页笔记,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内容,而我的课本都写满了评论,课文内容可能都读不了了,但您授课的方式、班上同学的积极参与,真的让我很感动。我平时并不容易动情,内心深处更是不易波动,但今晚我与这个主题产生了共鸣,而我认为这主要是您的功劳。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盯着天空,这样做也许不安全,但非常值得。我迫不及待地想上下星期的课,那样就能继续深入下去。我只是想要立刻向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也让您知道这堂50分钟的讨论课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如果我的行为令您觉得怪异,很抱歉,但我的心在今晚燃起了火焰,我只是将那烟雾向您的方向吹去了一点。
我们想要尽己所能保留住这位学生所描述的经历,以便未来让尽可能多的学生,而非只有那些有幸且有财力进入高校接受面授教学的学生,都能体验到这种经历,我相信在座诸位都会认同这一点。在线教育的未来正快速向我们逼近,在某些领域,它已经抵达。爱默生的好友亨利·大卫·梭罗曾这样评论更早前的技术革命:“我们没有来坐铁路,铁路倒乘坐了我们。”我只希望在我们回首那被取代的过往时,不会说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