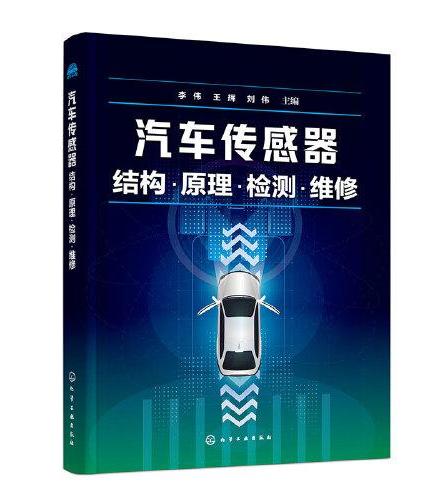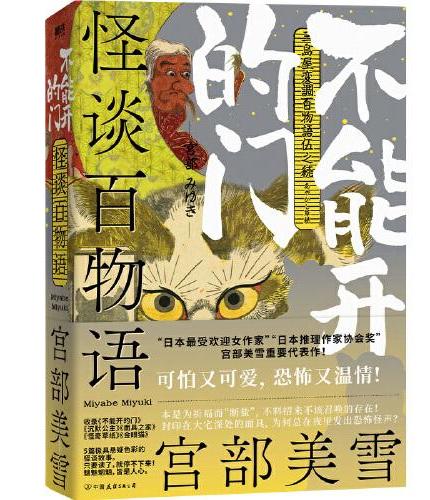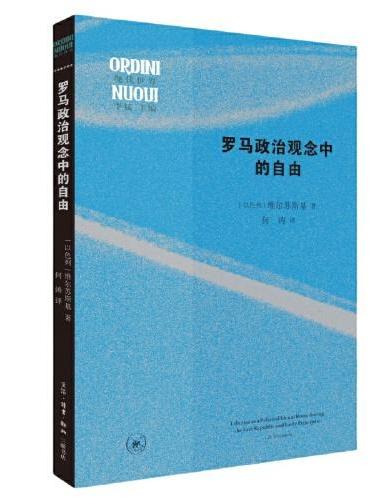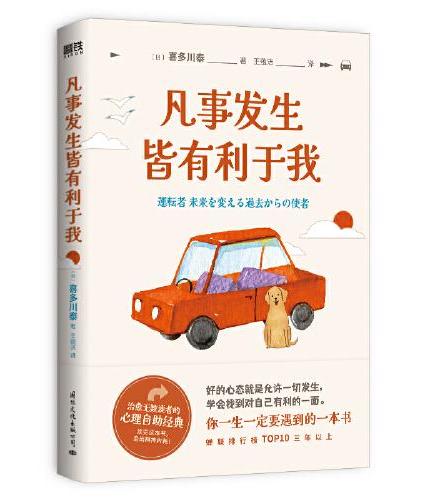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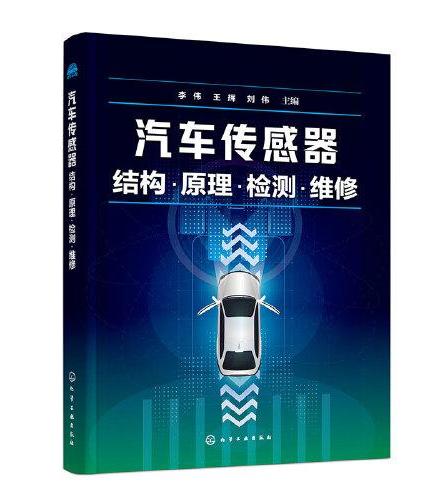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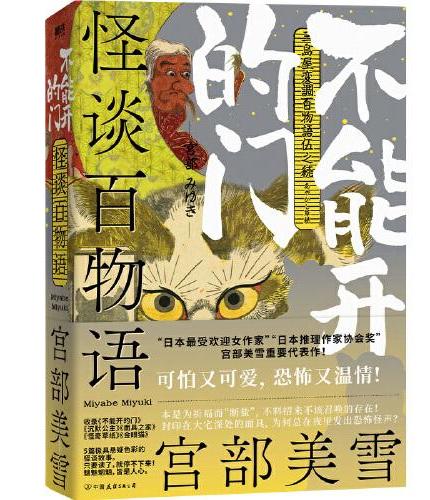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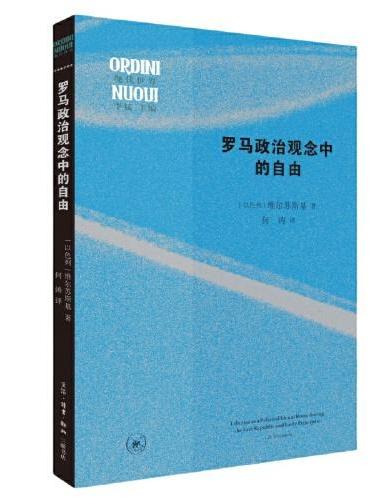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0.4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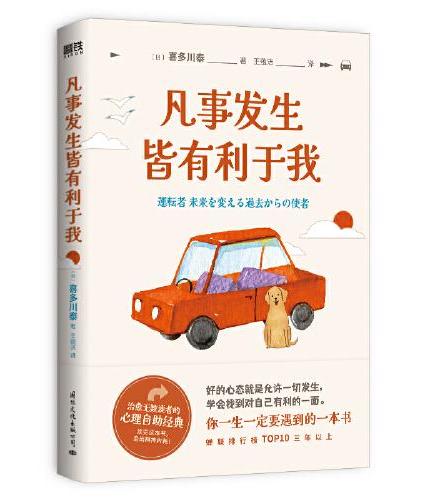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4.6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HK$
55.8
|
| 編輯推薦: |
保罗·奥斯特最新小说
继《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后又一部感人而令人难忘的作品,处处隐含哀伤而又流露希望
独家引进,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首次面世
|
| 內容簡介: |
迈尔斯·海勒儿时遭母亲抛弃,跟着再婚的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十六岁时,他在与继兄打闹中失手,导致继兄车祸身亡,迈尔斯的人生从此遁入了灰暗。后来,他从大学退学,远走他乡,与家人失去联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迈尔斯·海勒来到佛罗里达,在那里认识少女皮拉尔并与之坠入爱河。机缘巧合,他接受了鼓手朋友宾·内森的邀请,回到纽约,住进了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地区一栋被废弃的房子。这栋房子里还住着其他两位房客——正在写博士论文的艾丽斯·伯格斯特龙和画家埃伦·布赖斯。几个年轻人背负着各自的过去,带着心头的伤口,在平淡的生活中互相慰藉,陪伴彼此跨越了时间的伤痛,在告别与坚持中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口。
|
| 關於作者: |
保罗·奥斯特,1947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作品常探讨人生的无常与无限,笔下的主角也常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他擅长实验性的写作风格,并在流畅的文字间,暗藏值得再三玩味的人生哲理。文坛曾比喻他是“穿胶鞋的卡夫卡”。他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
保罗·奥斯特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纽约三部曲》、《幻影书》、《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隐者》、《日落公园》等。他的最新作品是2013年11月出版的回忆录《内心的报告》。2006年他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巨兽》获得法国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日落公园》获意大利拿波里奖;他编剧的电影《烟》于1996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最佳编剧奖;2012年,他成为第一位纽约市文学荣誉奖的获得者。此外,《幻影书》曾入围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偶然的音乐》入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玻璃之城》入围埃德加推理小说奖。他也是美国艺术与文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四十三种语言。
保罗·奥斯特现定居纽约布鲁克林。
|
| 內容試閱:
|
迈尔斯·海勒
一
已经快有一年了,他一直在拍摄被人遗弃的物件。每天至少有两个活,有时会多达六七个,每一次他和他的团队进入一间屋子,都会面对数不清的物件,那些被搬走的家庭扔下的东西。那些缺席的人都在匆忙间离去了,带着羞辱,带着困惑,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论现在他们住在哪里(如果他们能找到住的地方而不是在街头露宿的话),他们的新住所会比他们失去的这栋房子更小。每栋房子都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有关破产和违约、债务和没收抵押物——而他让自己承担起记录的责任,记录这最后的、残存的、分崩离析的生活轨迹,为了证明那些消失的家庭曾经在这里,那些他永远不会见到也永远不会了解的人的灵魂仍然存在于这些废弃物中,散落在他们留下的空房间里。
这种工作叫作出场清理,他属于一个四人小组,受雇于顿巴·利提公司,该公司承包了本地银行的“住宅维护”服务,负责清理那些有问题的房产。南佛罗里达这片蔓延的公寓地块充斥着这些被遗弃的建筑,由于银行要尽快重新卖掉这些房子来获取利益,这些空房子必须快速得到清理、修缮,准备好展示给可能的买家。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经济崩溃的废墟和无情扩散的穷困无处不在,出场清理是这个地区罕见的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毫无疑问他能找到这份工作是幸运的。他不知道还能忍受多久,但薪酬很不错,在一个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一份好工作就意味着一切。
刚开始的时候,他震惊于那种凌乱、污秽,以及完全被人忽视的状态。他走进的房间很少能保持屋主在时的原样。更常见的是暴力和怒火发泄过后的痕迹,离开时对物件任性狂暴的毁坏——水龙头打开着,水从水槽和浴缸里满溢出来;用锤子砸烂的墙、画着淫秽涂鸦的墙、布满子弹孔的墙,更不用说那些被狠狠扯下来的铜管、发白的地毯、起居室地板上的一堆堆粪便。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也许吧,是被剥夺财产者的愤怒所引发的冲动之举,是恶心但可以理解的绝望的宣言,但是,每一次打开一扇门,即使他并不总是感到强烈的反感,也总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无可避免的,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气味,那股酸臭的气味猛冲进他的鼻腔,那无处不在的,混合着霉菌、变质牛奶、猫粪、抽水马桶里的残留物和餐厅台面上的腐烂食物的气味。就算打开窗让新鲜空气吹进来也没法抹去这些气味;就算是最清洁、最细致的清除也无法消除这种颓败的恶臭。
接着,总是那些物件,那些被遗忘的财产,被遗弃的物品。到目前为止,他拍摄的照片已有上千张,在他不断膨胀的档案里能找到各种东西的照片,书本、鞋子、油画、钢琴和烤面包机、洋娃娃、配套的茶具、脏袜子、电视机和棋盘棋子、派对服和网球拍、沙发、丝绸女式内衣、填缝枪、图钉、塑料玩偶、唇膏、来复枪、褪色的床垫、刀叉、打扑克的筹码、集邮册,以及一只死掉的金丝雀躺在笼子的底部。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必须拍下这些照片。他明白这是一场徒劳的追逐,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但每次他走进一栋房子,都感觉到这些物件在对他呐喊,用已经不在那里的人的声音对他说话,让他在它们被清理走之前再最后看上一遍。小组里其他人都会拿他沉迷于拍这些照片开玩笑,但他毫不理睬。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微不足道,他鄙视他们所有人。没脑子的维克多,小组的头;结巴又唠叨的帕科;胖得不停喘气的弗莱迪——三个可悲的火枪手。法律规定所有高于一定价值的可利用的物品都必须上交给银行,银行有义务将它们归还物主,但他的同事们想都不想,看见喜欢的就拿。他们觉得他是个傻瓜,竟然对这些战利品无动于衷——一瓶瓶的威士忌、收音机、CD唱机、射箭用具、色情杂志——但他唯一想要的是他拍下的照片,而不是物品本身。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在工作的时候规定自己尽量少开口说话。帕科和弗莱迪已经开始叫他“哑巴”。
他二十八岁,就他自己所知,他根本没有任何上进心。没有熊熊燃烧的野心,在任何层面上,不明白打造一条看似光明的前途会给他带来什么。他知道自己不会在佛罗里达待很久的,那个他感到需要继续上路的时刻就要到来,但在时机成熟之前,他满足于维持现状,不做长远打算。如果说他在大学退学后独立生存的七年半里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这种活在当下的能力,把自己限定在此时此地,尽管这可能不是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但这也需要相当的纪律性和自我控制力才能完成。人生没有计划,其实也就是杜绝欲望或希望,满足于你自己的所有,接受每一天这个世界分配给你的那一小份——要这样生活你必须需求很少,少到人类可能接受的底线。
一点一点,他已经把欲望剥离到接近极限。他戒了烟和酒,他不再下馆子,没有电视机、收音机和电脑。他也想卖了车换一辆自行车,但他不能没有车,因为他工作时要跑的路程实在太远了。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口袋里还揣着手机,他很愿意把它扔进垃圾桶,但他仍旧需要用它工作,所以不能没有手机。那台数码相机是一种奢侈的沉迷,但鉴于这无尽的清理垃圾的生活所带来的阴郁和艰难,他感觉相机在拯救他的生命。他的房租很便宜,他住的小公寓地处贫困地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他允许自己的唯一奢侈就是买书,平装书,大多数是小说,美国小说,英国小说,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但说到底书跟那些必需品比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奢侈的开销,他也并不想戒掉读书这个癖好。
要不是碰上那个女孩,他也许在这个月底前就离开这里了。他已经存够了钱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而且他也晒够了佛罗里达的阳光——经他研究发现,他现在相信这阳光对灵魂的伤害比好处多。在他眼里,这里的太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政治家的太阳,是虚伪的太阳,它射出的光没有照亮事物,反而更遮蔽了它们——用那一成不变的、刺眼的光芒蒙蔽你的双眼,用阵阵充满雾气的潮湿冲击你,用幻觉般的倒影和闪着光的空洞之浪让你心神不安。到处是闪烁和炫目的光,但没有实质,没有静谧,没有喘息的余地。可是,也就是在这样的太阳底下,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女孩,也是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她,他继续忍受着这太阳并试图和它讲和。
她的名字叫皮拉尔·桑切斯,他是六个月前在一个公园里遇见她的,在五月中的那个周六下午,纯粹出乎意外的相遇,是不可能中最不可能的那种相遇。她当时正坐在草地上看书,离她不到十英尺远的地方,他也坐在草地上看书,而且碰巧和她读的是同一本书,还是一模一样的平装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十六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这是他第三遍读这本书了。他已经坐在那里二十或者三十分钟,沉浸在书中,所以完全与周遭环境隔绝,突然他听见有人在笑。他转过头,在那第一次也是致命的第一瞥中,看见她坐在那里对他微笑,手指着她自己的书的标题,他猜想她大概还不到十六岁,还是个女孩子,真的,一个小女孩,一个还在青春期的小女孩,穿着紧身毛边短裤、凉鞋、短小的三角背心,这装束跟任何一个来自炎热阳光照耀的佛罗里达下等地区稍有吸引力的女孩一样。还是个孩子,他对自己说,但她就在那里,裸露着平滑的四肢,表情略带警觉,但同时又在微笑。而他,平时很少对任何人或事笑,看着她深幽灵动的眼睛,也对她回以了微笑。
六个月后,她仍旧未成年。她的驾照上显示她现在十七岁,她要到五月才满十八岁,所以在公共场合他和她在一起必须很小心举止,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引来别人的怀疑,因为只要有哪个义愤的好事者打一个电话到警察局就可能把他送进牢里。只要不是周末和假日,每天早上他开车送她去约翰·F.肯尼迪高中,她是那里的高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向往着上大学并最终成为一名注册护士,但他从来不在学校门口放她下车。那样做太危险了。老师或者学校管理者可能会因为看见他们俩在车里而拉响警报,所以他在离学校三四个街区远的地方就停下让她下车。他不和她吻别。他不碰她。她为他的克制感到悲伤,因为在她自己心中她已经是个成年女子了,但她必须接受这种表面的冷漠,因为他告诉她必须接受。
皮拉尔的父母两年前死于一场车祸,去年六月学期结束后她搬进他的公寓和他一起住,之前她一直和她的三个姐姐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二十岁的玛莉亚,二十三岁的特雷莎和二十五岁的安琪拉。玛莉亚就读于一所社区大学,学习成为一名美容师。特雷莎在一家当地银行做出纳。安琪拉,她们中最美的一个,是某个鸡尾酒吧的女招待。据皮拉尔说,安琪拉有时为了钱会和顾客睡觉。皮拉尔急着补充说她爱安琪拉,她爱她的姐姐们,但现在她很高兴能离开家,那里充满了太多父母的回忆,而且,她控制不住,她痛恨安琪拉所做的事,她认为女人出卖自己的身体是一种罪恶,现在不用再和她争论这个也让她大松了一口气。是的,她对他说,他的公寓是个破败简陋的地方,她的家要大得多也舒服得多,但这间公寓里没有十八个月大的小卡洛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放松。特雷莎的儿子在小孩子里当然算不上坏孩子,而且特雷莎也做得不错了,她的丈夫驻扎在伊拉克,而她自己每天在银行的工作时间又特别长,但即便这样,她也没有权利每隔一天就把照顾孩子的重任压在她未成年的妹妹身上。皮拉尔想要做好人,但她还是忍不住讨厌这事。她需要时间独处和学习,她想要做点自己的事,而如果她总是忙于给孩子换尿布,又怎么能做自己的事呢?孩子在其他人看来都很可爱,但她不想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谢谢,她说,但是不行,谢谢了。
他惊异于她的志气和聪慧。甚至在他们相遇的第一天,当他们坐在公园里谈论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就惊讶于她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在读这本书,而不是哪个老师布置的功课。接着,交谈深入下去,他更是加倍地惊讶于她开始跟他争论这本书最重要的角色不是黛西、汤姆甚至盖茨比本人,而是尼克·卡拉威。他让她解释为什么。因为他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她说。他是唯一一个双脚着地的角色,唯一一个不仅能关注自己还能向外看的人。其他人都是迷失的浅薄的人,没有尼克的同情和理解,我们就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感觉。这本书就建立在尼克身上。如果这故事由一个全知的叙述者来讲述,就不及现在的一半好。
全知的叙述者。她知道这术语的意思,正如她也同样理解什么叫幻觉状态、生物起源、反对数以及布朗诉教育局案件一样。这怎么可能,他心想,对于一个像皮拉尔·桑切斯这样年轻的女孩而言,她出生于古巴的父亲一生都只是个邮递员,她的三个姐姐满足地安于日常生活单调的泥沼中,而她却出落得同她的家庭如此不同?皮拉尔想要知道更多,她有许多计划,她努力地学习,而他则完全乐意鼓励她去做任何他可以帮到她的事来获得更高的教育。从她离家搬进他公寓的那天起,他就开始针对SAT考试[①]。中的难点给她培训,检查她每一项家庭作业,教她微积分的基本原理(她的高中老师可不会教她这个),还给她大声朗读了几十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他,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抛弃了曾经享有特权的生活的诱惑,从大学退学的人,现在开始对她充满雄心壮志,推着她走向她能力的极限。首要任务是进入大学,要进一所好学校并拿到全额奖学金,一旦她进了大学,他感觉剩下的事就可以顺其自然了。现在,她还在梦想着成为一名注册护士,但事情最终将会改变,他很肯定,他完全相信有一天她有能力进入医学院继续深造,最后成为一名医生。
是她提出要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他可绝对不会主动提出这么大胆的计划,但皮拉尔的态度很坚决,抱着想要逃离的渴望以及每晚都和他睡在一起的向往,她求他去见安琪拉——她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所有家庭事务的最后决定者。他去见了这位最年长的姓桑切斯的女孩并成功说服了她。她一开始并不同意,说皮拉尔做这么重大的决定还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是的,她知道她的妹妹和他相爱,但她并不赞同这份爱,因为他们的年龄差距,这意味着迟早有一天他会厌倦眼下这位青春期的玩伴,离开她,留给她一颗受伤的心。他回答说结果可能正相反,他可能会是那个伤心的人。然后,把所有那些关于心和感情的话题放到一边,他用非常实际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想法。皮拉尔没有工作,他说,她在经济上是个拖累,而他所处的位置正好能资助她把这个负担从她们手里接过去。说到底,他不是要把她诱拐去中国。她们家离他的公寓步行只要十五分钟,她们想见她随时都能见到她。为了谈妥这笔交易,他提出给她们每个人礼物,她们想要但因为手头拮据而买不起的任何数量的东西。随后在出场清理的工作中,他在三个傻瓜同伴的震惊和嘲笑下暂时性地一改他原先的工作原则,到下一个星期他平静地偷出了一台几乎是全新的平板电视、一台顶级的电动咖啡机、一辆红色的三轮车、三十六部电影(包括一整套珍藏版《教父》)、一面专业水准的化妆镜、一套水晶红酒杯,这些他都按时交给了安琪拉及其姐妹们,作为他感谢她们的表示。换句话说,皮拉尔现在和他住在一起是因为他贿赂了她的家庭。他买下了她。
是的,她爱他,同样的,尽管他内心有着疑虑和犹豫,他也爱她,不管这份爱对他来说有多不合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他不是那种对年轻女孩有特别癖好的人。到现在为止,他生活里的所有女人都和他差不多年纪。所以皮拉尔对他来说并不代表某种理想女性的典型——她只是她自己,他某天在某个公园里碰上的好运气,一个纯粹的例外。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她吸引。他欣赏她的聪慧,是的,但这一点最终变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在她之前他还欣赏过其他女人的聪慧却从没感到被她们吸引。他发现她很漂亮,但也不是惊人的漂亮,从客观角度而言还谈不上美(尽管你也可以说每个十七岁少女都是美的,因为很简单所有的青春少女都是美的)。但这不要紧。他爱上她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或者她的头脑。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当一切都在告诉他应该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把他留在了这里?是因为她看着他的方式,也许吧,她凝视他时的咄咄逼人,她倾听他说话时眼中那种专注的强度,一种只有他们在一起时她才完完全全存在的感觉,他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为她而存在的人。
有时,当他拿出相机给她看他拍的废弃物的照片时,她的眼里会噙满泪水。她身上有非常柔软、感伤的一面,却同时具有一种戏剧感,他是这么感觉的。而他被她身上的这种柔软,这种对他人之痛的脆弱所感动是因为她同时又是那么坚强,那么健谈和充满欢笑,他从不能预测到她的哪一面会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短期内这可能有点让人难受,但长期来看他感觉这一切都对他有好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否定自己,在自我放逐中冷漠地生活,教会了自己控制脾气,用冷酷顽固的超然态度随波逐流,却在她过剩的情感波动里,她一点就燃的热情里,她面对一只丢弃的泰迪熊、一辆坏掉的自行车或者一瓶枯萎的花时所流下的自作多情的眼泪里慢慢活了过来。
他们第一次上床时,她肯定地对他说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他把她的话当真了,但他要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她把他推开说他不可以这么做。这个妈妈的洞是禁区,她说,男人那话儿的绝对禁区。舌头和手指可以接受,但不是那话儿,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永远。他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他戴着避孕套,不是吗?他们采取了保护措施,没必要担心任何事。啊,她说,但这就是他错的地方。特雷莎和她丈夫也总是相信避孕套,看看他们的结果。在皮拉尔眼里没什么比怀孕更可怕的了,她绝对不会相信那些可疑的橡胶,拿自己的命运来冒险。她宁可割腕或者从桥上跳下去也不要怀孕。你懂吗?是的,他懂,但有别的选择吗?还有那个玩乐的洞,她说。安琪拉跟她说过这个,他不得不承认从严格的生物学和医学角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安全的避孕形式。
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他服从她的愿望,把那话儿的穿越动作仅限于她的玩乐的洞里,而在她那个妈妈的洞里只有舌头和手指。这就是他们反常独特的爱情生活,虽然如此却也是非常丰富的爱情生活,一种充满蓬勃肉欲的关系,至少在近期看不到任何减弱的迹象。最终,就是这种性爱的合谋关系紧紧地把他绑在她身边,让他滞留在这片酷热的充斥着废旧空房的无名之地。他着迷于她的肌肤。他是她热火般的双唇的囚徒。他在她的身体里感到家的温暖,如果他一旦找到勇气离开,他知道他会后悔到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