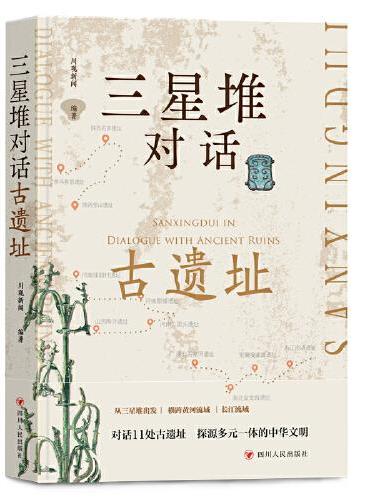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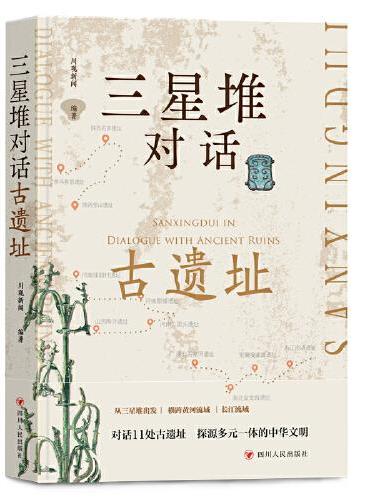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3.4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
卡特里娜(“同一颗星球”丛书)
》
售價:HK$
87.4

《
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方尖碑)
》
售價:HK$
188.2
|
| 編輯推薦: |
1. 梁启超、萧红、胡适、朱自清、鲁迅、徐志摩、郑振铎……他们有多广阔,中国文坛就有多广阔!
2. 他们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却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读懂他们,就读懂了一个时代。
3. 本书收辑的42篇文章均是民国时期那些文人蘸着感情写出来的相互怀念之作,作者又多是死者的好友,笔底凝结着许多的温存,许多的惋惜,许多的伤感,许多的沉痛……但我相信,此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帮我们打捞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还原一段精彩的人生。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一些相互怀念之作的合辑。
书中共收辑了42篇文章,这些文章分别出自鲁迅、胡适、徐志摩、郁达夫、萧红、郑振铎、朱自清、夏丏尊、许地山、庐隐、谢六逸、耿济之等之笔。这些文章充满温暖、惋惜、怀念、伤痛……而在生活中他们又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脾气,他们有些是好友、有些则不相投合、有些甚至可能还互相攻讦过,然而就是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文人世界。对他们,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所偏爱,但随便哪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
| 關於作者: |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等,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等。
鲁迅(1881.9.25- 1936.10.19):原名周树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
| 目錄:
|
第一辑 郁达夫: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着他们
志摩在回忆里
怀四十岁的志摩
回忆鲁迅
怀鲁迅
敬悼许地山先生
光慈的晚年
打听诗人的消息
第二辑 郑振铎: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永在的温情
惜周作人
悼夏丏尊先生
悼许地山先生
忆愈之
忆六逸先生
哭佩弦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第三辑 鲁迅: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忆刘半农君
柔石小传
为了忘却的记念
忆韦素园君
第四辑 胡适:这些人,那些事儿
追悼志摩
丁在君这个人
记辜鸿铭
高梦旦先生小传
追忆曾孟朴先生
第五辑 朱自清:背影渐远犹低徊
致白采
我所见的叶圣陶
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第六辑 傅斯年:致我所景仰的先生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第七辑 夏丏尊:清清淡淡的悠远流长
弘一法师之出家
致白采
鲁迅翁杂忆
第八辑 靳以:不论相见或是相离,总是记着他
忆崇群
忆圣泉
第九辑 杂忆:别了,我最亲爱的朋友
悼志摩(林徽因)
回忆鲁迅先生(萧红)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我与老舍(罗常培)
梦苇的死(朱湘)
穆木天(蒲风)
怀念阿英先生(柳亚子)
忆梁遇春(石民)
|
| 內容試閱:
|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残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在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的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是的,他十九日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日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残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地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的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一直到最近两个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起了倾盆大雨——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绘,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说:
“完全诗意的信仰!”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的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那一桩事,那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为此说来,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
他真的是个怪人么?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更是不对。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可是奇怪的!
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提且利和达文骞。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 那一套。”他知道我们是讨厌Ruskins 的。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客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a。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b,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笔吊他的惨变。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回忆鲁迅先生(萧红)
萧红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地的走去。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那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 还有别的朋友 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的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鲁迅先生笑而不答。“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的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 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 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里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犹太也许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用眼瞪着她,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而后说:“是做什么的呢?”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地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常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在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吞吞地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佣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