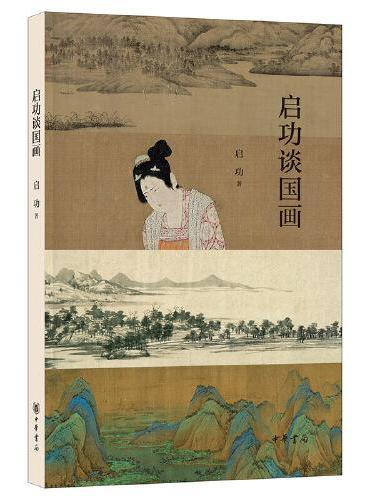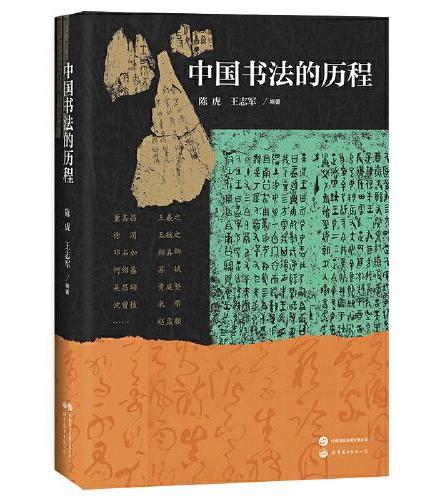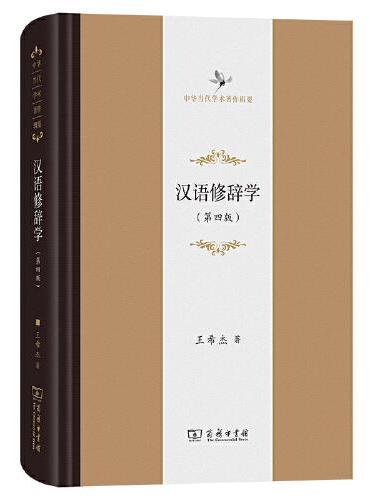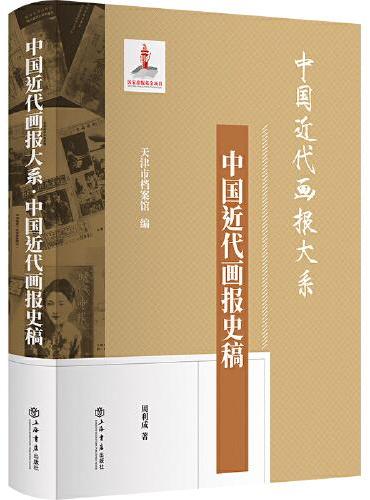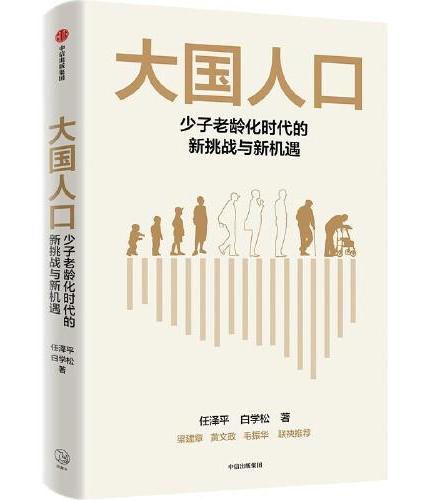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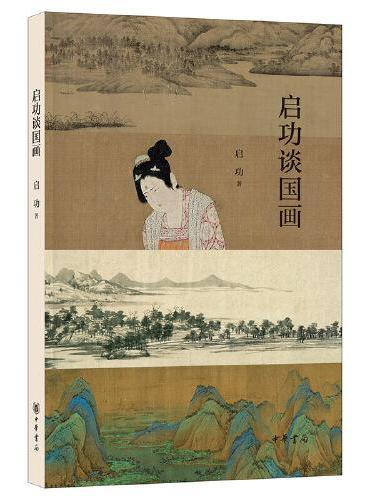
《
启功谈国画(启功著,中华书局出版)
》
售價:HK$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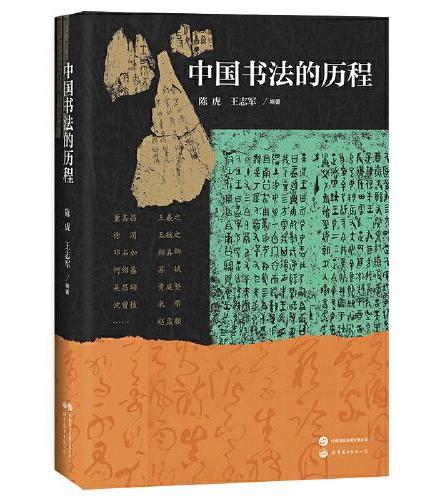
《
中国书法的历程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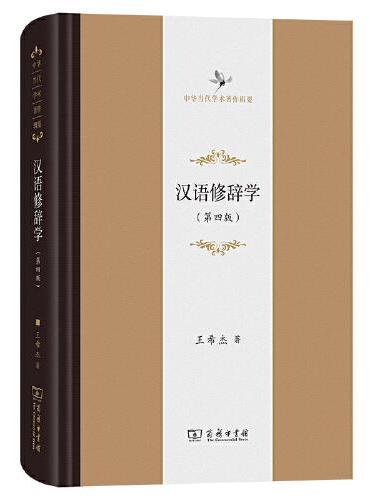
《
汉语修辞学(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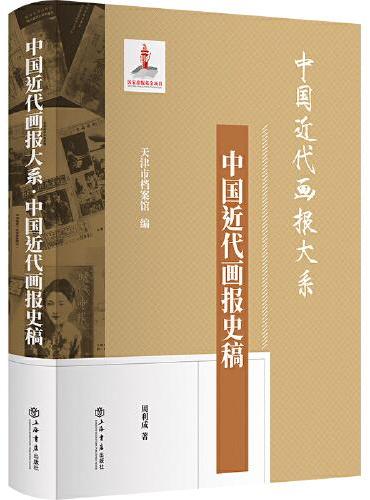
《
中国近代画报大系·中国近代画报史稿
》
售價:HK$
181.7

《
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艺文志·日本思想)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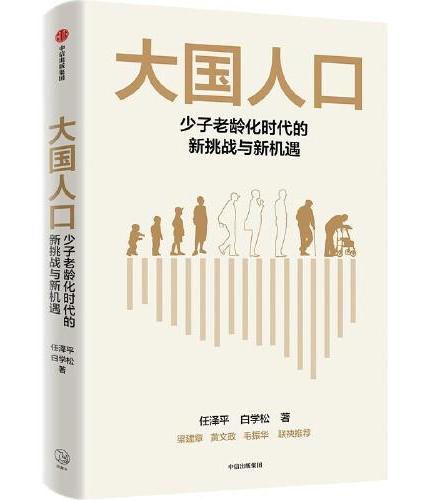
《
大国人口
》
售價:HK$
90.9

《
何以中国·君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
售價:HK$
112.7

《
文明的故事(全11卷-2024版)
》
售價:HK$
2631.2
|
| 編輯推薦: |
|
本套系包含国际大奖童书八本,这些作品分别来自英美日西等国,荣获英国惠特布莱德童书奖、聪明豆童书奖、《出版者周刊》最佳图书奖、美国“父母的选择”金奖、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日本野间儿童文学奖、西班牙艾德彼儿童文学奖等权威奖项。这套儿童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多样,主题新鲜有趣,非常适合亲子共读及自主阅读。
|
| 內容簡介: |
|
自从木头娃娃西蒂离开温暖的家,开始长达百年的漫长旅行,她就注定会成为一个传奇。在这段奇遇中,西蒂与水手结为好友,成为土著人的偶像,当上时装模特,沦为印度耍蛇人的道具……她的一生就像真正的冒险家那样惊险刺激,简直让人忘了她只是一个娃娃!然而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险,西蒂始终对生活心存希望、满怀感激。“热爱生命”一词在西蒂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想了解西蒂的精彩探险故事吗?让我们随她去看看吧。
|
| 關於作者: |
|
雷切尔·菲尔德生于1894年,是美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为孩子们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诗歌和戏剧。她于1930年创作的《木头娃娃百年奇遇记》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她于1932年创作的《卡利柯灌木丛》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她于1945年创作的《孩子的祈祷》摘下凯迪克金奖。除此之外,她还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刘易斯.卡洛书架奖。
|
| 目錄:
|
第一章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 001
第二章 上天入地,还好最后回来了 015
第三章 水陆并进的旅行 026
第四章 在海上 035
第五章 遭遇鲸鱼 045
第六章 与鱼为伴的日子 062
第七章 上帝,土著人和猴子 074
第八章 流落印度 085
第九章 结交新的小伙伴 097
第十章 参加音乐会 108
第十一章 拍银版照片,见到诗人 125
第十二章 我跟樟脑丸在一起,还去了纽约,成为模特 136
第十三章 度过一个可怕的新年,又回到新英格兰 147
第十四章 从干草仓出来,有了新职业 159
第十五章 熟悉种植园、邮局和针插 180
第十六章 故地重游 194
第十七章 被拍卖了 206
尾 声 216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
古董店里非常安静。我与西奥博德百无聊赖地待着。前天那只布谷鸟座钟被卖掉了。不然,那个木头家伙后面会不时出现探头探脑的老鼠,西奥博德也好有点事做。是的,西奥博德是一只猫,也是这个店子里唯一的非卖品。这让它自我感觉良好。我倒不想批评它,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应该感谢它。如果不是它,我现在可能也没有机会写我的回忆录了。当然,缺点是一回事,爪子是另一回事。我讨厌它的爪子。
西奥博德并不坏,不过也绝非善类。它有点暴力倾向。我从没见过一只猫能有它那样力大无穷的爪子和尾巴。最近,它还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总是跳到窗台上,让大脑袋挨着古董珠宝睡觉。如果亨特小姐看到了,一定会急得跳脚的。因为,前天晚上,西奥博德在睡梦中打呵欠时,差点把一只石榴红的耳坠给吞进去。不过,古董店开张时,西奥博德就在这儿,算是老人了,所以亨特小姐总是对它特别宽容,很少计较它那些乖张的行为。当然,亨特小姐自己也有些古怪。就像菲比的妈妈曾经说过的那个词——忐忑不安,亨特小姐就给人这种感觉。她在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喜欢死死地盯着你看,然后把你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把玩。你也许会慢慢习惯这种方式。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有教养的行为。必须承认,亨特小姐这样做其实并无恶意。相反,一旦她发现你是货真价实、物有所值的古董,就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正因为如此,当她第三次发现我夜里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摔了个狗啃泥以后,她每天都会不厌其烦地在店子关门前把我从高高的橱窗上拿下来。谁让她认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董娃娃呢?
此刻,我正站在她那乱七八糟的桌子上。我的脚踩在散开的绿色吸墨水纸上,背靠着青灰色的墨水盒,四周有许多雪白的账单和文件。不远处,一个旧的海螺壳放在一堆书写潦草的单据上。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无数比它漂亮的贝壳,不过只有这一个能勾起我无数的回忆。一看到它边缘上泛着的微光,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奇遇。对面的壁炉台上,一艘帆船的模型静静躺在玻璃瓶里。不过这船看起来不怎么样。起码,当初我们从波士顿港出发时,“戴安娜—凯特”号上的镀金比它强多了。也许,今天那只来自瑞士的旧音乐盒又会在那里自说自唱,反正也没人阻止它。不过,坐在这儿听它用叮叮当当的声音演奏名为《玫瑰和木樨草》的华尔兹舞曲,我总是觉得很不自在。它让我想起了当年在皮特尔先生家为年轻人举办的沙龙舞会。那时,伊莎贝拉就是和着这个曲子翩翩起舞的。是的,就在华盛顿广场对面,离我此刻所在的地方仅仅一街之遥。不过,当初可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和街边小店。
也许是因为瓶子里面的那艘船,也许是因为音乐盒,不过更可能是因为这支鹅毛笔,我动了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的念头。钢笔与青灰色的墨水盒是配套的,但是鹅毛管在今天看来,就像过去女士衣服上的鲸鱼骨头和小女孩的阔边帽子一样,早就过时了。当然,人总是难免念旧。克拉丽莎曾经当着我的面,用鹅毛笔把一大堆名言警句抄到本子上。正如亨特小姐和那位老绅士所认为的那样,我是这家店里最货真价实的古董了。我当然更喜欢用鹅毛笔写字,而不是现在这些新式的墨水笔,因为我对带尖头的铁制品没什么好感。所以,我会好好地像现在这样,拿着我的鹅毛笔写回忆录。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那应该是在一百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出生在缅因州。当然,我肯定不记得我出生的情景了。不过,普雷布尔家不同的成员经常反复对我讲当时的场景。听得多了,我仿佛也知道了当初老货郎是如何用一块花楸木一点点把我给雕出来的。那块花楸木很小,因此我的身材也就小得出奇,哪怕是娃娃也很少有我这么小的。不过,老货郎将这块小木头视若珍宝。这是他从大海那边的爱尔兰带过来的。随身携带花楸木被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传说中它可以驱邪避害。从老货郎开始沿街叫卖货物起,他就一直把我放在包包的下面。通常情况下,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他的生意会比较好。这段时间路途顺畅,天气也不是那么寒冷。农夫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便站在自家门槛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货郎摆好的各种玩意儿。不过,这一年,他向北走了很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大雪不客气地将他困在了一个荒凉的小村落。暴风雪顷刻之间席卷而来,将路封死了。他环顾四周,发现只有普雷布尔家亮着灯,只得走上前去敲响了厨房的门。
普雷布尔太太总是念叨,如果没有老货郎,她和菲比真不知道如何度过那个冬天。因为,除了打杂的安迪之外,他们另外三个人一刻不停地忙着烧火、喂牲口棚里的牛、马、鸡等。后来天气晴好了,但是路依然没法走。所有的船只都被暴风雪困在了波特兰港。普雷布尔船长出海了,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所以,货郎决定继续留下来,帮着做些零活,等到开春的时候再离开。
那时候,菲比只有七岁。她是一个乐天派,对人也很友好。她美丽顺滑的头发打着卷儿,从脸颊两边披散下来。正是因为她,我才从一块花楸木变成了一个六英寸半、比月桂树上的蜡烛也高不了多少的娃娃。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正方形的、舒服的房间里。房子里有温暖的火光和一个像方形的小洞一般的壁炉。壁炉中的火苗在一捆圆木上快乐地跳跃着。壁炉上面的铁架子上,挂着一只黑色的旧茶壶。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菲比说的。她对妈妈和安迪大喊:“看啊,娃娃的脸雕好了。”他们立刻走过来仔细地端详着我。老货郎此时正把我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就着火光将我翻来倒去,以便我身上的颜料可以快点干。菲比看着我的五官样貌,非常兴奋。她的妈妈则为老货郎的手艺惊叹不已。因为他居然能在那么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出“真正”的鼻子和快乐的表情。她们认为,这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用折叠刀做出这么精致的东西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壁炉台上等着被晾干。壁炉里的火光渐渐小了起来,墙上投下了奇怪的影子。老鼠们在墙内外不停地打闹嬉戏。窗外的大风将高大的松树吹得沙沙作响。谁能想到,不久以后,我会对这声音无比熟悉呢?
菲比的妈妈认为,在我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之前,她不能跟我玩。菲比不擅长做针线活,但她的妈妈坚持拿出了针线、顶针和各种布头。就这样,她们开始为我量身定做第一套衣服。我的这套衣服是用浅黄色的棉布做成的,上面点缀着许多小红花。菲比的手艺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平日里,她缝个十来分钟就不耐烦了。可现在,她实在太想早点跟我玩了,所以做得异常细致认真。
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到底怎么来的。本来,我有一个教名,叫梅西塔布尔。不过,在菲比看来,这个名字太长了点。一来二去,大家就叫我西蒂了。在普雷布尔太太的建议下,菲比将我这个独特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绣在了我的衬裙上。
“这样一来,”菲比的妈妈在最后一个字母也大功告成时说,“不管以后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都不用担心别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了。”
小姑娘大声喊:“她不会有任何事的,妈妈!因为她会永远属于我!她是我的娃娃!”
现在,我想起这些话语,简直百感交集。生活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许多倍。
几周之后,我穿戴一新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不过,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按照当时的规定,从星期六的日落时分到星期天的晚上,孩子们是不能玩玩具的。正是二月时节,太阳自顾自地早早消失在地平线,菲比沮丧极了。她央求妈妈让她在炉火边跟我再玩一会儿,就半个小时。当然,这无异于白费口舌。她妈妈为了断绝她的念想,干脆将我放进旧松木衣橱的最上层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普雷布尔太太那条上好的呢子头巾,还有菲比的爸爸上次从波士顿给她带回来的海豹皮暖手筒和披肩。我整个晚上都跟它们待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当大家准备就绪,即将启程去教堂的时候,情况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周日的出行对普雷布尔家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教堂有几英里远,要坐好久的雪橇。菲比早早地就把自己打扮停当了。在妈妈和安迪还在收拾的时候,她拿了一个脚凳,打开衣橱的抽屉。她弯下腰准备拿暖手筒和披肩,突然就看到了我。她努力地让自己忽略我的存在。
“不,西蒂,”她说,“今天是星期天,日落之前我都不能碰你。”她叹了一口气,因为她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她情不自禁地将我抓在手里。“其实,”她略带歉意地对我说,“妈妈说了,星期天是不能跟你玩的。而我现在不过是想帮你理理衣服,这样没事儿。”她的小脑瓜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把我放在暖手筒里。我就这样被放了进去。菲比顺理成章地开始实施下面的计划。“西蒂,谁也猜不到你会在我的暖手筒里。”她对我耳语道。从她的语气里,我就知道,今天早上我不会待在松木抽屉里了。
这时,她妈妈匆匆忙忙地进来,催大家立刻出发,否则就赶不上唱赞美诗了。我并不知道赞美诗是什么,但在她看来这是不容错过的。因此,她在抽屉里拿披肩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到我已经不在那儿了,也没有发现菲比紧张得满脸通红。
海豹皮暖手筒里温暖舒适。不过,菲比把两只手都放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被挤得喘不过气来。除了偶尔漏进来的一点刺眼的光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那是雪地里反射过来的太阳光。当然,我能感觉到马车带着我们在路上飞奔。我还能听到马蹄在雪地里吱吱作响的声音。老货郎吹着口哨不时地抽上一鞭子。雪橇上的铃铛欢快地一路唱着歌儿。不过,普雷布尔太太可不喜欢这个声音。她不断地责备安迪。因为,是安迪忘记把那些铃铛拿下来了。她说,挂着铃铛去教堂过安息日太不严肃了,指不定邻居们会说些什么。但安迪说,不过是铃铛而已,管它们是在雪橇上还是在教堂顶上呢。
因为这句话,菲比的妈妈把安迪狠狠地责骂了一番。如果不是因为马车已经到教堂门口了,她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我到教堂了,这可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娃娃进的地方啊。想到这里,我就兴奋不已。虽然还是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努力地去听大家都在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耳边依然时常回响起周围的人们起身时发出的各种声音。而且,我还记得他们合唱的那些歌词:
赞美上帝,护佑众生;世间万物,齐声颂扬。
听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无比神圣。不过接下来的布道和祷告太长了,我不打算听下去。菲比先是不耐烦,后来干脆背靠着妈妈睡着了。我的不幸就这样来了。我估计,她睡着以后,暖手筒就悬了起来。渐渐地,她的手就松了。紧接着我就大头朝下地从藏身之所——暖手筒,掉到了地上。这时大家正起身做最后的祝福,所以没人听到我落地的声音。暖手筒滚落到另一边,正好被安迪接住了。菲比被一把拉了起来,与大家一起站起来低头祈祷。
人们从普雷布尔一家人坐过的长凳边陆续走过,没有人发现我。我害怕极了。我听到门外雪橇和马车的声音陆续响起,希望菲比能够想办法回来找我。最后,我听到了锁门及百叶窗被合上的声音。我终于确定,没人会来救我了。我知道,菲比的妈妈此时正催着她赶快上路。她也绝对不敢坦白,她带着我来教堂了。我不再抱有希望。没想到,我第一次出门就陷入这么悲惨的境地。
我不太乐意回想接下来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到底过了多少如此艰难的日子。我只知道,即便面对大火和海难,我也没有这么痛苦过。这里冷得可怕,我觉得自己的手脚都快冻裂了。屋外寒风肆虐,整个屋子都被吹得咯吱作响,就连屋梁也不例外。门厅那边,一根旧钟绳来来回回地晃悠,发出沉闷凄凉的声音。
这里居然还有蝙蝠!我可从来没想过会跟它们待在一起。更难以忍受的是,有一只蝙蝠在普雷布尔一家人坐过的长凳边的角落里住了下来。要知道,那里离我仅几英尺远啊。那家伙白天把自己挂在一个灰色的球里,晚上呼扇着大翅膀到处飞。我害怕极了。有时,它飞得很低,翅膀都快碰到我了。我看到它那双小黑眼睛在黑夜里发出幽光,它还有尖尖的爪子。我希望那东西永远不要碰到我。我旁边有一本插图版《圣经》,不过这也帮不了我什么。《圣经》是摊开的,我正好能看到一幅可怕的画面:一只大鱼正把一个人吞进嘴里。当时,我认为我俩都很不幸。
一天,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感到特别激动。是教堂的执事在做日常巡查,看是否一切正常。我心里又重燃希望。但是,我要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我身处长椅下一个隐蔽的地方,周围是《圣经》和脚凳。更糟糕的是,我一个指头都动不了。我有必要对此做出解释:当初老货郎只给我雕了两根大拇指,每只手上其余的四根指头是固定的,就像连指手套一样。这样一来,我就只能靠脚了。但我的脚是钉在腿上的,而且我没有膝盖。不过,我的腿和身体是用钉子固定的。如果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的话,还能勉强动一动。这是我唯一的办法。所以我拼尽全力不停地抬腿。
咚!咚!咚!我被自己发出来的声音惊呆了。这声音在教堂里形成回声,听起来有点恐怖。执事尖叫一声,立刻把手上的扫把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丢到一边。他迅速往外跑,直奔后门而去,一不留神还撞上了几排长椅。他边跑边恐惧地大喊:“管他是不是鬼呢,我可不想再待下去了。”虽然自身难保,但一想到我的两只木头脚居然可以把他吓成那样,我还是忍不住有点小骄傲。
我应该庆幸,菲比不是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孩子。这个星期还没过完,她就承认自己没有遵守规定,把我带到教堂去了。她一再保证,如果能把我找回去,她愿意接受一切惩罚。于是,她被勒令照图样绣一幅特别长的十字绣。而安迪和老货郎则来找我了。
我难以用笔墨形容重新回到家时的那种高兴和激动。就连普雷布尔家壁炉里的火光,在我眼里也变成了世上最温暖最活泼的。炉火温暖着我的身体,也让闪闪发光的水壶和盘子愈发光芒四射。炉火让菲比的额头更加光洁漂亮。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啊!我低下头来,看到她正在帆布上用十字绣绣上名言:
说出真相或许痛苦,但能让人更加圣洁。
谁执意与真相作对,就没有真正的朋友。
我和菲比牢牢记住了这段话。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她妈妈强调,只有绣完最后一个字母,并且让她满意,菲比才能跟我玩。菲比需要很多天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几天里,菲比暗暗哭泣了好多回。可以说,这段话是她用眼泪和线一起缝制完成的。
我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同情地看着她。这对小女孩来说是一个教训。当听到菲比的妈妈不停地向她灌输为人要有良知、要遵守诺言之类的话时,我暗自庆幸自己只是一个娃娃,不必如此循规蹈矩。菲比对着绣样唉声叹气,我想,她肯定也希望自己只是个木头娃娃吧。
这一年,缅因州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三月中旬才开始慢慢解冻。一个月以后,道路依然一片泥泞,马车和货车都还无法上路。就连柳条都迟了几周才开始抽绿。五月份到了,安迪才能用柳枝做哨子。几乎一夜之间,普雷布尔家门前的丁香花都发芽了。马路对面的小树林里,紫罗兰、雪莲花和细辛竞相开放,满眼都是黄色和蓝色的小花朵。当然,还有五月花。不过,这得看你会不会找了。安迪和菲比就能找到。此后,我也经常在花店的橱窗里看到它们。不过,后来看到它们的时候,花儿都被笔直地包扎在花束里,与此时此刻漫山遍野自由绽放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路刚一通,老货郎就带着他的包袱和菲比的妈妈为他准备的一大袋食物出发了。菲比把我抱在怀里。她和安迪一直陪着老货郎走到三岔路口。老货郎走上了通往波特兰的路。菲比与安迪就在这里与他告别了。
老货郎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他的包袱很重,把一边的身子都压弯了,就像被大风吹歪的树一样。就要转弯的时候,他回头朝我们挥挥手。安迪和菲比也向他挥手作别,直到他远远消失在视线之外才停下。
如果不是由于菲比的爸爸马上就回来的缘故,我们肯定会觉得非常孤单的。他事先没打任何招呼,突然出现在丁香花丛中。他从波特兰一路驾着双轮小马车回来。马车前面被盒子、货物,还有航海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他还带回来许多其他的宝贝,比如丝绸、花呢头巾、象牙雕塑、珊瑚、鸟的标本,以及他途经每个港口时搜集的小玩意儿。我很想知道,如果亨特小姐看到这些东西会说些什么。
普雷布尔船长身材高大。普雷布尔太太经常骄傲地对别人说,他穿上鞋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呢。他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明亮的蓝眼睛。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几乎闭上了,只有眼角渗出一些光线,就像老图片上太阳的光芒。他很爱笑,在菲比讲话时笑得尤其厉害。这笑声很特别,好像是从他的大靴子里产生,一直往上涌,涌到嘴里才“哈哈哈”地冒出来。
当他亲吻菲比,并且把菲比高高地抛过头顶两三次,看看菲比到底重了多少的时候,菲比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的娃娃,西蒂。”接着,菲比就开始对他讲老货郎,讲那块花楸木,讲我如何在教堂的长凳下熬过一段日子。普雷布尔船长听完后大笑起来。他笑得太剧烈了,以至于衣服上的纽扣不停地跟着他上下颤抖,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小船一样。
普雷布尔太太看了,在一旁直摇头:“丹尼尔,这没什么可笑的。你这样宠着她惯着她,没几天她就会像只学舌鸟一样了。我平日里总是想尽办法好好地教她。这样一来,全白费了。”
我一直记着她的话。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学舌鸟到底是什么鸟。我也没有听到现在的人们提起过这种鸟。估计多年前,这种鸟就已经灭绝了。
第二章 上天入地,还好最后回来了
这个夏天我们过得很充实,如果都让我写下来恐怕篇幅会很长。我们坐着普雷布尔船长的轻便双轮马车到波特兰、巴思和附近的农场四处旅行。我们还驾驶着南瓜色的旧渔船远足。船长还教安迪驾船呢。天气晴好的时候,亲友们经常到我家来玩上一整天。在北方,这样漫长澄澈而又阳光明媚的白天是很少的,花儿似乎一股脑儿都开了。当毛茛、雏菊和恶魔草开得正艳的时候,野玫瑰含苞待放。然后就到了安妮女王的花边和一枝黄花绽放的时候。很快,大量浆果成熟。人们都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特别是对野浆果树而言。老实说,就是这些树害得我差点就被弄丢了。
事情是这样的:普雷布尔太太让我们去多摘一两升浆果好储藏起来。安迪和菲比决定去附近的那片树林采摘,就在路边,几天前我们刚去过。安迪带了一个大大的木底篮子,菲比把我放在小篮子里也带了去。等摘到野浆果,我就让位。她在篮子里铺上车前草叶,我感到无比凉爽舒适。那正是七月底的午后,我在这片小天地里怡然自得。当时,我无比庆幸自己是个木头娃娃。天知道,我很快就不这么想了。
我们到达那片树林之后,才发现已经来迟了。灌木丛不知被谁弄得东倒西歪,一颗野浆果都没有了。正在我们失望地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安迪想起来了:“海岸那头还有一片浆果树呢。我们赶到后湾那头,沿着海滩走到树林里就能看到。那些野浆果有两个大拇指加起来那么大呢。”
“但是妈妈不让我们离开大马路啊,”菲比提醒他说,“至少不能走到看不到大路的地方去啊。”
“可是,”安迪一旦拿定主意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是她让我们出来摘野浆果的,对吗?如果只待在这里,我们根本就摘不到。”
这话一点不错,菲比很快就将妈妈的话忘掉了。我们即刻便向后湾走去。通往后湾的路并不好走,要穿过一片茂密的云杉树林,林中只有一条窄路。
安迪对菲比说:“昨天晚上我听阿布那?霍克斯对你妈妈说,这附近又有印第安人出没了。他说那是些帕萨马科迪人,有好多呢。他们弄了一些篮子之类的东西卖,但你可千万不能随便相信他们。我们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到他们。”
菲比不禁打了个寒战。“我怕印第安人。”她说。
“快点吧,”安迪催促道,“我们不过是去后湾而已,还要走上好长一段石头路呢。”
这段路可真难走啊——特别是被烈日暴晒了好几个小时的那段石头路。菲比虽然穿了拖鞋,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一路。更惨的是安迪,他还光着脚呢。他不得不一边叫着一边跳脚,甚至不断跳到水边给自己降温。他们费力走了好久才到摘浆果的地方。菲比把我安顿在错综复杂的老云杉树根之间,让我能看到他们。不过,有时候他们走入很高的荆棘丛中,我就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了。他们的脑袋像一黄一红两个苹果,跳跃在一片浓密的绿荫之中。
后湾充满安宁祥和的气氛。云杉树的根部斜插进水中,黑色的树冠如数百支利箭射向天际。大海湛蓝一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远处的奶牛岛上,浪花扑打着海岸。空气中充斥着蜜蜂和鸟儿们欢快的叫声,夹杂着惊涛拍岸的声响,不时还有安迪和菲比彼此喊话的声音。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娃娃能像我此刻这样惬意吧。
突然之间,猝不及防,我听见菲比一声尖叫:“印第安人,安迪,印第安人!”
我看到她指向我身后的树林,她和安迪瞪圆了双眼。可惜我看不到什么印第安人,因为我不能扭头。安迪抓住菲比的手朝反方向狂奔而去。他们没命地沿着满是鹅卵石的沙滩跑,把野浆果撒得遍地都是。我只能听到菲比的惊呼。起先,我不相信他们竟然把我忘了。可事实就是如此。孤零零地傻待在那里真是可怕极了。身后传来树枝折断及一些人大声嚷嚷的声音,可他们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感觉无比恐怖。
这其实不过是五六个来采浆果的印第安女人,她们穿着软皮平底鞋,戴着串珠项链,披着毛毯。没有人发现树根中的我。我看到她们将东西不停地装到自己编的篮子里。她们看起来肥胖而和善,不过皮肤确实很黑,头发不大整洁。其中一个的背上还绑着一个印第安婴儿。他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从毯子里往外看,就像啄木鸟从树洞中探出头来一样。等她们装满果实从我身边原路返回时,已经差不多天黑了。
我暗自思忖:现在安迪和菲比应该会回来找我。然而,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我开始变得有些不安。此刻天空中布满了绚丽的晚霞,海鸥一群群地飞向奶牛岛,晚霞为它们的翅膀镀上了金边。如果我不是如此狼狈,这情景应该是无比美妙的。我突然觉得自己实在是渺小无助。不过和接下来发生的事相比,这简直不算什么。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我甚至都来不及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下午我都听到乌鸦叫,但并未意识到乌鸦事实上近在咫尺。我对乌鸦并不陌生,普雷布尔家附近有很多。当它们“哇哇”地聒噪时,我并没有提高警惕,直到我突然发现有一只乌鸦就在我的脑袋边上。此时天还没有黑,远处还是金色的。与此同时,我被一团莫名其妙的黑暗所笼罩。而且这团黑暗是带有温度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这还不算什么,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自救,脸就被一张尖尖的嘴巴啄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邪恶的一双黄眼睛正向我逼近。“哇——哇——哇!”
虽然我是用非常结实的花楸木做成的,我依然非常害怕这样的袭击。我想这次肯定完了。如果能把脸埋到苔藓里,看不到乌鸦这残忍的表情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乌鸦并不一定是真的残忍。乌鸦天生就是黑色的,有尖尖的嘴巴,这怨不得它们。不过,它们对抓到的东西应该温柔一些才对。显然,这只乌鸦尝试几次后,发现我根本就不能做它的食物。它更大声地叫唤起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不过,它并不打算就此放过我,琢磨着用我干点别的。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手腕被提起,整个人都升到了空中。我努力地想紧挨着苔藓和树根,但无济于事。后湾、云杉树林、浆果林都逐渐在我的视野里模糊起来。我的裙子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整个人被乌鸦带着忽上忽下。
“这下肯定没救了。”我想。我做好了随时粉身碎骨的准备。
不可思议的是,天意弄人,乌鸦居然也捉弄人,最终我停了下来。惊魂稍定,我发现自己在松树顶上一个又大又脏的鸟巢里,一抬头就看到三只小乌鸦好奇地盯着我看。一只乌鸦就够我受的,这下竟来了三只。它们虽然不如乌鸦妈妈那么大那么凶,可嘴巴就没合拢过,成天吵着要东西吃。我很快就开始同情乌鸦妈妈了。它每天都必须为孩子们寻找大量的食物,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很快就会被吃光,孩子们又开始“哇哇”大叫,乌鸦妈妈不得不再次出发觅食。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好食欲。不过我有的是时间慢慢见识,因为我在这里足足待了两天两夜。
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这个鸟巢本来够大了,但是对于三只精力充沛、羽翼即将丰满的乌鸦来说,这里就太小了。它们对我推来搡去,又啄又撞。雪上加霜的是,乌鸦妈妈也收起翅膀挤了进来,把我压在最下面,几乎窒息。小乌鸦们的爪子和窝里的树枝也不放过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度过第一个夜晚的。
天终于亮了,乌鸦妈妈出去觅食了。以前我总是透过美丽的玻璃窗看日出,现在我则在高高的松树顶上一边欣赏日出,一边感受鸟巢随风轻摆。人一旦随遇而安,总能感受到一丝美好。我一边惬意地摇晃着,一边想办法应付着小乌鸦们的挤压。我努力在树枝间扎稳脚跟以免被挤出巢。渐渐地,我学会了变换位置,还懂得了如何爬高一点,以便从鸟巢边缘向外看。第一眼可真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也不敢从这么高往下看了。正因为如此,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里离家其实很近。事实上,我家近在咫尺。因为乌鸦把我叼到了普雷布尔家旁边的那棵松树上。当我看到炊烟从熟悉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老马查理在牲口棚边吃草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最初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不久,我发现情况似乎更糟了。看着普雷布尔一家在树下走来走去,听着安迪和菲比的声音,而我却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这简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折磨。与此同时,来自小乌鸦们的虐待依然在继续。随着夜幕降临,我感到更难过更孤独。
太阳落山时,我从松针缝里看着日落,倾听风从松针间呼呼刮过的声音。如果我对回家不抱希望,可能会觉得无比美妙。而此时此刻,情况完全不同。我看着普雷布尔家烟囱里升起蓝色的炊烟,知道他们正在大壁炉里做晚餐呢。很快他们就会围坐在桌前享受晚餐了,不过没有我的份儿。
“如果菲比知道她的娃娃现在的情况一定会失声痛哭的。”我闷闷不乐地想着。小乌鸦们又开始挤挤闹闹了,我不得不从树枝中间伸出胳膊。小乌鸦们正变得越来越烦躁。它们把我挤得没地方待了,我不得不考虑离开这里。
夜幕降临,星星又大又亮地挂在天幕,如同黑暗中闪烁着的雪白水晶。我几乎感到绝望了。这种感觉比乌鸦的翅膀还要沉重,比夜晚还要黑暗。“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给自己发了最后通牒。我宁愿摔成木屑,也不愿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
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赶在乌鸦妈妈回来之前采取行动。因此我开始努力向鸟巢边缘挪动。我承认,斜眼向下看,明白自己必须纵身跳下黑不见底的深渊时,我恐惧极了。我记得这棵树下有一个大大的灰色石头,我和菲比经常坐在上面玩。那一刻,我灰心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给自己打气。这是普雷布尔船长的座右铭。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将这句话默念了好多遍。“毕竟,我不是普通的木头做成的。”
如果我能够选择角度往下跳,或者先伸一只胳膊再伸一条腿,事情肯定会容易得多。不过很遗憾,我做不到。因为我的四肢要不就都不动,要不就一起动。
“哇——哇——哇!”乌鸦妈妈马上就回来了,没有时间犹豫了。幸运的是,小乌鸦们也听到了妈妈的叫声。它们围着鸟巢粗鲁地拍打着翅膀,弄得我想待也待不了。我伸出两脚,两手跟着也出去了。扑通!我从鸟巢边缘滚了下去!
我犹如掉进了无底深渊。尖锐的松针和松果扎着我的脸,锋利的树枝撕扯着我的身体。我就这样一直往下掉啊掉。对我来说,这简直比从月亮上掉下来还要远。终于停下来了,我以为自己掉到地上了。可是,我的周围依然布满了松针和树枝。我伸长胳膊,并没有触摸到让人心安的土地。
天亮后我才发现,这个新地方比原来好不到哪儿去。我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落到松树下,而是挂在了树枝上。我就那样头朝下悬在半空中,衬裙遮住了我的脸。这种不淑女的姿势让我羞愧无比,甚至忘记了因此而带来的不舒服。而我却无法改变这一切。准确地说,我根本动弹不得,因为我被紧紧卡住了。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我很快发现,虽然我能把普雷布尔家里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但在别人眼里,我和松果没两样。这棵松树非常高大,树的下半部分几乎没有树枝,没有人会往树上找我的。所以,我头朝下地挂在树上好多天,经历风吹日晒雨淋也无人问津。我经常看到菲比在我下面走来走去,甚至坐在那块大石头上,而我投下的阴影正好落在她的鬈发上。悲催的是,我无法让她抬头看看我。
我悲伤地想,也许我会一直挂在这儿,直到衣衫褴褛,又或者直到菲比长大,不再需要娃娃。我知道她非常想我,我听到她对安迪说过。安迪也向她保证一定会再去浆果林找我。他们确定我是被印第安人带走了,菲比为此更加不安。而我,不过就在他们头顶上,衣裙覆面,就好像撑着一把伞。
造化弄人,最后还是乌鸦让我们团聚了。我从鸟巢逃走后没几天,它们就尝试着自己飞了。它们扑腾翅膀的声音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当然,我也从未跟乌鸦这么接近过。普雷布尔太太说这声音让她心烦意乱。安迪则花大把的时间用弹弓瞄准它们。虽然他一次也没有打中,但是那些乌鸦的动静大得就好像被击中了一样。终于有一天,他在松树下瞄准就绪时看到了我。大概是我的黄裙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但他还是很花了一点时间才琢磨出我到底是什么。
他终于认出了我。只听他高声尖叫:“菲比,快来看树上有什么!”他丢掉手里的弹弓去拉菲比。很快全家人都聚集在老松树下,讨论如何让我安全着陆。这可是个大难题,因为树干太粗壮了。即便普雷布尔船长把安迪架在肩膀上,也没办法让他爬上来。当然,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我挂在高高的树梢上,似乎只剩下砍树这一条路了。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普雷布尔太太的坚决否定。她说这棵树是镇宅之宝,就像黄铜门把手和松木衣橱一样古老。安迪试着往上扔苹果,但我被紧紧缠住,毫无作用。他们当然不敢用石头扔,怕伤到我。此时此刻,我真要绝望了。
普雷布尔船长离开了一会儿,等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刚削好的桦木棍子。棍子倒是够长,但他和安迪费力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依然纹丝不动地卡在那里。后来,菲比的妈妈一手拿着叉子、一手端着一盘甜甜圈出现在厨房门口。普雷布尔船长灵光一现:“你倒提醒了我。我可以试试把叉子绑在棍子上,也许能把她给钩下来。”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大叉子绑好了。尖尖的叉子在我身边挪来挪去,真够吓人的。不过我可没有心情挑三拣四的。当那比乌鸦爪子还要尖锐的叉齿戳向我时,我毫不退缩。随后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终于从树枝上被解救出来了。
他把我放到菲比手上时笑着说:“又多了个捕鲸的方法。”他把叉子还给太太时说:“叉子又多了一种用途。”
安迪告诉菲比:“真想不到啊,肯定是这些乌鸦把她从后湾带过来的。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人们说乌鸦是可恶的小偷呢。”
菲比高兴坏了,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更不会为此伤神。而我呢,真愿意就这样永远待在她的膝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