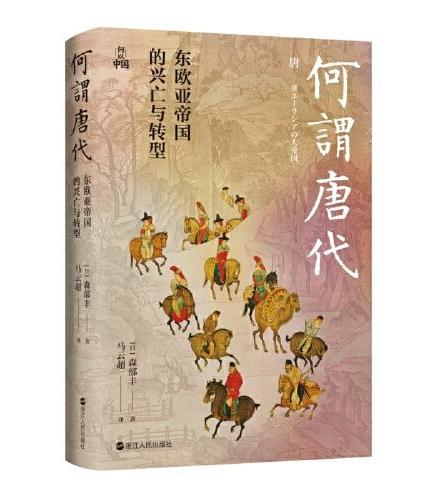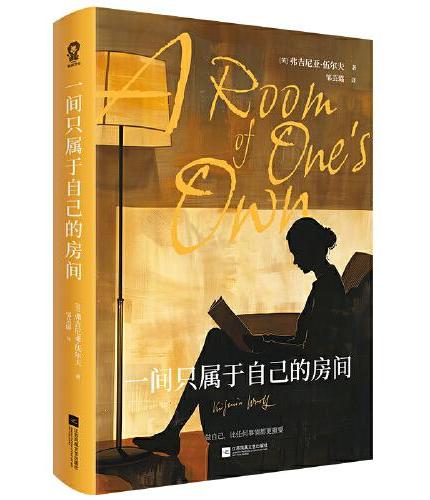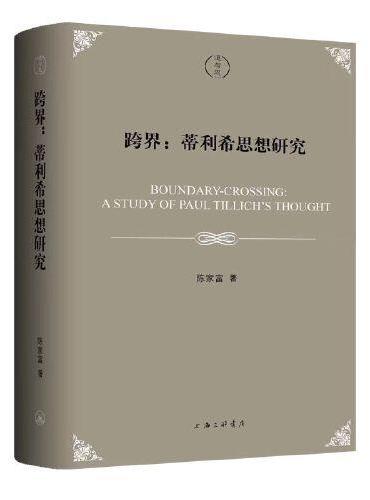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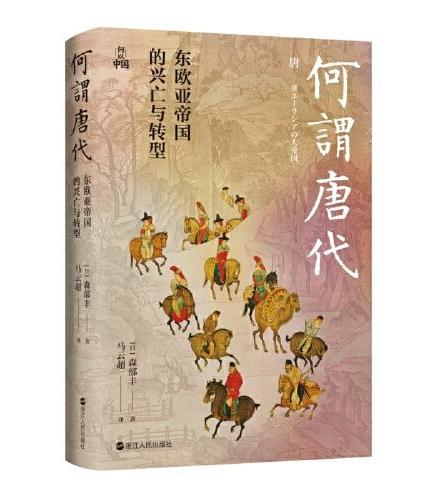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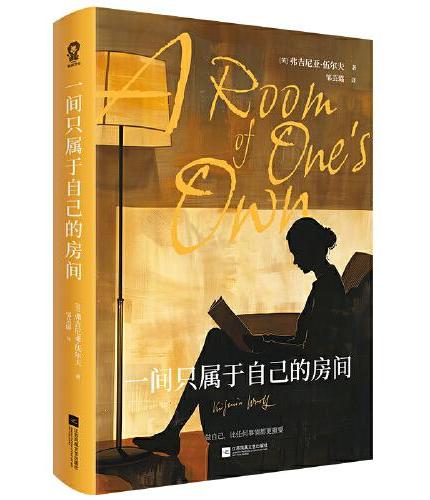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4.6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4.2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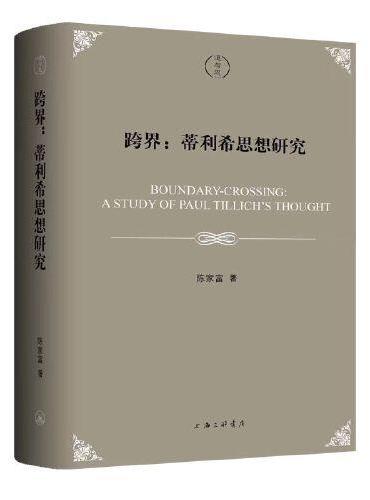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2.0
|
| 編輯推薦: |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优秀散文集。在书中,作者带着成年的疑问去回忆童年的点滴故事,在家族、乡土、城镇、社会的广阔画幅中,描绘了时代的变迁,涉及了传统、亲情、教育、文化等诸多话题,是一部画面温暖而思考冷静之作。
新锐散文作家李晓君的诚意之作!诗意,唯美,纪实,哲思,带你一同追忆流年似水的童年
|
| 內容簡介: |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着眼“爱”的主题,深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对童年记忆的深入挖掘中,展示了一个江南城镇的历史风貌和风俗人情,以及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景;探询了一代人成长的隐蔽命运以及时代变化的显性与隐性特征。
作者以诗性和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六○、七○年代人的共同记忆,对传统文化、后革命记忆、亲情伦理、小镇生活,有着锐利而精准的表达。其深挚的情怀,富有现场感的追述,为当代人的精神蜕变留下了一个生动的“侧影”。
|
| 關於作者: |
|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江西莲花人。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十月》《钟山》《天涯》《大家》等,逾二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暮色春秋》等。
|
| 目錄:
|
目录
出生地
梦,和另一个梦
鹬鸟,或河边的行走
自我的囚禁,以及小故事
画画的乐趣超越了现实
菖蒲的夏天
马厩以南
阁塘冲、破落的军官和养蜂人
溯流而上
家族的忧伤
时光中的母亲
欢 愉
父亲的医院与晚年生活
空 山
酿酒厂里的旧色县城
我们县城的疯子
陀螺的舞蹈
寂 寞
夏 天
小镇医生
一个邻居
老宅、婆婆和其他
电影记忆
广场上的月亮
毛主席纪念堂
黑夜中的隐者
性别意识
劳动的乐趣和对劳动的逃避
我的理想
来自大山的客人
对英雄的崇拜
镜中世界
父子之间
沿着河流往回走
冬天的感受
美的最初体验
街道生活
所有人的童年都是相似的
词语和证据
命运·时代·文体 冯仰操
|
| 內容試閱:
|
梦,和另一个梦
有一日午睡时,我梦见回到了上街的老宅,看到邻居老陈—一个卡车司机同时是我的养父(我出生时,按民间的说法要“躲母”三日,便认老陈夫妇作养父母),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他脸上遍布那个年代的雾气。他吐掉嘴里的“大前门”,用缠着胶布的粗笨手指按了按喇叭。我茫然地抬起头来,用无辜的眼睛望着白花花的阳光,我的脸有一边已经红肿了,那是噩梦烙下的印痕。我看着桌面,上面只有木头的纹理、几块木板拼凑形成的缝隙,一只苍蝇正挣扎着从里面翻身。窗子外面,喇叭里正在播放高亢的乐曲。
白杨树在孤寂而疯狂的年代里静静生长,有的被锯断了,留下一个个树墩子。有几次,我和母亲走在公路上—天知道我们走了多远的路,我们在树墩子上坐下来休憩。那时候母亲依然年轻,她握着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白皙细腻,一点不像现在皲裂苍黄。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像是生怕我会飞走似的。这一对母子,坐在公路旁,眼睛毫无内容地望着前方的田野、村庄和天空。旧公路一直延伸着,看不见它的尽头。公路没有浇黝黑的沥青,白亮的碎石和沙砾铺在上面,疾驰的卡车经过时,不时溅起一些石子。飞起的石子速度惊人,它们“噗噗”地射到旁边的田野里。
我仿佛睡着了。一只蜘蛛在我头上徒劳地奔忙着—它的乐此不疲,激起一个孩子莫名的恼怒,他随手捞起一件物什,将蜘蛛连同它的网从半空中挥扫下来,再狠狠地踩上一脚。在这“扑哧”的声音里,仿佛听见另一个声音:“命运”。我望着天上的云翳,以及它们下面移动的暗影—影子在大地上匀速移动,事物在暗影里呈现出一种辽阔的悲怆感。
离县城不远有座玉壶山。灰黄的山冈像是一个怪物—它背阴的一面,被人为炸出一片嶙峋的口子,人们不断地从里面掏出矿石,直到有一天将它完整地雕塑成一个镂空的建筑。山坡上有一个寺庙,佛像已被推倒,看庙的人已不知所终。曾经,我爬上山,在寺庙的石柱和祭坛上攀缘,看见细长的公路连着棋盘般的县城。我和同伴站在山冈的寺庙旁,就像古人才能体会到的那样,感悟到一种超度人世的平静。我们将手拢在嘴边,朝着山下大声叫喊。我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像片片飞絮飘浮在空中。我们沉迷于这幼稚的把戏,但除了空洞的山冈,没有谁会听见我们的胡乱呼喊。
我老是做梦,梦里有一个院子,我相信从来没有去过。但现在它出现在我面前,带着一种我仿佛在其中生活多年的气味。院子里,梧桐树叶腐败不堪,锈铁丝上垂挂着冰冷的冬雨,抹着石灰的砖墙已经发黄,爬满了水渍和霉斑。整个院落空无一人,但走廊里的白炽灯却亮着,木板楼梯上响着仿佛刚刚离去的脚步声,糊在书桌前的报纸,上面留着十几二十年前一个年轻人的指纹—他糊上报纸以后,转过身来,心满意足地将房间打量,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枝叶横陈的法国梧桐,树叶掉了一半,堆积在水洼里,剩下的一半挂在枝头,抖瑟着,摇晃着,枝杈间布满了铁灰色的寒气。屋檐上的水落在台阶上,转而流到下面的水沟里去。院子靠近洗手间的地方,挂着一件白色背心。
我充满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像走进一个不存在的时空中。一切都是静止的、脆弱的,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哗啦”地倒塌下来。我仿佛感觉到某个神秘的女人在此生活多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脑子很快浮现出我的老师来—语文老师是个漂亮的少妇,穿质地很好的裙子,扎一条不长的辫子,说话软绵绵的。她的先生是个穿白西装、打领带的英俊男人—这样的装束,在那个年代是多么令人惊奇啊!仿佛一个小学老师那样的女人,在这个院子生活多年,这个院子安安静静的,女老师也是安安静静的,但我又觉得她的内心是五彩斑斓的。她有一颗热忱而不安宁的心。
我仿佛又睡过去了,在梦中,我看到不知在哪本画报上看过的照片:一个陌生的广场,有着无与伦比的雕像,马的头部嘶昂、前蹄腾空,手拿盾牌的武士眼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喷泉后面是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阳光照在青铜马头……而我是在哪里?我从午睡中抬起头来—我仿佛有着永远睡不完的觉,永远,我要从巨大的甜蜜和空虚中抬起头来,梦中的奔跑戛然而止。我永远坐在黄昏莫名的寂静中,听见飓风响彻荒原……
我永远独坐在世界的寂静中。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们,他们都去了哪里?阳光照耀着大地上的事物,照耀着山冈、平原、河流和树林。我的影子和树木纵横交错的投影纠缠在一起。我的呼吸,混合着泥土的呼吸。
我来到大街上,看见几辆马车停在车站那里,赶车的人坐在黄昏里吸烟。这几匹马:瘦弱、肮脏、有气无力,看上去跟几条老狗差不多,可是照样若无其事地在昏暗中打着响鼻,漫不经心地甩着尾巴驱赶蚊虫。在我的注视中,三三两两的少年,从各自的屋子里出来了,他们满不在乎地沿着街道溜达,嘴里大声吆喝着,一副称王称霸的狠相。我看见他们的父母、姐妹也出来了。他们的父亲一脸坏笑的样子,他们的母亲嘴里永远骂骂咧咧的,他们的姐妹勾肩搭背,天知道她们迎风怒放的花季会遇到怎样的凶险。
我坐在黄昏里,坐在一个仿佛布满栅栏的局促的空间里。母亲过来安慰我几句,又继续在厨房里忙碌着。昏暗的白炽灯在屋檐下摇晃,墙壁上的影子也在摇晃,我觉得我的头被眼前的东西晃晕了。我继续躺下来,星空在蚊帐顶上浮现,我的思绪又被带到乡村夜晚的田野。我从记事起,每年都有大量的时间到乡下的亲戚家去。
我总是忽略母亲的存在,更愿意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母亲与我,就像黄昏的太阳对于早上的太阳,它们本身来自一体,却永远不会相遇。我的长相、脾气与母亲极为相像,通常在她眼里,我简直就是外祖父的化身。外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因此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大约从我懂事起,母亲就不再把我看作是个小孩—在她眼里,出现的是一个老人和小孩的双重形象。我觉得我的童年结束得比其他的孩子都要早,当我羞怯地向她发出乞求,我觉得她距离我那么远。而当她俯身向我呢喃,她会感觉,面对一颗过于早熟的心,温存的言语显得多么不合适。我用属于她的父亲的眼神注视着她—我看见她眼睛里的慌乱和羞愧。但是仅仅在一瞬间,我们又恢复了平静。交流的障碍永远横亘在两颗柔弱的心面前。
我像一匹待在厩里的马驹,焦躁、易怒,对栅栏里的生活充满痛恨。唯一的乐趣就是做梦。我有做不完的无穷无尽的梦,我有热烈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然而我却一次次回到大街上去。夏日的大街,太阳晒得路面的沥青在淌着汗水,我的塑料凉鞋踩在上面,必须用很大的劲才能将脚从路面拔出来。通常我走在树荫下的水泥人行道上,夏日正午的大街,我在树下的行走仿如梦境一般。我几乎快要沉睡过去,感觉不到脚下的地面,百货商店的窗玻璃摇晃着,使人晕眩;但我还是在短暂的余暇里瞥见包子店的女主人里的涎水,她睡着了,手里的绿色蝇拍掉在地上,苍蝇趴在白胖的包子上,幸福得快要晕厥过去。玻璃店的师傅还在忙碌,在寂静的中午,玻璃的碎裂声响得那样惊心动魄。一个寻常人家的媳妇,手里端着尿钵子,双眼迷蒙地从家里走出来,她好像刚从午睡中醒来的样子,身上散发着我们赣西女人特有的植物和河流的气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