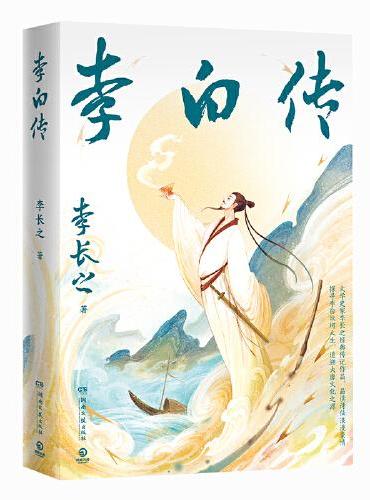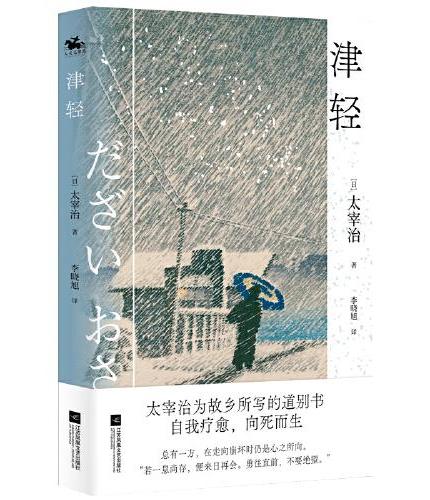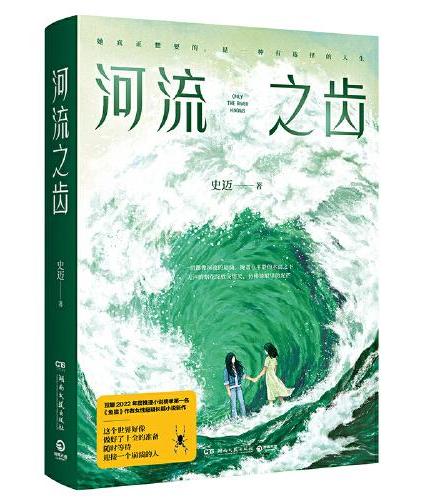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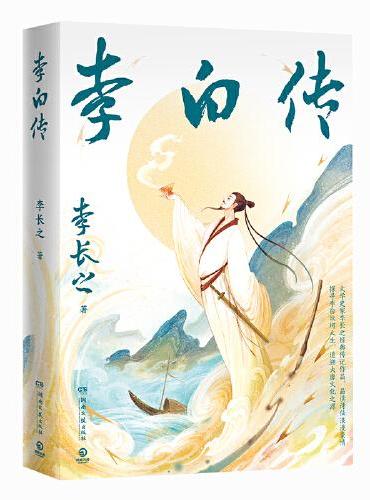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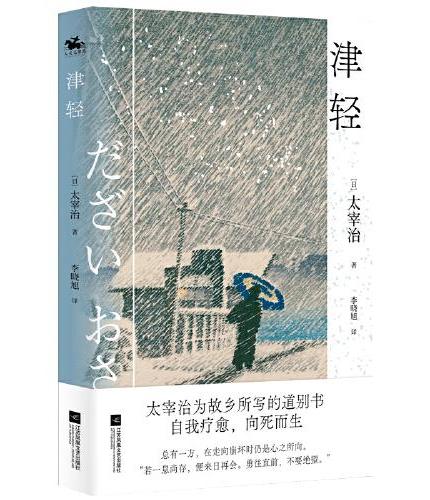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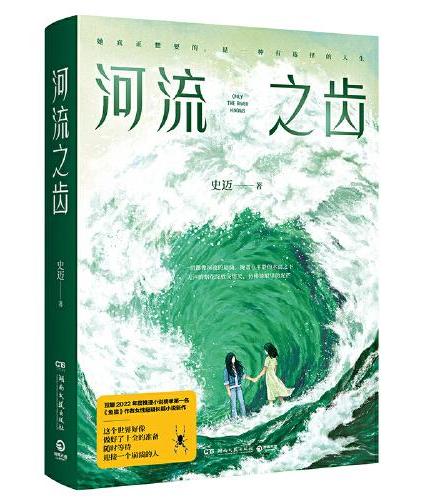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 內容簡介: |
《驴》是一部反思人性与兽性的作品
《驴》是一部民族病态史的缩影
《驴》是一部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精彩写照
《驴》被孟繁华誉为能与世界著名反乌托邦小说比肩的一部中国作品
《驴》很可能是一部历史名作
《驴》是一部非功利的多年潜心之作
|
| 目錄:
|
驴倌
驴圈
红驴
土粮食
小凤英
大闺女
禁坡
派饭
后悔
配种
拉练
情书
侉子
投机倒把
除圈
半拉子营生
贼
抓贼
五金
阶级教育
军婚
蹊跷事儿
记工
口袋
游街
破鞋底子
果实驴
丢人
征购粮
干哕
村里来了个傻娘们
破草垛
惹是生非
威胁
孝顶
分肉
风声
最后交代
最后一面
王吉合之死
后事
尾声
|
| 內容試閱:
|
山村野户里就数叫驴的吼声最响亮了,第一声一下子就蹿到了半山腰,稍候一下紧接着第二声便上了山顶,盘旋几圈儿后拐弯抹角地下到山谷,叫声渐渐消失掉了。
有了这吼声,天便亮了许多,山便活了许多。尤其是放驴归来,驴们挤蹭在戏楼坪上,有叫驴,有草驴,有骟驴,叫驴吼得就更加带劲。叫驴爱冲动,见一个叫别的就随着叫,于是叫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驴吼着风风裹着吼,顺着山沟往上飘,直飘到九霄云外。叫驴一边叫一边还撵着草驴乱跑,叫驴劲儿大,跑来跑去,叫驴便将前腿搭到了草驴的后背上,没来得及做什么事儿,草驴就向前突然一躲蹿,挣开了。叫驴进攻的目标大,不一会儿就跑累了,便挨到墙根儿喘气,身下慢慢脱出那长长的物件来。
有驴叫的地方一定是个村庄,循着驴的叫声走到十里皇沟的沟底就是皇沟村。皇沟东面是座令旗山,山下有九道岭,相传大概宋朝时,村里有一穷人家的爷爷死后埋到了第五道岭下的坡地上,第二年这家的媳妇怀孕了,临产时突然发现房梁上缠着一条长虫,男人见了便拿起一把铁锨捅下那长虫给铲成了两截,刚生出的男婴此时也断了气,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印痕。老人们听他们的老人们说这是真龙现了原形,不该这孩子成事当皇帝,原因是坟前明堂不够三十里;老人们还听他们的老人们说,当时连保国大将都有了,大虎头、二虎头和螳螂手力大无比,能把碌碡举到树杈上,每顿能吃斗米斗面,真龙天子没成事,后来这三个保国大将也就被饿死了。虽然没有出了一代君主,但这条沟依然叫皇沟,这个村依然叫皇沟村。皇沟村被崇山峻岭环抱,公鸡尖细的叫声唤不醒这里的大山,只有驴的吼声才能叫来皇沟的黑夜和黎明。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个特殊的时期,皇沟村发生了许多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驴倌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在驴圈墙上挂着半截铁轨。敲响铁轨是让家户里推碾倒磨的卸驴回圈,因为这轨声大都在早晨七八点钟敲响,所以学校里的学生写作文,大都这样写:“卸驴的钟声响了,我背上书包上学去……”尽管老师批评学生不能这样写,但学生们仍然驴我不分,好像不先写写村里这最洪亮的钟声,作文就开不了头,自己就没法上学一般。让老师熊怕了,学生只得换个角度去写:“一声‘卸驴喽’的喊声,惊得我放下饭碗,急忙挎上书包向学校跑去。”有一个孩子这样写了,别人就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作文里便充满了一片“卸驴”声。
人和驴真是很难分得那么清。就说驴倌儿王吉合吧,有好多人说他是驴下的,跟驴是叔伯弟兄,是头人驴,不过这仅仅是背地里的嘀咕,当着面仍夸他是驴群中跑出来的一个驴人,一个染上了驴脾气的人。
单说王吉合的长相,不值卦钱,就是额头上那七八道“深刻”,也没有多少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倒是他那红色饲养员和红色保管员的红色,让他瘦小的身躯高大了起来,黑黄的脸上放出了亮彩。你别小瞧这个喂驴的,他可是大队贫协会主任哩。再者说啦,驴倌儿也是官儿,管着三四十头毛驴,也够威风的。那年月,推碾倒磨,山村里都得用驴,没驴碾不出面,没面吃不成饭。驴方面的事儿,王吉合说了算,他不愿让你使,说驴病了、已派活儿了,气得你真想把他的丝瓜脖子给拧断,可那丝瓜是红色的,谁敢动。
说王吉合有家也没家,锅碗瓢勺在驴圈,吃喝拉撒睡在驴圈,连德智体美劳也都表现在驴圈里。说他没家不够准当,他确在父亲那里继承下了两间破平房,里面的固定资产有一盘土炕,一盘土锅台,一个圆篓子,三个瓮两个缸,以及多半片席子、少半片毡子。他在家的时候,老鼠串门还礼貌些,只是行走不稳重;从他搬走后,那些老鼠就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进进出出并旁若无人地寄住下了。
这院子五年前并没这么寂静,王吉合的弟弟王祥合经常丝弦梆子地唱着,兄弟俩儿也经常亲娘祖奶奶地骂着,所以这里还算是个热闹地儿。他们的爹娘死得早,谁也没想到吉合祥合兄弟俩还能跟屎壳郎滚蛋一样滚爬成了个人球球。
王吉合是个猴儿脾气,王祥合却是个大闺女性子,会做饭会缝补。祥合到了长胡子的年龄,看上了村里一个闺女,把心事儿闷在肚里却不敢吭声儿,连王吉合也不让知道。等人家闺女过了门儿,祥合在一天早上就赤着屁股跑到街上大喊小叫。王吉合把他弄回家穿上衣裳,他就骂吉合的爹娘,以后见了东西不管脏不脏就吃,见了女人不管是谁就撵着跑,疯得不透气儿。王祥合疯了一年多,后来清楚了些,高兴的时候也给做饭缝洗,不高兴的时候就骂他哥,他哥急了也骂他,好像不是一个祖宗,不是一个爹娘生的。
村里人说王祥合得的是色迷疯。色迷疯是喜欢女人,可王祥合是恨女人,女人都不敢到他家。他还疑心王吉合背着他找女人,只要王吉合一出门,他便跟在屁股后边。王吉合本来性子操蛋,不招女人待见,身后再跟上个疯弟弟,一晃四十大几的人了,又披了张红色的虎皮,把身上的零件儿都快捂出锈绿来了,却连个寡妇老婆也说不下。人们都说他是骡子骨头不留后,王吉合也自认为自家的坟头已经埋到地堾边儿,要绝户了。王祥合在一次疯傻起来一头扎进井里死了以后,王吉合就更没什么指望了。疯弟弟活着他还有块心病害着,去了心病倒觉得空空落落,喂上驴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把自己也归了公。平时除了秋夏把分到的粮食放回家里,再弄出些粮食碾磨吃饭外,王吉合就很少回家走走。院里少有人走动,便长出许许多多蒿草来。
生产队喂牲口的都是两个人,一个白天放驴一个黑夜值班,轮流进行。王吉合生性孤僻寡言,驴鸡巴甩了一样的脸,能拴住驴一样的嘴,要不几天不张嘴,要不一张嘴准能把你撅成几半截儿,把你噎得几天吃不下饭。人们并不想跟他搭伴,但饲养员这个营生实在太让人眼气了,除了自由,关键是能占点驴饲料的便宜,所以只好削尖了脑袋往驴圈里钻,捏着鼻子和他住一个屋睡一盘炕,还得看他的脸色,舔他的屁眼儿,顺毛拂捋他。王吉合是个独槽驴,不是踢就是咬,跟别人拴不到一块儿,而且他还在盛饲料的大瓮里做了记号,除了用粉笔沿着粮食在瓮壁上画一圈外,还要把粮食摊平并在上面薄薄撒一层灶里的柴灰,只要别人稍做手脚,他准能发现,发现了就去队长那里告状,往往一告一个准,就这样在他手里撤换了七八个饲养员,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王吉合说光我一个人就沾,队长觉得他一个光棍儿家也飞洒不了啥东西,从此就没给他配别人,于是驴圈便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
驴圈
驴圈在那个年月可是个要害地方,十几间平房一多半驴占着,剩下的是饲养员的宿舍,并兼作生产队办公室、会计室、记工室、会议室、饲料库,那时叫小队部。其实农村老百姓都不习惯这么斯文,就是小队长召集开会,站在房顶上,双手叉着腰腆着肚子也是这么喊:“一队社员都来驴圈开会喽——”连门口墙上挂着的半截铁轨,也分不清是对驴敲还是对人敲,反正铁轨一响,牲口和人都会马上支棱起耳朵来。
一队驴圈东向房,共有十二间,人占着四小间,驴占着八大间。驴占的八间房,宽8米,长25米,两排柱子中间一米半是条夹道,顺着两排柱子是驴食槽,北山墙处也有一排驴食槽,槽上方横着一根小碗口粗的木棒,拴驴用的;后墙靠着山坡,偏东一点有个陷在后山坡里的石券小窑洞。人占的那四间,宽5米,长16米,生产队一切集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人占的屋和驴占的屋都留有大门口,驴那边的大些,门都是两开扇木板门,门腰有木闩(农村叫插关儿),门顶还有木绊子;两屋中间有道过门,只吊着门帘。人占的房和驴占的房连在一起,统称驴圈。为了区分人和驴占的地方,也把人占的那屋称作“驴圈外间或驴圈外边那间”,把驴占的那屋称作“驴圈”或“驴圈那边”、“圈那边”。
驴圈外间,进门左手是一个大锅台,锅台后面是高高的炕垛,炕垛里面是盘土炕,炕和后墙之间有个一米宽的夹道;后墙冲门口放着一张三屉桌,左边放着一个小坐柜,右边顺墙摆放着五六个盛驴饲料的大瓮;三屉桌上方有个墙龛,龛里贴着一张主席像,龛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桌下、瓮前、墙根墙角放着一些板凳、板床、木墩、石头等物件儿,供社员们来开会或记工的时候坐。
社员们都说一队驴圈拴了条疯狗,人们除了开会、记工、劳动、问驴推碾倒磨等必须去办的事儿之外,很少迈进驴圈的门槛儿,都怕稍不注意让王吉合汪汪几声,甚至咬两口。别看王吉合跟人老是一副棺材面孔,但对牲口们却格外的亲热,嘴里有叨叨不完的话,驴也听懂人话似的冲他啊啊几声,舔他的手,吻他的脸,尾巴欢快地摇摆着。人们都说他是大叫驴转世。
驴圈其实就是十几间普通平房,木梁木檩木柱子,石头干茬墙,墙外白灰勾缝,墙里白土抹面,房顶用炉渣掺着白灰砸成,地面用白土掺着麦秸夯成。驴圈往往连着库房,这一块儿就成了生产队的“武装重地”,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和后来人们的记忆里,驴圈永远是那么高大、宽敞和神圣。
红驴
皇沟村形容一个人抠门,就说这个人把钱穿到肋条上了,而王吉合是把他的驴穿到自己肋条上了,社员们想问个驴使使就像抽了他的筋一样,既怕累着又怕磕碰着,能把你腻歪死了。平日户里碾面、队里干活儿把驴赶回圈,王吉合总是先摘下围脖,卸下鞍子,然后在驴身上摸来看去,没打着伤着才放人走;若是打着伤着了,他就堵住门儿跟你论理儿,脸对着驴骂你、对着你骂驴,直到嘴里嘟噜出白沫儿,白沫儿飞在嘴唇上嘴角上,直到他扎到饮驴水瓮里喝水解渴方才告一段落。出了门儿被骂的人才敢骂他,骂他是集体的一条看门狗。
这天黄昏,“黑鬼”和“弓脊”两头驴自个儿跑回了圈,后边儿没人跟来,王吉合就起了疑心。他给驴卸下驮篓和鞍子牵到圈外,两头毛驴的后蹄子跳来跳去,屁股躲着他不让看,他用手抓紧缰绳,把驴逼到墙角扳过屁股一瞧,驴屁眼儿外全是血,“弓脊”的还在往外滴着血。王吉合赶紧把驴拴到墙上钉的木橛儿上,进屋从鞍子里掏出两把棉花套子划火点着,嘴里还不停地吹着棉花,看燃得差不多了就走到驴后,两手各抓一团猛地上前按到两头驴的尾巴下面,驴疼得后蹄子蹦起老高,王吉合的腿上给踢了两下,他也顾不上疼,瘸着把两头驴拉回圈里饮了水,然后就拴到驴槽上了。
王吉合把驴安顿好后就找到队长家,气呼呼地把情况给队长说了。队长叫歪歪。歪歪说,这谁也挡不住,驴不打出不了槽,驴不打耕不了地,光说好话驴听不懂,你不打它就不知道干活儿,我看既然打了说说以后注意点儿就算了,要是打了吉合叔你,我可不饶他。王吉合说,你放屁,儿女不亲长不成人,牲口不疼活不久,没有驴,就你这生产队长也不顶鸡巴啥事儿,你去驮你去扛啊。一句话呛得歪歪差点得了噎食病。队长惹不起王吉合,赶紧说好好好,明儿黑夜开个会查清是哪个狗日的干的这损事儿,斗私批修沾不沾?王吉合说这么大的事儿能等到明天啊,歪歪说那我马上去广播开会。王吉合得了队长这话也打住心怀了,又叮嘱了队长几句才抬脚出了门。
歪歪随便扒拉了几口闲饭,拿了块菜饼子边吃边往驴圈走。到了驴圈场上,歪歪从地上捡起一块儿石头走到门口墙根儿当当当当敲了几下铁轨,然后爬上房顶叉着腰腆着肚子拉着长嗓大声吆喝道:“一队社员们,马上到驴圈开会喽——”连喊了三遍。
吃过晚饭,一队社员就稀稀拉拉地往驴圈走,不一会儿就挤了一屋子。来得早的占上了座儿,炕上、凳子上、锅台上、大瓮上都坐满了人,后来的有的蹲着,有的靠墙站着,有的到屋外找块石头搬进来坐着。女人们嘀嘀咕咕说笑着,互问吃了什么饭,鸡又下了几个蛋,猪又长了几斤肉,又积了几方粪;男人们大都吸烟,有的叼着旱烟袋吸旱烟,有的把旱烟用纸卷起来吸。烟叶里掺了棉籽油,吸起来冲得很,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不一会儿就把屋子里吸得烟雾腾腾,呛得女人们直咳嗽。
看人来得差不多了,队长歪歪就从人堆里站起来说:“社员们都停停嘴啊,今儿黑夜开个会儿,说说关于黑鬼和弓脊的事儿,今儿后晌干活儿,谁赶黑鬼谁赶弓脊来?谁捅了驴屁眼儿了?”歪歪说到这儿,下面嘻嘻哈哈起来,说歪歪你可真能逗笑,除非那些光棍闲着没事儿去捅驴屁眼儿,有老婆的还嫌那里脏哩。
王吉合当时正在圈那头喂牲口,听到人们起哄,就气呼呼地走过来大声说:“都别鸡巴不正经了,是有人拿棍儿把驴屁眼儿给捅流血了,都还高兴个鸡巴啥?”
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接着,队长一个一个问组长,组长一个一个问组员,不一会就把捅驴屁眼儿的人给追找了出来,一个叫秃爪,一个叫小阎王。队长恼着脸叫秃爪和小阎王站起来低下头,让社员们给他们提意见,批斗他们。出身不好的不气长,从不敢给别人提意见,只是支棱着耳朵听;有几个好事儿的贫下中农就站起来质问他俩为啥闲着没事儿捅驴屁眼儿。
驴
红驴
秃爪和小阎王站到了中间地上,猫下了腰。秃爪说,后晌赶驴往地里送粪,黑鬼磨磨蹭蹭不快走,就折了根棍儿捅驴屁眼儿,捅一下它就快跑几步,捅一下它就快跑几步,后晌还多往地里送了两驮粪哩。小阎王说,弓脊操蛋,躬着个腰不给耕地,打了两鞭子它就卧到地上了,再怎么打也不起来,急了我就拿鞭杆子捅它,它光欠欠屁股不起来,气得我就把鞭杆子一下子插进屁眼儿里了,弓脊跳起来拉着犁满地里乱跑,收也收不住,扔了家伙就往回跑,撵都撵不上,弓脊真鸡巴操蛋,欠揍欠捅。
听到这,王吉合把手里拿着的筛子往地上一摔,大声吼道:“反啦反啦,老虎吃了山神爷了,你俩比鸡巴日本鬼子国民党皇协军特务汉奸还鸡巴不是东西,驴干活儿慢就捅它们的屁眼儿,我看你俩也不是鸡巴啥勤谨人,干活儿拖着屁股不往头儿里走,谁拿棍子捅你们的屁眼儿了?牲口不懂人语,你俩就不说人话、不干人事儿啦?告你们说,打驴就是打它的老子,我就是驴爹驴爷爷驴祖宗,打它们就等于打我的脸。动不动就想动手,动不动就糟蹋牲口,都打死了还干不干社会主义,还革不革命?我王吉合是红保管员红饲养员,我的驴就是红驴,你们这么做不是反动反革命是啥?小阎王你真鸡巴是个阎王爷。”
王吉合一番话,说得秃爪和小阎王张口结舌,镇得人们目瞪口呆,天旋地转,只觉得周围的东西都晃悠起来。晃悠中一个小伙子突然从大瓮上跳下来说:“吉合爷爷,歪歪哥,我有个好主意,以后保准谁也不敢再动驴半指头了。”王吉合扭过脸瞪着眼说:“路宽,你又出啥馊主意啊?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拿破鞋底子扇你啊。”路宽嬉皮笑脸地说:“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如果说差了你再拿破鞋底子扇我也不迟。吉合爷爷,你老人家如果把咱队所有的驴都改成又红又专又革命的名字,看哪个人还再敢对你的驴子驴孙们吱吱声、动动手?”
狗日的路宽,你小子的心眼儿比马蜂窝的窟窿眼儿还多哩。细琢磨这小子的话,王吉合觉得还确实有些道理。散会后,王吉合靠在被子上,把他的驴子驴孙们按脾气、能力好坏和公母性别排了个子丑寅卯,将孝顶、黑鬼、秃尾巴、弓脊、铁耳朵、软难斗、鬼难拿、鬼剃头、滑头、拗到底、大闺女、大混蛋、二混蛋等等脏眼污耳的玍古名字,统统改为革命化的称呼,换成什么火车头、造反派、红卫兵、号角、红小兵、红大嫂、劳动能手、阿庆嫂等等等等。从地主富农分子家归公的驴,大都又刁又懒又不是东西,有啥主儿就养啥驴,就叫一些鸠山、座山雕、胡传魁、刁德一、王连举、蝴蝶迷之类的坏名儿,戴帽改造。
这样试叫了几天,队长歪歪来驴圈找王吉合了,说这么改,农活儿没法干了,有几个懒汉不干活儿光盯着谁打你那红驴了,谁也不敢捅牲口一指头,由着驴的性子来,一天连半亩地也耕不了,连三遭粪也送不够,驴都成了活祖宗了,就差给它们磕头烧香了,光砸戴帽儿那几头牲口的骨头,这队长我没法当了。王吉合火着说,闲着那么多壮劳力剁肉吃哪,留着力气背炕头睡老婆哪,不啃了驴骨头你们就是不高兴,再说驴不听话也可以革它的命呀,只是不能把它们都当成阶级敌人,能不能给驴说些它们听得懂的话?能不能动手轻点儿?告你说驴通人性,人就不能通点儿驴性啦?歪歪苦笑着说,好好好,你就惯着你那些红驴吧,明儿我们干脆都自个儿戴上笼头、备上鞍子、套上犁铧,叫牲口赶着社员们下地干活儿算了。王吉合梗着脖子说,像你们这些人一点儿阶级觉悟、阶级感情都没有,就欠劳动改造,驴还没言声儿,你们倒唧唧歪歪个没完,还不如牲口懂事儿哩。王吉合这些话,说得队长怀疑起他到底是不是大叫驴转世了。
一队社员都这样骂他,骂着骂着就把吉合骂得更红了、名气更大了,公社表扬、大队广播,小道消息还传说县里准备树他为典型,把他的革命行动推而广之、广而告之。惊得好几家被斗户的婆娘忙到驴圈给王吉合送纯萝卜馅儿山药面扁食,还顺手拿些脏衣服臭袜子去缝洗。对这些,王吉合都是半推半就,送来的扁食都让他犒劳了牲口,他不愿落下吃嘴的名儿。向王吉合问驴推碾倒磨的也少了,口粮本来就不多经不住推倒几回,加上他都把驴挂到自个儿脸上了,谁还敢去他脸上抠?婆婆妈妈的缠得没法儿了,他就说喂我点儿好料把我套上吧,蒙上眼跑起来不一定比牲口慢。可谁敢拿驴祖宗耍笑,只好大人孩子齐出动,推着石碾子往晕里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