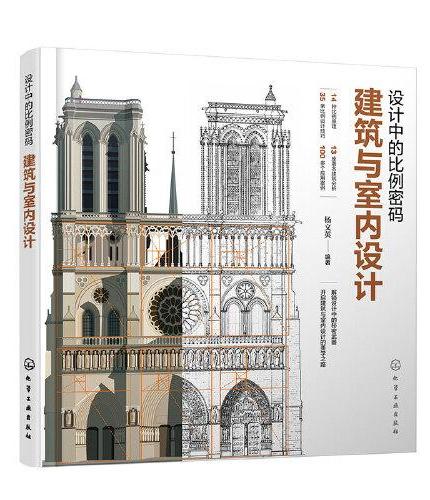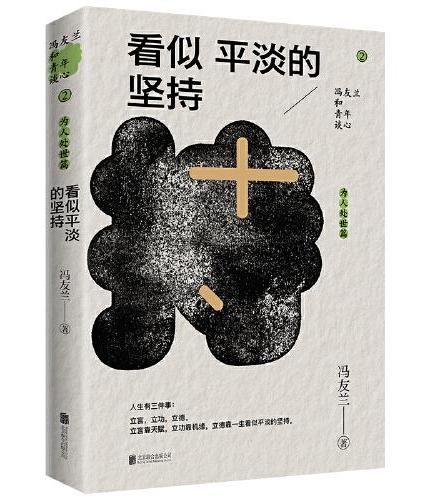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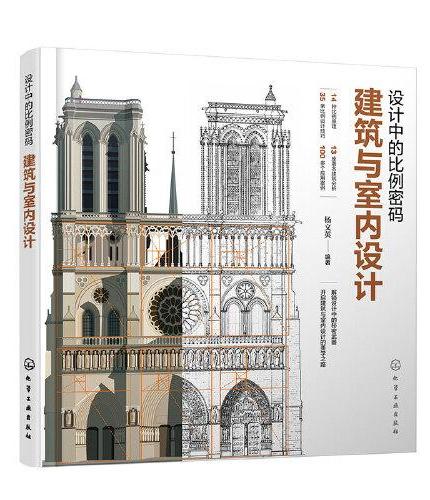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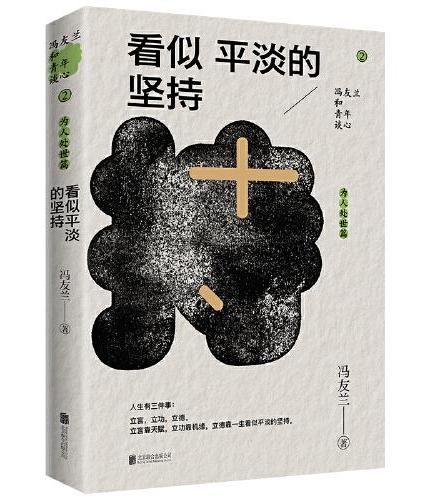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HK$
76.2

《
汗青堂丛书144·决战地中海
》
售價:HK$
168.0

《
逝去的武林(十周年纪念版 武学宗师 口述亲历 李仲轩亲历一九三零年代武人言行录)
》
售價:HK$
54.9

《
唐代冠服图志(百余幅手绘插画 图解唐代各类冠服 涵盖帝后 群臣 女官 士庶 军卫等 展现唐代社会风貌)
》
售價:HK$
87.4

《
知宋·宋代之科举
》
售價:HK$
99.7

《
那本书是(吉竹伸介与又吉直树 天才联动!)
》
售價:HK$
99.7
|
| 編輯推薦: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从晚清秀才到民国教师,从同盟会骨干到“延安五老”,谢觉哉先生的一生历尽了中国现代史的苦难与艰辛。奔波一生,劫波度尽,两位夫人,儿女成群,是革命者,也是有担当的丈夫、有爱心的慈父。时代洪流掩不住涓涓温情,岁月流逝洗不尽如山父爱!
|
| 內容簡介: |
谢觉哉先生,“延安五老”之一,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05年考取晚清秀才,参加革命前在湖南宁乡老家与夫人何敦秀育有四男三女;1937年9月在甘肃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王定国结为伉俪,育有五男二女,并长年抚养亲友们的十多名子女。
本书为谢飞老师近年潜心整理其父谢觉哉先生的家书选编,涵盖谢觉哉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115封家书。书稿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是1920到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老家夫人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文字生动,情感真挚,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乡妻子的惦念、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与对乡亲故友的感怀之外,还涉及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包括军阀混战、延安生活以及建国后的土改政策等,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第二辑是1950至1970年代谢觉哉先生写给王定国夫人及子女的书信,主要内容是夫妻之间的关爱、对子女的教育开导等,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书信中涉及读书、养生、提倡节俭等话题,展现了谢觉哉先生的生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个人原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第三辑是1950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家乡干部和友人的书信,通过书信了解家乡的情况与变化,对于当地干部的浮夸风等不良行为多有批评教育。全书百余封书信,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
| 關於作者: |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 “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部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制定与推行了《选举条例》、《宪法草案》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曾出版著述《不惑集》、《谢觉哉杂文选》、《一得书》、《学语集锦》等;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谢觉哉诗集》等。
谢飞,谢觉哉之子,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副院长、教授,并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电影作品包括《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多次荣获国内外电影大奖。
|
| 目錄:
|
读懂父亲 谢飞I
第一辑致何敦秀夫人、儿女及家乡亲人
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
致王养吾,自宁乡云山(1919年5月2日)002
致何敦秀,自长沙(1921年4月16日、28日)003
致继母等家人,自长沙(约1922年前后)007
致谢式坤,自长沙(1922年9月18日)009
致谢式坤,自长沙(1924年某日)012
致何秋岩,自上海(1928年12月)015
致何敦秀,自兰州(1937年春)017
致何敦秀,自兰州(1937年8月)019
致何敦秀,自延安(1939年9月8日)021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1月26日)025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2月16日)029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6月13日)031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4年1月2日)033
致又大婆婆,自延安(1944年4月21日)035
致何敦秀等,自延安(1945年4月3日)040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6年1月27日)044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6年2月8日)046
致谢放,自山西后甘泉(1948年2月6日)048
致谢放、吴爱春,自河北西柏坡(1948年5月3日)051
致谢子谷,自北京(1949年某日)053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49年9月7日)055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49年10月4日)058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0年1月21日)063
致何敦秀夫人及儿女,自北京(1950年8月15日)066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50年10月4日)069
致谢放,自北京(1950年12月23日)070
致谢谦芳等,自北京(1951年1月27日)072
致谢放、谢子谷,自北京(1951年2月11日)076
致谢廉伯等,自北京(1951年5月25日)079
致何敦秀,自北京(1951年9月7日)082
致谢子谷、谢冰茹,自北京(1952年1月1日)088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2年1月16日)091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2年3月28日)093
致何关淑等,自北京(1952年6月26日)095
致谢谦芳,自北京(1952年10月1日)098
致谢廉伯、谢鲁宜,自北京(1952年10月30日)101
致谢放,自北京(1952年12月23日)103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3年7月9日)104
致谢金圃,自北京(1953年8月7日)106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53年10月6日)109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4年4月16日)111
致谢冰茹,自北京(1954年6月11日)112
致吴岂凡、谢寄祥,自北京(1954年9月12日)114
致吴岂凡、谢寄祥,自北京(1955年3月2日)116
致谢廉伯,自北京(1955年4月21日)118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5年6月22日)122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5年10月16日)124
致谢廉伯,自北京(1955年11月10日)126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5年12月14日)129
致谢凡宣、谢典衡,自北京(1956年某日)132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6年10月16日)134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6年11月26日)136
致潘云冰,自北京(1957年5月17日)138
致姜一,自北京(1957年5月21日)141
致谢廉伯等,自北京(1957年7月8日)143
致谢笠仲,自北京(1958年2月4日)150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8年12月15日)152
致谢群英等,自北京(1960年3月29日)154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61年1月20日)159
致吴岂凡,自北京(1961年5月23日)163
致谢寄祥,自北京(1961年7月1日)165
致谢子谷,自北京(1962年4月26日)168
致谢子谷,自北京(1962年5月15日)170
致谢金圃,自北京(1963年5月23日)171
第二辑致王定国夫人及儿女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
致张曙时等,自北京(1952年12月23日)177
致王定国,自西安(于1956年6月18日来信上的批改)181
致孩子们,自北京(1957年1月30日)185
致王定国,自长沙(1957年3月22日)187
致王定国,自杭州(1957年4月5日)191
致谢飘,自北京(1958年10月6日)193
致王定国,自庐山(1959年3月10日)196
致王桂芳,自杭州(1959年3月27日)199
致王定国,自北京(1959年7月29日)201
致儿女,自广州(1960年1月前后)203
致谢飘,自北京(1960年9月26日)205
致王定国,自福州(1961年2月10日)207
致儿女,自福建(1961年2月28日)210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3月19日)214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4月2日)217
致谢飘、谢瑗,自北京(1961年4月12日)221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4月25日)223
致谢飘、谢瑗,自北京(1961年5月7日)228
致谢瑗,自北京(1961年7月11日)231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7月17日)234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9月27日)236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10月14日)238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10月28日)241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11月11日)243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12月19日)246
致儿女,自广州(1962年1月4日)249
致儿女,自北京(1962年3月8日)251
致谢飘,自北京(1962年5月16日)255
致谢飘,自北京(1962年9月9日)258
致王定国,自北京(1963年1月24日)260
致儿女,自北京(1963年5月26日)262
致王定国,自北京(1963年9月20日)267
致谢瑗,自北京(1965年5月10日)270
第三辑致家乡干部及友人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
致张润清,自北京(1954年某日)274
致尹泽南等,自北京(1956年7月17日)277
致张润清等,自北京(1957年1月10日)279
致李淑一,自北京(1957年4月某日)283
致陶承,自北京(1957年5月19日)286
致李学良,自北京(1957年5月24日)288
致姜国仁,自北京(1957年5月24日)291
致李学良、张润清,自北京(1957年7月17日)293
致姜石梅,自北京(1957年8月8日)294
致云山师范及附小全体老师同学,自北京(1959年7月)297
致汤菊中、严岳乔,自北京(1959年某日)299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0年2月16日)301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0年3月24日)303
致李学良,自北京(1960年10月10日)306
致李学良、张润清,自北京(1961年7月8日)308
致谢岳云,自北京(1961年9月8日)310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1年9月20日)313
致谢岳云,自北京(1963年5月前后)317
附录
一自传谢觉哉321
二六十自讼谢觉哉331
|
| 內容試閱:
|
读懂父亲
谢飞
一
谢觉哉是我的父亲。
在网上查询,对他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
但是,我真正了解我的父亲吗?我到了自己老年时候,才发现对他的了解并不多。2014年是父亲的一百三十岁诞辰,他大我母亲二十九岁。母亲王定国二十九岁时生的我,所以父亲与我的年龄差别是五十八岁,可谓“忘年父子”。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话,我和父亲生活的人生岁月,有着两代多的巨大的时代差距。
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也是少得可怜。1971年6月,当我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记得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我们家人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儿子良翮的搀扶下赶来见老友的最后一面。他儿子手里拿着董老手书的挽联,我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时光匆匆,一晃父亲去世已经四十三年了。我的青壮年时期,欣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忙于开创自己的事业,教书、拍电影;忙于成家、抚育孩子,也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去了解父亲。只是当我自己进入老年,专业和家务闲下来后,才开始去读母亲早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就组织人编写、出版好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等著作,才开始对他的思想、工作、才华以及生活、情感有了些实实在在的了解。
整整晚了四十多年啊,可谓“不孝子孙”!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到了七十二岁,才开始真正“尽孝”。好在还有这句谚语:晚做胜于不做。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在工作之余写作、发表了大量思想文化杂文,享誉社会。1956年12月24日,他在《爱父母》一文中写道:
人,从出生到死即从小到老:中间是“养人”——劳动力强壮时期;两头是“人养”——幼小时期和衰老时期。这是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绝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
记不得是谁说的话也是这一道理:人生三件大事,即结婚、生子、送老人。当你送完老人时,你的孩子就开始送你了。
去年开始,我轮替我哥哥谢飘,搬到母亲家住,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去阅读父亲的著述。母亲王定国也是位老红军,已经一百零二岁了,身体康健,生活基本自理。她最大的愉快是每天看到有孩子们在身边。还是在那篇文章中,父亲写道:
养父母,不只是给他们穿吃、不冻不饿而已,还要有亲爱的诚意和敬意,使老人们感到愉快。
对于早已离去的父亲,我们努力去读懂他的人生、思想,了解父辈们的足迹与悲欢,是后辈的责任与敬意。这些,促使我开始编辑这本《谢觉哉家书》。
本《家书》收集了父亲给家人的九十余封信件,最早的是1919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风后,用左手艰难书写的;我的湖南的兄姐与母亲将多数书信的珍贵手迹保存了下来,实属不易。看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看着父亲从青壮年到老年不断变化的毛笔书法,看着那些信封、邮票,我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电话、微博、微信等的使用,让人们远在天涯如咫尺;过去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思念、担忧、述说的需求与情感全没有了酝酿和表达的空间与时间。它给我们人类的文化与情感带来的是进步还是退化,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好在我们还可以整理出版前辈们的书信,像畅销多年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从中去了解前辈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以至社会与历史。
二
很可惜,没有收集到父亲青年时期给其父母的书信。父亲十六岁时,他母亲病逝;二十一岁时父亲去世。除了父母,家庭的主要成员就是丈夫或妻子,即配偶。现在找到父亲的书信,不少是给他的前后两位夫人写的。
说来有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听说过父亲的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没有见过她;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宁乡,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年纪都很大了,有一位哥哥谢放,1937年5月也到了延安参加革命;知道我们的一些侄儿、侄女,不少比我们年纪都大,许多也在北京上学。后来通过父亲的日记、书信,特别是1984年我拍电影《湘女萧萧》时,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才第一次见到何夫人的照片。知道50年代她也随其小儿子谢放到北京居住,直到1967年,八十八岁,没有吃过一片药,寿终正寝。也就是说,同住在北京多年,我们孩子们却对她一无所知。
编辑和通读了从20到40年代父亲给何夫人的家信,我才渐渐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会如此谨慎地瞒着我们孩子们,才逐步认识到时代的巨大变迁带给父亲的家庭生活的复杂境遇,才最终体会到父亲一生中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显示的理智、温情与人性的光辉。
父亲与何敦秀的婚姻完全是旧中国农村的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一中医世家,其父亲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小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候,父亲曾在何家附近的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的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了这个姻缘。结婚时父亲只有十五岁,何夫人比他长近五岁,妻子比丈夫大四至五岁,是当时当地的习俗。在1939年9月8日父亲致何夫人的信里,曾回忆说:
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
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头十五年中,共同生育了四男三女。
父亲和我母亲王定国的婚姻则是“组织安排”的。1937年,父亲已离开家乡、妻儿十多年了,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父亲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代表。我母亲在西路军战败失散多日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展开了营救失散红军的工作,半年后她也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母亲后来跟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讲(注意,不是直接和我们这些子女讲):那时,组织上说谢老年纪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做时任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协助,希望我母亲与谢老结为伉俪。母亲同意了,但晚上吃饭庆祝后,让她进谢老的卧室,她不干。母亲出身穷苦,小时候做过童养媳,不识字,她说:“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夫妻,她犹豫了,说希望给她时间考虑,她自己在四方面军时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希望组织上帮她打听清楚。后来查清张静波烈士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恋爱、后结婚”时代的现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欢嘲弄、调侃旧时代人们“多妻、多婚”的婚姻情况,而不去了解我们的父辈,以至人类社会很长时期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仔细阅读父亲半个世纪中给两位夫人的通信,我具体地感知了百年来中国人生活形式与制度的复杂存在与变迁,更感受到中国人几千年的“相敬如宾、珍惜亲情”的美好民族传统。
父亲是清朝科举的“末代秀才”,诗词文章,四乡闻名;而两段婚姻的夫人并不是什么“才女”,我母亲甚至还是文盲。母亲曾回忆说,结婚后,父亲写文章时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母亲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父亲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本书第二辑中收集了父亲在母亲第一次提笔给他的信(1956年6月18日)上的文字修改,就是他们教与学的一个有趣例证。在他们相伴的三十四年中,母亲不仅脱了盲,还跟着父亲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成为了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1963年1月,父亲书写了寿诗赠与母亲,祝贺她五十大寿:
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诗文表达了他们这对“先结婚、后恋爱”的伉俪令人羡慕的夫妻情谊。
父亲年轻时还跟着岳父学过一年多的中医。投身革命之后,教书、办报,长年在外。“马日事变”之后,更是与家里断绝了音讯。湖北洪湖、江西苏区、长征陕北,十多年的艰难革命生涯,父亲从来没有中断对家中亲人的思念。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给家乡写信、寄诗。在1937年寄给何夫人的诗词中,他深情地写着:
音书久断绝,生死不可踪。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遥知鬓发改,不复旧时容。
在遥远的西北高原,已经和我母亲在一起,并育有五个孩子的情况下,父亲仍一直与何夫人通信,问候与帮助家人的生活,并坚称“你永远是我的夫人”。直到1951年9月7日,父亲给何夫人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明确表示:
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同有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一样,父亲理智、平和地处理了在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夫人被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小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后,据说父亲和母亲请她来过家里,也多次过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何夫人曾对我母亲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 照顾得这么好。”何敦秀1967年去世后,母亲又亲自过去帮助料理后事,两人互敬互重的情谊,令我们晚辈赞赏、感叹。
夫妻的亲情是家庭的基础,感情与责任并重,包容与坚持相伴,付出与获得双赢。从书信中,我们后辈可以了解与学习到许多人生的经验与道理。
三
养育儿孙,是父亲家书里的主要内容。
父亲在湖南家育有四男三女,北京家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可谓“望族”。生而有养,养而有教,是为父母之道。书信集中收录的多数信件是写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的。
5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值青壮年时期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不少信件里,父亲都是在教育儿孙、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学习新知识,跟上新时代,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0年1月21日在给两位大儿子的信中,他写道: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 ,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并写出了那首有名的诗句: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把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显示了父亲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
“四十离家七十回”,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7年、1960年、1961年曾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
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甚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难等现状很有意见,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
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这些书信、言语中,显示的我们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给我们北京家里这些学龄中孩子们的信,就多是学习、品德教育的事了。父亲老来又得众儿女,分外高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1945年12月15日,在八年艰苦抗战胜利之后,父亲步毛泽东刚刚发表的震动全国的《沁园春雪》之韵,作了一首《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修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好一幅“群孩戏父”的图画啊!那时候的姐姐哥哥七八岁,我三岁,弟弟不满一岁,“一群骄而又娇”,围着六十出头的老父亲,“攀肩、索抱,持竿打仗、扭秧歌”,在父亲心中,将养儿育女的辛劳化为快乐,把培育后代与自己终生追求的“真理”、“新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岂非人生幸福的极致!
父亲在我们孩子们眼中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八岁的旧中国,他从五十岁起,在长征、延安时期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在我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我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成一片,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我们脑壳前威胁一下。现在当我老了,年过七十的时候,浏览父亲当年用他纯熟的毛笔书法写下的这数以百万计的著述,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去。在大量的政府、法制、民政等工作的文件、报告、文章之外,父亲写的最多的是诗词、日记和通信,这是他的私人天地,是他的精神、情感得以表达、活跃、丰富和宣泄的地方。
50年代,我们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我们集体上课:让母亲讲述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写毛笔字,等等。他自己则时不时给我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孩子们。60年代,自大儿子谢飘到外地上学起,父亲给我们的信就多了起来,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休养,或当孩子们给他写了信、送了礼物时,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1962年3月8日的“致儿女”一封信写得最长,也最丰富。他从住、吃、穿各个方面谈古说今,以自己和母亲的经历教育我们:
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
要求我们思想上“看过去,看别人”、“对人宽,对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动手”、“爱惜东西”。今天读来仍旧令人感慨、深思。
时光荏苒,许多书信都遗失了,本书信集只收集到九十七封家信。它们传递的内容丰富、宽泛,绝不限于我上面讲到的几点。父亲一生中,把写书信当作一个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不仅同家人通信,还和同事、朋友通信,更愿意和完全不认识的群众、读者、青少年学生通信。在他的书信存稿中,和内务部、最高法院、宁乡县委干部们的通信是最主要的部分;与自己文章读者、通过报纸杂志转来的青年、中小学生的通信也屡见不鲜。1954年11月,他主动给并不认识的宁乡县干部写信,希望通过信件了解家乡的情况和变化,从此与他们成为多年的信中好友;并让他们对家乡公众宣布:“谢觉哉愿意和人通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父亲心中,亲情、乡情、民情是连为一体的。所以本书也收进了他给家乡基层干部和友人的书信十八封。
全书总计收录书信一百十五封。
今天,人类进入了“大网络时代”,微博、微信、微说等正在替代传统的通信、交流方式。编辑出版《谢觉哉家书》一书,是为了让历史留存,让现代人不要忘记我们前辈们曾走过来的道路;在阅读与把玩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字、形式时,将前辈们以及人类长久积累的思想、情感、文化、才艺,幻化成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永远继承下去,发展开来。
2014年10月15日初稿
2015年2月3日修订
致何敦秀,自延安(1939 年9 月8 日)
敦秀:
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呢,应该写一首。
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 “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
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一个信没有也不能有。最近可以通信了,但回家的机会,还得等待。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
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记得那年fow xo队闹到家里,谁都跑了;你都独自一个和他讲理,气盛理直,把那些要放火烧房子的丘八骇住了。又自我出亡在外,反革命找我家里出气,通缉呀,没收呀,你一个妇人要应付这些横逆,听说你一点不惊惶,处置得还好。有朋友来信,说你有丈夫气,其实,平凡的男子不一定比得你上,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
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付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
可惜得很,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
再过一十九年即是我俩结婚的六十周年纪念,老话叫“重谐花烛”,要重新拜堂行礼。那时候,也许不要到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国安家泰,我能够告老还乡,重温夫妻旧梦。等着罢,这不是空想,而是可能达到的。
前信教你从满六十岁那天起,不要再“斩猪草”、“提猪食”了,少管些事,安静过日子,心里放宽广些,吃得好一点,包你活得更长久。
我近来身体很好,裤带子松了三四寸,每天读书做事,可以上十点钟。请你不要挂念!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你的丈夫在一万里外于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隔你的生日尚有三个月。
焕南 于延安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0 年1 月21 日)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