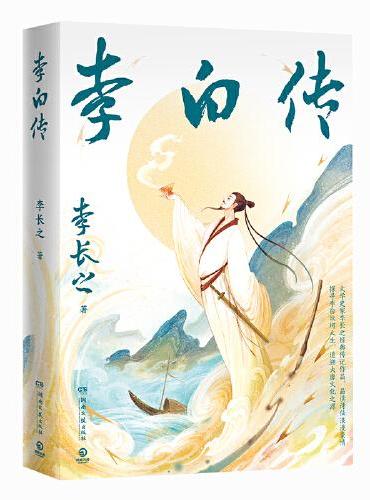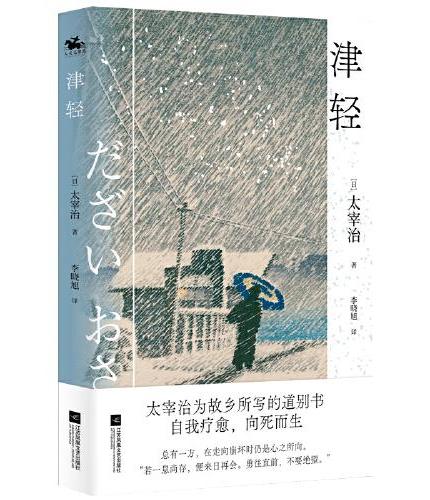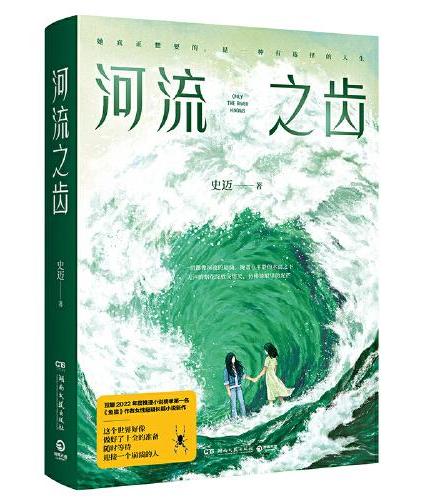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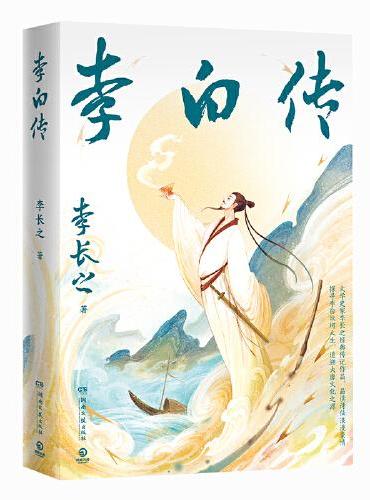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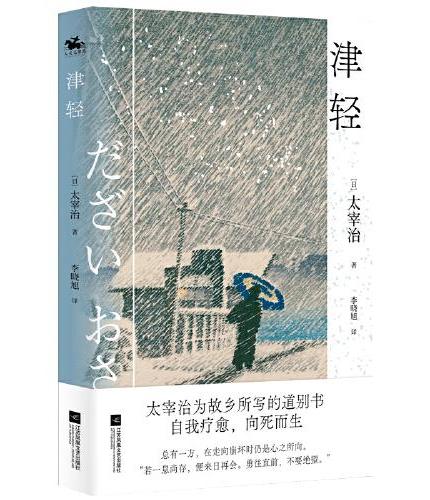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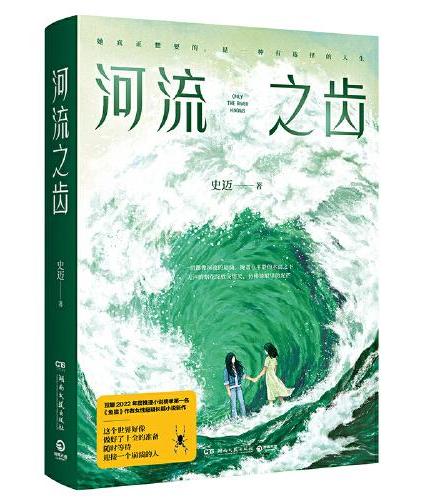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 編輯推薦: |
|
《距骨》充满了青春文学的细腻与张力,语言灵动又带着青春期特有的躁动和生涩。同时《距骨》也夹带着那个号称解放的六零年代的各种不羁:蔑视常规,反叛庸常,时髦放纵,追求自由。在安娜们“黑暗光明的痕迹上,凝结着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闪光的画面”。阿尔贝蒂娜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一生基本是在监禁和荒诞里度过,但是她却用一种超乎想象的冷峻和倔强审视她自己的生活,并将此在的痛苦转化为写作的灵感。2014年《距骨》新版的英文版封面上的肖像画,阿尔贝蒂娜娇小而漂亮,看起来就像一张脆弱又天真的孩童的脸。而2014的法版封面上的肖像,却很容易让人想到萨冈,激情放纵,毫不在乎。就像这两种特色的综合,在阿尔贝蒂娜的作品里,女主人公有一种让人怜爱的童真特质。她那么热切地梦想和拥抱“一种新的生活”,也充满彷徨:梦在那里?一个有一个的明天把我拉向何处?但同时那种近乎透明的天真正因为毫无边界,反而造就了一种近乎邪恶的残忍。偷窃、卖淫、越狱、欺骗,是的,所有这些,她不以为意,她不在乎怎么撕碎周遭成人世界的规则,也不在乎怎么通过伤害自己去抵达爱与梦想。距骨在本书中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象征。这是她为自由付出的的代价,这块无法愈
|
| 內容簡介: |
《距骨》讲述了19岁的安娜,因为抢劫被判入狱七年。一天夜里,她越过了监狱十米高的围墙,摔裂了脚踝,距骨骨折。她艰难地拖着受伤的腿爬到公路边缘。在浩瀚清冷的星空之下,她显得格外无助。此刻,她遇到了另一个不羁的灵魂——一个名叫于连的英俊小偷,他身上散发出有前科的人特有的气息,她觉察出他坐过牢。在这个刺骨的夜晚,于连骑着摩托车,载着受伤的安娜奔向了未知的自由。两个年轻人坠入了爱河。于连帮安娜寻找医院、寻找住处,辗转在一个又一个藏身之处,躲避警察的追踪,守护他们拥有的渺小而脆弱的爱与自由。于连后来因为窝藏罪入狱,而安娜为了生存,为了攒够足够的钱等待于连被释放再一起逃跑,她在红灯区干上了妓女的营生,也偶尔进行偷窃。两个恋人再次相逢,开始再一次逃亡,安娜在途中被警察抓获。故事在此处戛然而止。
距骨,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象征,这是安娜为自由付出的的代价。这块无法愈合的骨头,是她身体中由曾经的痛苦造就的他者,也是她荒诞生活无法摆脱的残缺。
|
| 關於作者: |
|
阿尔贝蒂娜萨拉森(Albertine Sarrazin,1937—1967),是一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出生在阿尔及利亚,2岁时被人领养,10岁时跟随养父母移居法国。她在年幼时曾被叔父强暴,15岁时被养父强制送进少年监狱。阿尔贝蒂娜一直坚持着诗歌、小说的创作,喜欢波特莱尔和兰波的诗歌。1964年,一家出版社接受并出版了她的手稿,她成为法国文坛第一位书写自己卖淫与逃狱经历的作家。1966年,她声名鹊起,获得文学奖项肯定,《距骨》一书亦被翻译到十多个国家,并被拍成电影。1967年,她死于一场荒诞的医疗事故。
|
| 目錄:
|
第一章 越狱
第二章 通向黎明的夜
第三章 逃亡的少女
第四章 入院
第五章 情人于连
第六章 缺失的距骨
第七章 激荡的“神父先生”
第八章 “我回来了,巴黎”
第九章 隔离的日子
第十章 重新上路
第十一章 以色事人
第十二章 偷窃
第十三章 伪装
第十四章 重逢
第十五章 亡命天涯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越 狱
天空远去了十米多。
我就这么坐着,不急。这一撞肯定击碎了石头,右手在一堆碎块上摸索。我喘着气,寂静慢慢减缓了眼冒金星的状态,可脑袋里还是在噼里啪啦。石头的白色棱角微弱地照亮了黑暗。我的手离开地面,爬上左胳膊,一直到肩膀,又向下经过肋骨直到骨盆:没事。我手脚还在,可以继续了。
我站起身来。鼻子猛地撞上荆棘,我像十字基督一样地瘫下了,想起自己也疏忽了检查一下双腿。明智又熟悉的声音穿透夜晚,低声哼 唱:
“当心,安娜,你会废了一条腿 的!”
我又回到坐姿,重新探查自己。这一次,我在脚踝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肿块,它在增大,在我的手指下搏动……
大夫,就诊的时候,为了能请病假,我跟您撒了谎,说自己不舒服,还说是在那些我自以为别人碰不到的地方。小姐妹们,不得不为你们把汤剂端到床上的时候,我这个总是走来走去送东西的模范啊,真羡慕你们消化不良……所有这些都结束了。现在,你们要照顾我了,你们或是别人,我的脚断 了。
我抬起眼睛,望向墙壁高处,这个世界待在那里,睡着了。我飞了,亲爱的们!我飞了、翱翔又盘旋了漫长而美好的一秒钟,一个世纪。我在这儿,坐着,从高墙里解放出来了,从你们当中解放出来 了。
就在今天下午,我塞了很多阿托品,往自己的大腿里注射了苯。罗兰德自由了,我一点都不想等她回来接我。我耍了点手段,让人把我送到医院去,因为在那儿能更方便地搜到药品,日子也消磨得更快。
“可你脸色发青啊!”教导员晚间巡视的时候对我 说。
“可能是撞墙上了。”我说,感觉脸颊如死尸一般,我努力看向身上短袖衫的背部,却脱了臼。大家恰好正在重新粉刷餐厅的墙壁,一面黄色,一面蓝色,两面青色,还有橙色的窗台,营造出一片阳光。
“不行,你脸色发青,说的是你!瞧你这张脸!是不是不舒服?”
可是没有时间享用我的第一杯椴花茶了。围墙另一边有个缓缓的斜坡,过了门之后,我不会从那儿下去。我选择了跳下。不管怎么说,我在下面了,离马路不远,我得一直走到那儿。如果就在离墙两步的地方,别人是不会把我扶起来带走的,难道不是 吗?
我和罗兰德重逢的地点和晚上依然遥远,我得先拖着这个碍事儿的肿块一直到公路那边……两次,三次,我试着放下脚后跟:雷击,穿腿而 过。
双脚没用了,我就靠胳膊肘和膝盖走路。我爬了二十米,撞上荆棘,又返回到石头上,努力认准方 向。
可能又流过了一个世纪,我什么也没找 到。
脚踝被封住了,脚和腿成了直角。我驮着它像驮个铅球,脚踝垂直地摇晃在碎石堆和荆棘丛的鳞爪中。夜晚厚重。在高墙里,在所有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我看着离大马路这么近的矮树丛,确信自己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它。我的计划在那时尚未到达这一步,但跳出去和逃跑的持续欲望在无意中形成了。还有,我向那群谨小慎微聚在教导员周围的姑娘们笑了,罗兰德的手钻进我的口袋里,我紧紧攥住它。我飞到下面的石头上,又站起来,唔唔,自己真是好笑,却也纯净 了……
我们拖着脚回到有光亮的地方。我让女友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我也在她的口袋里搜寻着,透过布料寻找关节,罗兰德,我感觉到了你在走动的骨头……我们在外套下噗嗤噗嗤地笑,有光照的小屋里满满的都是梦想,直到第二 天。
我爬行着。胳膊肘沾满了泥土,我在泥水中流着血,碰到哪儿的荆棘,哪儿的刺就扎着我,疼,但是必须继续前进,至少到达那束光亮,那儿有一座房屋在为我指路……在光束和我之间,有一道铁丝网,我靠着它倒下了。我还好,在这儿躺着,闭上眼睛,胳膊懒散无力……该死,他们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带走的。我会为这次休息付出服从的代价,还有新的痛苦,我爬向泥土,在那儿待着。也许墙壁会追随我的坠落,将我掩埋。
我直起身,靠着膝盖骨绕过铁丝网。一下膝盖,一下胳膊肘,一下膝盖,一下胳膊肘……还好,我适应了。我幻想着重新开始,不紧不慢:不再像个疯子一样向前冲,不再紧紧抓住石头从墙上爬下,不再脚一触到空地就放开手,我会为自己的着陆找个柔软的角落,那里的草长得茂密又软 和……
我爬过了别墅,它的灯光一直在闪烁。我紧挨着墙壁,在小路上的草丛里前行,胳膊肘,膝盖,胳膊肘……到马路了,明晃晃的马路被黄线分成几段。一个金属架摆在人行道上,打着一款精华液的广告。我抓住它,板子叮当作响,我要在这里搭便车……不,巴黎在反方向,得穿过去。第一步像踏在通红的铁块上,第二步像踩在明胶上。穿过黄线时,我倒下了,第一台压碎机正在朝我冲来……它来了,是辆卡车。它和我同一个方向,会去巴黎,我的碎布头黏在它的轮子上了。我看着它,看着它大大的黄眼睛。它朝我开 来。
卡车在几米远处改了道,开上路牙,停下了。我听到刹车的喘气,车门哐当一声,有脚步在靠近。我还是在等着被碾碎,闭着 睛。
小姐!……
有手指碰了碰我,试探着,犹豫,不 安。
我说:“如果您愿意,帮我离开马路……扶着我,好像有条腿断了。”
货车司机一直扶我到卡车踏板那里。我坐下来,把脚踝收到影子里。不想去看。有一盏路灯靠得很近,照亮了我的右脚:它沾满泥土,干巴巴的泥围着黑黑的趾甲,像链子似的一直爬到膝盖,被伤口划开道道条痕,鲜血慢慢地结成小珠。我在外套里紧紧地抱着自己,在口袋里握着拳头。我身上没有其他任何衣物,开始觉得冷了,一直冷到心 坎。
“您能给我一根烟 吗?”
小伙儿掏出高卢牌香烟,给我点了火。在火柴的光亮中,我看见了他的脸,那张长途货车司机在夜里都会有的脸:亮闪闪的皮肤,开始生长的毛发,还有这种憔悴又固定的表 达:
“您怎么 了?”
“我……哦,那个,在那个地方,我很安分的。您知道那片 儿?”
“知道,我每个礼拜在这条路上走三 趟。”
我指了指岔道,在混杂着树木和高墙的泥堆里有一座别墅的灯塔,它是唯一的坐 标。
那,也许您知道那里有什 么……
“嗯……知道。从那儿来 的?……”
“对,就刚才。起码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们应该还没开始找我。请您带我去巴黎。您不会有麻烦的,我保证。到了巴黎,您就把我放下,我自己解 决。”
男人想了想,想了很久,然后 说:
“我当然可以帮您,不过……您也知道,您的腿。”
“可就算……一直到巴黎,先生,我不会再要您做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不会说起您。相信 我。”
“我相信您。但您也拦不住什么,‘他们’的招数比我们多。我有老婆孩子,我不能。”
我用十指紧紧裹着脚踝,使劲撑在驾驶座上,努力站起来。
“好,既然这样,就别管我了。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在下一个村子通知‘他们’。忘了这次见面,祝……”
我本要说“祝好”,但突然意识到这句话有些可笑,意识到这根香烟的味道散去了,还意识到这个男人给了我十分钟。
“对了,”他说,“我还是可以帮您拦辆车的,也许会有哪个家伙捎带您……我说大话 了……”
随他做什么他想做的吧。我只想截掉这条腿,然后睡觉,一直睡到它重新长出来,自己从梦中笑醒。近来,茜娜对我写道:“亲爱的,我做了个噩梦,你从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很严重,耳朵流血了,可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在哭……醒来后,我拿着你的照片,开心得松了口气,因为这不是真的,而且我会见到你,和每个早晨一样,你的气色焕然一新,拿着大号牛奶锅径直走向厨 房……”
……
“这个点儿没什么车。”货车司机边说边走回来,“还行吗?”
“嗯,没刚才那么糟了。离开这儿吧,走吧,我已经耽误您很久了。话说回来,他们马上就会来找我 的……”
一阵引擎声突然出现在夜晚深处:有人在向前冲。我看到他的身影被路灯割开,做着大幅度的姿势。这时候车都开得很快啊!他会被压碎的……我缩进驾驶室的影子里,闭上眼睛。车停了,一扇门哐当一下,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靠近。透过余光,我看见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货车司机面前,司机在跟他说着话,指了指围墙,又指了指我……男人背对着路灯,留下清晰、蜷缩的影子,双手插在口袋里,领子竖了起来。虽然他们说话离我很近,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浓雾像棉花一样厚实又像玻璃一样半透半明,把我和他们分开,我在雾气里沉溺得越来越深,像在睡 觉。
“这只脚抬起一点?”身影说 道。
我麻木的膝盖再也不能把脚从踏板下收回来,就用双手拉着腿肚,帮它一把。然后,我机械地撑着脚后跟站起来,感到很痛苦、很绝望,就放弃了,任凭那只脚又落到阴影和泥土 里。
男人在我面前蹲下,拿着手电筒来回照着。我看见他光滑的金发,赤褐色的耳朵和双手。他站起来,关上灯,和货车司机一道走向他的轿车。随他去吧。我无所谓。我不再去听,也不感兴趣。后来,一切都来得太 快。
一只胳膊绕过我的肩膀,另一只轻轻滑到我的膝盖下,我被抬起来带走了。刚才那张男人的脸靠得很近,就在我的脸上,前进在天空和树枝里。他抱着我,安全又温暖,我离开了泥土,我走着,在他的臂弯里,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男人抄了一条近道,又走了几米,小心地把我放在地上。我适应了黑暗,看清了一棵大树,看清了草地,看清了水 洼。
“别跟任何人走,更不要动,”男人说道,站了起来,“我会回来找你的,等我。一直等 我。”
他走远了。不一会儿,我听到了卡车和轿车的引擎声,灯光划过,一切又恢复了安静、冷清,夜晚依 旧。
我没动。再过一会儿要是不怎么疼了,我就往马路那儿挪去一点。我在这个岔道里陷得太深,男人不会找到我的。我有时间。我知道第一座城市在四十公里外:四十加四十……那辆车里有人,我听到他们说话了,也许男人是想放下他的乘客再回来:“别跟任何人走……”我嘴巴冲着树根,笑了。现在,我整个人都躺着,浸湿在草丛里,一点点变冷。在身体的另一端,脚踝肆意地喧闹着,心脏每跳一次,都汇成炽热的细流。我在腿上有了一颗新的心脏,节奏依旧糟糕,不合拍地回应着另一颗。高墙里,黑色的树枝冻结在冰封的天空里。马路上,车辆来了又去,没有一辆减速,没有一辆开向我。男人必须回来,因为我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另一个机会,而且不能让人在早上——在这儿找到我。至于腿,我一点也不担心,总归会有的治的。我已经熟悉了疼痛,它缓缓移动在我的身体里,走访每一个隐蔽的角落,路过哪里就麻木哪里,它在延展也在消散。只是,在这儿或是在那儿,小小的意外火花让我惊跳,完全睡不着。我在口袋里碾碎了货车司机给我的高卢香烟的烟头,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战利品……也不是很糟糕,我有烟头,一个真正的高卢大烟头,而且我能随意把它扔掉或是弄碎。我把卷烟纸和火柴丢在了高墙里。罗兰德,罗兰德,我有一个很棒的烟头,可是抽不 了……
一根摇曳的火柴。一颗流星,一盏防雾灯。不,是我脚踝上的铁链照亮了整条岔道。一道道闪光旋转了一会儿,然后汇合,凝成一把圆形的光,镜面一样地闪烁着,一束巨大的光亮从我头上擦过,没碰到我,打在了树干上。我还感到有一阵短暂而沉闷的引擎声充斥在这个夜晚,但只有寒冷在耳朵里嘎吱作响,我肯定是在做梦。可是,车灯一直在那儿,我能很清楚地看见树皮,现在第二个也亮了,小小的,动个不停,贴着地面快速搜寻。这下好了,我被发现 了。
所有光都熄灭了,有人走了过来。是他,一定是 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动 吗!”
啊,我动了?可能吧。一切都变得可能。我觉得自己笑了,觉得自己环住了男人的脖子,觉 得……“好,好。”他边说边脱下衣服,在夹克里层的口袋里翻东西。他拿出一只扁扁的小瓶子,一盒香烟。现在有的是时间了,我们就着瓶口轮流喝酒,每吸一口,香烟上极小的火光就把我们的脸从黑暗中拉出来。抽完这包,喝完这瓶,然后,还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找回了一切希 望。
男人继续掏出东 西。
“给,我带了一条裤子,一件羊毛衫,还有一条绷 带。”
对啊,我差不多是光着的。我脱下外套,穿上套衫。可是裤子……这只肿大的脚再也弯不起来了,轻轻一擦就疼得要炸开,怎样才能把它塞进裤腿呢?我又穿上外套,说:
“你叫什 么?”
现在,我们是两个名字了,我们一起离开黑黑的树丛,等天亮了再了解其他的。先离开这里,快……
“起码绑上绷带吧?不想试一下吗?看,都结冰 了。”
“ 不了,行行好,不要碰它。就让脚光着,没 事。”
“ 随你吧。我骑摩托带你,抓着我。不舒服就说。你会骑摩托 吗?”
“会,以前经常骑,不用担心。出发吧,走 吧。”
我蜷缩着,紧紧围着酒精在体内产生的冰冻火焰,让那只脚悬在车轮旁边,两只胳膊趴在于连的肩膀 上。
另一个世纪开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