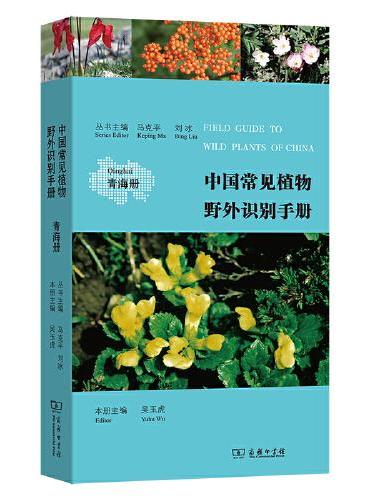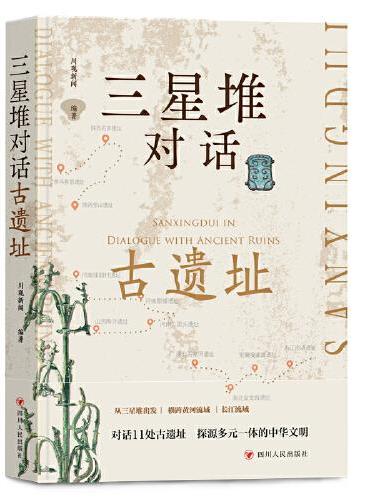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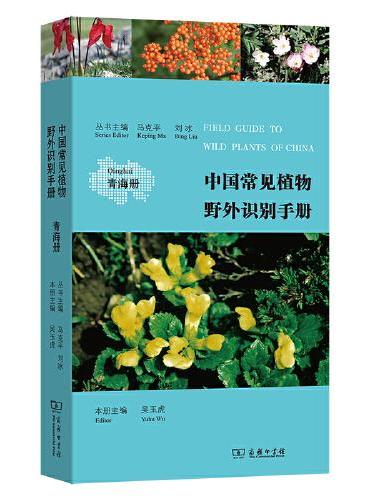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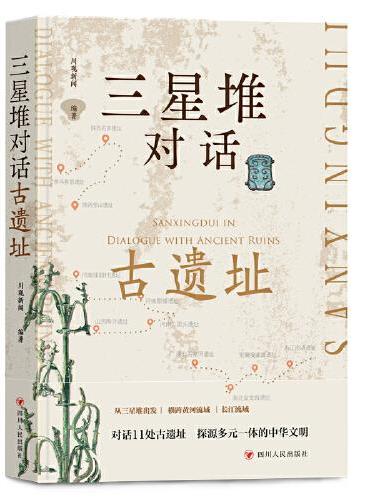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3.4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
卡特里娜(“同一颗星球”丛书)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ONE一个」高人气作者滕洋首部短篇小说集
畅销书作家自由极光、《陆贞传奇》编剧张巍拍手推荐
★《你觉得不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这本书是「ONE一个」高人气作者滕洋首部个人短篇小说集。书中的每个故事内容精彩,情节出乎意料且有多处感人至深的地方,贴合时下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你发了疯的笑,玩了命的哭,都于事无补。感情中的直觉往往是真的,自从认识了墨菲,整个生活都不好了。24篇让人又哭又笑的情感故事,既戳泪点,又戳笑点。
★本书中的故事情节都真挚感人,人物性格非常突出,并且,他们故事的主人公年龄都在三十和二十五岁以下,或者18到22岁之间,他们比一般的青春小说成熟,都有轻微的吐槽风,也都擅长把情怀和主人公的情感经历相结合。更符合现在沉浸网络和社交的年轻一代。
|
| 內容簡介: |
|
「ONE一个」高人气作者滕洋的短篇小说集,24篇色彩各异的情感故事,爱情中的直觉往往是真的,你觉得一定不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本书每一个故事都体现了这一主题思想,情节贴近年轻人生活又出乎意料。这就让书名的概念和内容的概念颇为一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
| 關於作者: |
|
滕洋:作家、编剧。永远顶着一个名叫短的头像,自称短短滕。近两年来在one一个app与《去你家玩好吗》等书中发表《异地恋》、《再见,puppy love》、《走马灯》、《两个无聊的人》等文,在网络被广泛热传。小说《失踪的韩左左》被改编成微电影,最新短篇《生活家》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
|
| 目錄:
|
01 Bū 001
02 MR. Lonely 010
03 20厘米留白小姐 019
04 零度 031
05 Good girl 040
06 楼间花园 051
07 旅程 062
08 朋友的朋友 067
09 青春涂炭 085
10 拳击手 097
11 杀手的故事 112
12 少年 131
13 生活家 146
14 失踪的韩左左 163
15 偷窥 174
16 我的幻肢朋友 192
17 现在高兴了吗? 202
18 小姑 209
19 幸运号码 218
20 兄弟黑三 224
21 异地恋 233
22 再见Puppy love 249
23 脏朋友 255
24 走马灯 261
|
| 內容試閱:
|
Bū
滕洋
Bū,对,前面是汉语拼音。具体怎么写,作者不知道。在中原部分地区,大多数时候,bū这个发音出现在大人逗小孩时,比如妈妈būbū,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妈妈抱抱。大概源自扑、捕、抱之类吧,一个人扑向另一个人、一个人捕获另一个人、一个人抱住另一个人。与此类似的还有波儿,在很多地方这两个字短促而迅速合成一个音念出来,变成一个类似英文bird去掉尾音d的发音[b?:r],在方言里代表吻或者弹脑门。
在使用这些方言的地区,人们在亲密而放松的私人场合使用这些发音。但有一种亲密关系却是例外的,你永不可想象两个人用这样的词谈情说爱。比如,强波儿之于强吻,公主抱之于公主bū,甚至是童谣里爱我你就抱抱我变成爱我你就būbū我,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也许跟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用港台地区方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言谈情,都没那么难接受,但一想到用河南话、河北话、东北话、陕西话演偶像剧,就会有点搞笑的意味。
杨强的,却悲壮地要打破这一规律。
杨强的,河北南部近河南某县,城中村人。大名叫杨二强,有个双胞胎哥哥。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可以代替北方方言里子的部分用法,比如一个姓李的人,人们可以称呼他小李子,在二强的家乡,通常会变为小李的。以此类推,在杨二强的家乡,一批顺子强子狗子变成了顺的强的狗的,幸好这里现在没有很多日本国际友人,不然想想排山倒海的杏的桃的百惠的也是挺奇怪的。这里的省道、村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杨的小卖部强的美容美发五的饭店之类的招牌。
综上,强的从不认为自己的杨强的大饭店有什么命名上的错误。倒是他那个能把巴黎口音说得和普通话一样标准的哥哥,每次回家,都要建议他把饭店的名字改了,强的多土气啊,来县里的外地人看到这个名字肯定无法理解的的名词属性,只会认为饭店的老板叫杨强。
可强的有什么办法呢?从当年产道冲刺他没挤过他哥那天,他的人生好像就混入了奇怪的东西。单拿名字说,要不是担心重名的太多,当年他们这个地方父母给孩子取名恨不得简单到直接用阿拉伯编号。他们哥儿俩算是好的,至少除了数字还分到了不同的汉字,如果随村里主流命名法,他哥叫一风,他就应该随着他哥叫二风。一与二,一横之差,就有了云泥之别:一从发音到字形都是简洁美好的;二呢?简直是数字界的贬义词卧底,与三八、二百五不遑多让。人们更愿意按名字定义的性格判断这两兄弟,虽然长了一模一样的脸,但朗诵比赛、国旗下的献礼这类严肃场合一般都喜欢叫一风去,过年捡鞭炮崩数学老师家厕所则少不了二强。
强的也很努力地抗争过,试图打造自己严肃沉稳的形象,不分寒暑在县政府大街十字路口蹲守,终于在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成功活捉一名跌倒老人,并扭送就医,获得了在初中第一学期第一周国旗下讲话的机会。
尽管在被窝里偷偷想象了无所次,但当校长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念出下面有请杨二强同学为我们演讲的句子时,二强还是感觉有点奇异陌生。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感,一直到他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讲完自己的稿件全文,主席台下一直隐忍的全校师生终于爆发出热烈的哄笑后,才被他理清头绪:从来都不是名字,他哥与他唯一的差别,是一风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
强的永远忘不了那个瞬间自己的感受,那些除了语文课都操着乡音的同学,在某种不知名规则的约束下,在某个评选最可笑的人的游戏中,齐齐站到了他对面推举他当选。他的目光焦急地四下搜寻,希望得到一点支持。他看到一风攥紧了拳头跟旁边笑得开心的男生理论,心里稍微踏实。紧接着,强的看到站在他哥旁边的女孩,对自己露出了一个微笑。
那天之后强的再也没有说过普通话,杨一风为了支持弟弟也在学校讲足了三年方言。还是那天,强的牢牢记住了庆梅他哥的同桌,那个人群里对自己微笑的女孩。很久之后,强的才知道,庆梅当时的那个微笑,只是出于对双胞胎的好奇。当时的强的,却只牢牢记住那是唯二没有嘲笑自己的人。强的当场决定,庆梅是值得自己蹲守一生、活捉扭送到心里去的姑娘。
庆梅是随父母工作调动从大城市来到他们这个县的,虽然庆梅跟一风、二强一样,都是在县医院出生、由县里的护士亲手bū到父母面前的,但庆梅妈坚持不让女儿学方言,在她心目中,庆梅是一定要回到大城市里去的。语言上的羁绊,万万要不得。
杨家兄弟成为学校里从不说普通话的异类时,庆梅也成了学校里唯一听不懂方言的异类。杨家兄弟倒也还好,不开口说话,他们就是女生心目中的县城贵公子、本地EXO。庆梅就倒霉许多,大部分女生都认为庆梅有种自带名媛光环的做作。可偏偏,强的就是喜欢庆梅。
苦追三年,中考前一晚,县政府大街走九遍,庆梅终于答应了强的的表白。强的兴奋得一夜未眠,虽然跟一风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一风循规蹈矩地进了市里继续读书,强的却执拗地陪没考好的庆梅回了县中坐同桌。高中三年平静如常,结束的时候,强的没有再屈就庆梅,小两口拼尽全力一起考到了离家不足一小时车程的省内大学。一风则进了北京的大学,学了外语。
少年时,强的与一风对未来全然没有走哪儿算哪儿以外的打算,从初中开始,学校把他们带到哪里,他们就留在哪里。杨家爸妈则不同,两个儿子他们总是想留一个在身边。此前,他们并未预计过到底会是哪个,只是一路走来,一风看起来是一定要离开的全县全年都不一定有一个能用得到外语翻译的地方。而强的,似乎很有守家待业的故土情结。杨家爸妈就轻松愉快地给两个儿子做了不同的规划:给一风准备了读书的钱,给强的盖了娶媳妇的房子。
强的也一度以为,别人大学毕业那天分手,他与庆梅则一定会毕业后结婚。他真真把庆梅妈说的庆梅一定要去大城市生活这句话当成了一句玩笑。闹呢?庆梅除了一口骗人的普通话,行为举止比他还要local。可现实,还是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萨瓦迪卡眼看庆梅战五渣的实力进了一线城市也混不好,庆梅妈干脆曲线救国,决定掏钱送庆梅去泰国一线城市曼谷留学。
为了留住庆梅,强的用他老婆本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颗小小的钻石去找庆梅。单膝在庆梅家门口的土路上跪也跪了,玫瑰蜡烛摆也摆了,隔壁抱孩子的二婶子、瘸了腿的大黄狗、走亲戚的非主流,围着哄也算哄了。但庆梅妈还是拒绝了她压根儿没让女儿出场,这位希望女儿踩着恨天高背上真驴牌行走在大都市地下铁的妇女,自然不想让女儿过这种只能坐一元钱扬招小公共的生活虽然,最近已经有了三蹦子改造的假五座出租车可依然是凑够一车才给送人。
与庆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首都机场。一辈子没有出过省的强的,为了庆梅跑到北京来找一风想办法,终于,还是撵上了庆梅的航班。彼时,强的穿着庆梅最喜欢的裆到膝盖的牛仔裤,挑染的头发已经褪了一些颜色,为了见庆梅刚洗过澡,自然风干的头发毛毛躁躁全部奓起来了集全机场之力都没有他的外表热闹。倒是庆梅,已经迅速以黑白灰的搭配,稳妥地融入了城市人群。她站得离强的很远,潜台词写满了距离。
这是强的的失恋瞬间,这一刻,他在庆梅的眼中看到了多年以前那个升旗仪式上的自己,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人再像当年那样支持他了:一风与庆梅用再标准不过的普通话告别,摆出一副无国界无家乡的国际通用寒暄姿态。而强的发觉自己像摩西分海,周围人是海,只有他是茕茕孑立的摩西。
强的生出了一种气愤的破罐子破摔感,他上前一步大声问庆梅:能不能最后bū你一下?
庆梅下意识地后退,扯出一个僵硬的笑脸:强,别闹了。
强的试图证明什么一样追上去,仔细看着庆梅,脸凑了上去,试图给庆梅一个吻。庆梅退无可退把行李箱横在两人中间,强的忽然大笑起来,用家乡话大声说:bir都不让bir了?那我强bir你?我和你bir别,在无人的街!
一风也因为强的玩笑笑起来,庆梅狠狠地瞪了一眼强的,拖着行李箱离开,再也没有回头。强的想,他对庆梅最后的疼爱也就是手放开了,他把他的失恋故事讲给别人听时,每个人都像听一个笑话。强的也就渐渐地真把这事儿当成笑话了,他在市里开了个精品服装店,可他的口音连累了他的品位一口土话的老板能有多高的审美,顾客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强的觉得很累,干脆关了店回家乡托亲戚朋友承包了一片山林,种有机水果、蔬菜,最后搞起了农家乐。这样总行了吧,他终于符合了所有人的预期。
庆梅在泰国很好,过上了别人QQ空间里的生活:每天发柔光过度的自拍。一风出国继续学他的语言,回国后留在了北京做翻译。庆梅与一风的生活在强的看来,都是高尚豪华的。强的有时想,如果他像一风,是不是跟庆梅就能走到最后了。这几年,强的没有再恋爱过,别人都以为强的忘不了庆梅,可强的知道,他的问题跟庆梅无关,是心病:他没有办法用家乡话谈情,也说不好普通话。这隐秘的心结,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每每只是在父母催着相亲时,拿各种理由搪塞。
于是,两兄弟先结婚的是一风:他娶了公司同事。也许是拖着行李箱全球奔走的生活让人感到疲惫,一风把正式的婚礼地址加蜜月都定在了强的的农家乐。强的本来想把林子砍一片儿,再辟个小广场出来给一风铺上草坪做个月亮门,顶好请个外国神父再来一套DOYOU?IDO的誓言,被一风严词拒绝了:大夏天的满院子人带着腋下两朵汗渍,不论见证的是谁的爱情都太热!
一风的婚礼比想象中的简单,没有牧师也没有司仪,有种日日精彩才向往简单的随意,可旁人已经脑补大概一风在北京过得也不是那么好,不然怎么会连个婚礼摄像都没有。
其实,是有的,祝宁就是婚礼上的摄像之一。新郎和新娘都想要不一样的婚礼影片,为了这个诉求,准备来参加婚礼的好朋友们像做项目一样开了好几次会,在婚礼摄影这个议题上,最终在挑选几个人佩戴苹果运动相机或是谷歌眼镜中,选择了车载摄像头。反正婚礼只有一次,车载摄像头不管结婚还是离婚都还是有用的。
于是,婚礼当天,祝宁作为摄像之一兼伴娘,和其他几个分处不同位置的朋友,都藏了改装后的车载摄像头在身上权当摄影机,事无巨细记录婚礼的每个细节。她想,这种偷拍纪实风格的婚礼录像,自己结婚时也要这么干。只是,她还没有另一半。不过,谁在乎呢,喜欢婚礼不一定非得喜欢结婚不是吗?
为了让镜头始终处于同一个位置,整场婚礼下来,祝宁拉了107次衣服。作为伴郎的强的,就记住了这个总在扯衣角的紧张伴娘。在后面的敬酒仪式里,强的也就格外注意帮紧张的伴娘挡酒。
实际,祝宁自成年之后,体验过很多情感,唯独紧张是稀缺的体验。作为一风和新娘的上司,她怎么也算是年轻有为的典范了。但祝宁还是很感激一风这个静如哑巴、动如触电的弟弟,特意用这边的方言跟强的道了谢。
祝宁会说自己的家乡话让强的非常意外,明明他哥介绍祝宁的时候,说了这位领导几乎是在国外长大的,精通几种外语。强的用家乡话跟祝宁再聊几句,祝宁应答就有一些勉强,但她还是见缝插针地追着强的纠正了自己的发言。祝宁告诉强的,语言上的模仿是拉近彼此关系的最简单直接手段,收集方言是她的爱好,如果不能在离开某地时像模像样地说几句当地方言,就觉得自己根本没来过这个地方。
强的跟别人学过普通话、外语,这是第一次有人要他教自己方言。整场婚礼下来,祝宁学了个七七八八,只是,她很难分清这里面哪些是强的开的玩笑,哪些是真的方言。一开始强的教她的东西还挺正经,比如老(一声)妹儿是月亮的意思、太阳是老爷儿,月亮是老妹儿。后来就是举一反三的公主bū阿哥bū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老妹儿代表我的心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过,效果斐然。那天夜里,参加婚礼的宾客走得差不多了,新郎新娘进了洞房。强的留下来招待他哥他嫂那些能彼此背得住手机号码的朋友,微醺的祝宁已经满嘴方言,逢人便讲公主bū阿哥bū的笑话,卡拉OK时把所有拥抱唱成拥bū。以至于,那一晚的所有情意绵绵,都有土话插足的影子。
强的心甚慰,想他终于也靠着方言为人师表了一回,炸老师家厕所、升旗仪式上丢人、机场被分手的过往,被扳回一分。最重要的,他发现自己被祝宁强力脱敏了。他不再害怕自己讲出的情话,迫切地需要找个人来验证祝宁给强的出主意,不如像学外语用情景对话的方式来练习吧,她学方言,他学感情。两个人就这么一问一答地演了一晚上当地情侣,到后来,所有人都昏昏沉沉地各自睡了,祝宁与强的却一直聊到了看日出。
祝宁给强的讲了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无国界的父母无家乡的烙印。
强的给祝宁看了庆梅的照片,实际上,他也只剩一张初中入学照,其他的都被父母一气之下销毁了。毕业照上的强的仍是那副县城黄毛纨绔样,站在他旁边穿白衬衣的一风则傻乎乎露着白牙笑容灿烂。庆梅站在第二排,居然是个杀马特。祝宁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这个留着倒扣榴莲头的少女跟QQ空间里那个永远发着旅行自拍的长直发森女联系起来,时间改变了一切,不变的只有口音。
太阳越过地平线时,祝宁轻轻拥抱了强的。
无论后来结局怎样,强的始终确信,那天早晨,如果他开口问祝宁能不能帮自己做把有机柿饼子批发到巴黎去的生意,他和祝宁既定的发展也可以是爱情:从摘柿子到做柿饼,再卖到国外,有一整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相处。可惜最后,什么也没发生,谁让他根本就没种柿子呢。
无论后来结局怎样,祝宁始终确信,那天早晨,如果她告诉强的,她实际很想过这种田园的生活,她和强的的关系也许就不会变成后来的哥俩好。
有些事儿,晚了就没必要再开口了。祝宁还是那个满天飞的无乡者,强的也还是守家待业的小老板。有时强的仰望天空,会觉得祝宁没准坐在哪班飞机上保佑自己。他们时常通话,祝宁终于像掌握外语那样纯熟地掌握了一门方言对的,她才没有什么收集方言的爱好,只不过,婚礼那天,她喜欢强地说方言时的神态,严肃而笨拙的搞笑,才会模仿强的的语言想要拉近距离。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半真半假地固定在了搞笑上。强的想想也只能这样,他真的一本正经去问祝宁想不想跟自己一起种柿子,怕,祝宁会当这是一个新笑话。
强的开始相亲了,强的变回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强的的新名片上用中英文标明了ErqiangYang杨二强。他想着,自己应该找机会问问祝宁,如果没有一口方言,她到底能不能分清自己和一风。毕竟,当初给祝宁看自己的初中入学照,祝宁就认错了人。穿白衬衫傻笑的是自己,黄毛杀马特才是一风。当年的庆梅也是一样,喜欢的是那个杀马特一风。如果不是他硬要和一风换了衣服、烫了头,想来,庆梅也不会跟自己有那么一段。
为什么女孩们喜欢的总是一风呢?强的想不清楚,只是,他也不想再把自己改造成别人希望的模样了。假如,再一个365天,他还放不下祝宁,那么,说什么也是要去找她,给她一个热烈的拥b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