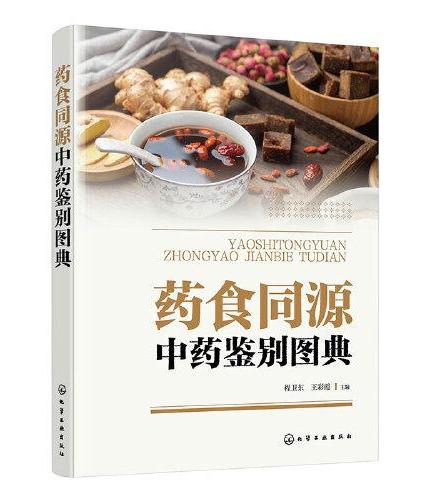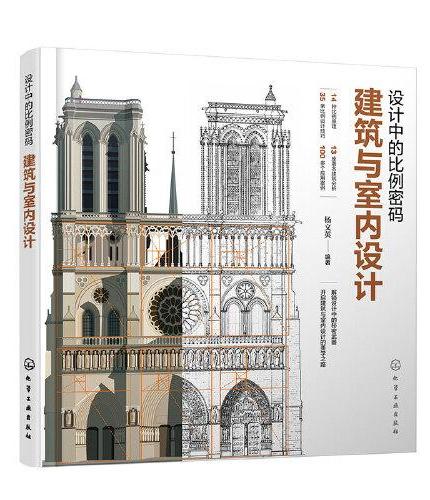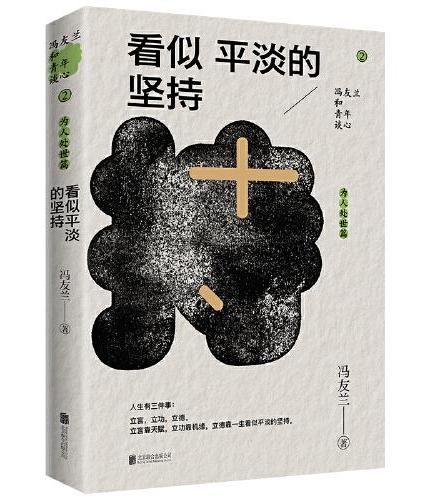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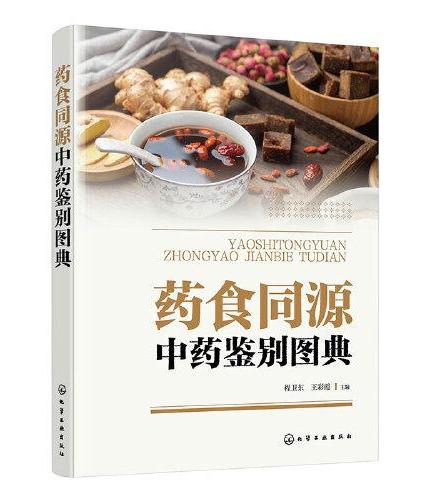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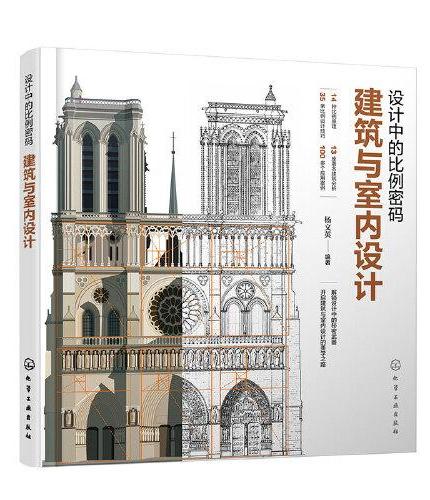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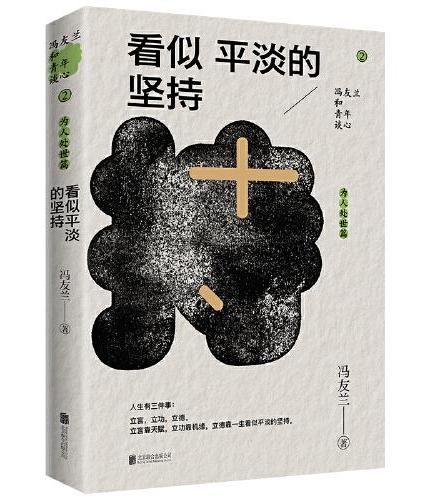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HK$
76.2

《
汗青堂丛书144·决战地中海
》
售價:HK$
168.0

《
逝去的武林(十周年纪念版 武学宗师 口述亲历 李仲轩亲历一九三零年代武人言行录)
》
售價:HK$
54.9
|
| 編輯推薦: |
评论认为,鱼禾近年来创作发表的系列长篇散文,从立意、结构、语言到文本形式,既有对散文创作诗性传统的优美继承,又有对散文言说界域和固有形式的果断突破,体见了散文创作无可替代的文字担当和浩荡宽阔的表达能量。
在鱼禾的世界里,总是有宿命般的悲情和好便是了的退让。这也许是一对矛盾,或也许,这是对生命之轮zui智慧的驾驭。对于一个有思想的写作者而言,幸福不是出其不意的惊喜,而是把握在手的笃定和坚守。每个人都有凭窗远眺的权利,可是思想者的凭窗,往往会成为一个事件和记号,他们能让运转自如的世界骤然停摆,听他们低声喝问:你凭什么自称和它们不同,你犹疑的过程,为什么这样长?(鱼禾《前提》)在她搭建的词语的深沟高垒里,我常常沉迷和彷徨,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种深深的陷落。因阅读而产生的丰富和荒凉,使我终于相信了一个人也可以地老天荒。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邵丽
这部私人传说,除了有作者对于私人经验的特别尊重之外,还有对于私人经验书写之价值的独到理解:我们的文学主张似乎有一种轻视智识的传统,沉甸甸的现实往往难以获得相称的反省现实是整体的而非碎片的,是日常存在而非突发事件。作家在写作之先,就应当
|
| 內容簡介: |
《私人传说》收入的作品,是鱼禾近年来以家族与故乡、成长经验与人性困局为主题的系列长篇散文代表作,这些作品先后发表或转载于《十月》《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莽原》《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物。其中《父老》入选《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2013年中国zui美散文》,《驾驶的隐喻》获第11届十月文学奖。
鱼禾近年来创作的系列散文,从立意、结构、语言到文本形式,既有对散文创作诗性传统的优美继承,又有对散文言说界域和固有形式的果断突破,体见了散文创作无可替代的文字担当和浩荡宽阔的表达能量。
|
| 關於作者: |
|
鱼禾,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摧眉》《相对》,长篇小说《情意很轻,身体很重》,读书随笔《非常在》。多篇散文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等刊物,其中《驾驶的隐喻》获第11届十月文学奖,《失踪谱》获莽原文学奖。
|
| 目錄:
|
自序:给亡父,和即将消失的我们
父老
放疗病区
乡愁,或另一种乌托邦
失踪谱
我的眼前大雾弥漫
前提
逃离
悬空:我的梦中居所
驾驶的隐喻
恋声
吸引
地图
高原反应
孤立
|
| 內容試閱:
|
类姐妹
女人之间特别容易过从甚密。两个女人,或者再多几个,她们无论熟悉与否,只要坐到一起又正好闲着,那就会不停地说话,海咸河淡,鳞潜羽翔,话题多得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若一旦熟识了,再要好起来,那就好得蜜里调油,不分彼此。女人们管这种关系里的彼此叫闺蜜。隐私,常常是女人之间维持友谊或话题的基础。既是闺蜜,自然要互相坦陈家庭琐事和男女秘事,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的家事,喜好,交往,甚至对另一个人的性关系,大肆指手画脚。
人与人之间那种热火朝天的相处,我一直难以理解有什么实质性的吸引,可以让人和人贴得那么紧密,以至于抱团成块,完全看不到这一个和那一个的界线?有一次乘火车入藏,我和梁奚买了两个相对的中铺。下铺有两个江南女人,她们原本不认识,但很快就聊起来。其中一个细细说起某次偶遇一对男女,说,一把年纪了,哦哟亲热得很,一看就不是原配,就像我们老夫老妻了,哪有那么亲热对吧,亲热成那个样子肯定不是原配,要么根本不是夫妻,哦哟不知道是哪样关系。我朝梁奚眨眼。我们大约也是一看就不是原配梁奚每次爬上他的铺位之前,总要攀在我的枕头边闲扯几句,或者递一颗果子给我。梁奚说,下面有两个原配女正在亲热。我们俩忍不住大笑两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谈论如此八卦的话题,实在是亲热得也很够了。我虽然刻意观察过女人之间的闲聊,而且有时候出于敷衍的必要,也试图努力练就这样的闲聊本领以至于彼此不尴尬,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几个彼此明白的挚友,我极少成功地和什么女人滔滔不绝地交谈过。聊一会儿我就会心不在焉。对方又找了一个话题来聊,我嘴上应着,心里想,不是已经说过了么。或者想,不过是俗套常识啊,有什么可说的呢。又或者想得很刻薄,你大姑子的右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不耐烦往往掩饰不住,对方大抵也能看出来,于是终于沉默下来。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喜欢坐到一排座位的边上,或者跟不认识的人坐到一块,以便避免这种长篇大论却又毫无意趣的聊天。外出乘车,也尽可能挑一个单座,免得跟什么人挤在一起,在漫漫长路上还要打起精神去罗唣。
有个很煽情的说法是,小时候命运给我们规定家人,长大了我们为自己挑选家人。这话总让我觉得窘迫。一个朋友圈如果太小太固定,时间久了,的确会弄得跟家人似的令人疲于应付。恋人或朋友之间是疏是密,本来是自由的,好就好下去,有一天不好了,也可听之任之,慢慢地变回熟人,甚至回到陌生,像一个人对食物的口味变化一样自然而然。而一旦被暗喻为家人,性质就变了。家人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了无限责任,无限的权利,无限的义务,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在这种关系中,任何道理、界限都会失效。事实上,这就和婚姻一样,虽非命定,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作茧自缚。男人之间还多少有些分寸,哥们儿虽然也暗示着某种荣辱与共的交情,但终究也只是哥们儿,你是你我是我,有界限的。女人之间的交道则很容易落入准家人的窠臼。
人终究是不规则的东西。两个或多个不规则的东西要想毫无间隙,如果我们诚实一点,会承认那是不可能的。久而久之,闺蜜必然也像日久生厌的夫妻一样互相嫌弃。我缺乏忍耐力。所以一直怕跟女人成为朋友又或者说,女人和女人没有朋友,只有类姐妹闺蜜。有时候看见两个女人勾肩搭背腻在一起,我会有某种生理性的不舒服,心脏仿佛在痉挛。我特怕什么人处着处着就喊我一声姐姐或者妹妹那让我觉得多少有些猥亵。喊我名字就行,我总是这样对别人强调。我对那种黏黏糊糊的亲密感到难堪,有压力,调动不起足够的神色去应付。
沉默
某次友人聚会,轮到我行酒令,我想了一个很不厚道的办法,说,咱们来试试不说话的感觉我计秒,大家沉默一分钟,忍不住的自饮一杯,若全忍住,我喝三杯。一分钟的沉默,在独处时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长度,但是在一个酒局上,那一分钟的沉默好奇异啊,就像在澎湃而下的瀑布中剪开了一个洞。我看着手腕上一格一格旋转的秒针,觉得时间正在被我们的沉默拉长。一分钟过去了,一圈人纷纷深呼吸,仿佛不是沉默了一分钟,而是被窒息了。我喝下三杯酒,问,我坐庄了,再来?众人端起酒杯嚷,不要,受不了。
对于沉默的喜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难找到一个清楚的起点。一种喜好唯有到了特定的程度你才会意识到。就这样,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许多情形下的说话都让我觉得兴味索然。这或许就是传言中的孤僻吧。我总结过,但凡勉强跟什么人亲近过度,哪怕其中有一丝勉强,那么不久,准会出现僵局我不愿意再理会他,或我态度淡漠到不近情理,令人不愿意再理会我虽然彼此并没有能溢于言表的嫌隙,找不到陡然中止亲近的理由。在交际或情意传递的意义上,我的态度没有确凿的动机。只是我对于疏离的喜爱越来越强烈,任何一种密不透风的相处都让我深感局促。这种局促感如果不能藉由距离和沉默得以化解,就必然化为厌倦。并不是别人做错了什么。当然谁都会做错点什么。做错点什么并不是事情的原因。
在某种交往中陷入疲惫,眼睛就会变冷,把对方的好与不好都看得明白。而一旦开始评判,交道就完了。对方那点好在感觉里越来越钝,那点不好却日益触目。当然,换个角度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在嫌弃什么人,那必然是,对方也在嫌弃我了。因为我的不掩饰与不担待,别人的嫌弃也许开始得更早一些。对于心思的冷热变化,我的感觉总是毫厘不差。在家人团聚的场合,在兄弟姐妹之间,在所谓好友圈里,不过三五个人闲话,也会不时见到某两个人凑到一块咬耳朵。事实上,他们也不避讳这一点他们的关系更近。近到什么程度呢?近到了可以互相数落这个家庭或类家庭里其他人的不是。一瞬间我就烦了。这么嘀嘀咕咕的,不如各自待着爽快。
说到底,并没有什么比自知更清透的了解。我们以为存在于人群之间的所谓知己,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的镜像罢了。在某个时期,一个人坐在你面前,恰好,这一面活生生的镜子里映出了你的影像,清晰,大致对称。于是,那人成了你的知己。说穿了,都是凑巧。我们各自走在路上,怀揣各自的经验、判断和目标也可以说是各怀鬼胎,唯有速度接近的人才可暂时互相见识。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开始跑步,或者其中的一个要停下来歇歇,便一拍两散,各自开始新的际遇。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人总觉得可以在自然际遇之外显示自己的高明。人们喜欢虚构情分,在人际聚散中加入一种成分不详的强力胶。你要孝悌友善恭敬。你要担待亲人及朋友的错误甚至恶劣。你要奴隶般地感恩念旧。你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要赴约吃饭。你要登门致意。你要从一而终。但强力胶也不能使不规则的东西无缝联结。所以许多时候,我渴望从众声喧哗中凿出一点沉默,就像在澎湃而下的瀑布中剪开一个孔洞。
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以呼吸的相处我常常在对方弹雨般的质疑里张口结舌。我试图阻止,但阻截的话一出口,便会招引更密集的弹雨。有一天我们在伊城东郊的野外驱车闲逛,质疑又一次无端降临。在越来越激烈的问话里,忽然加入了乌鸦的叫声。那是东郊经常出现的景象大群大群的乌鸦,从不知什么地方骤然飞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鸣叫。车停下来,我呆住,他的质疑也停止了。我们呆望着那群乌鸦在空中凌乱地飞翔。在空阔的郊外,在有风的阴天,乌鸦的叫声斩钉截铁。那一刻我便确定,我们之间的质疑和阻截,热情和敌视,都要结束了,就像一切喧哗终将归于沉寂。我对于话语的鄙薄,也许,就是在那一天,在那个乌鸦群集的午后开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