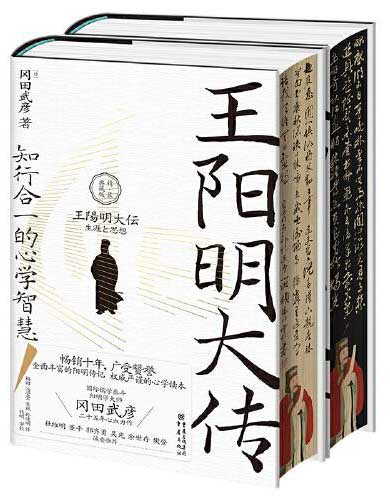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一个人·谁也不是·十万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思自我的巅峰之作)
》
售價:HK$
54.9

《
重写晚明史(全5册 精装)
》
售價:HK$
781.8

《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
售價:HK$
132.2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HK$
80.6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HK$
12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HK$
60.5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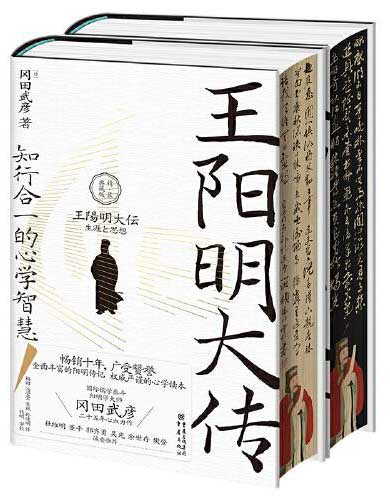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221.8
|
| 編輯推薦: |
李晏是个传奇,他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历程中的活化石,他的镜头所记录的一切,未来可以称为历史。
黄磊
每个剧场,每一出戏,都能看到李晏忙活的身影。几十年下来,他为当代戏剧史建了一套完整、丰富的*手图片档案宝库。每张图片背后都有他亲历的精彩故事,且听他慢慢讲来。
杨葵
有位记者问科学家霍金:世上有什么事情感动过你? 霍金答:遥远的相似性。 每次想到这个回答,我都被感召和激励。年少轻狂,幸福时光。舞台神圣,流水年长。李晏这本书,记述的就是这种遥远的相似性。
史航
李晏精准、细腻的镜头,捕捉了台前台后珍贵时刻。
赖声川
纯粹是一种精神,成长是一个过程。李晏,是一位自发纪录中国戏剧发展的摄影师。他是凭借热爱、凝视、集中、累积的高度勤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中,走在熟悉和重复的剧场里,发现着不同又相融的戏剧画面。一部相机,一双眼睛,一份心灵。注定在舞台上,发现情感、性别、事件和空间。他用观看的方式,通过他的镜头,纪录中国,纪录戏剧,纪录发展,纪录成长。纪录注定的时代舞台上,跌落的、逞强的、冷静的、欲望的、压抑的、纠缠的种种属于戏剧的动作。多少年,李晏的眼睛和他手中的相机
|
| 內容簡介: |
|
濮存昕题写书名,林兆华、赖声川、田沁鑫、黄磊、史航、杨葵等联合推荐。被誉为中国戏剧摄影第一人大陆杜可风的摄影家李晏三十年戏剧摄影生涯的回忆录与摄影精品集,书分两册。一册回忆录,详述作者三十年戏剧缘,如何怀揣戏剧导演梦,误打误撞以摄影见证了当代中国戏剧的发展,林兆华、牟森、孟京辉、田沁鑫、赖声川等等标志性人物在他笔下展现了最富个性的一面;一册三十年戏剧摄影集,以时间为序,以具体戏剧为点,每部戏佐以或长或短文字,赏析与钩沉兼有。两册并作一书,即是一部个人化的当代戏剧史。
|
| 關於作者: |
|
李晏,1964年4月21日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71年春随父母移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新华通讯社。读中学时开始对文学、摄影发生兴趣,曾连续五年报考戏剧学院而未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拍摄戏剧剧照,用图片摄影的方式纪录了中国(以北京为主)当代戏剧的发展历程。三十年来,在用摄影纪录戏剧的同时,还为戏剧的宣传、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报道、评论,以及图片,被媒体喻为中国当代戏剧的活化石。2012年至2015年,在北京、台北、上海、云南束河、长沙举办过六次剧照展览。
|
| 目錄:
|
卷一
002 壹 当年
038 贰 双M时代
106 叁 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
140 肆 剧场,有它的灵魂
220 伍 人热都有个小板凳,屁股大的可以占俩、仨
242 陆 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262 柒 那些曾经在剧场里盛开的花朵
292 捌 穿帮
302 玖 跟着《暗恋桃花源》去流浪
330 零 咱们下一个人生十字路口再会
卷二
1 八十年代 12-51
2 九十年代 52-237
3 新世纪 238-487
|
| 內容試閱:
|
壹当年
认识孟京辉
1994年12月30日夜,《我爱》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混作一团,交谈、拍照,然后渐渐散去。导演孟京辉、舞美设计赵海指挥着部分演员和工人卸台,我坐在旁边帮不上什么忙。孟京辉很平静的样子,既看不出兴奋,也看不出失落。不多的布景和道具,一小时不到就全部装上卡车,赵海也随之离去。临走前,孟京辉最后环顾了一下剧场,和我走进冬夜的黑暗中。
那年冬天不太冷,孟京辉的短大衣敞着怀,围巾随意搭在脖子上。我除了摄影包,怀里多了一缸金鱼。我俩默默无言,缓缓走向美术馆东边的二十四小时都有饭。在没有簋街的年代,这家通宵营业的小饭馆儿是京城文艺青年热衷的去处,与它同样有吸引力的还有新街口的禾丰包子铺。一进门,就看见先到的《我爱》的部分演员和他们的朋友们正在喝酒,气氛非常热烈,孟京辉平静地与他们打过招呼,我们继续往里走,又碰见了中戏沈林博士与几位中外朋友。
这家饭馆儿由三间连在一起的平房组成,夜里生意一向很好,拥挤而喧闹。只有中间屋靠窗的一张小桌空着,虽然是冬天,而且是深夜,但吃饭的人多得不可思议。我俩面对面坐下,我把鱼缸放在靠墙的地方。金鱼是《我爱》的道具,每场演出中,戈大立都要往鱼缸里磕十三颗生鸡蛋,然后再不停摇晃十三次,可谓受尽折磨。那天晚上收拾道具时,场工要把它们倒进下水道,被我阻止了,好歹也是四条性命啊,何况参加了五场演出,也算为戏剧做过一点小小的贡献。后来,这缸金鱼被我养在办公室里,死一条便补充一条,始终保持四条的数量,直到1998年筹备开酒吧时,疏于喂食和换水,才全部死掉,我把它们埋在了一棵丁香树下。
酒、菜上来,我俩不紧不慢地喝着啤酒。平时不太喝酒的孟京辉那天喝了不少,记得我们总共喝了十瓶。从《我爱》开始排练到演出到刚才卸台,孟京辉应该非常疲倦了,可那天他的精神异常饱满、亢奋,与进饭馆前判若两人,一扫刚才的寂寥与失落,滔滔不绝,基本是他说我听。
在酒精的作用下,孟京辉兴奋地说着自己以前的故事,说着别人的故事。讲他在大学如何办诗刊,如何从一名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个中专学校的语文老师,如何与牟森认识并在他的《犀牛》里做演员,有一次演出差点被意外吊死,又如何考上中戏研究生,如何斗志昂扬地想排戏,齐立如何自杀,毕业后如何百无聊赖地坐在学院小操场边的台阶上看着师弟师妹穿梭,而自己从此踏上长达一年的寻找工作之路但是,关于刚刚结束的《我爱》演出,他却几乎只字未提。
那个冬夜,孟京辉可爱得像个孩子,既不在乎那些年轻演员是否邀他一起喝酒,也没因刚刚结束的演出而沾沾自喜可能当时他根本没意识到,《我爱》已经成为中国实验戏剧史上的一个符号。
那天孟京辉的中心话题是成功与死亡。我的感觉是,当时他对于 成功 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奢求,甚至还比较满足现状成为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导演、导出了像《思凡》《阳台》这样有影响力的话剧。但我从调侃和聊以自慰中感觉到了他的悲怆与不甘。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所以在谈论的时候并不感到紧迫与恐惧。齐立是中戏舞美系八八级学生,他的名字首先是与一部著名的小剧场戏剧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齐立,在史航流传甚广的文章《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中是这样记述的:那出戏叫《思凡》,那出戏悄悄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舞美八八的齐立一直痴迷于节气,相信那是我们祖先与大自然的约会,只是后世子孙失约已久,于是,一年来每个节气他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纪念,悄悄履约。有时候是在楼梯扶手上刷小广告,有时候是在布告栏里贴版画,有时候是在露天的垃圾桶上留言,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白衣白裤,伏在操场堆砌的几条大冰块上面(都是齐立自己买来,用三轮拉到学校),号称冰葬齐立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今日春分,今日立夏,今日清明,今日大暑。我们喜欢他的这些提醒,宿舍管理小组和校方不太喜欢,嫌他公器私用,窃据宣传栏。大雪是齐立心目中最有意思的节气,他觉得应该隆重庆祝,隆重到排一出戏,就像农闲时乡间该响起锣鼓唢呐。于是他找到戏文八九的关山,找到孟京辉,也找到《思凡双下山》的昆曲剧本。1992年12月7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的台历都是我从图书馆馆长办公桌上撕下来的,然后复印在了说明书上。关山在演出者的话里这样宣告:前世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 那一天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录音机和音箱搬到宿舍窗台上,重复播放着那些饱含雪意的歌曲,从《一剪梅》到《北国之春》。我们盼望真的下起雪来。晚上演出更是沉醉的狂欢,小和尚小尼姑在结尾团聚,剧场外已经有人点起了鞭炮,演员们谢幕的时候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舞台似乎直接暴露在星空下。那天晚上没有下雪,但是散场以后约二十分钟,外面下起了大雾很快就看不见齐立了,他在演出一周后默默自戕。理由可以被分析出多层,但,伤痛只有一种。(《读库》0601)
说完齐立,孟京辉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梅耶荷德。我当然知道,考戏剧学院准备专业课时,曾读过他的著作,虽然似懂非懂但总归知道。他又问: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这真把我问住了。然后,他用了很长时间述说梅耶荷德之死。这个时候,他没有看着我,目光越过我头顶聚焦在某个点上,仿佛他眼中有个具体的梅耶荷德的形象,在与之交谈。当讲到梅耶荷德顾不得穿大衣跑到雪地里,踉跄着追逐政府文化官员的汽车,挽留其继续把戏看完的时候,他的思绪似乎也停留在那遥远的冰雪世界里。
当时我以为他谈到梅耶荷德只是偶然,因为前面说到了齐立的死。后来看了陶子专访孟京辉的文章(《今天》文学杂志2005年4期春季号)才知道,他对梅耶荷德是何等热爱。梅耶荷德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大师,他中戏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梅耶荷德的导演艺术》。梅耶荷德所经历的、所实践的、所得到的波澜壮阔的时代与反叛的性格、独特的演员训练和演出风格以及对戏剧革命性的继承和发展、有自己的剧院与众多的观众,正是孟京辉追求的目标。
我们离开饭馆时已经五点多了,这是1994年最后一天的清晨。深蓝的天空映出一抹朝霞,马路上已经有了早起的人们和无轨电车。我俩打了一辆面的回家。在摇晃的车上,孟京辉重又恢复了沉默。我努力保持着平衡,不让鱼缸里的水洒出来。
时光倒退五年,由尚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孟京辉和导演系本科八七级学生张扬发起,一群无所事事又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决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即1989年的12月31日,在戏剧学院操场边的巨大煤堆上演出萨缪尔贝克特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此举被校方所闻,予以制止(孟京辉编著《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 新星出版社)
五年之后,孟京辉又遭遇相似的尴尬。由于没拿到演出证,《我爱》不能公开演出,只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在位于东城区南阳胡同六号的中演文化公司排练场内部演出五场,入场券全部免费派送。
心中有目标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差距,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艺术家个体之间的矛盾。所以在那个微醺的凌晨,孟京辉在冷静、坚强和少有的严肃中,透露出少许淡淡的忧伤。
也许当时孟京辉还不十分自信,甚至对刚刚结束的《我爱》是否成功都不确定,所以才不愿提及,用往事和梅耶荷德隔离自己的情绪。那一晚,我感受到了孟京辉最真实的一面,纯净如水,后来再没听他如此真实地袒露过心声。那个时候的孟京辉激情荡漾、满怀责任感与崇高理想,同时又愤世嫉俗、怀才不遇。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当我陪法国《解放报》一位女记者去家中采访他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无比自信、眉飞色舞的孟京辉。那次采访随意而热烈,话题广泛。女记者是中国人,也是学中文专业的,她对《我爱》激赏有加,说以她的想象力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剧本排成舞台剧。孟京辉自信并略带匪气地笑道:这算什么呀,我可以把一张北京市交通图排成一部特别好玩儿的戏!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诗人受到尊重的年代,还是一个可以坚持理想的年代,还是一个可以幻想并且不需要为幻想付出代价的年代。
刘震云曾说过: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该说的话,在作品里也已经说了。许多艺术家都这样,艺术似乎具有补偿作用,可以弥补艺术家自身的某种缺憾。而孟京辉是个例外,他不仅通过作品说话,在生活中也特别能说,并且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声情并茂、辞藻华丽,如果继续当语文老师,肯定也特别胜任。我认识他时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他在给人讲故事。
1993年8月8日晚上,黄燎原借生日之机,把一大群朋友请到他刚创办不久的汉唐工作室的所在地北太平庄七省联合办事处,聚会带认门儿,其中就有孟京辉和廖一梅。我去的时候,孟京辉正口若悬河地给几个人讲一部刚看过的电影《下次我演谁》,他身边坐着中学生一样文静、乖巧、留着短发的廖一梅。因为听说他是搞戏剧的,我便坐下来听他谝。接着他又说起正在排一部让日奈的名剧《阳台》。那天,我俩没过话,他也不认识我是谁。
8月22日上午,我和黄燎原等人去王府井中央美院(原址)的一个画廊看展览。黄、孟约好了在那里碰面,商量《阳台》宣传的事情。孟儿带去了几幅剧照,构图、拍摄技术都很糟糕。黄说:这怎么能用,没其他的了? 孟儿嬉皮笑脸地说:没别的啦,我觉得挺好的,凑合用吧。搞得小黄同学很无奈。见我背着相机,求助道:晏儿,你去给拍点片子吧,最好拍得怪一点。于是,我跟着孟京辉去了排练场,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厅。
那天下午,剧组原本的日程安排就是拍照,用于印节目单、海报等,已经找好一位姓戴的摄影师,人家带着灯,我就沾光跟在旁边一通狂拍。结果由于我的效率高,孟京辉先看到了我的照片,甚是喜欢,印节目单时,用了一半我拍的照片。那是当时我见到的最厚的、最讲究的节目单,像一本小书,我的名字赫然印在上面,这是我第一次与戏剧发生了直接的关联。
9月18日《阳台》首演后,我三夜没睡觉,为剧组洗了上百张剧照。暗房里的红灯很容易使人发困,最后一个晚上,几乎是洗一张照片打一个盹儿,因此许多照片显影过度,不得不重洗。通过这次合作,我和孟京辉成了好朋友,我的呼机经常显示出他家的电话号码。
《思凡》是孟京辉早期重要作品之一,从1992年至1998年共演出近四十场,凭此剧参加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研讨会,获优秀演出奖和优秀导演奖,奠定了他在实验话剧院乃至中国戏剧界的地位。而此前,1992年中戏研究生毕业后,孟京辉怀揣导演学硕士文凭却报国无门,整天在中戏校园溜达、踢足球、看姑娘,兜儿里揣一把牙刷在师弟们各宿舍蹭吃蹭住。后来,是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先生慧眼识珠,把孟京辉调进剧院,从此才开始了他既在体制内,又游走于边缘的戏剧生涯。
《思凡》是孟京辉到实验话剧院后排的第一部作品,不再是刘天池、吕小品、宋丽博等主演,而换成一水儿实验话剧院的青年演员:郭涛、佘楠楠、邹倚天等。在实验话剧院小剧场逼仄的舞台上,七名演员演绎了几个贯穿古今中外、煞是有趣儿的爱情故事。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提及的细节是,每当有少儿不宜的地方,便用一块写着此处删去字的白布遮挡住演员,此时观众无不会心大笑贾平凹的《废都》当时刚刚出版。
1998年复排时又换了一批新演员,有刚毕业的朱媛媛、廖凡、周杰、孙强等。当时孟京辉还在日本,基本是演员自己对着老版录像抠出来的。他一回国,紧张合成后就演出了。这一版的舞美比较复杂,也很漂亮,使用了大量棉花,整个舞台像一个软雕塑,设计者是尚在中央美院任教的美术家焦应奇。
从三个不同版本的演员也可以看出,当时孟京辉网罗了众多实力派演员,这些演员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戏剧界和影视界的佼佼者。
很遗憾,我没看到1992年12月7日中戏那一版。
我是在初春乍寒的1993年初,通过报纸报道《思凡》知道孟京辉的,但那年首演时并没看。11月18日《思凡》重演时,我第一次进实验话剧院小剧场看了此剧。之后一年多里,只要此戏演出我都会去看,总共看过十多
遍,当然是沾孟京辉的光。到目前为止,除了《切格瓦拉》和《暗恋桃花源》,我看的次数最多的话剧就是《思凡》,当时甚至能背下大多数台词。
某次演出,我请朋友陈晓妮和佛教杂志《法音》的编辑纯一法师看戏,孟京辉也认识纯一。开演前,晓妮呼我,说因为堵车要迟到一会儿。最后一遍铃响过之后,却突然停电了。没有空调,剧场里马上闷热起来,观众只好重又回到院子里。过了十几分钟,晓妮和纯一刚到,电也来了。演出完,孟京辉知道这个小巧合后,调侃纯一:你这么牛啊,你不到我们都不能开演。
1989年4月,剧协在南京举办了中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其中有一部《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编剧,谷亦安导演),从内容到表现风格都与以往的话剧迥异,引起了诸多争议。研讨会上,当戏剧界的众多著名导演、批评家都对这部作品横加指责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强硬地表达了对这部剧的支持,对自己师长的对抗,他便是刚考入中戏导演系读研究生的孟京辉。
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研讨会,是继1989年之后又一次小剧场戏剧盛典,参演剧目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情感操练》、辽宁人艺的《夕照》、上海人艺的《留守女士》和《喜福会》等十三部。《思凡》作为参演剧目之一,荣获了优秀演出奖和优秀导演奖。11月19日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场举行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孟京辉一如往常地不修边幅,与气宇轩昂的李默然等老艺术家同站在领奖台上,颁奖者是夏淳等。
典礼结束,外面飘起了雪花,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孟京辉和我从儿艺剧场又赶往北京站口的国际饭店,因为参加研讨会的日本代表团邀请孟京辉前去一叙。日本专家大概有七八位,我能记住的有丹羽文夫、濑户宏和杉山太郎,在交谈中,后两位一直在做翻译。这之后,我和丹羽文夫、濑户宏还打过多次交道,而杉山太郎因车祸英年早逝,这都是后话。那天的谈话是在大堂咖啡厅进行的,时间约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孟京辉向日本专家介绍中国实验戏剧的发展概况和自己的创作经历。正是这次谈话,才有1995年孟京辉携《思凡》和《我爱》赴日参加爱丽斯戏剧节演出(《我爱》在日本演出时的剧名是《温床》),和1997年至1998年应丹羽文夫之邀去日本游学、考察半年的事情;也才有了我和日本留学生合作,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谈话结束,日本人纷纷掏钱AA交咖啡钱,我和孟京辉面面相觑,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
走出饭店已是午夜,外面变成白雪皑皑的世界。孟京辉打了辆面包车,把我捎回儿艺剧场取自行车。那天我基本是推着车走回宣武门的,因为地面的积雪太厚,根本骑不动。
那两年孟京辉不像现在这么忙,经常叫上我一起看戏、参加各种活动。当时,盛志民、路费汉强在东三环内新源里附近的外交人员俱乐部(现在的沈记靓汤)地下一层搞了个摇滚酒吧,我们经常去那玩儿,黄燎原、何勇等也经常去。那个维持时间不长、赔本儿赚吆喝的酒吧在中国摇滚史上着实留下了一笔。
那时候还有面的,方便且便宜,而我则经常骑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所以一直保持着令同龄人羡慕的身材。孟京辉非常佩服我一点:无论玩儿到多晚、喝多少酒,第二天八点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哪里知道啊,当时我还没有宿舍,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之后,某个阳光明媚、温暖冬日的午后,我和孟京辉坐在公交车上,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新剧的构想,我要进行一次语言的实验,把某个汉字玩儿到极致,让观众先对这个字产生好感和敬畏,然后再产生反感,最后直到一听这个字就恶心、想吐! 他说的这部剧就是《我爱》。
这部剧从1994年7月30日到10月23日,总共写了三稿。我知道时,剧本已经基本完成。编剧有四位:孟京辉、黄金罡、王小力、史航。可我一直记得编剧中有廖一梅,没有孟京辉,这次一查资料才发现,当时廖一梅还没有参与孟京辉戏剧的剧本创作。
史航就是写《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的那位,也是后来成为著名电视剧编剧、影评人、网络红人、电视主持人、客串演员的可爱胖子。当时他还没这么红,也没这么胖,中戏戏文系毕业后留校,但当时不是当老师,而是在图书馆工作,与我是同行。他的名片上印了一句特矫情的自我介绍:历史的史,航行的航。史航的经典段子是,无论你说什么,只要是艺术范畴内的,尤其是与文学、戏剧有关的,他马上可以说出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如果他认为某本书好,便一下买十本装在包儿里,向你推荐时,你已经有了便罢,如果没有或表现出丝毫怠慢神情,他立马掏出一本送你,送完再去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