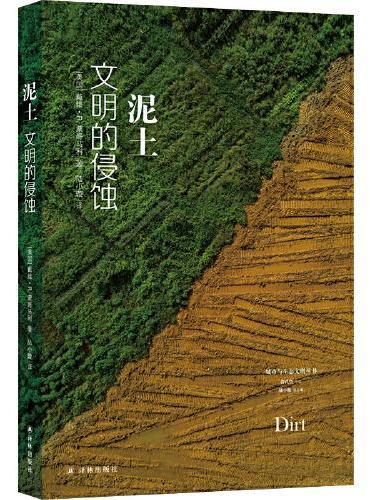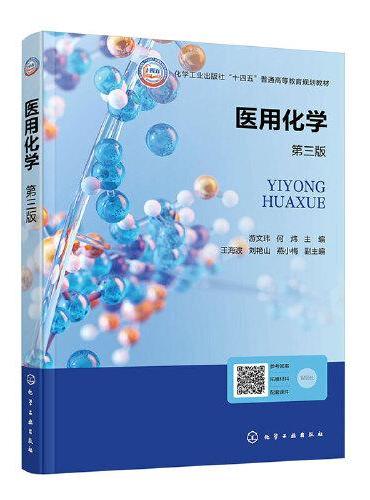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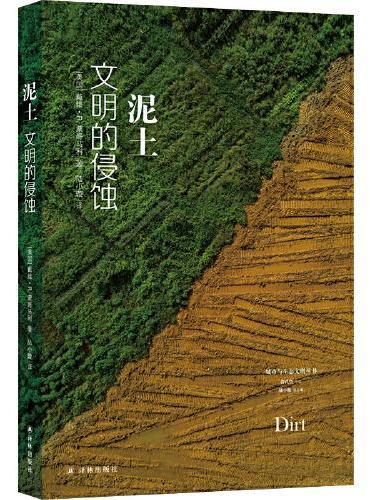
《
泥土:文明的侵蚀(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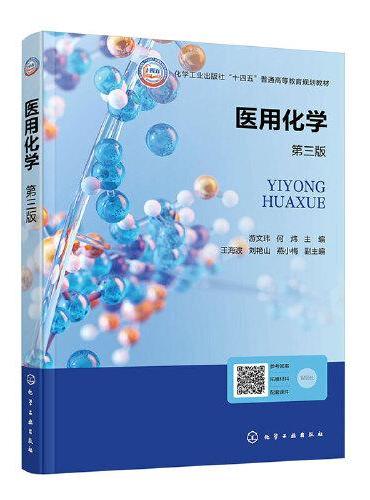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
医用化学(第三版)
》
售價:HK$
57.3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
| 編輯推薦: |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之叶辛卷 《飓风》。
著名作家叶辛精心打造的力作,畅销约10万册,内附作者手稿 。 富家公子真正的身世却是个谜,恐怖的飓风袭来,一切荡然无存。他能否回到从前,夺回失去的一切?
|
| 內容簡介: |
|
姜宾扬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十七岁了,可是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同自己母亲的关系,关于他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却始终是个谜。在十年浩劫如飓风般席卷而来的前夕,他正沉浸在与漂亮姑娘尹丽妮的初恋之中,竟然没有觉察到他所置身的富足豪华的姜家花园即将破败崩溃
|
| 關於作者: |
|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去贵州乡村插队十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会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曾担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风凛冽》《三年五载》《飓风》《在醒来的土地上》《华都》《缠溪之恋》《客过亭》《圆圆魂》等。其中,由其本人根据《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
|
| 內容試閱:
|
原序: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五十年了。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就在上个月,我去黑龙江图书馆演讲时,还收到了哈尔滨知青们送给我的厚厚两大本哈青文选。为的是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年。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五十周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啊!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四五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已是社会的中坚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有人说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七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客过亭》。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近10本。这些作品的汇集出版,我想,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长篇小说书系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知识青年的五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1966.4一场震撼中国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悄悄掀起。姜宗豪是有这种直觉和预感的。随着四月的来临,寒冽的西北风大大削弱,迎面吹过来的,更多的是潮润的东南风了。晴雨相间的上海天气,很难让人预测哪天夜间和黄昏会出现暴冷暴热。平时很注意冷暖衣着的姜宗豪,现在的注意力几乎不在气候上。他必须关注形势。印象最深的便是进入四月以来报上的文章,自去年十一月批《海瑞罢官》的长文刊出至今,话已经由所谓的评一变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之类。姜宗豪再笨,再在政治上貌似幼稚,都看得出来,报上骂的是古人,是编戏的学者,其真正目的,却是旨在掀起一场风暴。难以在精神上摆脱的是,这一预感近日来一天比一天来得强烈了。他不能预见这一狂风骤雨将以一股什么样的势头在中国大地上席卷,更不能想象这场风暴将给亿万芸芸众生带来些什么。他唯一关切和担忧的是自己的家业,以及这偌大的家业如何承继。他历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时常来骚扰他,以致他对政治敏感得近乎神经质了。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了他,共产党要搞一次大的运动。是的,风暴确实是在酝酿中掀起。每一个字伴随着他的怦怦心跳出现在脑际。是安逸富庶的日子让人满足,还是天天如此、无波澜的生活窒息了人们的欲望,姜宗豪说不清了。反正,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一潭静水般的天天如此的岁月:发财的念头是早已断绝了,但同时却也免除了破产的可能。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保证了他近百万的家资,保证了他仍能居住在世人羡慕眼红的花园洋房中,只要不搞运动,他安全舒服地支取高达六百元的工资,领取款额不小的定息,开开神仙会,享受点统战待遇,他比一般人生活得优越。上海这个地方,自一八四二年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被洋人称作东方明珠的冒险家乐园的一切痕迹都已荡然无存,但是只要有铜钿,就能买得来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还是难以清除。姜宗豪在任何场合,都能感觉到向他投来的种种羡慕尊崇的、妒忌的有时甚至是谄媚的目光。他觉得日子满可以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如同春节礼盒上的贺词:年年如意,岁岁平安。他不懂共产党为啥还要搞运动,为啥不喜欢平静?难道平静的世界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吗?难道政权在哪些地方显示了不稳的迹象吗?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姜宗豪听出是佣人邹素贞的脚步。邹素贞在半开的书房门轻咳了一声,呼唤般低声说:姜先生。姜宗豪走到门边去:人来齐了吗?宾泓从学堂回来,我就同她讲了,你要和他们讲一件事,她没再出去。大小姐来了姜宗豪不经意地蹙着眉,素贞的称呼总是改不过来,喊宾汶还叫大小姐,她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他问了一声:牙牙带来了吗?没有。我问了,她说阿婆讲,牙牙太小,春天里传染病多,不让带。虽然牙牙还小,不会讲话,但是看不到她,姜宗豪还是有点遗憾。他咕哝了一句:怕风吹,叫辆出租车来嘛。是呵,我也这样讲。素贞是老佣人了,摸透了姜家老少的脾气,说的话总能投人脾气,她不无遗憾地吁了口气,宾涓到里弄办事处转了一圈,也回来了。就是宾扬还没回来。唔,姜宗豪沉沉地应了一声,他去哪儿了?不晓得。这些天,每天放学,他都回来得比以往迟。邹素贞沉吟了片刻,像终于打定了主意般说,姜先生,我要告诉你,那只白鹭花园里的那只白鹭,还是飞去了。姜宗豪受了惊般问:飞走了?飞走了,没再回来了。终于飞走了。姜宗豪叹了一声,语气里透着悲凉,他自己几乎不曾觉察。姜家老少都熟悉这只白鹭,头颈雪白,羽冠乌黑,它的嘴长、脚长,抖开双翅时,洁白的全身像是泛着银色的光泽。每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花园里传来几声粗哑低沉的鸣叫,白鹭便算是来姜家花园报到越冬了,它机警而性静,耐力极强。一整个冬天和早春,白天它几乎都栖息在花园里粗壮的香樟树巢里;夜幕降临以后,它鸣叫几声,拍翅飞到市郊去觅食鱼蛙、小虫、小鸟。天明之前势必回来。姜家的人都很喜爱这只远方飞来的白鹭,从不去逗它、骚扰它,有时候,白鹭在巢窝里呆得厌烦了,飞落在花园的草坪上,在几近干涸的池塘边散步,姜家的人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着了这位客人。昨天清晨姜宗豪站在阳台上伸腰曲背活动筋骨没见白鹭,早饭时随口问了一句,想必邹素贞留了神,特意来回这句话了。一抬头的当儿,姜宗豪见素贞仍站在身前,不觉有点诧异了,他沉思默想好一阵儿,她还站着干啥?姜先生,还有一件事什么事?何翠卓来了。邹素贞说话的声音放得很低很低。她来干什么?她来干什么?姜宗豪一腔的烦恼全被这句话逗了起来,挥着手道,说说我不在。怪我,已经说先生在了。邹素贞赔罪般低下了头。唉姜宗豪眼前掠过何翠卓同三个女儿在楼下客厅里坐着相对无言的尴尬相,眉头皱得紧紧,她在客厅里吗?不,在我那里。姜宗豪没再说话,转身就走。邹素贞的屋子在厨房旁边,进花园大门绕过林荫小径,走进后门三五步就是。从二楼上下去,不走大扶梯,可以走屋角的小楼梯,转角楼梯下到底,几乎就是邹素贞的屋门口。站在幽暗的门口,姜宗豪迟疑了片刻。他听到了一丝声音,细加辨别,才明白是自己的喘息声。太紧张了,三个女儿都在前面客厅里,儿子宾扬随时都要回来,而他他一个堂堂男子,却同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躲在佣人房里。姜宗豪眼前飞迸着闪烁光斑的星花,心里堵上了一块硬石。那天那天猝然发生的一幕,陡然出现在眼前。怪他和何翠卓太不检点,怪宾扬进来得太不是时候。能怪他吗?他走进父亲的房间从来没有佣人的习惯,轻咳一声,或是小心地叩叩门。这花园里的一切,这幢楼房里的一切,哪样东西将来不属于他呢?哪个地方他不能走进呢?他当然自在地随随便便走进来了。那么怪自己,怪何翠卓喽!天地良心,那天他俩私下在一起时,是最正常最守规矩的了。他们不是躺在床上,他们离床还远得很,她连外衣都没脱,他们只是相偎相依地坐在沙发上,他搂着她,她像根藤子缠着他似的抱着他,并没其他非分之举。恰恰在这时候,宾扬门也不敲自由自在地走了进来,就像走进客厅倒水喝,走进餐厅找东西吃。何翠卓的脸色倏地变得一阵阵苍白,双眼里露出恐怖的神情。姜宗豪只觉得两条搂紧她的手臂僵直了,心在跳很少有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心跳。他应声抬头的那一瞬间,看见了儿子惊骇的脸,看见了宾扬眼里显露的嫌恶神情,看见了小伙子脸上常会有的愤愤然的表情。门砰一声撞上了。姜宗豪吃了一惊,佣人卧室的门几乎是无声地打开了。他看到了一张凄苦的、清瘦而憔悴的脸,脸上一对忧郁得绝望的大眼睛,在光线晦暗的黄昏时分,这张脸总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还要年轻,年轻好几岁。1980.9在那场震撼中国的风暴陡然掀起的年头,他怎敢想象离座站起来走向濒临花园的窗口那一瞬间,姜宾扬突然意识到,他那封写了撕、撕了写,总也起不了头的书信,应该这样开头,直截了当地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哥哥。每当想起远在外地的哥哥姜宾成,宾扬脑际总会浮起哥哥讲的一个故事。那不是一个有趣味的故事,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严格地说那只是常识。宾扬那时候还很小,头一次从宾成哥哥的嘴里听说我们人类生活的大地是个球。他觉得这太令人惊奇了,将信将疑地望着宾成哥哥,缠着宾成哥哥给他细细地讲清楚。不料宾成哥哥越讲越玄了,他不但以肯定的口吻说到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他还叫宾扬大为吃惊地说这只球在十三四亿年之后,将要爆炸,地球上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宾扬怎么能相信呢,他逮住宾成哥哥的后衣袖追着问:姜家花园也要爆炸吗?马路也要爆炸吗?黄浦江和外滩也要爆炸吗?宾成哥哥说如果那时这些仍然存在,是会爆炸的话未说完宾成哥哥让爸爸叫走了。宾扬眨巴着眼睛,纳闷了足足一晚上,那天夜里,他整个上半夜不曾合眼,孤零零一个人睡在静幽幽黑漆漆的屋子里,大睁着双眼想象爆炸那天的情形哈,那时候他真是太小,连十三四亿年是个什么概念,他都搞不清。现在他懂了,宾成当年并没有骗他,五十年代的地学研究成果是这么说的。到了八十年代,到了今天,地学界的许多学说认为,自今日起计的五十亿年到六十亿年期间,太阳将会恶性地膨胀起来,它所释放的热量将会使地面温度升高到一千度,使海洋化为一整片覆盖苍穹的迷茫云雾,整个地球会变成《圣经》所说的一片地狱之火。到这焚天浩劫的岁月来临时,会是个什么景象呢?宾扬又读到的一本书里说,其实人类活不了那么久。地质记录表明,任何动物品种的平均寿命大约都只有五百万年,连一亿年都不到呢,何必去思考那五十亿年悠邈岁月后发生的日崩月裂之事呢!但今天宾扬不是以童年时代杞人忧天的心理来看待这一科学预测的。是呵,人可以不去考虑不可确知的未来,可以不管五十亿年后地球上将是一片腾腾烈焰或五百亿年后地球会变成生命全无的冰天雪地,太阳将闪烁如星,月亮会被地球拉近。这些洞见未来的话同巫婆法师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一样可以被置之脑后。但人应该了解他作为一个过客生活的这个地球,应该了解漫漫的岁月和他生活的这块土地的演变及幻化无穷的可能性,从而更加珍惜他在人世间那短暂的几十上百年的时间,以便他竭尽所能地活得更有质量些。新挂的印花窗帘拂上了宾扬的脸,尽管有风,天气却热得和酷暑天里差不多。虽已进入初秋,大伏天的余热仍然未消,这便是民间常说的秋老虎吧!给哥哥的信总写不好,姜宾扬归罪于临近中午的这股难耐的酷热。他拂去了印花的涤纶纱窗帘,目光落在花园里的草木上,除了那条幽僻的通后门的小径边一长排花盆被搬走了之外,花园里的一切面貌依旧。在这夏末秋初的日子里,满眼里的花草树木,似乎比当年更为繁茂、更为悦目了。幸好把他家从这幢花园洋房里赶出去以后,这里的住房分配给了六七家知识分子,房屋本身,连带洋洋大观的花园,都没遭到掠夺般的损害。当初这幢楼房,若是住进了街道办事处的某个单位,搬进了里弄生产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那么,眼前这派面目依旧的感慨,是呼唤不出来的。瞧,在几近干涸的池塘那边,当年一到冬天便会飞来的那只白鹭,是经常在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记得,池塘水蓄不起来的日子,老佣人邹素贞曾向爸爸提议,请几个人来将淤泥挖除,重新灌上一塘清水。爸爸说,宾扬喜欢游泳,经常买不到跳水池的票,干脆打个报告,申请在花园里建个小游泳池吧。爸爸的申请递到区体委就给卡住了,人家根本不理会资本家的申请。但是宾扬当时很受感动,爸爸考虑问题,从来是把儿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哦,爸爸,现在这题目该由宾扬来做了。他当然不可能旧事重提,修什么私人游泳池,但他得尽快请人清除淤泥,把清澈澄净的池塘恢复起来。那是他美好童年的回忆,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