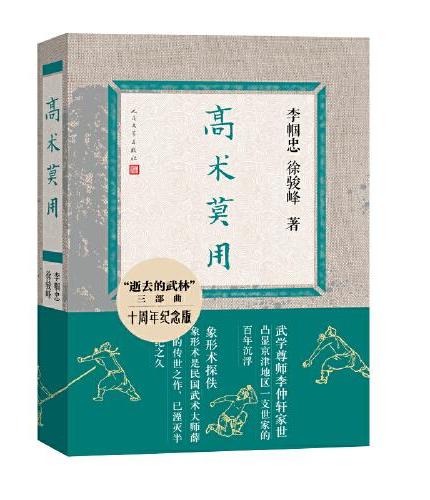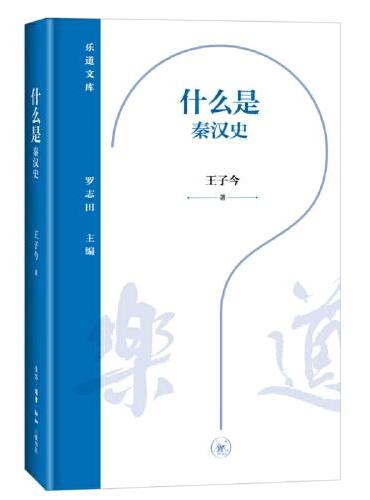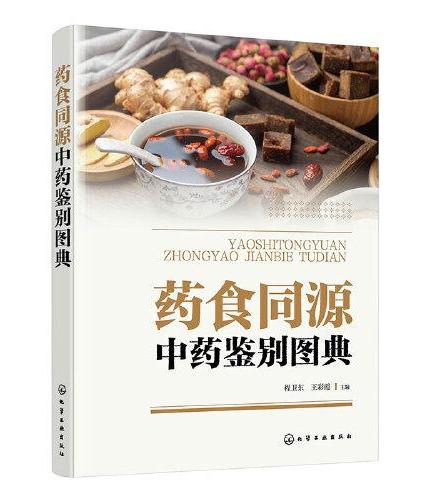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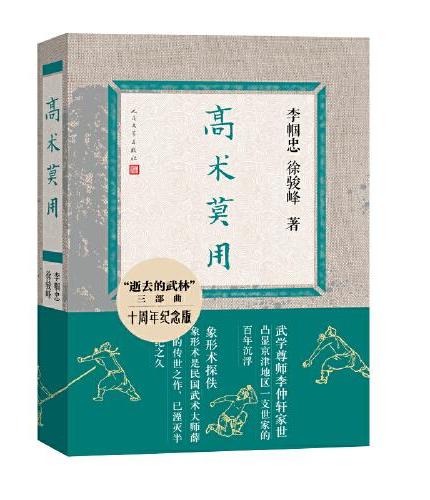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HK$
54.9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HK$
98.6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77.3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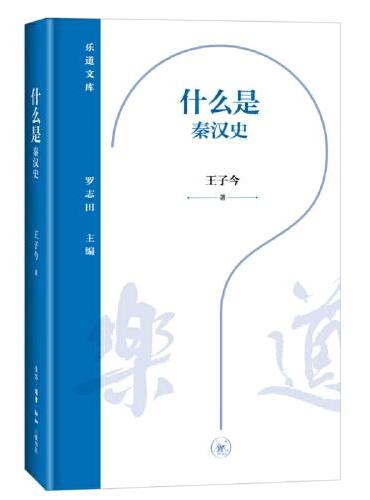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HK$
80.6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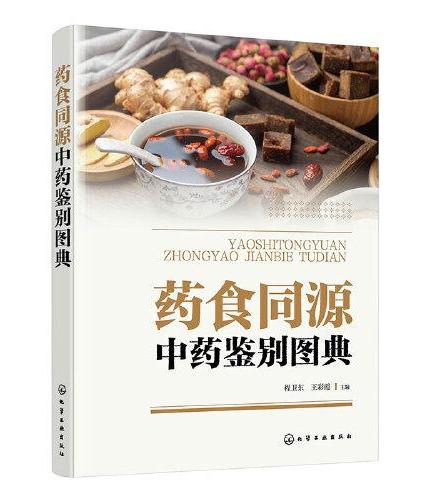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
| 編輯推薦: |
☆《爸爸爸》作者韩少功击节赞赏,称本作品具有社会学和史学价值。
☆ 笔记体小说写文革,篇篇精彩,拳拳到肉,一个小女孩眼中摇曳多姿的牛鬼蛇神
☆ 滇南矿区被尘封多年的畸情故事,尊严在烂泥中潜滋暗长,欲望在水泥地上生根发芽。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推荐作品。同名大电影紧张筹划中,可能比张艺谋《归来》更值得期待
|
| 內容簡介: |
《铅灰暗红》是一部长篇小说。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记录文革时期的非常故事,讲述被纪录者独特的生命姿态。
借主角小女孩红英之眼,目击众多残渣余孽五味杂陈的故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淡的,咸的。悲的,喜的,奇的,怪的,神的,仙的,冷的,暖的。正常的,非常的。在貌似轻松的说笑里,惊觉人类历经曲折却能归于美好的重要依据!
聆听那些被历史喧嚣轻易盖过的一丝微弱之音。献给在时代缝隙里开出生命奇葩的人!
|
| 關於作者: |
半夏,原名杨鸿雁,中国作协会员,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致力于长篇小说及自然人文随笔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心上虫草》、《活色余欢》《潦草的痛》《忘川之花》。获得首届老舍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云南省政府的四个一文艺人才新人奖,昆明市政府文艺奖茶花奖、边疆文学奖等。
小说随笔等散见《天涯》《小说月报》《十月》《小说界》《山花》《大家》《美文》《红豆》《飞天》《安徽文学》《滇池》《边疆文学》《凤凰周刊》《伊犁河》《西部散文家》等处。
|
| 目錄:
|
目录
自序
引子
一匹受惊的马
偷看美人柳惠兰
老翠
霸地草
大厚的声音
八姨的表情
花夭
民兵五连连长
罗盛教的老乡
姚舜父子失踪事件
花子老五捉奸记
粪贼
苹果园里的坟
黄君的爱情
张嘴闭眼之间
五七干校来的小鱼鱼和胖虫虫
转弯子公社
鲁宁老师
一根在血管里游走的缝衣针
九车间的甜蜜情人
背锅老二跛子老四憨包老大
细细打磨的钩针
俱乐部
一只搞穿梭外交的兔子
水红色的指甲花
雁鹅肉
后记:狗屎花和勿忘我
|
| 內容試閱:
|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
我在我每一本长篇的自序或者后记里都会引上这一句话。
是的,是时候了,离开那时有了三十年的距离。这样一段岁月逐渐拉长的距离,让我可以对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有一种客观的回忆了。
一段时间里我较集中地读了一些著名作家围绕着一座城一个镇甚至一条街区展开来写的长篇小说或随笔,它们都采用了这样的结构,没有一个线性发展的主体故事,所有的篇章都可独立成章,有隐约的联系,但只是人物或事件的某种牵扯。土耳奇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印度裔英籍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捷克作家杨聂鲁达的《布拉格小城画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或许都可以作掌上观,它们都是我非常热爱阅读的作品,有的不仅只读了一遍,而是反复地读了两遍三遍。
别人写过文革时代结束前后的无数城市的故事,甚至一座城市里某条街某个围墙圈着的大院里的故事,写过无数县城小镇乡村的故事,可是我还是要写下属于我的故事。
我那个地方早年的故事肯定有不同于城市不同于乡村不同于县城的独特之处,我的那个地方是中国的一个冶金工业重地。它地盘不算大,但是那里的人真正地是来自全国来自五湖四海。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故事,何况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故事。
那个地方的故事枝枝桠桠,盘根错节。穿越时空,我可以把那地方的故事,以一块一块碎片来打补丁似地缝缀它。那是我年方10岁的眼睛看见的故事,我的眼睛里还没有揉进杂质,我的眼白还微微地蓝着,我的瞳仁还像皂荚树剥开来的苦里珠一样黑漆漆的。我10岁左右的生活还是一种童年视觉,那时我还没有来月经还没有发育成一个羞涩的少女,我的两个乳房还瘪瘪的,两个小小的乳头,一圈小小的乳晕就像衣服上的两粒按扣,钉在我瘦叽叽的身子上。
10岁孩子的记忆力空前绝后的好,那时候听过的一种声音看过的一张人脸的表情闻过的一丝味道,都会在一瞬间让我把那个地方的人和事重新捡起来,拼出一个图景来。
我热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喜欢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顾长卫的《孔雀》,王小帅的《青红》,喜欢刘欢的歌曲集《六十年代生人》。我自信地认为我的个人记忆将与他们的个人记忆汇聚成一种集体记忆,精彩互补。
余秋雨先生在写作了《借我一生》后,原创了一个词汇记忆文学,有很多人反对记忆文学这种说法,认为记忆是真实的客观的存在,是纪录,而文学是创作,有提炼、升华和想象,有技巧。
我想说的是记忆其实是不完全可靠的,想一想,我们的大脑并没有把自己经历的所有人和事全部记下来,而是有选择地记忆,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忆常会引起争论,因为每个记忆者记忆事情的角度不同,视点不同,记忆的结果就不同,甚至完全不同。
在个人记忆之外其实还有着相关的其它往事,这些你当时没记住的往事只是隐匿于你的记忆之外,并不能说它没有存在过。你印象深刻,强烈地记住的人和事一定是因为它们曾像一粒子弹击中过你,你当时被惊动被感动被触动了,你大脑沟回间大脑皮层上记忆神经元敏感地捕捉过这种刺激,然后它们可能沉睡,直到环境适宜时苏醒。
2007年9月我从云南到了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为期五个月的学习。我随身带了寥寥四五本书到学校,其中一本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他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没有带他那本在世界上发行量很大并藉此获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原因只有一个,我想我更喜欢阅读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还是人自己,我认为每一个人从小长大,他一直是在参与着这个世界的建构的,一个叫奥尔罕帕慕克的人他如何就成了今天的他呢?
我从来不讳言,《铅灰暗红》这本书相当于我的成长自传。但是它又不单单是一次对人生经历老老实实的复述,它还有大量虚构和想象,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错过那个时代的一些细部。那些细部就是时代的缝隙里的景象,它们曾是活生生的。
在书里,我写了好些稀奇古怪的人,其中有各种流氓坏分子,有各种真疯或装疯的疯子,甚至一些残障弱者,有惨死者暴死者,这些人中有性情扭曲者或不顾一切的思想解放者。现在,我认认真真地思索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我发现,我的某种审美品味竟然是被称为流氓的人启发的,我的成熟而被事实证明的判断竟然是某个社会的残渣余孽教会的。那个年代,他们想追随主流,却置身边缘,这些人的人生滋味值得我今天咀嚼,我把我书里的人物看成是时间窄缝里开出的一朵朵奇葩。
公元前388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敦促雅典城的长老们放逐所有讲故事的人,认为他们对社会是一种威胁。柏拉图指出:作家摆弄的是思想,但不是以哲学家那种公开而理性的方式,而是将思想掩藏在艺术那诱惑人心的情感之内。柏拉图断言,讲故事的人都是危险人物。某种意义上我倒是希望自己成为柏拉图特指的那种作家,一个讲故事的危险人物,把思想隐藏在了诱惑人心的情感之内,因为那会表明我的文字有一种过硬的思想质地。
我悄悄地藏身暗处,看着光亮的世界,分辨其纹理,理解、体会并穿越别人的生命。于是,我通过书写,再次聆听到了那被历史的喧闹和欢乐之声轻易盖过的一丝微弱之音。
我把书定名为《铅灰暗红》是因为,铅灰与暗红这两种色块在一起很和谐很好看,那散发着金属冷光辉的铅灰色衬以一抹暗红,会在一派凝重间突然跳跃出一点温暖一点生动我盼望着我的读者读这本书时有这样的感受。
多年前反映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打动了我,整部电影一直是黑白画面展示纳粹的残酷和犹太人的悲伤,但在电影结尾时画面突然变成了彩色,半个世纪后,那些被救助而幸存下来的人们前往墓地纪念恩人辛德勒,这时,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从画面上缓缓走过。
是那个红衣小姑娘让我因为悲伤而含在眼里的泪花夺眶而出,那一瞬,我的悲伤得以化解,我的情感得以释放。
在我40岁的某一天我决意要把30年前的一段生活记忆复活,并且固执地确信只有我才能完成那段日子的记录,这事非我莫属,而且必须完成。一种眷念一种无法割舍的纠扯便开始缠绕我,让我不得安生,这是我的宿命,而今我即将50岁。
我要在线性的时间维度里,淘洗过往的记忆。我认为我付诸文字的叙述真的会有社会学和史学的价值,而一张张我的私人照片传达的信息也是对公共生活的显影,因为,不论是现在写下的文字还是那些旧照片,它们最终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历史了。
真正让生命丰美的,往往是即将遗忘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田深处的老根,虽然忘了浇水却还没有枯死。
我的心里装着很多故事,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我鲜榨了它们,在它们还没有干枯的时候。
2016年2月19日修定
那个人来了!屋子里没开灯,黑黢黢的,但是那个人拔窗子插销的声音外面的人听见了。
嗝吱!一声,两扇窗子推开了。那个人个子真的高,窗台很矮,他的腿好长!他轻手轻脚地低了头弓着腰,他是右脚先伸出来,然后身子重心一移,然后一脚就踩在了石灰上
这是三十多年前在老咀山矿人嘴巴子上跳来跳去的一个情节。
花子老五是老咀山矿机修车间的钳工,姓郭,他大哥叫郭老大二哥叫郭老二,五兄弟中他在家排行最小,所以他还在他妈肚子里,就有人指着她妈的肚子说这郭老五啥时候落地?郭老五是前世就定了的称呼。为什么后来去了他的姓而添一个花子呢?花子当然就是叫花子里的花子那两个字。
郭老五的哥哥郭老大、郭老二当兵去了,郭老三招工去了滇南一个新上马的矿山,郭老四下乡当知青。郭老五读书不成器,小学混了六年,初中读了一年就不读了,十四岁便闲在家里干混。闲着没事做郭老五又手痒,他成天便揣着一个弹弓射人家窗玻璃射小姑娘射麻雀玩,一时间来他家告状的人络绎不绝。郭老五他爹除了忙着陪不是就是掏钱买玻璃给人家去换,八级老钳工老劳模的父亲郭胜利面子扫地。
红英的同伴何丽被郭老五用杏子核作子弹射中了正在发育的小奶奶,疼得当即就弯下腰去嚎淘大哭,何丽她爸爸知道后提着一把砍柴刀去了郭老五家。那天郭老五他爹还没下班,郭老五他妈吓坏了,听了何丽她爹的怒斥抖鳞壳颤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作孽,作孽呀!我让他爹回来打断他的腿剁了他的手!我们赔我们赔,我们带你家姑娘去医院看,多少钱我们出,营养费我们出。求你们饶过这小砍秋头的!砍血脑壳给老哇啄的!(注:骂人的话,老哇=乌鸦)
郭老五他妈只差给何丽他爹跪下嗑头了。何丽被郭老五他妈领着去职工医院照了X光,当然没多大的事,何丽只是皮肉青肿了一块,但是郭老五家还是拎了五十个鸡蛋和两斤红糖给何丽家,塞了二十块钱给何丽的妈,一再陪不是算是把这事了结了。
郭老五家不缺钱,他的四个哥当兵的当兵当工人的当工人当农民的当农民,他爹又是技术过硬的八级老钳工,工资高得很。老咀山矿成立之初郭胜利从上海来到云南支援边疆,郭老五他妈也跟着来了。郭胜利带着老少一群徒弟,想抽烟有人点着火双手奉上,想喝茶有人给泡好捧来,想喝两盅小酒有人忙不迭去小铺子里量,买米买炭劈柴盖鸡舍的事都不用他的亲儿子动手,众徒弟就抢着办了,那日子舒坦得很。
郭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不劳老两口的神,老大老二还不时从部队里写回家信来,比赛着向父母汇报又立了几等功,老三外地当了工人有收入,攒了钱逢年过节给爹妈寄来个包裹,内里装一包好茶叶一瓶蜂蜜什么的。老四也不给家里添什么乱子,个把月走一段二三十公里的山路回家来一趟,带走几瓶咸菜,带来的却是一背篓洋芋几棵大粪泼栽的卷心白菜什么的。
郭师傅一个月近百元的工资收入,老伴呢在缝纫社做衣服,也有三四十元的收入,要说家里白养个老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偏偏这老五游手好闲之际惹事生非。郭老五的妈就在老伴面前唠叨甚至哭诉,逼丈夫再去找领导说情要求给老五招成正式工人,她想小老五有了正事做情况就会好。
老咀山矿征招工人都是成批成批地解决,个别招工太难了,另外老咀山矿的孩子初中高中毕业参加不了工作就只好去下乡,要不就去当兵,可是当兵的好事也要三几年才会来一次,每次名额也少得可怜。郭胜利的五个儿子中就有两个参了军,这已经是看着郭胜利是劳模是老共产党员的面子了,那年头是谁想当兵谁就能当的?当个兵要查三代查根子,所谓根红苗正才会招的。当兵的吃穿国家给转业退伍国家给分工作,而且分的工作一般都会是好工种的,因为在革命军队的大熔炉里锻炼过的人是可靠的。
郭老五家的墙上挂着两个哥哥穿着军装的大照片,而郭老五平时也是把两个哥是解放军的事拿来讲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两个当兵的哥哥是郭老五称雄的资本,他对别人说:我大哥给了我一顶军帽,我二哥后来回家探亲又给了一顶。
郭老五,一人就拥有两顶军帽!单凭这一点郭老五就够让很多老咀山矿的小青年们羡慕不已了,因为弄一顶军帽戴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事。
罗萍的哥哥好不容易弄到一顶军帽,爱得不得了,不时取下来给那帽沿子弹弹灰,显摆显摆,或者按帽廓大小折一纸圈衬在帽子里以便戴着时显得挺刮些板扎些,可他的军帽竟然只戴了两天就被一伙人从头上给抢跑了。
郭老五的军帽是没人敢来抢的,一是因为他在老咀山矿打小就积攒下的坏名声二是他一个人就有两个当兵的哥,这是老咀山矿绝无仅有的事。
所以郭老五他妈撺掇老伴拿老脸抵着再去找领导说情,特批郭老五参加工作这事,郭胜利就觉得太难为情了,矿里面够照顾他家的了,老咀山矿还有人家兄弟姊妹七八个,闲在家里吃白饭的就有三四个的,郭胜利不去。郭老五他妈没法就使了一个阴招,跑到老咀山矿的大水闸边坐着哭泣,扬言没心肠活了跳水淹死算了。
郭胜利被逼无奈只好找了一个身边没有子女照顾,老伴身体不好的理由恳请矿里特招小儿子为工人。郭胜利万分羞愧地去找领导说情,没想到领导竟然通情达理地满足了老劳模的要求。别的人家见郭老五那样混的孬种都特批为工人了,也去找领导反映自家的困难,领导板着个脸两句话就把人挡回去了:人家奉献了两个儿子驻守边疆保家卫国,人家是劳模一辈子不求回报只讲贡献,你哪条可以跟老郭比的?
郭老五虚报大三岁年纪,正式参加了工作,而且分在他爹所在的机修车间,成了一名钳工,由他爹带出师的一个徒弟教他技术,郭老五一下子从师徒关系上成为他爹的徒孙辈,在他爹面前断不敢乱来。
郭老五穿上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后果然规矩了好多,上班时间反正逃脱不了他爹的手掌心。对于钳工技术郭老五很着迷,他恳学恳专加上继承了老爹的一双巧手,很快便有了一手不错的钳工技术,能独挡一面了。
郭老五虽然是穿工作服的人了,却因年纪小总是跟车间里别的青工们有点格格不入,别的青工一般二十来岁,都忙着找对象谈恋爱,非常讲究个人仪表卫生,人家一下班就争着跑澡堂洗澡换上干净衣服。那时青工们流行穿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装穿白色的回力球鞋,球鞋洗不出原先的白来就用白粉笔、牙粉或者是滑石粉上色,搞得一尘不染的。偏偏郭老五离经叛道,上班穿啥下班穿啥,脚上一双翻毛皮鞋从上脚就要到鞋底磨刈或者鞋帮炸线才会丢掉。
郭老五的蓝色工装衣裤这里一滩机油那里一滩机油,脏得看不出本色,油腻腻的黑得发亮。澡他还是洗的,比别人洗得少,内衣脏得不行也换的,可是外衣外裤他就是不换,据说也是穿上身就等着第二年发新的才可能换掉。他妈看不下去让他脱了要帮他洗,他犟嘴说,我爹说了随时要保持工人阶级本色。郭老五到俱乐部看电影别人都避他不及,说他身上就一股机油的味道,感觉他是鼻子耳朵头发里都上了弹子(轴承)油。
很多年后红英想起郭老五来忽然有一点明白,郭老五其实追求个性解放,三十多年前他就有一种西方嬉皮士的自觉,他可不是学别人,他就是骨子里要特立独行。
郭老五参加工作后的这副德性,一些女青工背着他议论:这小杂种成天脏兮兮的,跟街子上那些从河南安徽逃荒来的有什么两样?纯是个小叫花子!有一个结婚成家了的女工王大姐瞧郭老五那脏样跟他开玩笑:郭老五,瞧你那花子滴夺的样子,干脆叫你花子老五得了!听你大姐我的话吧,不然将来讨媳妇就难了!除非你愿意像罗康,找个老翠那种懒得烧死麻蛇吃的女人做媳妇!人家罗康那身皮好像还没你这身窝囊。
郭老五邪吊着眼睛:王大姐,你叫呀花子老五!嗯,这绰号好听,独特,我就喜欢与众不同,花照样可以是花花公子的花花天酒地的花水性杨花的花,王大姐,我郭老五从今以后就依你说的叫花子老五了,我就花子给你们瞧。
花子老五的名就这么定了,但花子老五在老咀山矿的名声闹大是他竟然捉了矿办秘书杨祖林的奸。
杨祖林是矿办的红人,老咀山矿的政治文化中心、最热闹的工人俱乐部搞文艺调演什么的他都是第一主持人,那时不叫主持人,叫报幕员。杨祖林普通话讲得很标准,他老家是河北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在省城做官。杨祖林从小就是棵红苗苗,读了个工农兵大学文凭,学的是化学分析专业,1974年大学毕业,他那老革命的父亲不容他选择直接安排他上滇东北琅县的老咀山矿锻炼。
在老咀山矿当矿长的毛正清把老战友的儿子杨祖林直接安排去冶金实验室搞化学分析,可他却不喜欢搞专业,倒热衷于出黑板报搞文艺调演那类事。杨祖林从小见过些世面,挺能整的,还不时写点消息通讯什么的向省报投投稿,老咀山矿的好人好事生产捷报上了党报,领导很高兴长了脸,外出便随时带着他。另外,老咀山矿每天定时用高音喇叭广播的播音稿起码有一半是他写的,杨祖林的名声一时大震。这样子,二十六七岁的英俊青年杨祖林就成了老咀山矿女青年心目中的才子,成了抢手货,喜欢他的女青年托人说媒的只差踏刈杨祖林的门槛了。
杨祖林是受了父亲老战友特殊照顾的,他一个人住着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这在别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结婚证领了一年半载的分不着住房的都有,杨祖林单身汉一个就可以一个人住一间。房管科的头头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杨祖林每天都要给领导写发言稿写广播稿,跟别人挤一屋就写不成稿子了。这些都是杨祖林成为众多女青年趋之若骛的本钱。然而,尽管喜欢杨祖林的女青年很多,可是一直也没见他跟谁有什么瓜扯,暗恋他的女青年对他的好感就又增添了一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