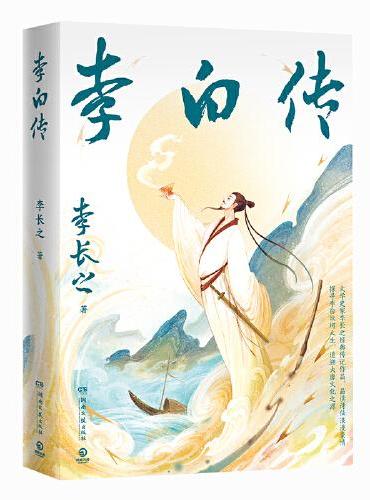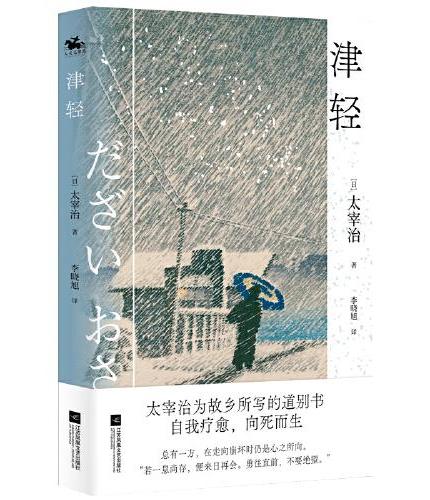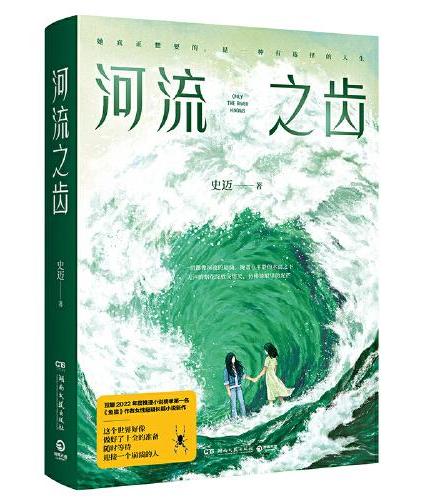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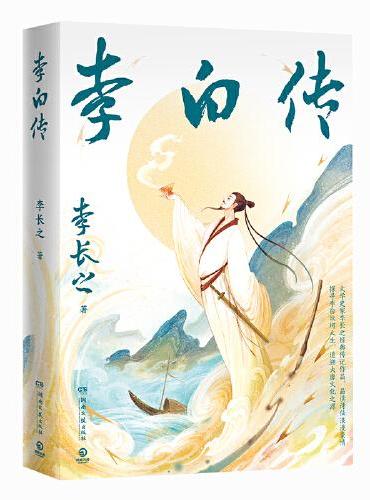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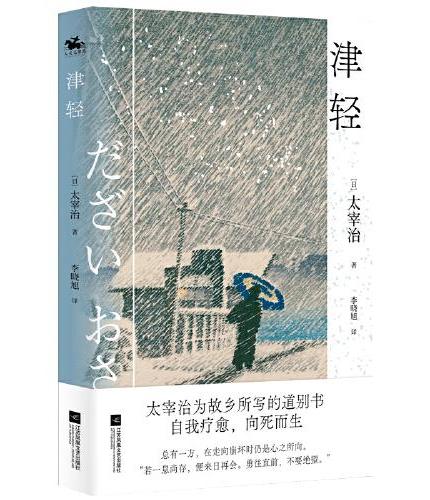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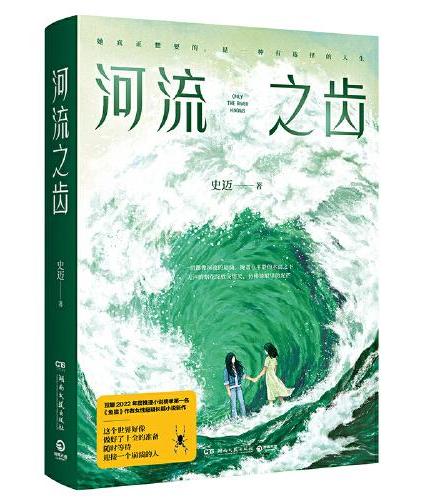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 編輯推薦: |
流动的思想、文学的盛宴;
对当今中国作家群体和文学现状的真实记录;
介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写作。
|
| 內容簡介: |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话语。用访谈的方式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们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说出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深刻洞见,说出对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真知灼见,通过作家们的话语凝练出文学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
作者访谈了十多位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王蒙、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格非、周大新、柳建伟、刘醒龙、叶延滨、欧阳江河、范小青、李浩、徐则臣。他努力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场域。前人对作家的访谈,是谈文学创作,*多谈一点对时事的看法。而作者与作家们谈的,大多并非囿于文学本体,而是以文学为引子,一方面向内探求主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往外延伸,涵盖了很广的范围。
本书谈到的问题:如何谈论知青文学;张抗抗作品中的女性叙事;小说中的乌托邦概念;福山的思想;文学的边界与启蒙思想;作家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有什么渠道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相关政策产生影响?
|
| 關於作者: |
|
顾超,男,1986年8月生,江苏苏州人,武汉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毕业,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博士毕业,曾任全国学联驻会执行主席,现为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团委书记,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秘书长。博士期间在SCI检索期刊上发表4篇文章,工作后弃理从文,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天涯》《探索与争鸣》《雨花中国作家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政治学评论文章十余篇。
|
| 目錄:
|
第一篇 文学与政治 1
我的真正的追求,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 3
文革状态不会再在中国出现 9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是中国最主要的女权问题 23
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34
和弦 48
第二篇 何以为文 69
在阅读中被塑造和修复 71
纯文学只跟人的最高心智有关,跟语言的最高虚构方式有关
78
文学一定要表现人应该怎样 83
文学从来就有对社会的观照 90
在很小的缝隙中表达自己 96
和弦 102
第三篇 共同价值 125
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内部要理顺 127
文学以传达爱来推进共识 135
和弦 143
第四篇 文学公共领域 163
文学公共领域是一种交互主体 165
辩论平台与网络空间有意义吗? 171
作家的公共利益 188
第五篇 走向文学的善治 207
文学治理的客体 209
当代文学之伤 217
中国文学的守夜人 236
|
| 內容試閱:
|
访谈对象:
张抗抗,1950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张抗抗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我们的访谈是在2016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在她的宾馆驻地完成的,她有一种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风度。我们的对话从知青开始,但很快就转到了女权和女性的问题。」
顾超:您的写作是从知青起步的,看到您写的文章里提到,知识青年的说法是自欺欺人,这跟同样当过知青的陈丹青的说法很像,他说知青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还有您说知青一代只有我们,没有我,这都很深刻。如果请您在当下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论知青,您会怎么说?
张抗抗:其实,我说这个话已经很多年了,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但是近几年来,微信上一直在转发传阅我的那篇《无法抚慰的岁月》,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篇随笔写于1997年,是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周年而写的。当时也就是坦言了自己的一些感想而已。去年两会时,崔永元和我说起知青。(他在政协和我一个小组)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个大型的知青口述实录。我就把1997年出版的那本《大荒冰河》(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里我的单行本)给他了。他看到(我)用《无法抚慰的岁月》作为那本书的自序,问我:二十年过去了,你现在的看法有变化吗?我说没有,我坚持这些看法。但如果现在重新谈论这个话题,我希望会讲得更好。现在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不了解文革,知青也就无从谈起。还是建议他们先读一下那本书吧。该书后来多次再版过,更名为《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自述》等。
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梁晓声的事儿你知道吗?神情有点紧张有点诡异,我心想梁晓声是个正直正派的作家,一向敢言,他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解释说:是这样的,前些天,有人谈起文革从未被彻底清理过,感觉文革随时会卷土重来。我曾说过,如果文革再次发生的话,我要么自杀,要么出国。刚好在任大炮的事情之后,这段话一度流毒甚广,被人们在网上转来转去。其实这段话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只是我对文革的一种态度。梁晓声是知青作家,我和他有很多共识。很多历史的真相都被屏蔽了,我觉得非常可怕。为什么梁晓声会发出这种慨叹呢?因为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思潮,包括那些普通的老知青,始终认为文革时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文革所指向的批判目标是正确的。他们的子女或多或少也会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文革那种非理性、反人性的暴力行为,在某一些条件下,它会像土壤中没有得到清理的细菌一样被激活。如果青年一代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残酷、疯狂的年代,那么人们完全有可能不自觉地去重复这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真正能够了解文革的历史。知青是文革这个大的背景下的产物,谈论知青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因为怀念自己曾经火热、辉煌的青春,而怀念那个愚昧的年代。
顾超:您的作品有很多女性叙事,但您自己不承认是女性文学。从《情爱画廊》到《作女》,您想表达的女性的内在理想是什么?是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吗?中国女权意识的解放似乎跟西方很不一样,特别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似乎不是中国女性最渴望获得的。
张抗抗:我确实不太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定义不能涵盖我的创作。1985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地平线艺术节,我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我们需要两个世界。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女作家都尚未具有自觉的女权意识,我谈的只是自己的一种直觉。我说:我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我才是女作家。这和西方女权主义很不搭调。西方女权主义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女性的政治权利。中国和西方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不一样,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比如,中国这样一个封闭保守落后的国家,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统治之下,女性对于自我、性别与性的认知度,还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谈何参政议政?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范围从欧洲美国一直到东南亚国家,都已经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女总统女总理,而我们几乎望尘莫及。所以,性别意识有一个前提:如果缺少对人的尊重,也就是人权、人和人之间的暴力与奴役问题不解决,女性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性别教育是很可怜的。就我本人而言,在成年之前,性知识几乎等于零。共和国建国以后,以立法的形式首先解决了男女平等的问题,然后是同工同酬、妇女生育的产假等福利待遇。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女性解放达成一致。政府在体制上建立起了基本的男女平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西方女权主义70年代仍然在为之激烈斗争的那些努力目标。但是,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是没有根基的,农村妇女还处于嫁汉穿衣吃饭的阶段,经济完全没有独立,更谈不上人格的独立。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激进口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性别差异,把女人等同于男人,只强调人的共同性,缺乏性别的差异性。在我们的青年时代,都接受了男女应该一样的教育,一直到80年代女权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后,对我逐渐产生了影响,才开始质疑这个一样有很多问题。后来我和女性主义批评家李小江有过一次比较长的对话,她希望了解我的心理经历,我说我的性别意识很健康,没有特别的反抗诉求。因为我家里是两姐妹,我是姐姐,还有个妹妹,没有哥哥或者弟弟。但我从小没有遭受过性别歧视,父母很爱我们,没有感觉到性别带来的不利比如说有的家庭里,女孩儿从小就不受待见,所以成年后她对性别就会特别敏感;而我本来就没有感觉到性别压抑,成长过程也还比较顺利,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并没有遭遇来自男性的特别压迫。我的作品很少诉说女性的苦难,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但是李小江说我的女性观是未经清理的,缺乏女性自觉。所以女权主义批评家总是把我列为另册的。尽管有很多女作家坚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还是不愿意给自己这样一个冠名,我对主义过敏,我没有主义。因为我是为人写作的,为女人也为男人。在过去中国处于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遑论女性权利?例如文革,就连人的起码尊严都没有,女性权利从何谈起?所以,我要说,每个人的认知度不一样我觉得千万不要一样,要更多的不一样才好。中国的女性权利是由制度提供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恩赐,而不是女性争取来的,这就缺少了一个女性自我认识的成长阶段。我说的是成长,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虽然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经济自立,但同时要担负工作与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的双重劳累,女性没有时间学习进步,共和国建立的前三十年,女性在国营企业单位里,并没有太大的工作压力,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喷泉为什么能喷得很高,因为喷泉是有压力的。中国女性名义上被赋予了政治权利,也就是投票权吧,但这个权利要落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