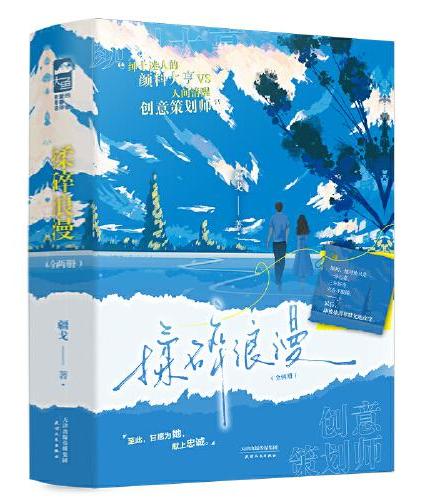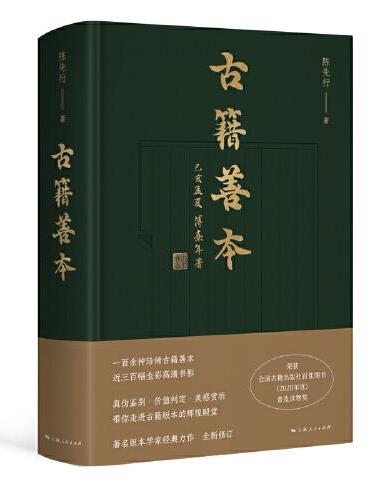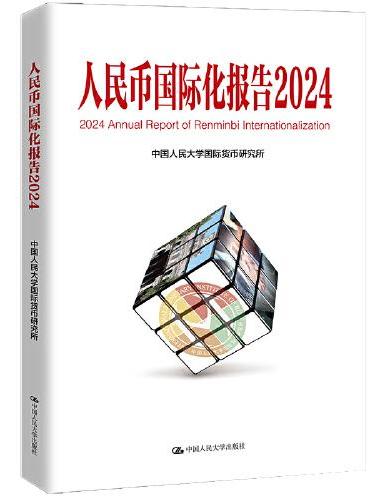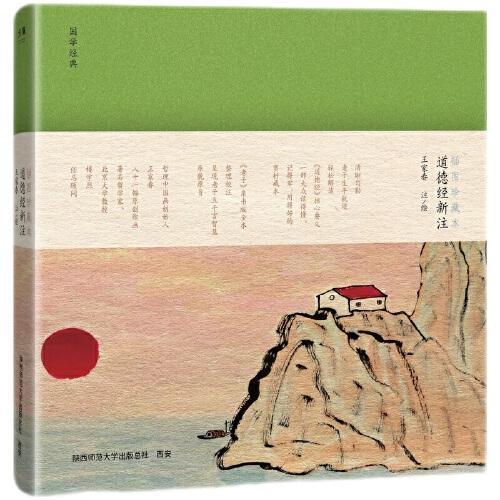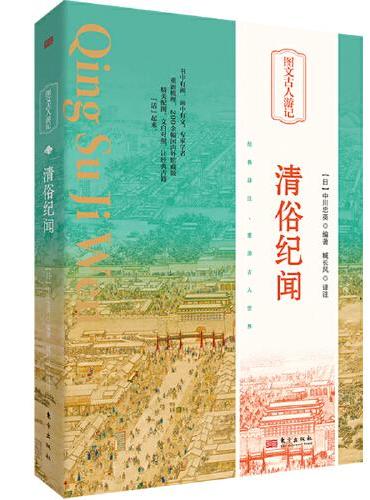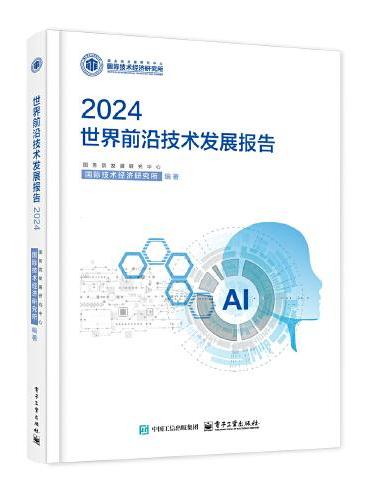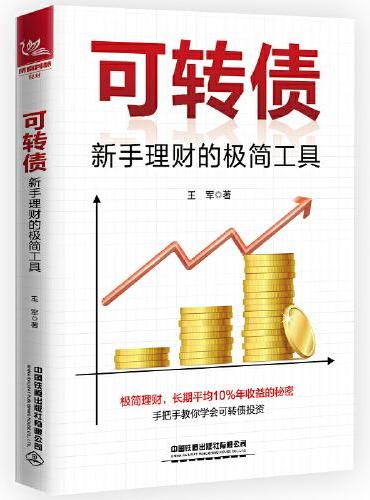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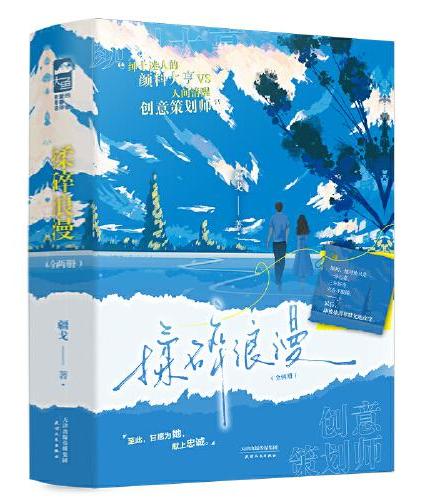
《
揉碎浪漫(全两册)
》
售價:HK$
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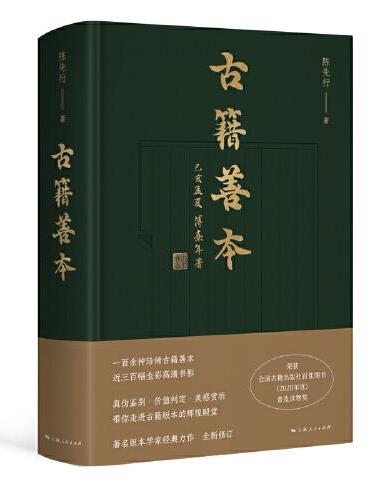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HK$
5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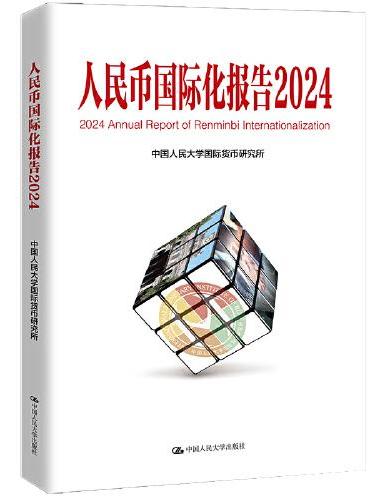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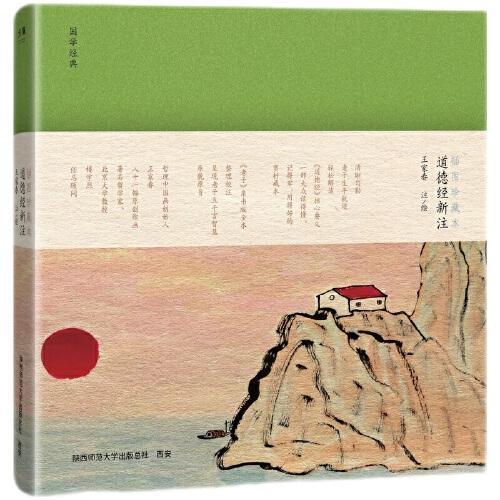
《
道德经新注 81幅作者亲绘哲理中国画,图文解读道德经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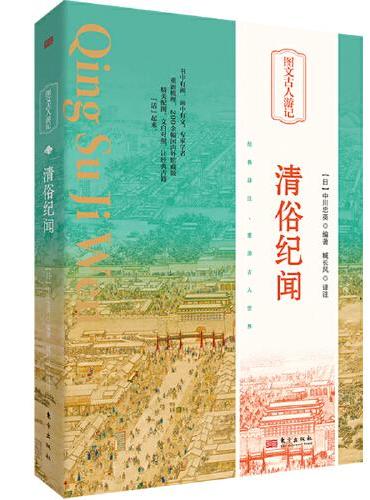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镜中的星期天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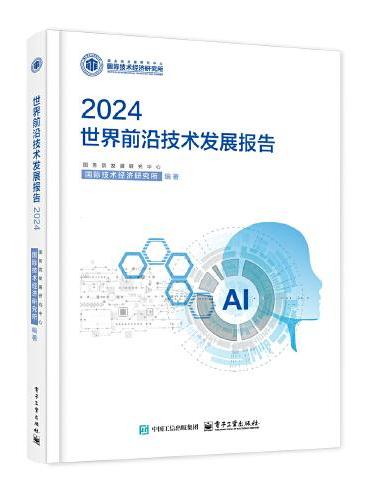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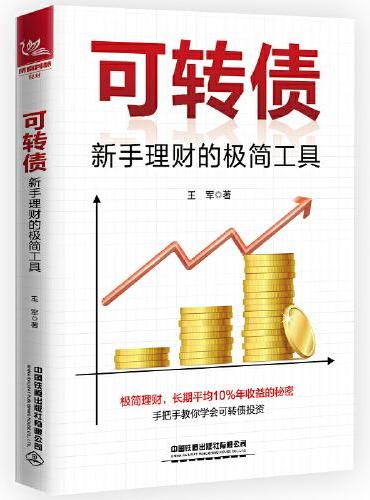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
| 編輯推薦: |
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经典代表作名师教学设计精装典藏版
看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如何在艰难岁月相扶相帮、相濡以沫
荣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感动万千读者的儿童文学佳作
特邀实力画家郭警绘制精美油画封面
曹文轩本人十分重视和满意的版本
|
| 內容簡介: |
|
曹文轩纯美长篇小说精装典藏版系列,收入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7部具有代表性和知名度、体现极致风格与文学品位的经典长篇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根鸟》《细米》《红瓦黑瓦》《山羊不吃天堂草》《蜻蜓眼》,和1部全新感人长篇《樱桃小庄》。在这些故事中,曹文轩写苦,把苦写到凄美;写美,把美写到纯粹;写爱,把爱写到无疆。作品致力于描摹少年们内心的千回百转,编织出瑰丽多彩的成长瞬间,讴歌苦难和成长,挖掘人性与人情,奏响一曲既丰富又纯美、既优雅又刚劲的交响乐章,构建出一个有情、有趣、有哲思、有回味的文字世界。8位教学名师精心撰写教学设计,助力整本书阅读与教学。套系作品自1991年出版以来,荣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剧本奖、童牛奖优秀编剧奖、美国弗里曼图书奖文学金奖等各类奖项,《青铜葵花》入选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出版者周刊》2017年度*图书榜,并被译为十多种文字出版。
|
| 關於作者: |
|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统一语文教材主编之一。主要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蜻蜓眼》《樱桃小庄》等。创作并出版绘本《飞翔的鸟窝》《羽毛》《柏林上空的伞》等五十余种。出版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出版《曹文轩文集》(19卷)。百余种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日文、韩文、瑞典文、丹麦文、葡萄牙文、俄文、意大利文等文字。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输出版权优秀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重要奖项七十余种。2023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
| 內容試閱:
|
序
曹文轩
《蜻蜓眼》无疑是我个人创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书。
三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故事。我将与它的相遇看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看成是天意命运之神眷顾我,让我与它相遇。当初,一接触它时,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宝贵,价值连城四字就在心头轰然作响。我很清楚,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一个作家,他遇到了什么。但即使在榨干了故事主人对这个故事的记忆之后,我依然没有产生将它很快付诸文字的念头。
我是一个喜欢珍藏故事的人,而对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更会在心中深深地珍藏着。藏着,一藏三十多年,就是不肯让它面世。感情上是舍不得(那种感情十分类似于一个父亲不想让他心爱的女儿出嫁),理性上我知道,一个作家必须学会对故事的珍藏。这是一个本领珍藏的本领。珍藏的好处是:那故事并非是一块玉玉就是玉,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它还是那块玉,而故事却会在苍茫的记忆的原野上生长。岁月的阳光,经验的风雨,知识的甘露,会无声地照拂它,滋养它。它一直在生长,如同一棵树,渐渐变得枝繁叶茂,直至浓荫匝地。三十多年间,有时我会想到它想到它时,我就会打开记忆之门去看看它,更准确的说法是观赏它。我发现,我观赏的目光正在由平视逐步抬高,而改为仰视,不断抬高的仰视。我知道,那棵树,在长高。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终于有一天,这棵树不再是树,而从植物变成了动物,这个健壮的动物,不再安于在记忆的原野上走动,它要去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了,任何栅栏都不能再阻拦它了。沉睡,哈欠,继续沉睡,一跃而起,精气神十足,它一定要走出记忆之门,到光天化日之下。放它出来,到大世界去!我听从了这一似乎来自天庭的声音。
于是,它就成了《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种宝物,是一种椭圆形的珠子。在小说中,它只有两枚。但我知道,现在它就不是两枚了。一册《蜻蜓眼》就是一枚。它将繁衍成多少枚呢?我想不是谁都能说出这个数的。
挨着珍藏这个字眼的是沉淀这个字眼。回想三十多年的珍藏,冷静一想,我发现,其实不是故事在变,而是我在变。我的思想在变,我的审美观在变,我的趣味在变,我的情感以及情感方式在变,我的目光在变。而这一切的变,都是往更可靠更成熟的方向去的。许多当时令我冲动的情节与细节,时过境迁,不再令我冲动,而归于平淡。而当时并不上心、觉得微不足道的情节和细节,反而在逼近我的目光,并熠熠生辉。一些当初的见解在瓦解,而新的见解在生成。我感到,自己书写和驾驭整个故事的能力在一天天地增强,心虚在不断地被新生的力量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满满的信心。前后比较,我觉得昨天对这个故事的领会与把握和今天对这个故事的领会与把握,有天壤之别。
也许是我对故事反应迟钝,也许是我的深思熟虑,我通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很难做到逮到一个故事马上就将它变为文字。我写了这么多年作品,写了这么多作品,还很少发生过早晨刚得到一个故事,晚上就立即将它转换成文字的事情。通常,我不善于写当下,而只善于写过去。但我自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写今天早晨发生的事和今天早晨听到的事。
像蜻蜓眼这样的故事,我只能取端庄的写作姿态,用庄重的语调去书写。事实上,我的写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姿态,这样一种语调。我不太善于也不喜欢甚至说是很不喜欢那种油腔滑调的写作语调。我写过一些谐趣的文字,如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笨笨驴系列、萌萌鸟系列,但我将这样的笔调理解为谐趣或幽默。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谐趣和幽默。这种喜欢一样体现在端庄的、庄重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等作品中。但我是将这种谐趣和幽默归入智慧这样的境界的。在写作倾向上,我可能更赞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写作。那时的作家,姿态是端庄的,语调是庄重的。无论是雨果、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也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的姿态与语调都是如此。即使讽刺,姿态也是端庄的,语调也是庄重的。在《巴黎圣母院》中,在《高老头》中,在《战争与和平》中,在《静静的顿河》中,在《呐喊》《彷徨》中,在《边城》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们的姿态和语调。但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以及泛滥,这种姿态与语调被冷落了,直至被嘲笑与否决了,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冰冷的、讥讽的、嬉皮笑脸的或是自虐式的嘲讽,仿佛整个世界无恶不作、荒谬绝伦,不配以端庄的姿态面对,不配用庄重的语调叙述。当年朱光潜先生在区别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时,说西方美学追求的是崇高,中国美学追求的是秀美。而如今,无论是崇高还是秀美,都几乎消失,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还是西方的文学,都统一到了阴冷的、令人叹息和无望的谐谑上。崇高、秀美几成明日黄花。
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被无情地否定了。这个世界没有正义,没有善良,没有美好,有的只是阴险、无聊、萎靡不振、蝇营狗苟、变态然而,这个世界真的就完全如此吗?其实,我们的头顶总有灿烂的阳光,许多时间里,月色迷人,星空下总有夜曲在远处响起,爱情无处不在,博大的母爱、父爱常常让我们心头流淌暖流,春天里百花齐放,秋天里更是色彩斑斓,而当冬季来临,白雪皑皑的世界,使人感到一片纯洁和冷静其实,那些拒绝端庄、庄重的作家,他们一直享受着这个世界给他们的种种远超普通百姓的好处。喝着咖啡或葡萄酒,在舒适的空间里自由地驾驭文字,荣誉、金钱,他们往往应有尽有。但他们就为那份虚拟的深刻,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统统过滤掉,而只留下了一堆黑色的渣滓。然后,便开始令人绝望的谐谑。如果他们说文学的端庄、庄重乃是虚假,那么他们的这般姿态就一定是诚实的吗?
我不相信我取端庄的姿态,用庄重的语调来讲蜻蜓眼的故事,就一定无法深刻即使真的无法深刻,我也不想改变这种姿态与语调。
做人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作家也得做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必须这么想着。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
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视为他的写作资源,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哪块土地上的生他养他的土地。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不聪明的,很不聪明。因为,那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就铸就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却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导致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长故事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故事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独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这一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个故事会给我带来什么带来荣耀,带来幸福,带来来自世界的目光。
但只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眼睛却穿过滚滚烟云去眺望天地连接之处,眺望国家界碑之外的广阔世界的人。目光永远比双足走得更远,而心灵则能走得更远。这个人,这个愿意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个关乎文学性命的道理,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写作的永恒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聪明人,《蜻蜓眼》也许充分显示了我的真诚愿望。
2016年6月1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