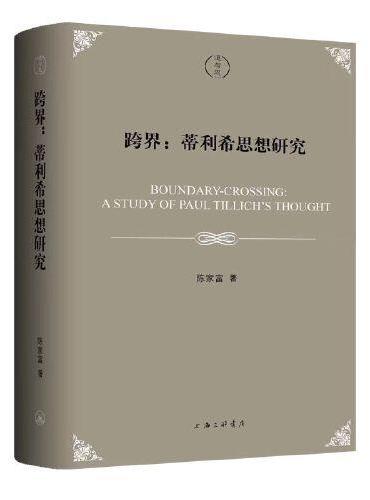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4.2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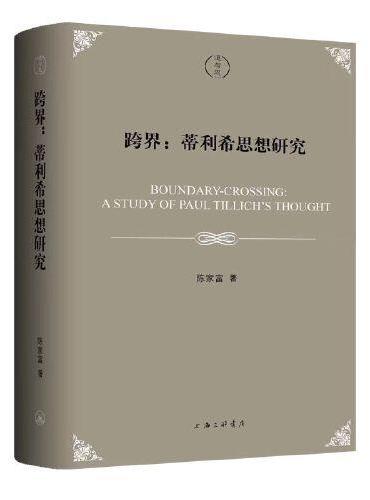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2.0

《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
》
售價:HK$
201.6

《
养育男孩: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
小原流花道技法教程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
格列卫是史上个针对致命癌症的成功疗法,《我不是药神》电影中所提到的格列卫即是本书所讲述的主要治疗药物。本书故事完整,可读性与科学性俱佳,可以让读者了解一种癌症从发现病因到找到疗法的全过程。原著曾获《华尔街日报》2013年度非虚构图书十佳。
|
| 內容簡介: |
|
格列卫是史上个针对致命癌症的成功疗法,本书从基因水平对促成这个疗法的科学和医学发现进行了全面记录,帮助读者了解现代癌症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每年全世界有7万多人被诊断为慢粒,这本书记录了他们的命运如何发生彻底改变。
|
| 關於作者: |
原作者:杰西卡?韦普纳(Jessica Wapner),自由撰稿人,写作领域为健康、医学和科研。作品见于《科学美国人》、《纽约时报》、《科学》、《自然》、《洛杉矶时报》等。《费城染色体》是她的本书。专职从事写作前,韦普纳是《血液学与肿瘤学临床进展》和《胃肠病学与肝病学》的创刊编辑主任。
译者:彭茂宇,遗传学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科普专栏作者。曾经翻译出版《免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目錄:
|
序章深入骨髓
部分染色体和疾病
1条线索
2三百个字
3研究一种鸡病毒
4号码对,地点错
5鸡肿瘤基因的意外根源
6完美煽动者
7激酶挂钥匙的地方
8化学性摘除器官
9移除毛发和脂肪
10有趣的新蛋白质
11人类癌症基因初露峥嵘
12拼出染色体易位
13“那个词就是癌基因”
第二部分理性设计药物
14先成为医生,再成为科学家
15将一个蛋白质转化为药物靶点
16利用病毒做马达的机器
17摘取触手可及的果实
18为药物寻找一种疾病
19两个结局
20离开波士顿
21杀死细胞
22有得有失
23“要想给人用这种药,除非先打倒我”
第三部分人体实验
24快的答复
25提高剂量到200毫克
26他们没有的
27聊天室中的私语
28救自己一命
29百分之百的缓解率
30好压力
31立字为证
32汗牛充栋的数据
33胜利之父
第四部分后续
34价格问题
35弱点暴露
36初的五年
37第二代药物
38每种癌症都有种格列卫
尾声生存期
时间表
词汇表
文献
图片来源
致谢
作者采访
导读
|
| 內容試閱:
|
研究一种鸡病毒
就如在旱季沉睡的种子,等到道雨水的号令而发芽,对于费城染色体的研究兴趣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复苏。驱动研究兴趣的主要是技术进展,在60年代早期,能够研究染色体作用的技术还不存在,还有10年的漫漫求索路。
同时,还有另一项进行中的研究,以后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与费城染色体交汇。这项研究的对象不是基因,而是病毒。
建立于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大隐隐于市,坐落在纽约市上东区,保持着安静知性的氛围,持续催生着无数科技发明。有2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在此进修或做研究。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中诞生过许多科技突破,领域覆盖乙型肝炎、肥胖症、糖尿病、癌症、皮肤病、传染病以及其他疾病和难题。建校初十年,该处名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曾有位名为佩顿·劳斯(Peyton Rous)的研究者在此研究过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是种在身体中穿行的白细胞,它们在体内聚集于腋下和其他部位的淋巴结中。
劳斯出生于1879年,他在单身母亲的照顾下,和两个兄弟姐妹一起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长大。他的父亲去世时,母亲没有返回得克萨斯州,虽然回乡的话她和子女就能得到娘家人的帮助。她选择留在巴尔的摩市,因为她认定这里能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让年幼的劳斯对科学萌生兴趣的却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他在家附近的树林里穿行时沿路所见的野花。劳斯将观察到的野花记录整理出来,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上逐月连载,这是他人生中次公开发表的论文。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后,劳斯决定将职业重心放在医学研究而非行医看诊上。1906年至1908年,他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当病理学家,1907年他还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市短期工作,关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写道“周遭没有战争的迹象”。1909年他加入洛克菲勒大学,在实验室里当研究员。那年秋季,才入职几周的劳斯接待了一名来自纽约州长岛市的农妇,她患有关节炎的手里捧着一只常见的家养芦花鸡。这只母鸡的胸前有一块高高隆起的肿瘤,从其条纹羽毛之间凸出来。那只鸡大约是15月龄,劳斯在1910年的论文中描述它是只“健壮的年轻母鸡”,它的肿瘤已经长了两个月。农妇希望劳斯能动手术切掉这个硬瘤。
劳斯同意了,几天后,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了建所以来的首次鸡手术。在1909年10月1日,劳斯用乙醚麻醉母鸡后切开它的腹腔。他切除了大部分的肿瘤,它是个形状不规则的球状肿块,红里透黄,在劳斯的手术刀下分崩离析。可惜手术并不算成功: 因为残余肿瘤转移到腹腔脏器中,母鸡在术后1个月死亡,但从这次手术中获得的肿瘤组织,成了科学界永久的遗产。
插图5: 这就是佩顿·劳斯在1909年用于做手术的芦花母鸡。从母鸡的肿瘤中分离到的病毒,帮助发现了病毒触发癌症转化的机制,并终揭示了癌基因是发源自健康基因的事实。
不想错失良机,劳斯决定仔细观察所获肿瘤。他切下一小片肿瘤,将其细细研碎,然后把研碎的组织挤过滤孔极小的过滤器,这种过滤器不但能阻挡鸡肉组织通过滤膜,甚至还能挡住细菌。理论认为,这样滤出的肿瘤提取液中只会包含与肿瘤生长相关的元素。研究者发现,如果把这肿瘤提取物注射到其他家禽中,它们也会在几周内长出像芦花鸡身上那种凸起肿瘤。这种癌症会传染。要解释这种鸡癌症的传染性,只有一种可能: 致病的根源必定是某种滤过性病毒。
劳斯并不是个揭示病毒和癌症之间联系的人。在19世纪40年代,有位意大利科学家观察到,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城中修女患上宫颈癌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已婚妇女患病的概率则高得多。虽然引发宫颈癌的罪魁祸首——人乳头瘤状病毒——要直到1983年才会被发现,但很明显是一些有传染性的元素导致了这个现象。就在劳斯给芦花鸡开刀的前一年,有两位丹麦的科学家证明了鸟类的某种白血病也具有传染性,但在当时,白血病并未被看成是种恶性肿瘤,所以这项发现被忽视了。在19世纪,人们知道羊群中有种肺癌具有传染性,而在20世纪初,人们也在马中发现了传染性贫血病毒。但这些发现都不如后来被称为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RSV)的影响深远。是劳斯首次明确无疑地证明了癌症可以由感染诱发。
但是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RSV才会真正走入癌症研究界的聚光灯下。那时候,人们对病毒的兴趣渐增,认为癌症借用病毒作载体进行传播。这兴趣源于两个原因: 个原因,人们越来越怀疑病毒会在人体中传播癌症,这是建立在劳斯对芦花鸡的观察,以及其他动物中传染性肿瘤的基础上——如果动物能因此患上癌症,人亦何殊?医疗界热切盼望着阐明癌症如何产生的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在肌体中隐匿身形,躲避免疫系统的追杀的方法,而病毒看似是个可能的答案。
另一个原因同样重要: 病毒正在成为一种科研利器,用于研究癌症怎样将健康细胞转化成生长失控的肿块,终夺取宿主生命。病毒能在实验小鼠中诱发癌症,因此成为绝好的载体,让科学家在变量可控的条件下观察癌症发展。在人们对癌症为何产生、如何产生都一无所知的年代里,任何可能揭示答案的途径都值得关注。“已知信息寥寥无几,任何线索都值得一试,”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病毒学家史蒂芬·戈夫(Stephen Goff)评价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潜心研究病毒,在早期对推动领域进展起了大力。
在癌症研究历史上,新知识的面世常常接踵于新技术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为霍华德·特敏(Howard Temin)的病毒学家决心开发出更新更好的方法,用来研究病毒——特别是RSV——如何引发癌症。特敏认为,既然已知这种病毒能传播癌症,如果能观察到传播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他能在鸡或小鼠体外的环境下,在培养皿的冷光中观察这一过程,那么或许能揭开这个微妙机制的秘密。1958年,特敏和同事哈里·鲁宾(Harry Rubin)一起大功告成。
特敏和鲁宾使用的技术叫“转化灶分析”(focus assay),这种技术以正常细胞作背景,用鲜明对比凸显出癌细胞的存在。用致癌病毒感染体外培养的细胞,然后将它们铺到培养皿上任其增殖。被病毒转化的癌细胞会增殖得更快,因此会长成隆起的群落,一层叠一层的癌细胞与单层生长的正常细胞群落形态迥异。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能定量地测量转化过程——包括癌细胞生长速度有多快,转化程度有多严重,需要多少病毒来引发细胞癌变,等等。通过转化灶分析技术,特敏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只需要一枚RSV病毒粒子,就能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这项技术能让研究者观察被病毒感染的正常细胞转化成癌细胞的过程,它改革了整个癌症研究。“每天都有新技术出现,让研究者能进行新的探索,”戈夫说。这项技术的意义,好比把老式拨轮电话改成按键电话那样。它大大加速了癌症研究,并让特敏声名显赫。不久,使用该技术的研究者惊讶地发现,RSV是由RNA而非DNA组成的病毒。
病毒能造成程度惊人的破坏,它们本身却是微小而简单的。毕竟,它们都不能算作生物,因为如果没有宿主,它们甚至不能自主繁殖。DNA病毒和RNA病毒是病毒的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病毒的本质都是由蛋白质以及脂质分子组成的外壳所包裹的一团遗传信息。病毒携带的基因极少,通常只有四五个。在病毒学发展初期,人们以为DNA病毒与癌症相关。但多亏特敏的转化灶分析技术,研究者逐渐意识到RNA病毒也能将健康细胞转化成癌细胞。
致癌的RSV中储存的不是DNA而是RNA,这让人很迷惑不解。那时的每个科学家都知道,细胞在分裂期间合成DNA——分裂是细胞增殖的方式,在生物的一生中始终在发生——而细胞分裂的过程看似很清楚: DNA转录成RNA,RNA翻译成蛋白质。尽管世上的生物千姿百态,生物体内的细胞也多种多样,细胞中的DNA复制过程却是出奇的简单。整个遗传密码都由4种核苷酸组成,这4种核苷酸分别为A(adenine,腺嘌呤)、T(thymine,胸腺嘧啶)、G(guanine,鸟嘌呤)和C(cytosine,胞嘧啶)。这些核苷酸按固定方式两两配对(A与T,G与C),一对接一对组成两条互补链,缠绕成双螺旋式的阶梯。RNA不包含胸腺嘧啶,取而代之的是尿嘧啶(uracil),这是RNA与DNA直观的区别。在细胞复制期间,DNA双螺旋会暂时解旋,这时候,细胞会合成一条与DNA链互补的RNA单链,并将其用作蛋白质合成的模板。DNA是指导性蓝图,RNA传递DNA的信息,蛋白质则是根据蓝图合成的功能原件。
已知一些DNA病毒能在动物中诱发癌症,其机制当时尚未为人所知。而RNA病毒又是另一回事。因为RNA只是传递信息的信使,而不是保存信息的终形态,所以RNA病毒中的RNA不应该能对人类基因组造成永久性损伤。能造成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就是一种RNA病毒,它是种危险的病毒,但并不会整合进感染者的DNA中。当它被清除时,它就消失了。流感病毒亦同。当我们患上流感,并不会有流感病毒插入我们的基因组中,让我们从此一生都流感不休。这类病毒终究都会被肌体清除掉,并不能永久影响我们的基因组。
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癌症跟基因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这个理论主要来自于逻辑演绎,并无直接证据支持。该逻辑是,如果某种疾病能存在于多代细胞中,那么一定发生了些永久性的基因改变。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疾病在每个新生细胞中都存在,那么意味着这些细胞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就像癌细胞那样。但在那时,RNA病毒能导致永久性的基因变化的想法还是荒谬不经的。
虽然没有证据支持,特敏断言RNA病毒能制造DNA,而这些DNA会在肿瘤的基因组中。当时众所周知DNA是RNA的模板,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这种假设显得离经叛道,让特敏被众人挞伐。“(特敏)在很长时间里被人当成疯子。”戈夫回忆道,他那时年少,但不久后也加入了RNA病毒研究领域。
在那些认为特敏言之有理但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他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徐徐升起的病毒学界新星,在特敏搜寻将RNA转变为DNA的神秘成分的过程中,巴尔的摩也出了一份力。特敏认为,这种病毒具有某种特殊的酶,能将RNA反转录成DNA。酶是一种蛋白质,通常协助细胞进行生化反应,加速反应过程或保障反应运行正常。在1970年,特敏和巴尔的摩都发现了这种酶。他们将其命名为“逆转录酶”,RNA病毒也在后来被重新命名为“逆转录病毒”,得名于其与常规相反的复制方式。能导致癌症的逆转录病毒,被人称为“致癌逆转录病毒”。在1975年,巴尔的摩和特敏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桂冠[同时分享该奖的还有美国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病毒学先驱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他曾是特敏的导师]。
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继续研究RSV以及其他的“转化性病毒”,试图弄明白病毒感染怎样导致癌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工作的科学家花房秀三郎 (Hidesaburo Hanafusa)进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结果: 一些所谓的“转化性病毒”,实际上是由两种病毒混合而成(不过劳斯的RSV不属此列)。当把这两种病毒链分离解开时,其中一种病毒能导致癌症,却不能自主复制,而另一种能自主复制,但却不会导致癌症。花房发现,这两种病毒之间仅仅有一个基因差异。如果其中一种病毒少了另外那种病毒的帮助就不能致癌的话,那么这个差异基因一定是致癌的关键。
接下来的突破来自于对温度敏感的RSV变异型的研究。每种对温度敏感的变异型里都有个基因受温度调控。这类基因在温度较低时能正常工作,但温度升高时就会失灵。科学家通过这种技术,一段段地关闭RSV的RNA,借此研究基因功能(虽然RSV的遗传信息储存在RNA而非DNA中,但它的生理功能依然由基因和蛋白质来达成)。当温度升高导致特定基因关闭时,病毒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不同之处暗示了被温度关闭的基因功能。仿佛是寻找让入侵者溜进来的窗口。每个对温度敏感的变化都提供了线索,指向那些未关的窗。
1970年,曾与特敏一起研究转化灶技术的哈里·鲁宾的实验室里,有位名为G.史蒂文·马丁(G.Steven Martin)的研究者分离出一种RSV的变异型,在35℃时它能诱发癌症,而在41℃的环境下,它虽然能继续复制,却失去了诱发癌症的能力。马丁那时就知道,这病毒里对41℃敏感的那部分RNA,正是能够并且足够导致肿瘤形成的基因。那就是侵入点。
这个基因后来为人所知的名字是src,读作“萨尔克”(sark),叫这名字因为它在鸡中能诱发肉瘤(sarcoma),就和佩顿·劳斯60年前开过刀的那只母鸡一样。“这是当时癌症研究界激动人心的理论,”雷·埃里克森(Ray Erikson)说,他当时还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农村小伙,正要投身RSV研究: “很明显,在病毒中有个特定的基因,它启动时能够转化细胞,在鸡中导致肿瘤。”此后不久,关于src的研究会从根本上撼动癌症研究界,在研究和治疗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革将以CML打头。但在初,还是要有人去搞清楚src到底是做什么的。就这么一小段DNA是如何把健康细胞转化成杀鸡肿瘤的?在转变过程中细胞发生了怎样的连锁反应,src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想要搞清楚src扮演的角色,就需要弄明白其编码的蛋白质。那时的科学界认为,每个基因在细胞内都编码一种特定的产品,这是生存必需的机制。src编码的产品是什么?“当我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一个小实验室做研究时,我把这个课题当作所能研究的问题中重要的一个。”埃里克森说。他为了追求科学事业离开了家族农场。埃里克森和他的实验室立志从宿主细胞的10万余种蛋白质中,筛选出混在其中的Src蛋白质。这个志向将“海底捞针”一词推到新高度。而这个追寻之举,将在日后显示出其地位,它是让人类发现癌症致命阴谋的重要的研究之一,另一项研究则是发现费城染色体。
4号码对,地点错
在埃里克森展开研究之际,英国报道了一种新的对染色体进行着色的方法。直到1969年,可用的染色法只有吉姆萨染色法 (Giemsa staining),它原本是用于检测细胞是否感染疟疾和其他寄生虫,但用来给染色体着色也很有效——染色体正是因其能迅速吸收染色液而得名——染色体 (chromosome) 一词源于希腊文中“颜色的 (chroma) 身体 (soma)”。染色体本身透明,不过染色后就易于辨识了。但吉姆萨染色法只能将染色体染上单一的颜色,正如诺埃尔和亨格福德在实验中意识到的,该方法有用却限制颇多。而那时,有传言说新的“条带”(banding)技术能将染色体以全新的方式染亮。
染色体看起来就像一对对齐腰绑在一起的粗短蠕虫,或者换一种更文雅的说法,就像一对对无头的舞者。它们漂浮在啫喱水般的胞质之海中。染色体全部由遗传信息组成,细看时这些黑棒就如紧紧卷曲的花体字,它们是由一个个单独的DNA分子及其附着蛋白质压缩而成的旋转阶梯。在人类中,这些紧紧压缩的双螺旋结构一共包含有20500个基因。[据人类基因组计划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和后来的DNA元素全书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ENCODE) 的首期工程揭示,人类基因组中只有1.5%的部分编码蛋白质,剩余的大部分遗传信息可能有功能,但目前仍不清楚具体作用。]
在遗传学研究的早期,科学家往往采用人类之外的物种来研究染色体的功能。因为利用血液和骨髓的研究技术还未问世,而要找到愿意捐献组织给遗传学研究的志愿者也非易事——适合遗传研究的组织常常是性腺。该领域的首个重要发现是通过观察海胆和马蛔虫获得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德国科学家西奥多·博韦里(Theodor Boveri)证明了关于染色体的3个本质事实: 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每条染色体包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每个受精卵从父母双方各获取一套染色体——为了构建一个胚胎,生命的故事需要有双重保障。这3项事实以三足鼎立之势,支撑着整个遗传学界。
实验结果也让博韦里相信,癌症是由基因异常导致的,这个理论至今仍屹立在现代癌症研究的中心。2006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启动了癌症基因组地图册项目 (the Cancer Genome Atlas),这个项目旨在给不同种类癌症的基因组进行编目,是全球开展的诸多同类项目之一。正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测量了人类DNA上20000多个基因的核苷酸序列那样,这个项目测量的是癌症组织DNA上的ATGC序列,序列上极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由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结构。比如说,有的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是指导细胞在恰当时机进行程序化死亡的,如果该基因的某个T被A取代,它就有可能失效,让细胞几乎永生不死,而这种异常的永生不死,正是许多恶性肿瘤的特性之一。核苷酸序列上的改变可能对细胞不造成什么影响,也可能来得快去亦快。但有些改变可能会是致命的。在基因序列上找到关键性突变,也即那些导致肿瘤形成、生长以及存活的序列,正是现今肿瘤研究的中心目标之一。
早在1914年,博韦里就已在这个方向上砥砺前行,但他的假说并未引起同行的注意。博韦里的想法太超前,就像未来访客,当时无人能懂。正如诺埃尔和亨格福德不明白为什么CML细胞会有这么短小的费城染色体那样,与博韦里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更是缺少相应的知识体系,来理解癌症和基因异常的关联这种想法。当时的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