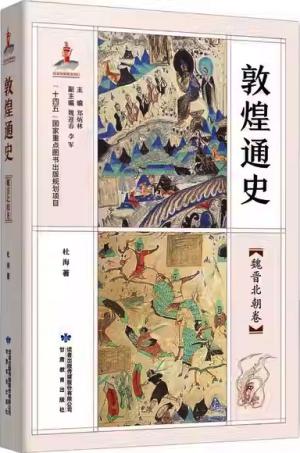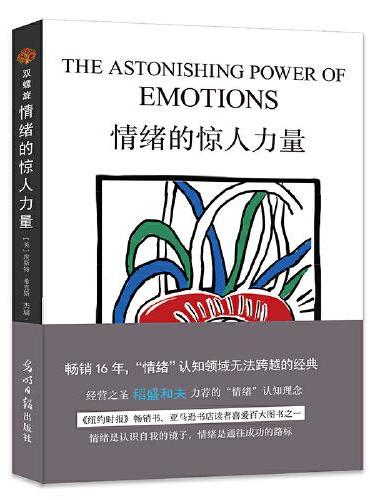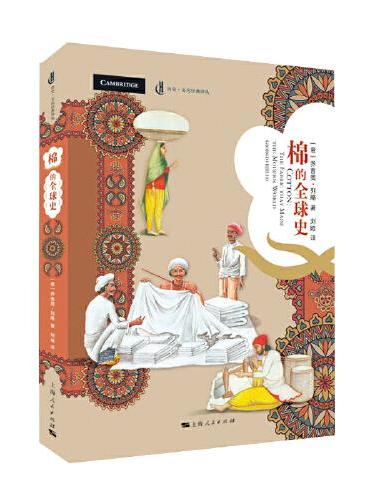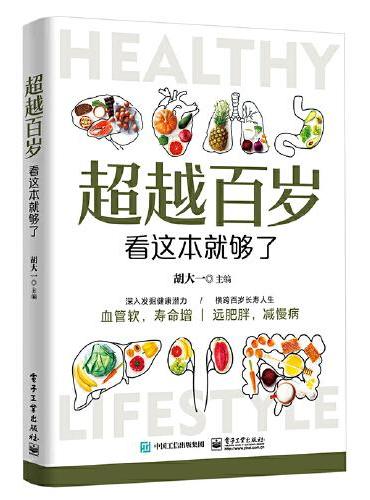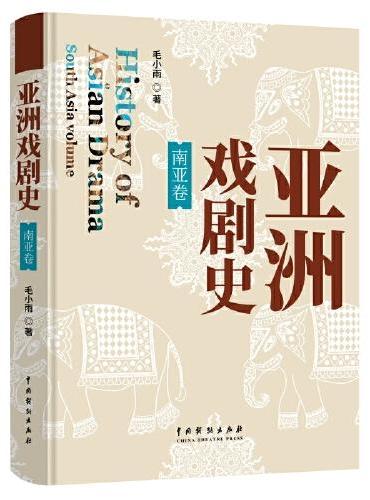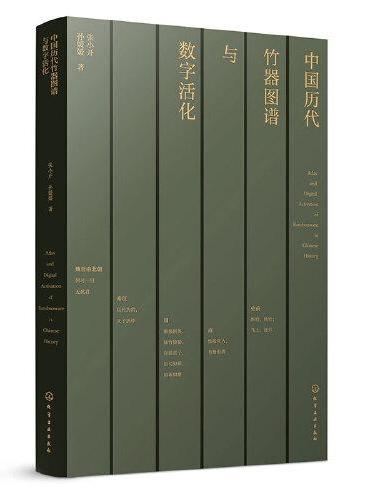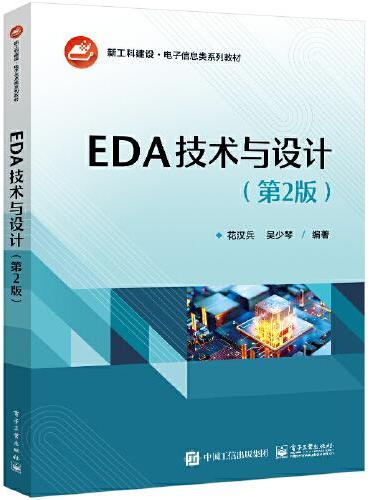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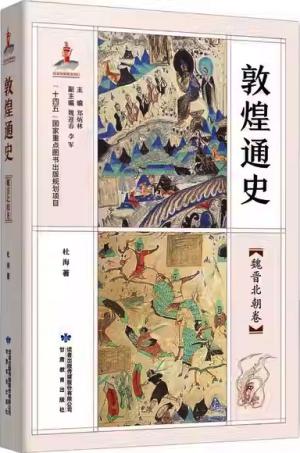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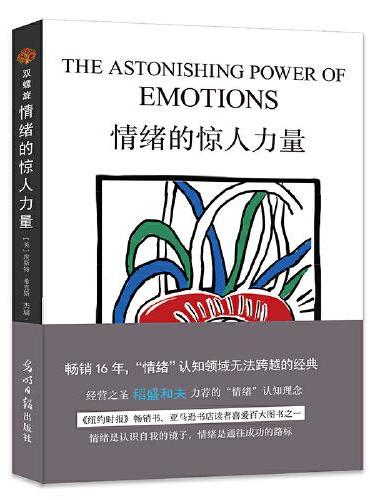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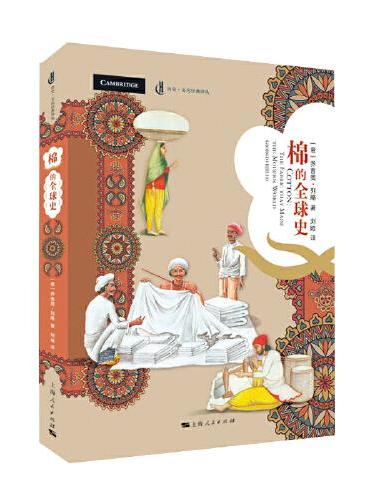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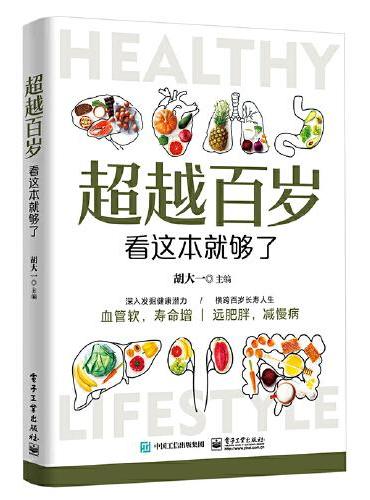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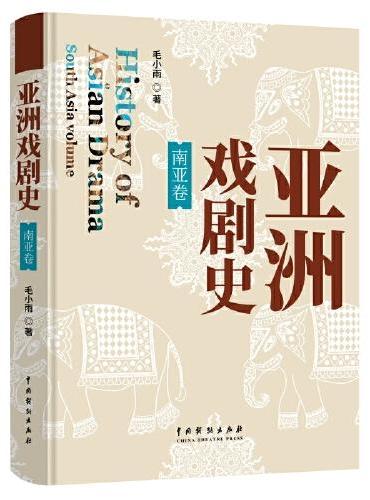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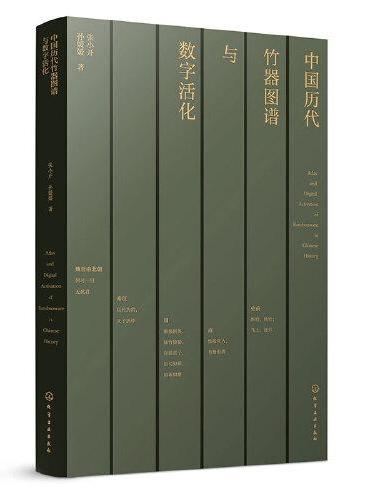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HK$
5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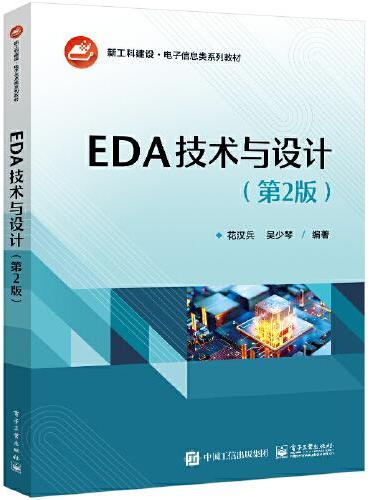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HK$
85.0
|
| 編輯推薦: |
|
作者长年旅居西北fu地,对西部的人文与自然有着非常深切的审美体验。他的文字以细沙般的流漾,深入精神的缝隙,从而弥合成实实在在的坚挺与chao拔,真切表现了沙漠边地的自然风物和自己的生命感受,带给读者多样而奇异的审美体验。
|
| 內容簡介: |
|
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D二、世界D四大沙漠,其中包含了苍天般的额济纳、流沙推移的沙漠、常年在戈壁上的牧驼人、外来的耕种者、骑马的土尔扈特、消失了的哈日浩特、被时间遗弃了的诸多生命个体。《黄沙与绿洲之间》是杨献平关于奇特有趣的沙漠生活的又一次书写,汇集了他近年来富有Du创精神及心灵意义的十九篇散文作品。作者以身处巴丹吉林沙漠二十一年的个人体验,呈现了沙漠与绿洲之间散落和存在的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用孤身深入瀚海绿洲上万日夜的青春履历,揭shi了时代之中少数人,奇崛而华彩的现实遭际与命运。
|
| 關於作者: |
|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曾获冰心散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已出版和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匈奴秘史》《冒顿之书》《南太行前传》及中短篇小说多部,散文集《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世上好的事情》《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历史的乡愁》,诗集《命中》等。
|
| 目錄:
|
目录
弱水流沙之地/ 001
那斯腾/ 014
巴丹吉林:沙漠中的人事物/ 022
秘密的河流/ 043
乌鸦或幻境/ 055
沙尘暴中的个人生活/ 073
虚构的旅行/ 084
额济纳的农民生活/ 094
唇齿之间的痕迹/ 103
在沙漠失声痛哭/ 113
犹如蚁鸣/ 122
简史或自画像/ 131
夜行者/ 147
风中的河流/ 162
沙漠爱情故事/ 169
盛夏的沙漠,秋天的沙漠/ 185
巴丹吉林:落日与废墟/ 201
疫情之下,陌生人的痛与乐/ 228
黄沙中的城与乡/ 239
后记 从南太行到巴丹吉林/ 253
|
| 內容試閱:
|
弱水流沙之地
无边的苍黄,沙丘此起彼伏,尤其是月光之夜,浩大的瀚海,却有着处子的静谧、深邃与坦然。在以往的想象中,沙漠狂躁,风暴和沙尘随时都在崛起和横扫,垄断和遮蔽天地间的一切,可没想到,古人所说的瀚海泽卤,也有着温驯与美好的一面。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年少、迷茫的我,从南太行山区的乡村至冀南平原,再到石家庄,乘坐绿皮火车,一路向西,起初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到哪里,“哪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和气候,包括它的自然和人文,等等。直到我落身于巴丹吉林沙漠,才顿然明白自己的目的地。那时候我肯定是一个穷小子,而且出身乡村。在那个商品经济甚嚣尘上的年代,资本逐渐成为人的另一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支撑,作为一文不名的小青年,我的仓皇和迷茫程度可想而知。我初的梦想是在城市有个容身之处,哪怕像某座大厦背后闲置起来的一块砖。但残酷的是,我从草木繁茂的南太行纸片一样跌落在一片空旷之地。
它的名字叫巴丹吉林,是一片巨大的沙漠,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据说为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它是阿拉善台地的一部分,外接蒙古国,域内有著名的贺兰山、额济纳、弱水河,以及当代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二十世纪一〇到三〇年代,因出土大量的居延汉简,而备受瞩目。南即河西走廊,处在古老的丝绸之路蜂腰地带。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等古城坐落在祁连山北侧的大戈壁和绿洲之间。
从酒泉市向北,过金塔盆地,紧接着无边的大戈壁。莽苍苍的天地,远处的荒山秃岭犹如龙脊,蜿蜒在天边。我睡了一觉醒来,看到飘舞的雪花,硬扎扎地飞旋而来,撞得窗玻璃吱吱有声。四周的荒野上,也被大雪敷上了一层棉絮式的白,整个天地,顿然肃穆了起来。再次进入城镇,然后是间隔很远的村庄,干枯的白杨树、荒着的田地包围它们。没有楼房,只是黄土夯筑的四合院,一座座排列在平阔的荒野中。
进入单位,我发现,成排的杨树上落满了乌鸦,它们干燥的叫声也是黑色的。如刀的风捧着轻浮沙尘,逐渐覆上了我单薄的身体,而且在内心也开始有所动作。我当时就感到了沮丧,如同一根树苗,还没有扎下根来,就被暴露在了孤独的旷野之中。这是一座神秘的军营,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部边缘。西边有河流,在沙漠之中,细小的流水在巨大的河床之中,像是艰难蜿蜒前行的白蛇。两边是成片的杨树,杨树里包裹着村庄。再四周,是铁青色的戈壁滩,表面有各种各样的卵石,沙子粗大。这里或许是3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前的浩渺海底。即使站着不动,也有一种摇晃和被淹没之感。
春秋冬是风沙的疆场,石子在风中成为奔腾的蚂蚁或者箭矢。往往,早晨起来,被子上蓬松着一层沙子,掸掉后,它们就会在水泥地上蹦跳如舞蹈。夏天是美好的季节,风沙不惊,烈日垂直。草木尽管稀疏,但大都会集中生长。尤其是戈壁边缘的海子,嫩草和红柳一起迸发,因拖拉机而闲置了的驴子、马、骡子甩着尾巴,把太阳向西边驱赶。日落时分,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幅充满古意的油画,家园和边疆的味道浓郁。而秋天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没有了岑参诗歌中的“胡天八月即飞雪”,只是一种被强力拧干了的冷,刮在人身上,感觉比手术刀还锋利。
西北漫长的冬天,犹如一场酷刑,同时也是一种历练。但是,作为容身于沙漠的人,特别是出身乡村的小伙子,我内心隐隐的惶恐与担忧比冬天还要深厚,表面不动声色,内里乱云飞渡。我知道,一个人首要之需,不是如何在某个地方随遇而安,也不是任由时间把自己带到此时彼时。我始终很清醒,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俗世中人,烟火百姓。斯时,我的人生刚刚开始,前路那么漫长,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安身立命,自给自足,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也不会是一个称职的人子、人夫和人父,甚至都无资格考虑。这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相信很多如我这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知和体验。
生存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每个人必须面对,深度开掘,身体力行。那时候,身边有不少人因为有各种层面的关照,或鱼跃龙门,或原地转换。我曾一度对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感到悲哀,有时候也迁怨于自己做农民的父母亲,他们如果是要员、财阀,哪怕是暴发户、走私者都可以在此时助我一臂之力。有时候郁闷,一人坐在小片的杨树林里喝酒,我当然买不起好的,就喝二块五毛钱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辛辣,且带着一股浓郁的红薯发酵了的味道。我极不喜欢。但酒也是跟随饮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的。自己喝得晕晕乎乎,站起身来,对着满树的叶子大喊。叶子们在季节中交换颜色,从诞生到坠落,就像人的宿命。
有一次,趁着傍晚,夕阳在戈壁涂上鲜血之色,我一个人往戈壁深处走。戈壁上结着一层硬痂,脚踩上去,硬痂裂开,露出白森森的土,还有一些黑色、白色、红色或者杂色的卵石,猛一看,似乎是一群沉埋的眼睛从低处向上看我。我吃惊,瞬间呆住了。蹲下来仔细端详,却发现,它们也在看我,而且都不会眨一下眼皮。我想,这戈壁之下,一定埋藏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这戈壁之中,也一定有着我可能无法参详的心事。我继续向北走,那是沙漠腹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看到了金黄色的沙漠,在尚未黑去的天空下,如同一张膨胀或者飞起来的黄金地毯,高低不平,但异常灿烂。路上不断有骆驼草、沙棵和芨芨草。还没有接近,就呼啦啦地飞起一些沙鸡,或者跑出几只野兔。还有些蜥蜴,以恐龙的姿势和速度,在沙子上一闪而过。
有意思的是黑甲虫和蚂蚁。我在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看到,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巴丹吉林沙漠——今天的额济纳附近建立过气象站,见到过沙漠中的毒物——红蜘蛛、蝎子和四脚蛇,并按照当地的风俗,抓了这些动物,塞进瓶子里泡酒喝。对于他所记叙的情景,我总是觉得恍惚。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样的一些异邦人,他们所为的,不过是为了探险及其所获。其实,人类在大地上的诸多生活痕迹和遗留物,说是文物和历史,但根本问题是,唯有时间才可以造就,而历史的代价,却是无数人、无数次的生和死,乃至无数事物的诞生与消亡。
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就像沙漠与高地,北方与南方,这世上,人也是有区别的。相似的脸庞,甚至文化习性,但我,和他,和你之间,是各个不同的。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不是其他,也不可代替。对于命运前途,俗世生存,我也是我,如何能得益或埋怨于父母亲呢?再者,每个人的出身都是荣耀的,不管身在何处,怎样的环境,有人生养并给我以人的基本生活、尊严、知识、文化和梦想,已经是足够幸运了。为此,我深深感恩。
五年后,我暂时离开巴丹吉林沙漠,去上海读书。这对于平民子弟而言,是异常难得的人生际遇,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深刻在我的内心。在喧哗都市,枕着彻夜的灯光、飞机和车船声,我发现,这里并不适合我。而初令我厌弃的巴丹吉林沙漠却叫我怀念至极。我觉得那个天高地阔,风吹尘土扬,春夏模糊,冬季漫长,且人烟稀少的人间绝域,或许正是适合我以生命和灵魂客居、旅行的地方。
当时,有许多同学力图留在上海,以各种方式。我对此毫不动心。而且,使我强烈想要回到巴丹吉林沙漠的另一个动力,是我自己的出身和职业。我以为,自己出身乡村,好的选择,不是谋求在大城市的俗世生活,而是在某些适合自己的地方,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无意义,没有价值,甚至终被风吹散,一败涂地,只要去做,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幸,再次回到巴丹吉林沙漠之后不久,我结婚了。其实,对于婚姻,我内心里是反抗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适合结婚,而且是一生;但从父母的角度考虑,孩子不结婚,他们就不会放心,也会觉得人生不够正常。
在很多时候,人一旦长大,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一切都要跟着传统的惯性走。再后来,我有了儿子锐锐。这一切,像做梦一样,在巴丹吉林沙漠展开。那些年,我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和弟媳妇,包括那时候还在襁褓中的侄女儿恬恬,也都先后来过巴丹吉林沙漠。我还建议父母亲和弟弟迁徙到附近的村庄或者城镇。是母亲态度坚决,穷家难舍,终作罢。今天看来,母亲的这种决定是对的。男女婚姻,在今天这个年代更趋复杂,也不可靠。人们在借助各种“工具”进行自我解放和开发的同时,也逐渐地失去了自己。
几乎每年,我都要到沙漠深处去一两次。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古日乃牧场,看到海市蜃楼。那情景,果真如传说一般,亭台轩榭,歌姬妖娆,花朵奔放,草木葳蕤。我知道,那只是一个幻象,但其中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叫我蓬勃不已又黯然神伤。在无边的戈壁上,牧人骑马牧羊,牲畜们在芦苇丛中,以及荒寂的莽原上低头吃草,抬头喊叫。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他们的赛马节。个子矮但耐力异常的蒙古马在戈壁上腾起烟云。我还认识了美丽的女子青格勒、格日勒和牧民巴图。先后十多次去了额济纳,在路博德修建的烽燧,乃至西夏的黑城遗址瞻仰与抚摸。
在额济纳的胡杨林中,我想到古代雄伟的战争与异族宫阙,想到庸俗的肉身之欢与精神之爱。在老子的弱水河畔,大禹、晋高僧乐尊、唐玄奘、李元昊、冯胜、左宗棠及彭加木的途经之地,我发现,巴丹吉林沙漠从上古时代起,就是一个神话诞生、流传与飘逸之地。两汉时期,这里是汉匈作战的前沿;后唐时期,巴丹吉林沙漠成为丝绸之路回鹘道的交通要冲。胡曾、王维等人在此走马吟诗,在水波潋滟的居延海边,抒发帝国豪情与个人抱负。而令人神往与叹息的便是公元前99年,年轻的酒泉教射骑都尉将军李陵带着“五千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沿着弱水河出发,深入漠北寻击匈奴主力,以阿尔泰山中断,以五千人马对敌八万人,“苦战八昼夜,杀伤过当”,终“四百人脱归”,李陵被俘,从此陇西李家败落,李陵悲苦一生之后,埋骨大漠。
这种悲情,我想千古以来,是无以排解的。皇帝和他的臣子、将军等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我注意到的情况是,有史以来,王朝的兴衰都系在某些人身上,成也人,败也人。能臣良将乃至谋略之士对于王朝兴衰、盛世乱世的作用,实在是强大无匹的。如李牧之于赵国,张良之于刘汉,郭子仪之于李唐,刘伯温之于朱明,刘秉忠等人之于元朝,等等,莫不如此。反之亦然。而李陵之悲剧,及其全军之勇决,实在是一曲旷古悲歌。
我觉得奇怪,巴丹吉林这一片沙漠之地,何以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往事呢,而且还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很多时候,我去到居延海,想起王维在此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情景,也想象乌孙、月氏和匈奴在此驻牧的种种已经不可知的细节。空阔的天空之上,流云如帆船,如丝绸,如裂帛,倒映在涟漪不断的居延海中,忽然觉得《易》以“兑”为“泽”的比喻和引申,简直是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水中有天,天又如水。水天一色,也天水相映。
可怕的是风暴。大的如龙卷风,起初晴朗的天地,远处忽然一片黑暗,接天连地的风柱如怒龙,似天宫倒塌,卷着诸多的沙子和尘埃,迅速奔移,有的时候,会将牛羊骆驼等动物卷入其中,即使不死,也会瞬间凭空上百里。有几次,我正在黑城拍摄纪录片,忽然遮天蔽日,天空变黑,呼啸的大风犹如奔腾的万千马蹄,轰沓而来。我们几个赶紧缩在黑城的墙根,用衣服包住头脸,蜷缩在墙根。许久之后,大地安静下来,睁开眼睛,一切复又如初,刚才的风暴,犹如一场梦魇。沙漠中这种行止不定的风暴,使我觉得,人生的某些磨难也大致如此,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无常才是世间万物之恒常状态。
就像这黑城,当年作为西夏王朝的威服司军镇所在地也好,元代的亦集乃路总管府也罢,都是人居之地。明朝的冯胜在此遭到了元朝守将卜颜帖木儿的坚决抵抗,大军围城半年之久,也没有破城之道。这位卜颜帖木儿,在当地的传说中,被称为“黑将军”。哈日浩特之黑城名字便由此而来。就此,冯胜军中有占卜者曰:“黑城地高河低,官军在城外打井无水,而城内军民却不见饥渴之象,必有暗道通水,如将水道堵截,(我军)则必胜无疑。”冯胜依计而行,大破黑城。后弃城而走,这座古城也由此废弃。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史·列传第十七》中只寥寥说:“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黑将军之类的,大抵是民间的穿凿附会,带有某些主观情绪,以及强烈的个人好恶。但正史也有很多的玄虚之说,如《明史·列传第十七》记载说:“(冯胜)生时黑气满室,经日不散。”这也算是另一种穿凿附会。对于民众来说,传奇和传说,才是他们真正喜闻乐道的。中国人的内心甚至骨子里,自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玄幻色彩,这大致是原始的万物有灵的自然性认知和“崇圣”的集体精神的体现和延宕。
王朝之间的冲突,一个取代一个,这种推演似乎有些残忍。但对于英雄,则始终有着某种崇敬与渴慕之心,也时常从他们的命运中,觉得了某些吊诡与玄秘。与此同时,利用节假日,我时常行走于巴丹吉林沙漠周边的乡村之间,与当地的老人攀谈。我感兴趣的话题是,这里的人们初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迁徙到这里并传衍至今的?从多数人的回答来看,巴丹吉林沙漠其中的额济纳、鼎新、巴彦淖尔等绿洲地带的人们,都说自己的先祖源自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等地,迁徙至此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在某些朝代被征调戍边,二是参与屯田,三是流放和贬谪者的后裔。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近些年由武威民勤及青海等地陆续移民而来的。
但更多的回答则是,不知道自己的先祖究竟来自何处,也不怎么关心。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还是有些失望的。慎终追远这种儒家气息浓厚且笼罩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甚至信仰的传统,在西北地区是有些淡薄的。这可能是这一带历史上民族流变剧烈、融合的时间和深度较深而导致的。从另一方面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乎“当下”,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就像我们身边流淌的弱水河,名字出自古老的《尚书·禹贡》。她从早期匈奴人命名的祁连山,流注到大漠深处的居延海。“弱水”这个名字,是指这条河流“鸿毛不浮,水弱不能载舟”之本性。但这条河流对于居延乃至阿拉善台地及其中诸多的生灵生命,有着多与少,生与死的意义。从史前年代到今天,一条河流造就、养育,甚至掩埋与冲刷的事物何止万千。她给予人和草木,以及双峰驼、黄羊、野驴、蜥蜴、蚂蚁、蜘蛛、沙鸡、狐狸等的润泽与灌溉之恩,是无与伦比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西游记》中说弱水便是沙和尚所在的流沙河,诗曰:“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还有人说,弱水位于鬼门关前,是人世和阴间的界河。至于苏轼“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则是一种艺术上的泛指和夸张。
有些年的春天,我和许多人一起,以踏青的诗意名义,骑着自行车,在沙土和灰尘的道路上迎着渐渐热辣的日光骑行。此时的弱水河,河床巨大,而流水弱小,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以湍急或者舒缓的方式流动。河水只占了河床二十分之一的样子,远看如同一条白色的丝线,在戈壁、沙漠与绿洲之间,孤独地流淌。两岸散落着诸多的汉代烽燧与关隘,如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等。站在残缺已久但还坚韧的烽火台之上,俯瞰河道犹如峡谷,在平阔的戈壁大漠中蜿蜒奔纵。细小的河流,静默得让人想起自身的某一条微小血管。大漠长天,苍茫无际,烽燧坐落其中。一个人站得再高,在瀚海泽卤,无异于微尘碎沙。漠风吹袭,猎猎有声。即使无风,站在烽火台上,也有大风不住席卷。
那风是高于平地和人间的,属于半空,甚至灵魂的和精神的大风,只有登临如烽燧古关这样的人文建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一以贯之的强劲与汹涌。遥想人类绵长的冷兵器年代,在此戍守的将士们,他们的豪情和勇气,似乎正延续了人类的某一些本性甚至偏执的理想。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性。有史以来,相互之间的攻伐与防守,充斥于史书的每一页,贯穿于每个人先祖的血液和命运。
有一次,我们外出踏青,回程路过弱水河在鼎新绿洲为湍急的一段,河水看起来平静,但内里却极深,暗涛在我们赤裸的腿上显示力量。其中几位女生害怕,我们又不好意思抱着背着,只能让她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把她们一个个地推过来。
还有几次,同乡在当地谈了对象,我跟着他们去弱水河边玩儿。正是中午,荒芜的戈壁上没有一棵大树可以遮挡日光,我们躲在红柳丛中,汗流浃背。他们初恋,在这种表皮发红如渗血的灌木丛中眉目传情,我则百无聊赖。为了不影响这对情侣,我一个人走到弱水河中,洗了手,再捧起一把喝下。冰冷的河水让我次体验到了冻彻心肺与凉风穿胸的感觉。再后来,我恋爱之后,也带着女朋友去过一次弱水河岸边,也在红柳丛中躲避毒辣的日光。这世上,只要有人和生命的地方,就有爱情和婚配,只要有人,一切荒芜之地,也都会变得诗意和美好。
在沙漠,个人的生活是和众多人一起的。同一个单位,分工不同,但都隶属于一个大的集体。分工合作,为了一个大目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积极的,也是有意义的。人类是一个整体,但因为文化传统和文明的不同,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迥异与差别,自然也有冲突与和解。军人和军队的存在价值,就是以战止战,以能战和善战,使得和平更持久甚至成为一种永久的状态。但地域文化乃至气息、气质对于人的潜移默化力量也强大无比,多年的沙漠生活,我身体甚至灵魂里,都弥漫着强烈的沙漠的味道。
你在此地,就被笼罩,而且是一种无孔不入,但无法琢磨和审视的气息,无时无刻不被浸染。我还发现,自己已经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了,它的一枚沙子,一片绿叶,甚至是一粒浮尘,我都觉得异常亲切。就像在沙漠珍视并努力呵护树木花草一样,我与沙漠的关系与日俱深。
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对我说,沙漠太艰苦了,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我就从内心里有些排斥,甚至会因此觉得他们的说法带有侮辱性质。在我心里,巴丹吉林沙漠似乎不是一个地域,而是与我同气连枝的同胞兄弟了。在巴丹吉林沙漠,我一直感到庆幸,有一片沙漠,那么一些人,连同沙漠中稀少但却各有姿态和尊严的动植物与我日日夜夜地相互关照与扶掖,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此外,我还觉得,这么多年了,我的性情乃至品性没有多少改变,尚未在庞杂的俗世和当下社会中被八面玲珑、随行就市、佯装与“自装”等影响和改变,甚至还为自己卑微的出身感到自豪,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使得自己的儿子的生活条件,比当年的自己好过百倍。那些年,我也不断带着儿子回老家,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住在乡村,儿子也没有嫌弃乡村的贫穷与孤陋,更没有造作与自恃、虚大与搞怪的流行病。人生如此,我还能要求什么,一个人,在大地、人群之间立身,爱人,人爱,这就足够了。
巴丹吉林沙漠尽管远离城市,在沙漠之中像是一座孤岛,风沙频繁,出门便是铁青色大戈壁滩。人的生活极其简单,相对于外面的世界,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尽管,任何的“世外桃源”都只是相对而言,也都只是一个幻境。
夏天夜里,我坐在月光照彻的戈壁滩上,看远处天空上的繁星,光芒凌厉或者温和地照耀着苍天和大地,偶尔会有夜间捕食的蜥蜴爬上腿脚。微风开始发凉的时候,大地静谧,整个人间好像都沉睡了,唯独我一个人在这瀚海之中。那种空旷中的孤立和孤傲,自在里的沉静与沉实,是当下这世上极少人可以体验到的。
赫拉克利特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倾听自然的话。”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时刻,我都在谛听,也在努力觉悟。十年前,我的身体离开了那个场域,进入都市。空旷与繁华,喧哗和寂静。这种明显的区隔,容身的环境,使得我总是有一些恍惚与不安。每当深夜,我会想到,其实我是适合沙漠戈壁的,尤其是中国的西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活着,不唯自己,当我们成为别人的儿女、儿女的父母亲,就有了基本的责任义务。
这些年来,身处成都,繁华与嘈杂同体连生,身在闹市的孤独,以及生存的各种掣肘与桎梏,可能更惨烈。很多时候,尽管巴丹吉林沙漠在我印象中越来越缥渺,甚至充满了某种遥远的迷离的意味,可我的内心和灵魂,却时常不自觉地飞跃关山,一次次地回到那一片广阔无垠与大野无疆。
直到现在,我还坚持以为,那浩瀚空阔的穹庐之下,苍茫之中,大地之上,弱水流沙之间,对于人及其他万物而言,它所具备的无边的澄明与混沌、雄浑与精微,都是其他地域所没有的。一个人在沙漠生活过,历练过,他的内心和思想,也更为雄浑、博大,甚至天真一些。在世事中浸泡久了,也真的觉得,古人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其实并不虚妄,即使在这个年代也有积极意义,那就是,一个人修身的目的,还是梦想能够为更多人做一些事情,哪怕饥饿中的一块干粮,瞌睡时的一只枕头。就像巴丹吉林沙漠和其中的弱水河,一颗沙子无以成沙漠,一滴水肯定无法穿越浩大的苦寒与荒凉,唯有积沙成丘和涓滴入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