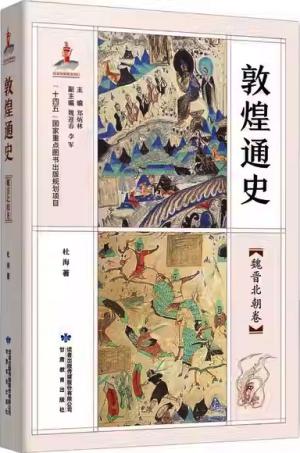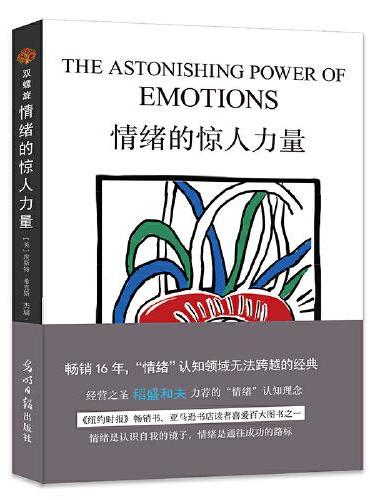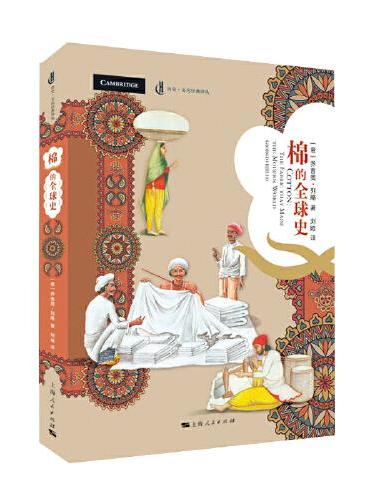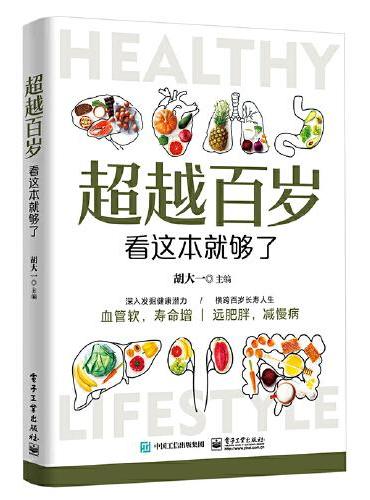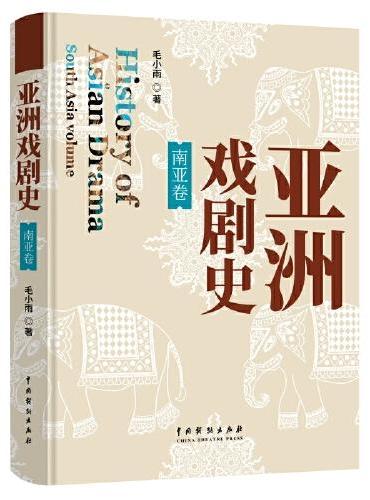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真谛全集(共6册)
》
售價:HK$
1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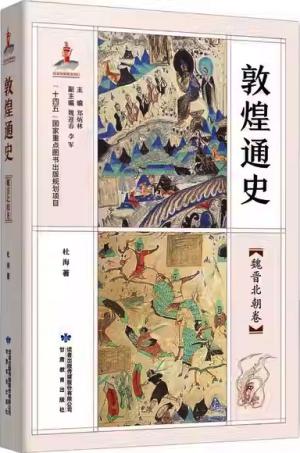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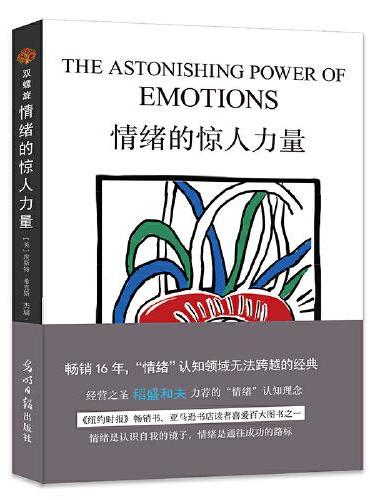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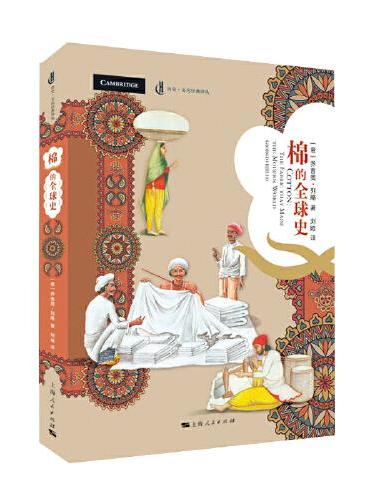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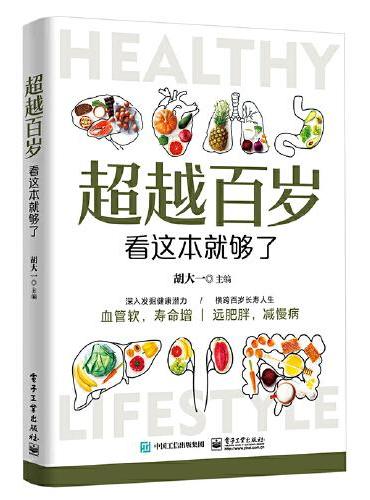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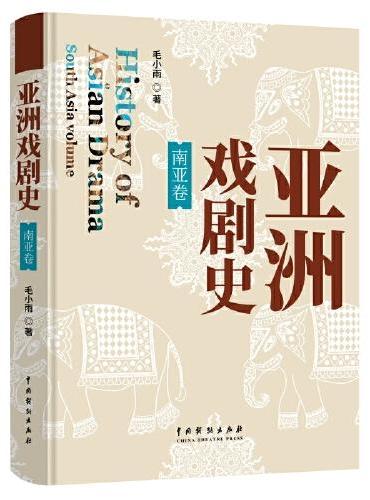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
| 編輯推薦: |
|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是典型的学者型诗人,具有极高的中国文化修养,其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哲学文化和德国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引经据典、博古通今、融汇中西,写作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集中既有顾彬治学游历的痕迹,又有着顾彬对社会价值问题的思考和评价。
|
| 內容簡介: |
|
《房间里的男人:顾彬诗选》精选了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诗歌精品,可以看到他对生命的爱,对存在的倾听,对他者的体认、宽容和同情。其中《房间里的男人》涉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面相,既有作者游学游历的痕迹,又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其中充溢着诗人强烈的“同情心”;《临渊之悟》包括爱情、女人与记忆,受伤的语言、受伤的生命,悲哀中的快乐等;《动荡的安宁》是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艺术上受到德国现代短诗和中国唐宋诗词的影响,语句简洁,追求意象;《猴子构造》中,诗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化用,对汉语表达和资源的吸收,使他和汉语言文化达成了一种“亲密性”。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汕头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编著有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袖珍汉学》《东方·方向》,主要译著和作品有六卷本《鲁迅选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半个世纪,他为中国和欧洲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汉学专家。因其在学术研究、翻译及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曾获多种奖项,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友谊奖、德国翻译界奖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
译者简介:海娆,旅德作家,翻译,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著有长 篇小说《远嫁》《早安重庆》,译作《顾彬早期作品》(四卷本)、傅安娜《汉娜的重庆》等。
|
| 目錄:
|
辑?房间里的男人/001
前言/003
诗作:1-81/006
第二辑?临渊之悟(1974—1979,1985)/083
前言/085
从桂林到阳朔的船上/088
香港喜来登酒店的中国小姐/089
从九龙看香港/090
十一月的北京/092
…………
第三辑 动荡的安宁(1976—1985)/141
前言/143
假设/146
她也/148
动荡的安宁/153
身体没有信号/157
…………
第四辑 猴子构造(1963—1976)/207
前言/209
杂色生活/211
(各地)散诗/227
题赠/236
人物肖像/246
…………
跋 有关早期诗作的说明/357
|
| 內容試閱:
|
跋
有关早期诗作的说明
在我的生活中,总是令人惊异地出现一些值得思考的瞬间,以致我从不相信偶然。当然,教会的坚信课也一再发生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许60年代初,我在萨尔茨贝格,一个埃姆斯河边的天主教村庄,听人说起“天意”。附近村庄的贝克尔牧师告诉我们几个福音派归正教会社区的孩子,《圣经》里没有“偶然”一词,一切早已在上帝手中。那一两年里,我们每周一下午,在人民学校的教室里相聚。我在转学到同样是天主教地区的赖纳迪翁石安努文理中学之前,曾于1955年到1956年在那里上过课。与之毗邻的墓园很小,我没想到,大约二十年后,我母亲(1923—1977)和祖母(1889—1977)会在那里相邻而葬。萨尔茨贝格,我写作开始的地方,至今仍然与我相连,仅仅上坟一事,就催促我每年一次回程。
一切都自然而然。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是与现居柏林和伦敦的中国诗人杨炼所进行的一次朗读之旅,它给了我理由,让我敢于触碰几十年来未曾触碰的我年轻时的作品。在2014年1月末2月初,我们在各地文学之家和孔子学院向热心听众介绍了杨炼的诗集《同心圆》。诗集大约一年前由汉斯出版社出版,它充满折磨的翻译花了我三年时间,有些烦恼我曾经谈及。在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我们共同走过了七座城市。多数坐火车,少数坐飞机。在必须逗留之处,无论是火车站大厅、机场候机室,还是火车车厢里;也无论是站是坐,诗人都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有时放在膝盖上,有时就搁在手臂上,不一定非在桌上不可。他看起来很积极地在写作。我问他在忙什么,他解释说,他刚为中国一家出版社编撰好他的全集。八卷本,也许十卷。因此他必须阅读每一卷,如果有印刷错误,就修改。
在他神秘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自嘲。他喜欢用“太幼稚”来形容他某一时期的写作:太不成熟,太孩子气,太天真!这让我惊讶,因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作品,就是我不仅翻译,也很欣赏的那些作品。难道我过去的选择错了吗?但搞文学的人都知道,你不能太相信作家关于自己的言论,低估和高估在写作这一行是常事。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出版那些他不再看好的文本。我还隐约记得约阿横·沙托依乌斯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放在地窖里的东西,就别再去碰它。他的意思是,过去写的东西或草稿,也许曾被有意无意搁放一边,以为还会捡起来的,都该永远待在那里。因此我过去将近二十年里也这样。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突然不再确信了。于是我想明确地知道,杨炼为什么要编辑再版那些今天让他在我面前会发笑的旧作?他的回答于我差不多就是一次真正的挑战:作为一个作家,你有义务将你的成长记录下来。如果喜欢我作品的读者只知道那些被我认为好的作品,由于缺少背景,却不能正确评估它们,整个人生,整个写作,全部作品,一切都成了凭空而来。
于是我突然想到自己的“早期作品”,它们自1985年就躺在波恩的“地窖”里,再没被我动过。如同天意,而非偶然,和杨炼在维也纳的朗诵会前,我认识了出版人瓦尔特·费林格尔硕士。尽管我没有作品给他,他仍然令我惊讶地想了解我。我承认,当时除了我的早期作品,因为上面提及的原因让我有所怀疑,我并没有其他尚未出版的作品可以示人。一连串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后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应该继续听所有诗人的柏林朋友约阿横·沙托依乌斯的,还是更应该听杨炼的?难道奥斯卡·帕斯提奥和马丁·海德格尔不应该是我很好的前车之鉴么?出生罗马尼亚的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认为,即使他写的斯大林颂歌,也属于他的全集;而来自布莱高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后将他的“黑本子”也愚蠢地出版了。难道我没在“文革”期间写过这样或那样可疑的诗吗?难道法兰克福学派没在20世纪70年代对我产生政治影响,并在我逗留北京期间(1974—1975)发展成“我知道一切”的症状?我真的该屈服于八棵葩出版社老板瓦尔特·费林格尔的诱惑吗?当我在维也纳大学新校区,喝着我心爱的维特林尔葡萄酒,与人谈话时,我决定冒险,并随即在2014年2月开始寻找我的诗歌“遗物”。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它们在我搬离柏林时都寻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地,即使不情愿长久被尘埃和蜘蛛网保护起来。
在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预测公众挑剔的眼睛呢?对此,我为每本诗集写了前言,以做些解释。我一直在写作,但在2000年前几乎没有出版作品。“一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除了少数例外,我如此长久未出版作品?默默无闻,甚至包括我那些出版名目:当我把在文学杂志如《乡音》或《科技时代的语言》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全部列入名册,我早年在诗集如《高中生诗集》或者《我们》中发表的作品,依然无人知晓。
当我还是高中毕业班学生时,我在一次大会上听过马丁·布伯尔的一首诗,题目叫《你》。我模仿它写了一首,就好像我没有读过它那样,或许是改写。我的版本发表在校刊《论坛》上。其他的诗歌或散文也在那上面发表,其中一篇用的笔名阿斯特·艾希腾布悉。但它们都不应该在此出版!那次大会应该是以人为主题,于1963年在波恩附近圣奥古斯丁的圣言会举行,或者在巴登·俄恩豪森,和新教神学者古斯达伟·门西林一起。不管怎样,那以后不久,我成了圣言会成员出版的《真理》杂志一名活跃的编辑。那是一本面向青年作者的杂志。我审评别人的文章,很遗憾,带着固执和傲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圣奥古斯丁是年轻写作者每年聚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朗读并评价彼此的作品。我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记者和文人。
因为马丁·布伯尔,我开始了写作。这个犹太哲学家并不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人。第二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罗曼语言文学家雨果·弗里德里希。1964年秋天我在策勒皇宫花园的椅子上,读到那本后来译成中文的《现代诗结构》的前言。斯特凡·马拉美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想成功,应该为抽屉默默写作二十年。很久以来,这促成了我不同方式的沉默:我写作,但不发表。充其量,我自费出版我的作品,给与我境况一样的人阅读,或者去当时流行的中学和大学的朗读会上读,和汉堡的亚历克山大·施密茨以及明斯特的米歇尔·本克一起。他们一个受到埃兹拉·庞德的影响,一个受到哥特弗瑞德·本的影响。我呢?我迷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如同我在雨果·弗里德里希介绍的作品中遇见它们那样。我尤其痴迷圣约翰·萡尔斯,其结果是创作了“蓝诗”,即在蓝色的纸笺上用黑墨水写成的诗。它们不用逻辑连贯,全部直接来源于法国赞美诗风格的灵感。不合逻辑是它们的原则。但我后来狡猾地把它们差不多全都毁了。当时芭芭拉·布鲁恩·苏尔特·韦斯林(生于1946年)手里还有些,在她赖纳的公寓里。她把它们借给我复制,并请我随后归还。但我没有复制,而是毁掉了它们,为此我感到抱歉。也许后还剩一首,名叫《爱情之歌》,在《论坛》中。我毁掉的那些作品,不仅是芭芭拉认为的我好的诗,还有些别的人也这么看。但我自己从不这样认为。
“蓝诗”并不是我迄今为止否定的作品。如上所述,在早年出版的刊物中还有一些诗作,这次同样较少被收入。我并不完全赞同杨炼的话,有时更趋向严厉的约阿横·沙托依乌斯。
我真的只沉默了二十年吗?大概有三十年吧,写作的困境伴随着我。在1985年到1988年之间我只写了少量诗歌,1988年到1994年之间我甚至一首没写。但我翻译了许多中文作品,从1991年开始写散文。为什么从2000年开始,我突然每两年就会出版新书,每本超过100页,以至于一些好心人如北岛必须警告我,我写得太多太快了。我的回答总是同样的话:如果我死了,就不能再写了。我必须现在就做想做的一切。为什么?
1998年,我远离那些我喜欢的作品,它们曾让我作为读者热情高涨,但作为作家,它们后却限制了我的创作。我的意思是,比如,乔治·特阿克尔和卡尔·科俄洛的东西,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我在写完《房间里的男人》(1970年)和《猴子构造》(1971年)之后,更加偏爱短小的形式,所有语义上的枝蔓被彻底删除。这涉及意象,涉及经常出现在诗歌后的单个意象,中国中世纪美学在此产生了作用,诗歌中的特定句子被少量或者似乎是古典词汇所限制,却足以隐藏作者的意图。《动荡的安宁》是这种类型的后诠释。
自从1994年我重新找到我的诗歌语言之后,1998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第四个孩子在1994年出生。从死亡中诞生,如理查德·瓦格纳戏里所说。四年后我在麦迪逊,从2月到4月做客座讲师。我的写字桌在一幢老房子里,由樱桃木制成。我的诗变长了,充满莫明其妙的叙述。梁秉堃(梁斌军)后来不厌其烦地声称,我是通过他才成为诗人,意思是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翻译。这不一定对。但事实是,他让我接触到后现代主义,于是我总是发现更多理由,对所有生存的偶然进行思考,而较少费心去质疑天意。
也许是我那时的工作让我后决定,把被我遗弃的“孩子们”从抽屉里拯救出来。在1995年到1999年之间,我不知怎么就写完一本新诗集。那期间我年年带着中国诗人在全德国跑,居然到处都有面对兴致勃勃听众朗读的可能,尤其是我翻译的作品。约阿横·沙托依乌斯几年前在柏林除评论之外还说过,我必须把一些东西放进抽屉,那之后,“语言文学之家”的负责人卡琳·亨帛尔-索思,于1999年秋天请我打开我的诗歌保险箱,让她阅读。随后,她为我在她的“家”里举办了一场朗读会。让我吃惊的是,我成功了,听众出人意料地多,并轻松接受了我的尝试。这位德语老师又找到一家出版社,就在我莱茵河边的新家乡。就这样,我的本诗集《旧绝望的新歌》(2000年),在文学之家朗读会的陪伴下,正式出版了。出版人斯特凡·韦德勒赞助我到第三本作品《影子舞者》(2004年),因为卖得不好,如他抱怨,我必须寻找别的出版社来替换他。迄今为止,人们更愿意读我的翻译,或学术著作,而非文学作品。作为翻译和学者,你不必也去写作,这话大家耳熟能详。至少在德语国家如此。
在中文国家得以传播多亏翻译,翻译得精彩才更容易有读者和买家,让我轻松卖掉至少300本书,那是每个德语诗人心目中不让出版社蒙受经济损失的数目。是的,我甚至远远超过了出版方的指标。原因很简单:文人在中国,不管是不是教授,什么都可以做。他甚至有义务,以多种艺术形式同时发声。如果我既想画画或者写书法,那里没有人会抱怨,只有在德国才会感到尴尬。但别的却合适:通过学术我获得课题,通过翻译检验我的德语。当我作为翻译应该获奖,为什么没人问,为何我的翻译有读者?难道我的语言凭空而来?或者自2000年以后,就不在我的日常写作中被打磨发光?
瓦尔特·费林格尔看得很远。他看见了我没敢看到的:我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正在成长的中文市场。因此他请中国作家德惠·布朗(笔名海娆)翻译我的作品,她的翻译让她位于法兰克福郊外的新故乡成为一处新的德语诗家园。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迄今为止,除我之外,还没有一个活着的德语诗人出版中文诗集。相反,我的同事和我已经翻译出版了数十位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并让其在德国深受欢迎。
感谢出版人和译者,我很高兴,因为他们的支持,我得以重新认识自己。出版人允许我,可以追忆后写作的五十年,并认为我长期的沉默是对的。海娆的翻译也迫使我,对我大部分很复杂的德语进行思考,并去面对那些由于时间久远而变得陌生甚至难懂的语言上的变异。这期间我阅读自己,如我读者中的一员。
在编撰这组青春诗作时,我只进行了少量修改,主要是句子排列,和少数我至今仍然眷恋的旧的拼写法。我看重视觉美。日期注解,尽管现在我感到陌生,一般还保留着,因为它们于我是一座返回遥远过去的桥。我没能总是记住当时的很多背景,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私人的。但总的来说,诗中的“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物形象,对读者讲述读者。
德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尽管在每天清晨付出极大努力—我主要在早晨5:00—7:00写作—但我几乎没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师。韦德勒出版社的安格丽卡·森格尔和现在在上海同济大学工作的马海默,是我不可企及的德语专家。当然,多年以来,他们不是用惊人的语言天赋影响了我的人。我还得感谢其他人,他们终生为语言奋斗,并让我分享他们的成果。
顾彬
2014年5月1日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从桂林到阳朔的船上
水在河面行,
而非天空下。
此路于船轻松,
于山沉重,
未磨之刀,
切不开羊皮纸。
天空把云
囚禁了三天,
如身体之于心。
彼此皆不安,
但别离之前毫无征兆。
(1985年3月16日)
香港喜来登酒店的中国小姐
她也是
实然和应然的统一。
出生于纸箱或棚屋,
怀着注定要挨饿者的希望,
后拥有了梦想,
却隐去了真名和出身。
能拥有今天,她感谢
从她的生命中摄取活力的人们。
从九龙看香港
比如夜里的九龙,
进入纸醉金迷和归化之夜。
人们披裹麻袋,藏身纸箱。
有脚跨过,
唯你独尊。
但在清晨,
楼宇层叠冲天,
香港,
在雨雾中沉寂。
石头和雨滴
恍若在美中握手言欢。
这里曾经的诗人,
很想分配这些场地,
把自然给水泥,水泥给自然。
但我们早知道,
自然比人造之作厉害。
它终会掩盖,
那些让人难受的东西。
十一月的北京
对于旅居异乡者,
本埠的一切都来自梦中:
介于枇杷和柿子间的脸,
除了颜色,无所寻觅。
北京德国使馆的圣诞宴会
1.
每个人都像从冥府冒出,
为了在年终之前,
再活一次。
2.
荷尔德林,
这来自童年的名字,
夹杂在人们的谈笑中
直到吃喝结束。
北京紫竹园咖啡馆
仍有几座新桥,
冬日阳光下水凝成冰,
天空的塔和树,
不值一提。
据说,
苏州在此这样建成:
乾隆当年下江南。
那里一如往昔,人美,
水秀。月下的笛声
和山上的鲜花,
让世界飘然坠入梦乡。
那就以梦挡风,
阻止沙尘入肺,
桥相连,水相依。
一条苏州的街巷就此形成。
人们可在那里巧笑,
商贩可在那里经营。
百年之梦落地生根,
百年之战由此引发。
今天我们知道,
没有必要南园北迁。
在这里的太阳和火炉之间,
两腿交叉,双手把杯,
看附近的厂区:
门下无非是女工们
笑声爽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