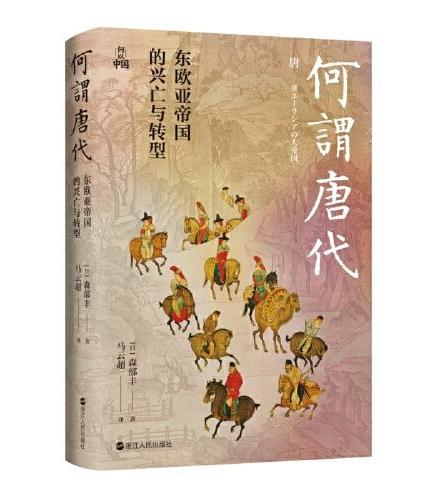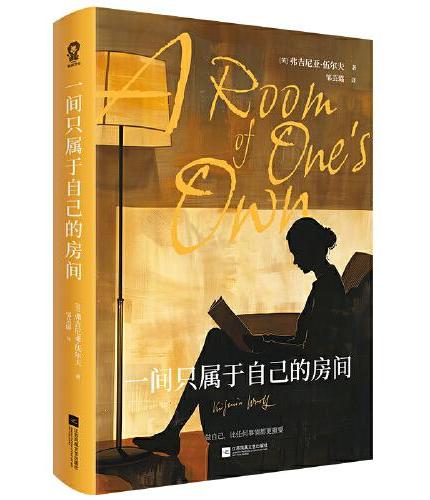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HK$
100.6

《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
》
售價:HK$
109.8

《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聚焦亚洲、中东和南美洲被忽视的本土农业文明
》
售價:HK$
99.7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6.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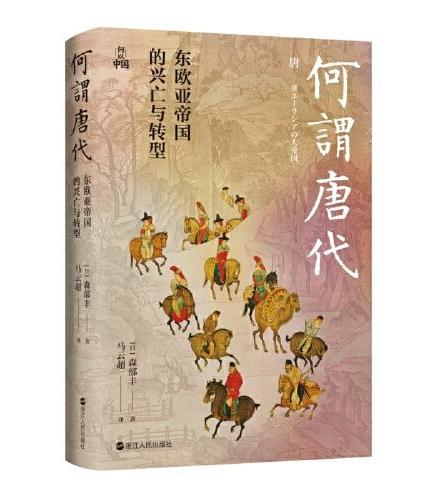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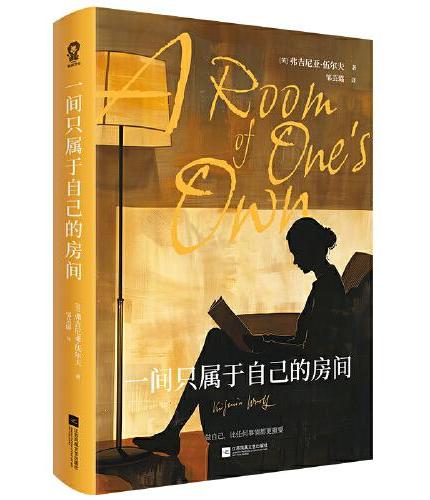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4.6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4.2
|
| 編輯推薦: |
★ 一代人的精神故土,怀乡散文的集大成之作
聚焦“漂泊”“寻找”“成长”等元素,关注远离故土漂泊在外的年轻一代,从回望、追溯的视角讲述童年往事,以及乡村与城市的交融和变迁,引发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 影视界知名导演、编剧合力推荐
《人世间》导演李路、编剧王海鸰,《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士兵突击》导演康洪雷,知名演员萨日娜、丁勇岱、郭涛等影视界知名导演、编剧、演员,联合倾情推荐。
★ 细致还原西北乡村风情,从旧时光中寻找“我”之存在
成熟的叙事结构,质朴而优美的文笔,细腻而充盈的情感,高度还原西北乡村的风土人情,让读者与故事中人一起感同身受,引发强烈共鸣。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从我心尖上揪下来的故事。 童年里的温暖、世界的奇妙、动物们不屈不挠的生存斗争、人和动物年年岁岁的相处,都是我记忆中乡间田野里的万物牧歌。 午夜梦回,我经常看见另一个我,每天在村口牵着牲口,早出晚归。 我想,那个我,应该一生都和动物们生活在一起,它们陪着我老,我照看着它们活。
|
| 關於作者: |
苏先生,作家,诗人,电影编剧,影视剧制片人。
在家乡生活二十年,后北漂十余年。喜欢在早晨散步、和老人聊天,周末必须坐在路边晒太阳,经常和陌生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收集了无数个人生故事,拥有一条边境牧羊犬。
致力于写微火、写熄灭、写漂泊者,沉迷于某种命运,在灰烬中寻找答案。
曾出版小说集《没有街道的城市》《星期一没有什么可说》,散文集《给所有的失去一个温暖的结局》《一封来自时间的检讨书》等。
|
| 目錄:
|
第一辑?家人
一下雪就回老家的兔子
上集市把自己卖掉的猪
软脚的小牛犊
天上掉下的猫
喜欢亲嘴的鸽王
羊粪杏树的故事
第二辑?邻居
一直都在挨打的马
寡妇家的驴
吃百家饭的大黑狗
挡路者马蜂
坟蝶
第三辑?来客
逃离的猴子
被抓错四次的鼠兔
流窜作案的黄鼠狼
打先锋的麻雀
每年到家里来一趟的蛇
第四辑?亲戚
每天傍晚出现的羊
会哭的树
去驮水就逃跑的骡子
第五辑?私货
借宿的鸟
戏精剧场
第六辑?他乡
北京救猫记
“流浪三雄”
一条边境牧羊犬的三十条侧写
后记
这是从我心尖上揪下来的故事
|
| 內容試閱:
|
后记:这是从我心尖上揪下来的故事
检视以前的生活,我发现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错位,比如我身处城市,但十多年来一直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我的职业需要强社交能力,而我却懒于口头表达;我一直向往乡村生活,却在城市苦苦挣扎。
有了微信等社交平台之后,很多人际关系和记忆都被激活。我被拉进了初中三班微信群、高中十一班微信群,但实际上我初中是在二班,高中是在十二班。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是我和同班同学比较疏离,和其他班的同学走得比较近,时间过滤掉了很多没有留下太多痕迹的人和事,留下了值得记住的时刻,就产生了这种错位。
这种错位让我在狰狞的城市生活中重新与两个很重要的老同学建立了联系,他们像两大支柱,在这些年里一直支撑着我和故乡的联系。
其中的一个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他每天要开车到各个村镇中去维护POS机客户,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去熟悉我生活过的那个县,走遍了我连脚尖都没沾过的地方。他用手机记录下乡村一年一年的变化,每周都会给我们发照片,四季不停。我们甚至还翻出了县志和曾经的各类报道,去追溯一个村子、一个镇几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另一个老同学生活在天津,他致力于推广家乡失传的各类美食,追寻我们记忆里的味道,让一道道童年美食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唤醒了我很多没有头绪的乡愁。在这两个老同学的影响下,我一次次回望着童年。
2020年7月,我从供职六年的一家互联网影视公司辞职,第二天起床后便马不停蹄地从北京回到了甘肃老家,急迫得像十多年没有回去过一样。我到家后正好赶上秋收,这是我离家前一直会做的事情。我每天跟在父母后面,和庄子里的人聊天,努力让他们重新接纳我。
但庄子里曾经的树不见了,小路消失了,房子拆了、院子塌了,学校也不见了,连月色都不一样了,晨阳再也不到房檐下了……满眼都是陌生的景象。我憋了一口气,像失去了什么,但无法确定。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甘肃天水市遇到了一群过马路的羊,它们把我围住,车鸣震耳,羊群依旧岿然不动,长时间待在在高楼大厦中的我感受到久违了的亲切。晚上我在酒店的露台上打开电脑,写一个很久都写不完的小说,突然想起一双双眼睛、一棵棵树、一只只蝴蝶。一时间我脑子里冲出一方结实的“绿岛”,然后发现不断给我添水的那个姑娘并不是服务员,而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归客。她说她好久没回来了,这几天回老家转一转,看我一直在喝水,不断空杯,就顺手给我添了水。
那夜,我开始动笔,从动植物的角度构建起一部童年史,写了一部西北乡村的挽歌。
这是一批迟到了的故事,我应该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把它们写出来,但那个时候我跌在茫茫人海里,根本捡拾不起这些生灵,那时的我比三十多岁的我好奇心强百倍,一心只往前看,从没往后看过。
离开家乡的这些年,在人群刻意制造的热闹最为迷醉的时候,我常常瞬间陷入悲伤,无意直发的那种对虚假的排斥让我苦不堪言,那些表面维护的热闹啊,是多么的虚弱。
在马路上,面对散乱的人流,钻入我脑子里的只有下一个目的地,没有余地去贪恋片刻闲散。
我会在深夜陷入自我矛盾。那些势不可当的、洪流般的情绪,我自知它们源头渊远——那些被万物生灵教化的经历,那些有意无意的生命交会,如同命运的深洞里回旋而出的一阵阵强劲的烈风,一次次吹到我的心里。
我特别羡慕那些一直在一个地方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稳定,被多年的交情围绕,每年回家都有一群好友,暑期、寒假,三十岁、四十岁,直至追悼会上,在短暂相聚后又散落四处,然后又再次相聚,他们的人生有断有续。
而我的交情是飘零的、散的,能回想起的都是分别。
午夜梦回,小学毕业时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班主任刚把我们送出学校,学校大门就被锁上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镇中心小学在那一刻只能留在记忆里了。初中的毕业典礼是在晚上,出了校门,我看见楼上的灯瞬间全部熄灭,我走在街道上,被街上广告牌的灯光晃了眼,初中就被锁在了我心里,寒冷,干燥。我对高中的最后记忆是校门口挂起的那些条幅,红艳艳的,在欢庆、在祝贺,也在远送,我不喜欢那种远送的感觉,因为那道关上的门把我们都送到了远方,之后的日子就都变了。
所以我只有一整块一整块的童年交情,越往前追溯,日子反而越完整、清晰。我的交情都来自于一些“物”。
在北京的某天,我睡醒之后,往事哭诉不止,内心的种种潮湿感袭来,我看到过去的一连串无法被定义为正确或错误的童年往事,我决心靠记忆来还原它们。
《浮世画家》里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或不能承认这些错误,才是最丢脸的事。年老之后,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我用毕生的精力去捕捉那个世界独特的美,我相信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
童年之美,乡村之美,自然之美,对我来说,是血液里最顽固的力量,它们支撑我来面对现在的世界和生活。
小时候,我喜欢待在我家祖坟后面的一片林子里。林子里有一棵古怪的大杏树,据说树苗是我太爷爷从远方挪过来的,他尝过这种树结的果子,说像蜜一样甜,但这棵树被挪到这里之后的三十年却从未结过果子。树没死,太爷爷死了,爷爷死了。我每天盘坐在树上背课文,发现只要站在那棵树上,读两遍课文就能背下来了,后来我的技术日渐熟练,能躺在树上睡着而不会摔下来,于是待在树上的时间就更多了。
我看见从外面回来的人,他们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走走停停,尤其是站在坟头或地角时的那种定,就像被抽空了魂。他们似乎在找什么,看向每一处的每一眼都显得异常深重,脑子似乎里在搜寻某些踪迹。
我不明白这些人的样子为什么如此相似。直到我离开那棵树,离开我的苏庄,离开我的镇子,一溜烟到了三十四岁的时候,每次回到老家我也变成了那个样子。这里瞅瞅,那里摸摸,不明白自己在找什么,不想说话,怕表露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静静地看,世间万物都不如这土地上的一隅永恒的旧貌。
对我们这一代小镇青年来说,“出走”太主流了,太毋庸置疑了,过分正确,藏匿着过于卑微的不解释。我也是出走的人之一,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学不会在出走后怎么生活。
写“物”很容易陷入抒情之中。汪曾祺老先生在《蒲桥集》中说过,《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而他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他在自选集中有言:“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并在自选集序言中表示他比较排斥过分的抒情,散文不应该沉溺于抒情。
我在写这些“物”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魔咒,所以尽量克制了,做到平实、家常。我不想往天空上写,写得那么高悬,我想写到泥土中,往土地底下写,越接近生命越好,越接近根和脚,以及泥土越好。
乡村凋敝,生命力在逐渐减少,所有的村庄都像沉默不语静等时间消逝的老人,已经没有了活力。在我的家乡,除了凋零的人口,其余的生命也在减少。牲口也很少了,机械代替了它们,满地都是被遗弃的宠物。我每次回家都能在街上看到被淋湿的猫猫狗狗,它们都夹着尾巴,在这里翻翻、那里找找,它们都是被迁徙到城市的主人遗弃的。
过去的农村,包容力很强,没有一条流浪的宠物,任何一种生命进入一个村庄,都能活下去并且能找到一个“家”。农村地形复杂,动物们随处都能找到安身之所,到处都有食物,觅食很方便,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美。
我上高中时,用一条狗的视角写了流浪的生活,那是一条离家出走的狗,违背了狗不嫌家贫的原则,在城市流浪了几个月后最终回到了村里。整篇文章充满了童话色彩,写完投稿后我就忘了。几年后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办事时,遇到了一个和我在一个时间投过稿的作者,闲聊时她说,她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和她的作品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我说我以为没有发表呢,原来是发了。
可能那时候我就想写写小动物们了,一直到三十五岁这一年,我才决心写出这些故事来。
这是我从心尖上揪下来的故事。童年里的温暖、世界的奇妙、动物们不屈不挠的生存斗争、人和动物年年岁岁的相处、在田野乡间的万物牧歌。
午夜梦回,我经常看见另一个我,每天在村里牵着牲口,早出晚归。
我想,那个我的一生应该还和动物们在一起生活呢,它们陪着我老,我照看着它们活。
最后,谨以此书纪念我那金黄色的、一去不返的童年,以及那无比迷人的纯真。
2022年7月18日 北京
长腿的麻绳子
一生中,我们时常会做盘点,或是回望,某些事情便会在这种不经意的时刻出现,尤其是物。物把人和人、人和时间串联得严丝合缝,物缘妙不可言。
在讲这条长腿的麻绳子之前,我先讲几个和物相关的小故事。
书
北漂后,有一年我是凌晨三点回到老家的。当时,老家刚发生了地震,我的卧室兼书房是上锁的,如果我不回去,这间房子即便着火或者被洪水淹没了,也没人进去。
由于地震,书房的墙和屋顶之间裂开一个大口子,在凌晨三点时抬头往上看,就像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顺着墙一直往上堆放的几百本书全部被雨打湿,被土弄脏了。
我没有睡意,就一本一本地擦书,那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第一次那么大规模地检阅自己读过的书。好书很少,烂书很多。有些书读的是潮流,有些书读的是心境,有些书读的是名气,有些书读的是私好,有些书读的是情色,有些书读的是名利。
第一次见到我这些书的外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移动公司的人,另一个是县政府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
那年,我们镇上要建移动信号塔,县政府和移动公司派了人来选址,选好址却联系不到那块地的户主,挨家去问,问到我家了,我说奶奶可能知道。
奶奶那年八十岁,谁家地里长什么草她都知道。奶奶当时去园子里割菜了,我便把他们喊进我屋里等奶奶。看到那么多书,他们惊叹,在这深山野村,居然还有一位藏书爱好者,他们看到感兴趣的书就翻出来聊上几句,不知不觉就到了饭点,我好客,便留他们吃午饭。我做了浆水面,他们吃得很香,吃完我们喝着茶继续聊书。
地震后的某年春节,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要娶媳妇,他在县政府工作,他父亲一生好客,朋友遍天下,那天大车小车从小伙子家门口一直排到了村口还没个完,有些车直接在镇公路边停下了。这场喜事声势浩大,蔚为壮观,我负责跑腿儿,迎客送客,兜里揣着几十个炮仗,跑前跑后地放。
我沉迷在放炮仗的欢乐里,没有留意周围。突然身后过来一个人,他握住我的手喊:“小苏,你这放炮仗的手艺很不错呐。”我抬起头,看这人白白净净,一副干部模样,有些面熟。我想了想还是没记起来,他接着说:“我在你家吃过浆水面啊。”
我说:“哎呀,想起来了,装移动信号塔那回。”
闲聊几句,他问我:“现在在哪里,干什么?”我说:“在北京漂着呢。”
他们上车走后,新郎官过来问我咋还认识他的领导,我说:“那年他来咱们村选移动信号塔的位置时认识的。”小伙子补充了一句:“难怪他经常提起咱们村呢。”
照片
春节期间,某天半夜我和父母聊天,聊着聊着父亲提到了一件事,说当时的照片在那个超大的相框里装着,我说要去拿过来看看。父亲说:“房子翻修后都不挂相框了,那些相框都摞起来压在那边的工具房里了。”我说:“没事,反正还不想睡,我去拿。”
我拿着手电,进了工具房,从几十袋麦子后面的缝隙里搬出了十多个相框,上面满是灰尘。相框里的照片从黑白的到彩色的,照片里的父亲从少年到中年。他中年之后的照片就很少了。贴有彩色照片的那些相框里出现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我们再长大一些后,相框里只剩下父母的旅游照,他们的合影也少了。
我把相框搬到院子里,扫了扫上面的灰,抱了好几趟才抱回屋子里,又用湿布好好擦了擦。父母拿着相框,看一张说一张,我就一边擦一边听,过去的时光就像钢琴曲那样流淌出来。我说:“干脆这样,把照片从相框里拿下来,一张一张看,看个清楚。”父亲说:“别拿了,装上去太费劲了,有几百张呢。”我说:“明天我去买几个相册装起来,这样你们就可以随时翻着看了,比放在相框里忘了好。”
现在,每年回家没什么事干时,大家就翻出相册来,一起回味过去的日子。
我时常看见母亲会在休息时翻看这些相册,偶尔扑哧一笑,偶尔蹙眉凝神。
家谱
我们家的家谱放在一个形似房子的盒子里,盒子雕刻得很精致,把前面的门打开,家谱就立在里面,这个东西被称为“柱”。字简单,意思也明了。
每年,家族中谁家要是做红白事,或者有其他需要祖宗参与的事,都会把“柱”请到自己家里去供奉几天,然后“柱”就留在这一家,等下一家需要时再请走,没人请了,就继续留着。
春节时,老苏家的人就会去“柱”所在的地方上香。
所以每年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总会有人出来问,“柱”今年在谁家啊?我们这些常年在外面的小辈都不知道,便你问我我问你的,直到问清楚了才肯作罢。家里那些被问到的老人就会眉头紧锁、眼睛上扬,凝神思考这一年老苏家发生的事:二月里嫁姑娘,是在你吉爷家;三月里开了庙会,是在你意爷家;五月里小童结婚,是在小童家吧。哎,不对,不对,腊月里你英奶奶请过去给小孙子订婚了,是在英奶奶家。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快速梳理一番老苏家今年发生的大事,我每次都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也是我每年春节回家感知岁月流逝、人丁更迭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仪式。
仪式就是有这样的意义。
麻绳
现在来说这根神奇的麻绳。
平时麻绳挂在牛圈外面的墙上,因为使用环境的复杂和特殊,麻绳呈现出铁色,还有了光泽。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成了那个颜色,也无从考究。
父亲出门打工后,有一年回老家,因为车况不好,到家已经是月光如洗的半夜了,他在从县城往镇里走的路上捡了这根麻绳。每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总要打一个通俗易懂的比方,他说他本来以为这是一条在路上休息的蛇,走近看才发现是一根粗麻绳,粗得像一条大胳膊。
那根麻绳刚到家里时根本没什么用,太粗了,没法用在任何农业生产的环节,基本上是个废品。家里很多次打算把它当柴火烧了,但它挂在房檐下,让人总也想不起来。
麻绳第一次派上用场是在初夏,它被大哥拿出去做了秋千。大哥把它的两头分别拴在两棵杏树上,因为足够粗,连坐板都不用装,直接坐绳子上就可以荡秋千了。
后来我堂叔看见了,便拿去在盖新房装檩子的时候用了,那时候家里条件都好点了,人们盖房子都舍得花大钱,得用三根一人粗的檩子。檩子是牌面,也最贵,不能有闪失,所以这绳子可靠着呢。
麻绳被这么一用,全村人都知道了,谁家盖房子它都会到场。后来跑长途车的人也来借,冬天车陷进雪地里了,煤车陷进水渠了,麻绳也免不了要上场,大事小事它都在。后来这麻绳在我家里待得越来越少了,有人来找它时,它经常不在。
偶尔我也能看见它被挂在牛圈外面的墙上,有人来借时,我说我去给你拿,当我去拿时,它又不在了,经常搞得我很恍惚。直到一个下雨天,我在窗户里看见有人披着雨衣把它挂在牛圈外面,喊了一句:“麻绳挂好了啊。”我这才明白,有人用完后就把它挂在那里了,谁要用就又把它拿走了。
有时候有些人有急用,便挨家挨户地问:“麻绳在谁家呢,晓得不?”有人说上次小童家用来压麦垛了,去小童家问;小童家说被小仓家拿走了;去小仓家追,小仓家说被堆堆拿去挂大车了;又去堆堆家寻……
有一天我爷爷要用麻绳,他在牛圈外面看了看,说:“这麻绳是野的,长了腿,到处跑,现在都不知道跑到谁家里去了。”
我看了看空空的墙面,心想,这麻绳要是有记性,肯定记住了很多大事、要紧事。
清庄
苏庄每隔几年就会清理一次村子。
清庄活动是从地理位置最低的地方开始。几十号人,举着火把,拿着各种灯具,手里敲敲打打的家伙什儿很多,制造出各种声音。从晚上开始,一直到清晨才结束,要把村子都走上一遍。
这些人每到一户人家,只有其中一人负责进院子,其他人会去平时很少有人去的角落里敲敲打打,用灯照一照、用杆子敲一敲、用消毒水喷一喷,目的是看看那些死角有没有未知的生命,是不是藏匿着逃犯。
这些年里,人们清庄时找到过很多小动物,也找出过几名乞丐、疯子、傻子。清庄那一晚人们都不睡觉,专门干这件事。
清庄的时候,很多家养的、常见的小动物都能平安无事,但那些陌生的、躲起来过日子的动物多数都会逃到田地里去,之后便很少回来了。它们知道被人发现了就活不下去,便去寻新家了。
苏庄的牲口和动物喝同一眼水,啃同一座山的草,耕同一座山的地。它们相互都认识,有些见了会打个招呼,有些彼此看不顺眼便互不搭理,有些性格古怪,有些随和热情。它们和苏庄的人共同经营着苏庄。还有些在田间生活的动物,它们有的是从苏庄里“搬”出去的,有的和苏庄里的动物是朋友。各自守着各自的地盘,记录着一年四季,盘算着节气,计划着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