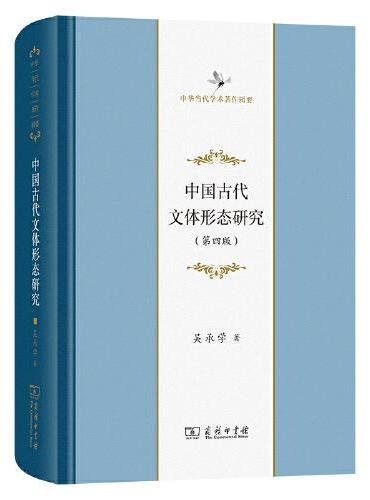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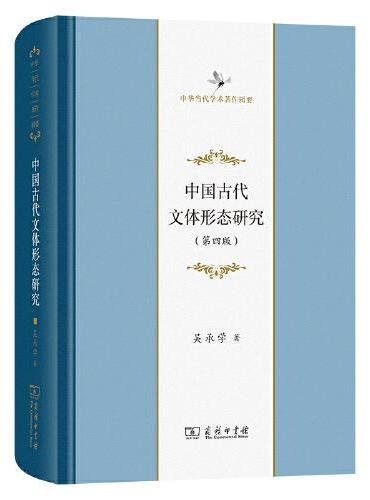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68.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HK$
99.7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HK$
88.5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HK$
62.7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HK$
53.8

《
打好你手里的牌(斯多葛主义+现代认知疗法,提升当代人的心理韧性!)
》
售價:HK$
66.1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 一代人的精神故土,怀乡散文的集大成之作
聚焦“漂泊”“寻找”“成长”等元素,关注远离故土漂泊在外的年轻一代,从回望、追溯的视角讲述童年往事,以及乡村与城市的交融和变迁,引发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 影视界知名导演、编剧合力推荐
《人世间》导演李路、编剧王海鸰,《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士兵突击》导演康洪雷,知名演员萨日娜、丁勇岱、郭涛等影视界知名导演、编剧、演员,联合倾情推荐。
★ 细致还原西北乡村风情,从旧时光中寻找“我”之存在
成熟的叙事结构,质朴而优美的文笔,细腻而充盈的情感,高度还原西北乡村的风土人情,让读者与故事中人一起感同身受,引发强烈共鸣。
|
| 內容簡介: |
|
六年前,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团乱麻,被谎言、虚华、无序和无数冲动包围着,越缠越紧。我必须逃,从心里逃出一个全新的“我”。 于是开始整理过往的记忆:一份亲情,一段路途,一件童年往事,一场瓢泼大雨,一次偶遇,一种寂寞……那些记忆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从纷繁缠乱的枝桠逐渐长成了现在的这一片小树林。 如果光线合适,温度合适,气味恰好也合适,我们总会寻到一段旧时光,一段早已忘却的日子。
|
| 關於作者: |
苏先生,作家,诗人,电影编剧,影视剧制片人。
在家乡生活二十年,后北漂十余年。喜欢在早晨散步、和老人聊天,周末必须坐在路边晒太阳,经常和陌生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收集了无数个人生故事,拥有一条边境牧羊犬。
致力于写微火、写熄灭、写漂泊者,沉迷于某种命运,在灰烬中寻找答案。
曾出版小说集《没有街道的城市》《星期一没有什么可说》,散文集《给所有的失去一个温暖的结局》《一封来自时间的检讨书》等。
|
| 目錄:
|
一棵树顶住的房子
独居的三伯
姑姑月兔
爷爷的咳嗽
共享书屋
两个复读生
一个兵
杨存女
挖光阴
一水洗百净
这风尘仆仆的跪倒
摸奖
父亲的信
一个人静静地黑
一个村庄的身世
回家吧,回家了
走远
麦子,麦子
跑肚
献天爷
上粮
人间棉花糖
打春
捏瓦呜儿
自行车上的梦
新课本
偷“背”字
扫毛衣
笼火
送婚书
耍故事
后记
我要写出内心的恐惧和与之抗衡的力量之源
|
| 內容試閱:
|
后记:我要写出内心的恐惧和与之抗衡的力量之源
很多人会在成年后持续不断地做着小时候的一个梦,每次梦境都会都延长一点,再延长一点,一直到年老,才能做完这个梦,走出这个梦。
走出来,就再也不会做这个梦了。
这种梦很多都源于内心的恐惧和担忧,是小时候遇到事情时的无助和无解带来的。
在三十五岁这一年,我走出了三个梦:骑车的梦,考试的梦,寻找父亲的梦。
六年前,我发现自己成了一团乱麻,越缠越紧,还不时出现新的线头。直到某天,我甚至感觉要窒息了,据说窒息前都会挣扎几轮。我挣扎了,用了许多办法。但挣扎有用吗?无非就是让自己感觉还有生命体征而已。真实的自己被谎言、虚华、无序和无数冲动包围了,我必须逃,从自己的心里逃出来一个全新的“我”。
于我是开始整理过往的记忆:一份亲情,一段路途,一件童年往事,一场瓢泼大雨,一次性爱,一种寂寞……都像种子,之前某些纷乱缠绕的枝桠也开始变得顺溜,就有了现在的这一片小树林。
我要写出内心的恐惧和与之抗衡的力量之源。
我时常看到在公交站台上的自己、在黑暗中静坐的自己、在路途中紧闭嘴巴的自己、在火车上抱头的自己、在人潮里张望的自己……谁能望穿自己一生中所有的冬天?谁能偷看到自己一生中所有独自承受的痛苦?这是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让时光倒流,把时针往前拨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清除后来的人生经历,把之后的一切都忘记。如此这般,我才能站到那个时间点上平和地讲出这些故事来。
故乡其实仅仅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她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在现实中已经没有了。
有一年秋收,父亲头天磨好了十二把刃子,用报纸包好后放在塑料袋子里,让我给他们送到地里。在田间小径上,因为贪恋路边风景,我把刃子全部弄丢了,还毫无察觉。面对父亲和母亲站在烈日下的麦地里的那种绝望,我第一次感受到自责这种情绪。我真是该死,一把刃子最便宜也要四块钱,贵的要十块钱,父亲在收麦子前兴致勃勃地磨出来的刃子,就被我那么轻易地、不负责任地弄丢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十多亩麦地就是天大的事情,而我当时的世界里似乎没有重要的东西。
我厌恶自己。
那一年,父母亲用割草的镰刀刮了麦子,麦茬散乱,他们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不是借不到刃子,而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对谁都张不开口,也是因为家里太贫穷,秋收前是我们家最穷困的日子。
时间走远,生活就成了故事。生活毫无道理可讲,对后来的人就越发有了故事性,呈现出无法理解的形态。当我说出这些往事的时候,自己也会恍惚,为什么当时的自己是那般的狭小局促。
生命里呼啸而来的成长,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一直试图给自己建立某种秩序,按照秩序去执行、去生活,却发现自己的每根骨头和每一寸肌肉都在抵抗这种秩序。
一直到今年,我给自己造了一座“监狱”,把自己关在里面,开始书写那种泛白的干涸,那种能再次被提起的孤独,书写那种摧枯拉朽、柔肠百结的疼。
我们总归是需要一些回味的,比如疼痛、青涩、莽撞和自罚。
我迷恋光线和味道,能见到记忆中的花朵,花朵能出现希望,希望能把时间变长。
每次拉上窗帘,眼前变得黑暗,我就像去了一个陌生的、呈现混沌状态的地方,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很失落。这种黑暗和晚上的不一样,知道它可以被浪费,知道它随时可以结束。
如果光线合适,温度合适,气味恰好也合适,我们总会寻到旧生活,寻回某段早已忘却的日子。日子里的自己,没有重量,没有光芒,心中也没有他人。
我经常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语而关上电脑去睡上一大觉,然后又睡一大觉,到了某个黄昏,那个词语冒出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四天了。这三四天里,我被失败、等待和被抛弃的感觉笼罩,每个深夜都像失恋了一次,疲倦的情绪压着心口,这是一种还未想到死亡,但接近死亡的感觉;是对某件事还有期望;是因心痛而勾勒出的情感,先要有痛,才会明白痛的力量。
某天,我做了一个梦:午后,我去放风筝,风筝从故乡家中的窗户飞出去,飞到了我北京的住所的后面,我使劲收线,只收回来四件已经洗过的衣服。
时间就这样瞬间过去,伤口在此处愈合后,又会在另一处开始。把站着的摁倒,把奔跑的放弃,时间合成生活后就成了极其平凡的日子。
每当我一个人在旅途中、在夜深时,总能听到外面细微的风、陌生的车流,还有很多我不明所以但总是连续不断的喊叫,它们常常把我拖进梦中,连接起我那几个长年都连续不断的梦:那段时间,在那个年纪,他每天都需要一个人走一条浓雾笼罩的路……
一个村庄的身世
因为曾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人的角度理解了一次生活,理解了一个村庄。
上高中时,有一年我从学校跑回家,在家里待着,待到了漫山遍野的桃花全部绽放的时候。每天傍晚我都会溜溜达达地去山上走一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山顶变成了花海,整片山被花香覆盖,我的鼻子闻不见其他任何味道。不光是桃树,荆棘树也开始挂红黄不明的果子。折下几枝桃花拿在手里,几只蜜蜂被桃花吸引,我举着桃花把它们从一处带到了另一处。山顶的广播塔上的喇叭还是像我上小学时那样,会定时响起,我坐在山顶的树林子旁边,把脚垂到崖下,眼睛望向远山,耳朵听着广播,似乎十多年间这里的日子从未移走,一切还是老样子,植物一年四季枯荣往复,大山岿然不动,只有街道延长了一截又一截。
恰好在这一年,轮到我们家的人来当“会长”。
“会长”是每年负责庄子里东岳大帝诞辰祭祀的人,每年要各家轮流来当。会长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请剧团唱戏,一个人负责处理庙宇祭祀事宜,还有一个人负责财务,要处理收钱、采购、花销等事。这一年我父亲要负责庙宇祭祀。父亲本身就在庄子里的剧团里,之前我跟着他看热闹时也断断续续见识过整个流程。东岳大帝的诞辰是农历三月二十八,负责财务的会长会提前半个月挨家挨户地收钱。三十多年前,每家每户要出一匙胡麻油加一碗面,这个惯例持续了十年。后来大家觉得收集面和油比较麻烦,会长提着油桶和面袋子挨家串户也不方便,便改成了每口人交五毛钱。如今,每口人要交三十五块钱。庄子里的秦腔剧团成员也都老了,现在再进行祭祀时会请专业的剧团来唱戏,唱四天四夜。
父亲在银川的工程没有做完,回不了家,但负责庄子里的祭祀时是不能推脱的,他每天都会追几个电话来,心急如焚。后来庄子里的阴阳先生对他说,只要让孩子招待好他们这几个干这一行的人就行,他们会把这件事办好的,庄子里的祭祀活动进行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自觉,不用父亲操什么心。
庄子里负责庙宇祭祀的几位先生后来几天都在我家里忙来忙去,我负责裁纸、磨墨、兑红、泡茶、添水、晾晒纸张,他们负责画对联和符纸、抄经文、写祭文、准备各类旗子,母亲负责给他们准备餐食。这群老先生每天在干活间隙都会聊很多庄子里的事,从几十年前的事到现在的事、从老人到年轻人,也说到过一些奇事怪事。他们描述的多是苦难,因为他们这个行当最常见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苦难。我倚在门框上听,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几位先生时不时看我一眼,偶尔也问我:“你咋看?”我笑笑,说:“我晓不得。”他们也笑笑,说:“你长大就晓得了。”几位先生家里的孩子都是我的同学,有些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出去打工了,还有些读到初中才出去打工,另外一些和我一样,在读高中。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如何,我也不知道某天我会用文字记录这些事情。
几天后,我跟着他们去庙里打扫,只在春节、清明、端午和农历三月二十八这几天里,这座庙才会开门,其他时间要进去的话得找会长拿钥匙。我们拔掉院子里的草,把神仙擦拭干净,又给神仙换上新的衣服,门窗全部擦洗一遍。在主殿里扫地时,一位先生说:“神仙知道庄子里每个人一年来的好运和霉运。”我点点头说:“是。”我说因为我觉得神仙什么事都知道的。他继续说:“你看这墙上和庙门口的旗子,都是人们还愿时送的,很多人在去年许下了愿望,来年都实现了。”我这才理解他真正的意思。他继续说:“没人敢骗神仙,许了愿望,就得来感谢神仙,得把好吃好喝的、功德旗都送上来。”我在主殿的墙上找了一圈,找到了前几年父亲送给神仙的还愿旗,那时我身体虚弱,父亲祈愿之后我的身体好转了。父亲的还愿旗已经被后来几年的旗子遮住了,只能在上面看见我的署名,那是我的小名。庄子供奉的神仙只认小名,你在外面叫什么名字他管不着,在庄子里叫啥在神仙面前就得是啥。出主殿后,我看见院子正中间的祭台上都是现杀活鸡时留下的血迹,有些人挣到大钱后会杀鸡献给神仙。先生让我去庙门口放一挂鞭炮,我把鞭炮挂在杏树上,这活儿我很熟练,每年大年初一的零点,我都会来这里放一挂。放完之后,我回主殿的台阶上坐着,庙落在庄子的最高处,风吹着我们的脸,先生说:“你这炮一放,庄子里的人就知道庙门开了,一会儿就会有人来上香。”十多分钟后,果然有人来上香。几位先生继续聊了起来,他们说前些年庙里香火不旺,人都穷,这几年祭台上的香烧一个月都不会断火,房檐下还挂了很多能燃上月余的盘香,有人还给庙里添置了物件。他们越聊越多:庄子里上一代人中是谁谁最早发家,迁走前还来庙里祭拜过;这一代人谁谁在某年发了大财,给庙里捐了几个大香炉,估计离迁走不远了……在他们的讲述里,时间似乎一下子从很早以前滑到了现在,出生、发迹、离开、死亡,一个人的一生就在这四幕里完结了。
我从庙门口看出去,庄子里人家的屋顶上,黑瓦被太阳照得发出淡淡雾气。是啊,每家每户真实的生活,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只有在神仙面前,人才最真实。一座庙见证着一个村庄,它能看见被掩盖了的另一面。人们跪在这里许愿,许健康、许财富、许功名……
只有一座庙才能看得清一个村庄的身世,看得清那些出走的人,回来的人,失意的人,得意的人。
庙里的事情忙完后,负责剧团唱戏的会长让我去帮忙晒剧团的戏服。我们把戏箱抬到戏场的院子里,一件一件地拿出来,他说:“这可是咱们庄子这四五十年的家当,一年添置几件,零零散散地积攒这么多年才攒下来了这份家业,可得细致点,别摔了磕了。”那天,我看着满院子闪闪发光的戏服,才知道了一个村庄的日子和一个家庭的日子过法是一样的。戏服晒了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开饭前,除了几位先生,乞丐福舟也来了。
福舟是镇里有名的乞丐,是全镇最出名的人。他比我大十来岁,是个哑巴,有点歪头和痴呆,每天都在镇里闲逛。他有个很厉害的本事——每个庄子里只要有祭祀这一类的公共活动,他总会知道,还要去那个庄子住上几天,吃香喝辣,和神仙们享受同样的待遇。每个庄子也都会好好地招待他,人们总觉得他是神仙的一个化身。之前好多次路过我们家的时候,他也会来要碗饭吃。他每次来都带着自己用的碗,我盛好面,再端出去倒在他的碗里,他从袖头里拿出筷子,几下就吃完了,吃饱前他是不会离开的,会一碗接一碗吃。
农历三月二十八这天,庙里的神仙会被抬进戏场的大院,然后会被抬到戏台子的正前方看戏。庄子里的每家每户都会端出两个人头那么大的馒头,在上面点上大红的桃花、杏花,再炒一盘献菜,端到神仙面前,放上半个钟头,等神仙吃完,再端回家。福舟此时就会坐在神仙旁边,人们会给他好多好菜好肉。他是镇里活得最长的乞丐,至今还活着呢。
戏场院子里的人多得脚挨着脚,除了庄子里的人,每家每户喜欢看热闹的亲戚也会来。亲戚们一来就会住上四天四夜,跟着神仙一起享受,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
我三十五岁这年的夏天,有人在我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些老同学们在一条路的尽头站着小便,另一名同学拍下了他们的背影,传到了群里。
那一刻,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遗憾中,想到自己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走到路的尽头撒一泡尿了,这辈子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我每次回家总是想去看看,然而又总是在巴掌大的地方忙前忙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处走走看看了。深夜,思来想去后,我找到了答案,因为我没继续生活在那里,所以不会再仔仔细细地翻那些山,穿那些庄,并踩那些路了。
照片上的那条路是我们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只有我们那两届的学生走过那条路,后来学校搬迁,那条路随之就被废弃了。那是在树林子里绕着树、躲着坑,经过十多个人的集体探索才找出来的路,是一条我们走出来的路,偶尔有几个放牛的人、挑粪的人,也会从那里走一走。如今它已经不能叫作路了。它又回归了自己本来的模样,成了林中草地的一部分,开始杂草丛生,路的痕迹渐渐被隐藏,庄子里的人甚至不知道,这里曾经悄悄地出现过一条路,又悄悄地消失了。庄子里可能还出现过很多没人知道的东西,也都悄悄没了:来过一只牲口,来过一个乞丐,半夜有一个醉汉路过,雨水在某个河沟里形成了一个涝坝后来又悄悄地干了,有个稀奇的动物曾在某个洞里住过后来又跑了……
一个村庄由什么构成?一眼井,上千个相互认识的水桶,十几个木匠,两个阴阳先生,一百头牲口,几百户人家,一所学校,几个有名有姓的无赖,几条河沟,几个涝坝,一座瓦窑,一个大戏台,两名医生,一个神婆,几个说媒的……
只有站在山顶上,挨家挨户地去瞧,才能看清楚一个村庄。谁家消失了,房屋倒下了,院子里被荒草占领了;谁家几十年后又突然有了人,谁家还有老人,谁家开始干起了新的营生,挤掉了原来干这门营生的人……只要人需要活下去,就会有矛盾滋生,只要有劳动,就有声响。
去年秋收时,我回家去,站在门前和聚集在那里的叔叔伯伯、婶婶大娘们聊天。我尽力地说着一些他们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尽可能地说着关于这个庄子的话,让一群在庄子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能再次接纳我——一个已经离开家乡多年的人。
我说起对面山上的那一眼窑洞,婶子说:“这你都记得?”我说:“咋不记得?我在这里都长到二十岁,咋能忘?”
伯伯说:“能忘的都不知道回家了;能回家收麦子的,都是没忘记家的。回家远不远?”
我回:“回家好远,好远啊,但家永远是要回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