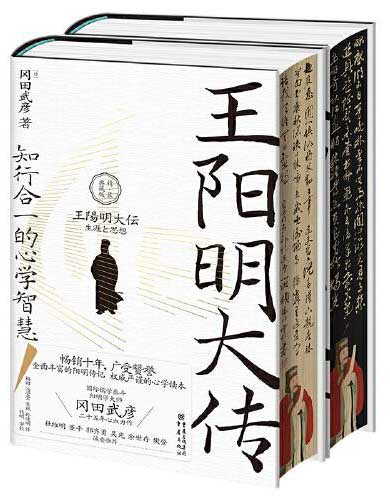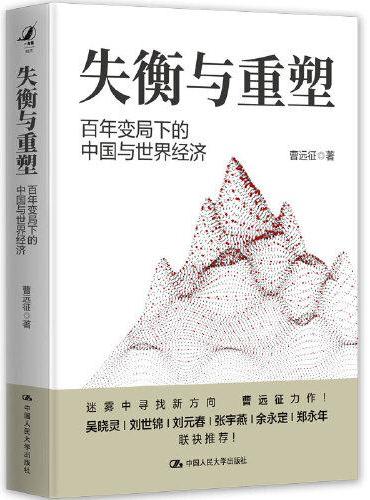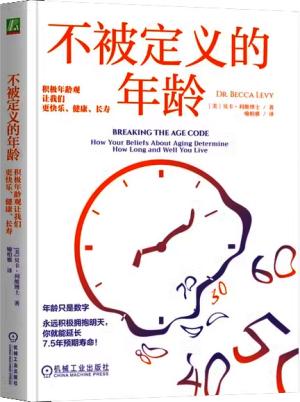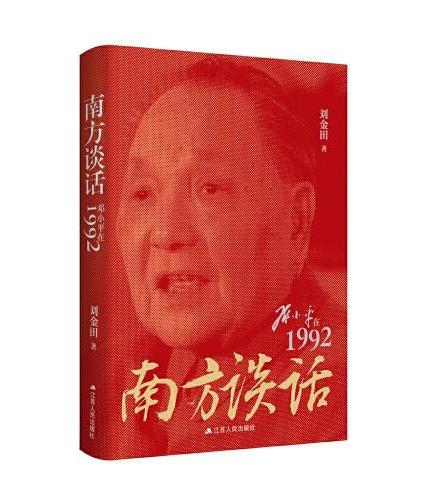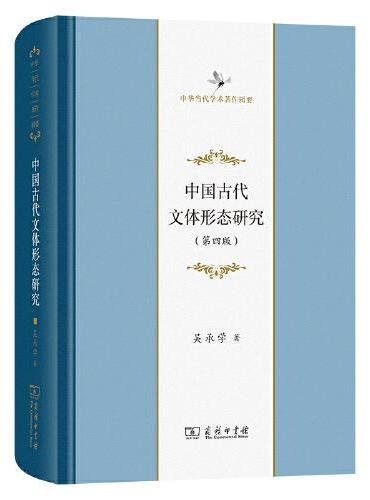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HK$
60.5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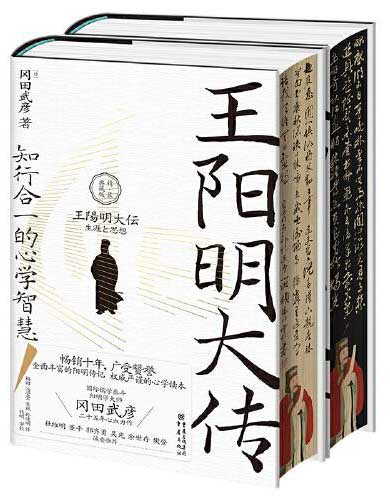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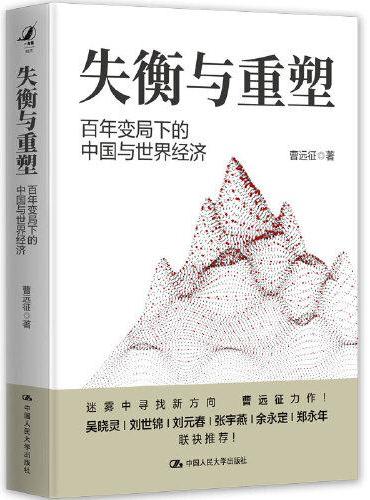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HK$
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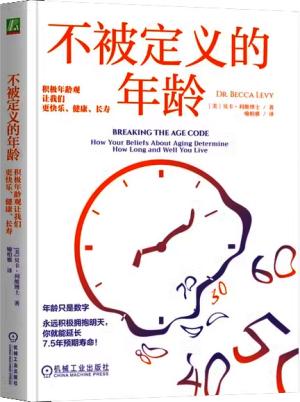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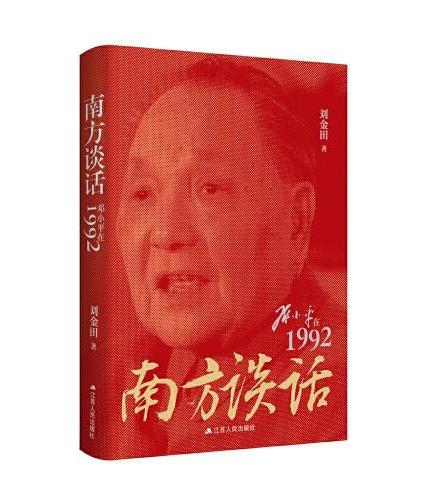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HK$
80.6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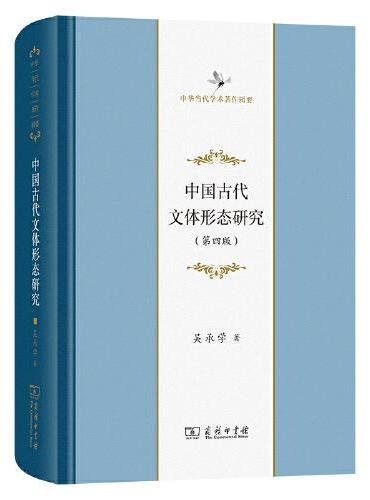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68.0
|
| 編輯推薦: |
★军旅作家刘跃清倾情力作
★霜冷长河,冰封不了军人的忠诚热血
★精彩呈现临汾旅的英勇顽强与不畏牺牲
|
| 內容簡介: |
|
上世纪90代中期,我参加“临汾旅”历史陈列馆整修,在收集整理旅史资料过程中,无意间走进军区副司令李长胜的精神情感世界,听他说起波澜壮阔的军旅人生:他的战友,一个叫李跟娣女红军战士背一口大铁锅参加长征,一直走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李长胜担任某团团长,团里有一位叫王黑塔的战士,一位真正战斗的英雄;解放战争时期,李长胜和长征途中的女战友刘小花产生深厚感情,由恋爱到结婚。为了胜利,李长胜树立起解放战士典型王祖强,但他的通信员黄二胖很不服气。因为一张手帕,老兵李如虎一定要纠正他的党龄问题。以几位鲜活的人物为线索精彩再现“临汾旅”铁血辉煌的征战历程。
|
| 關於作者: |
|
刘跃清,中国作协会员,曾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10月出生于湖南隆回,1990年3月入伍。现供职江苏省政协。出版中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多部,并多次获奖、转载。该书为“南京市栖霞区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
| 內容試閱:
|
黄昏,老鸹呱吵。开过饭了,一挨天黑队伍就要出发。王黑塔把盆呀铲呀刀呀刷洗收拾一番,把大黑锅扣在背架上固定好,掂了掂:“老崔,这锅还是你背。”崔麻子蹲在一旁吸喇叭烟。
“这儿有个砂眼,烧之前得糊一下,铲子不要碰这。”王黑塔指着锅底说。崔麻子呛得直咳。他抽的是榆树叶。
“王黑塔……”黄三胖帮他拎起背包,王黑塔接过,手搭在黄三胖肩上按了按,一扬手背包搭在肩上,钻进那群汗息浓重的队伍。
王黑塔回战斗班后,扫地、烧火、刷洗等活由黄三胖干。劈柴,崔麻子不让,说斧头不长眼。挑水,只能挑小半担。黄三胖就在这个时候听炊事班几个老兵说起王黑塔以前的事。团保卫股原来是叫王黑塔去劳改队的,营里、连队帮他说好话,才把他下到炊事班。
团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劳改队,有兵也有官,都是些犯了错误,或被怀疑为奸细。有的是违反群众纪律,有的是丢失或损坏武器,有的是“开小差”被抓了回来等。时间有几个月到一年半载不等。当然问题严重、证据确凿的直接被架了出去,用木棒敲了脑壳,这样节省子弹。劳改人员跟随队伍走,战前筑工事,战后抬伤员,冬天烧木炭,行军当骡马,反正苦活脏活首先想到他们。战时,保卫干部权力大着呢。他们背着盒子炮出现在哪儿,让人发憷。所以有道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找谈话。
王黑塔下炊事班前是一排三班长。他和连队干部说过,不当班长,就当机枪手。连长、指导员答应了。可是支委会一碰头,还是让他当班长。
王黑塔话不多,不会开导人,但他枪法好,能一枪打熄百米外罩在柳条筐里的烛光。他会使多种武器,打仗不慌,敌人冲到哪该开火了,到哪该转移阵地了,沉着冷静,兵们跟着他心里踏实。他也帮兵打洗脚水,用马尾帮挑脚板上的泡,睡放马桶的角落。他几乎不花钱,把偶尔分得的伙食尾子买纸烟大家抽,买花生大家吃;有兵落下,他帮拎武器、背包;有兵病了,他找崔麻子做鸡蛋面,然后是一句话,趁热吃。李长胜说:“别看王黑塔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但大家服他。”
打仗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这一刻不晓得下一刻的事。打赢了还好,有人帮起个堆,运气再好点,上面立块木牌牌,做个记号。打输了,撒腿跑都来不及,只能听天由命了。
王黑塔班上有个姓陈的老兵,河北人,当兵前在日本人开的煤矿里下窑,在不到一米高的窑道里拖着个筐子像狗一样爬,他们村里和他一起下窑的陆续死得就剩他一个了。八路打来,日本人跑了,他当了兵。几仗下来,陈老兵发牢骚:“当兵是死了没人埋,下煤窑是埋了还没死。”这话让李长胜听到了,冲他吼:“狗日的,你死了,如果我活着,一定埋你。”
“好!指导员,你说话可要算数。”
不久,陈老兵战死,和一个罗圈腿小鬼子扭在一起。他一只手抠住小鬼子的喉管,小鬼子缩着脖子,眼睛鼓得像螃蟹眼。小鬼子的手抓在他脸上,两颗眼珠连着血丝垂落在外,小鬼子的两个指头戳进他眼窝里……周围零乱的小草像浇了一层血浆。
陈老兵是李长胜亲自埋的,扳断小鬼子的手,才把它从陈老兵的脸上移开,把眼珠子塞回眼眶。李长胜抱起陈老兵,轻轻放进一个腐得快散架的碗柜里。掩埋组的人跑过来帮忙。“滚开,我自己来。”李长胜哭喊着骂道,“狗日的,高兴了吧,还睡碗柜呢。”
打仗,最考验人的是生死关。党员、骨干挤在一间草屋里,烟雾缭绕,商讨怎样巩固部队。有人说党员、骨干睡门口,每晚把全班的裤子集中起来当枕头;有人说在门、窗上拉绳子,绳子上挂铃铛,一头拴在骨干的手腕上;有人说一个看住一个,察言观色,快到谁老家了,就安排人跟着,拉屎都跟着……
王黑塔微闭着眼睛坐在门口,像口扣在地上的铸钟。
“王黑塔,你说说。”李长胜说。
“哦,好咧。”王黑塔扭头看着大家,“说啥?”
走呀走,每天走得嗓子冒烟,鼻孔扑灰。指挥所那帮人拧着眉头在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上一比划,兵们就甩开膀子迈开腿走,很多时候不晓得往哪走,有多远,有时候转了几天又回到老地方。
队伍快到河南地界了。李长胜让王黑塔看住刘猛子一点。他老家登记的是陕西潼关,但他说话很像河南某地人。
刘猛子打仗勇敢,大刀片子舞得像风车,曾接连砍削五个鬼子,刀刃卷口,血溅得迷住眼。最惊险的一次就是他哧溜冲到鬼子机枪工事下,趁鬼子射击间隙,一把拽出机枪,顺势塞进一个手榴弹。他握枪管的手吱吱冒青烟,几天都端不得碗。刘猛子最先是几个“南蛮子”叫的,说他们那不要命的叫猛子。
李长胜和刘猛子一起蹲茅坑时聊过,还把他列为党员发展对象。
刘猛子不肯,说他没觉悟。
李长胜说:“杀鬼子豁出命就是觉悟。”
“那王黑塔觉悟比我高,先发展他吧”。
“他是啥觉悟,你是啥觉悟?乱弹琴!”
从那后,每次开思想骨干会议就把刘猛子叫上。他也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党员。
刘猛子不但勇敢还一下子变得更勤劳。扫地,打水,铺床,手脚麻利,看看大家实在没什么要帮忙的,去帮别人捉虱子。
刘猛子开小差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他这是耍名堂,打算要走了,心里觉得对不住大家。他是典型的“战后怕”。打仗时杀红了眼,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怕,过后想起那血肉模糊挺得像河滩石头一样的尸体,就怕了。
刘猛子是和王黑塔一起站哨时跑的。那天,刘猛子本来是和一个新兵站岗的,指导员朝王黑塔撸了撸嘴说,新兵今天练刺杀,让他和刘猛子去。才上哨,刘猛子就折了段树枝说:“晚上着凉了,闹肚子。”他把“三八大盖”递给王黑塔,小跑到不远处的灌木丛后。王黑塔隐约能看到他蹲着的背影。一会儿,他去了一趟;一会儿,他又去了一趟,一趟比一趟远,一趟比一趟时间久。刘猛子苦着脸说:“用木棍刮屁股太遭罪了,尤其是拉肚子。最舒坦的是让狗舔,狗的舌头湿润柔软,舔得比困女人还舒服……”
“你就不怕它把你垂着的东西当猪大肠咬掉?”王黑塔说。
“还真有这事,我们村里一户人家喂了一条……”王黑塔转身朝一边走,刘猛子追着说。
后来,李长胜问起他们在一起的情形。王黑塔把刘猛子解手的事说了。
刘猛子最后一次去解手时,把枪连同子弹袋一起交给王黑塔,还拉开枪栓,里面有一颗黄澄澄的子弹已经上膛。
王黑塔一直等到日头偏西,接连站了三班岗。当他把刘猛子的枪和子弹交给连队时,李长胜很生气,说他报告迟了,让一个新兵去,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王黑塔班上的兵接二连三的开小差。连队开小差的几乎全集中在他班上。其中一个还带枪走的。
团保卫股盯上了他。连队、营里很恼火,把他的班长撸了,下到炊事班。
王黑塔回到一排三班,当机枪手。
夏天的夜晚,月色流淌。
崔麻子四仰八叉躺在麦秸堆上,呼噜打得像吹口哨,忽高忽低。黄三胖挨崔麻子躺着,在腿上挠了几下,翻身,一条脚搭在崔麻子身上。“崔麻子,老崔……”王黑塔兴冲冲跑进来。
“什么事?”崔麻子咕哝一声。
“帮我做份病号饭。”王黑塔晃了晃崔麻子。
“这么晚,谁病了?”崔麻子慢腾腾地爬起,揉着眼。
“顺拐回来了!”
“哦。”崔麻子醒了。炊事班全醒了。
晚点名时,顺拐开小差就悄悄传开了。李长胜阴着脸像谁欠了他八百担。顺拐是根据地入伍的,来的时候骑小毛驴,戴大红花,乡亲们敲着响器送,他未过门的媳妇还红着脸塞给他一个崭新的碗套和两双袜子。他队列训练老同手同脚,兵们叫他顺拐。他一到队伍上就想家,蒙在被子里哭,听到炮声就尿裤子,其实炸点离他还远呢。看到烈士的遗体抬下来,他就发呆。
炉火映着黄三胖已变得圆胖的脸。崔麻子揭开锅盖,搅动勺子,哧地一声,热气腾腾。王黑塔搓着蒲扇般的大手说:“卧个鸡蛋吧?”
“那是留给病号的,我婆娘来都没吃。”崔麻子嘴上说,还是从角落里摸索出一个鸡蛋。
崔麻子边敲鸡蛋边问:“他是怎么回来的?”
“走到半路上念大家的好,反悔了,就回来了。”
月色里,王黑塔颤悠悠地端着一大洋瓷碗鸡蛋面走出炊事班。崔麻子望着他的背影说:“他想把大家都拢住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