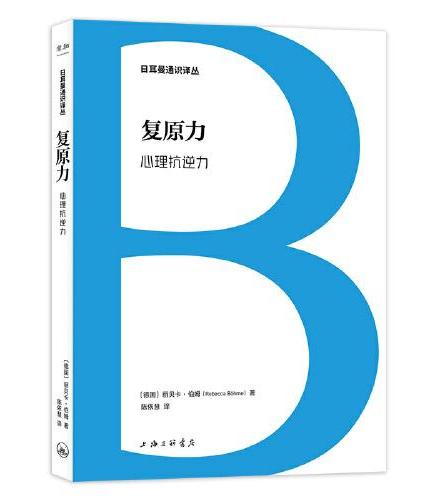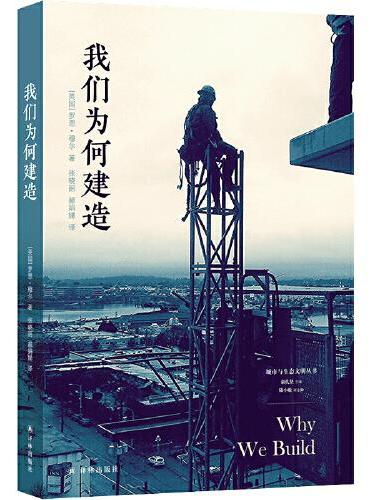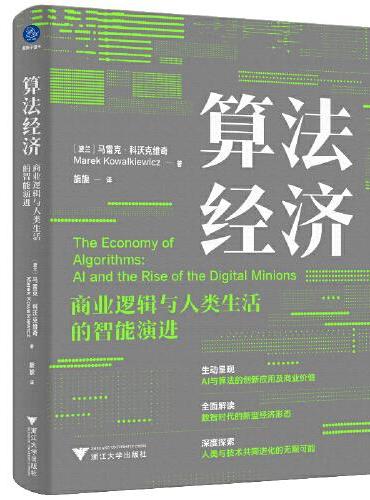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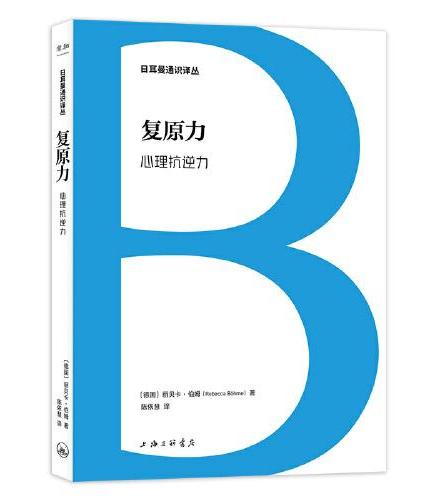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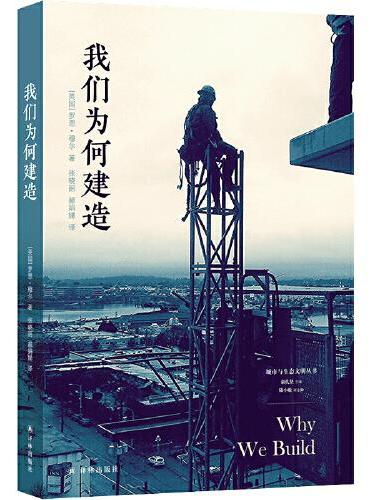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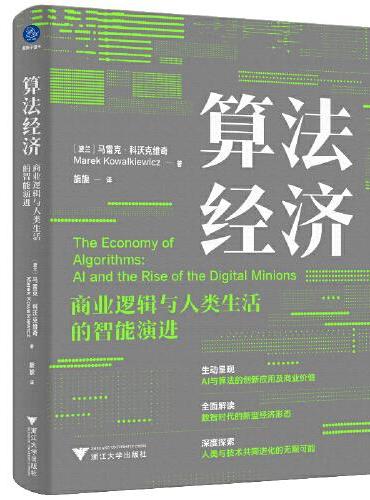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入作者近几年创作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小说形象具体地描写了中国低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所关心的生活主题以及社会风气,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关注小人物命运,充满大情怀,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多变,意味深长、充满哲理。
|
| 關於作者: |
|
胥和彬,笔名河冰,重庆市大足区人,中学高级教师,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大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短篇小说集《闯关》《守门人》,报告文学《母亲的足迹》等。主编《师生作品精选》《天下大足》《帝师刘天成》《大足先贤》《重汽之魂》等地方教材。
|
| 目錄:
|
目录
田野上的心愿 001
守门人 021
“嫂子” 046
黑背 068
方丽的焦虑 119
钓 148
荒月 173
|
| 內容試閱:
|
免费在线试读
田野上的心愿
这正是八月中旬四面热如砖窑的天气,老四上穿一件
背心,下穿一条短裤,坐在堂屋的饭桌上做试卷。虽手持
一把蒲扇摇动,但老四还是忍不住地叫热。试卷做着做着,
老四心里就发毛了:也不知道今年到底“狗火”运气旺不
旺啊?
老四把试卷一掀,撕下一白纸条儿,从中间裁断,一
片写“旺”,一片写“栽”,捏成团一抛,纸团落在了饭
桌上,老四闭了眼伸手摸了一个,拆开一看—旺。老
四一下高兴得跳了起来:“狗火旺喽!”
“四娃子!—快提点凉水来哟!我们口都渴得冒烟
喽!……”母亲在稻田里朝他尖声喊。
老四提着一把乌黑的瓦茶壶,头扣一顶汗渍斑斑的斗
笠,眯着眼走在热烘烘的、反射着太阳光的田埂上。在那
上面行走,仿佛踩在了烧红的铁板上,烙得脚板心像针刺
一样疼。
“这鬼天气,真的好热!”老四用手擦了一把脸,忍
不住地骂了一句,他看到田埂边上的黑蟋蟀被这一声惊得
直往稻林里跳。
但他马上又缩回了话头。因为父母还正在田里辛劳地
挞谷子,父亲抱病都仍在坚持,他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当农民的真苦啊!”老四想,“老师常说,白饭白饭,
从下种到吃上饭有一百次劳作的工序。要是我真的狗火旺,
考上了,我一定要更加勤奋学习,到时研制一种机器,只
需在家里的计算机上操作,稻子就能乖乖地粒粒归仓,那
该多好呀!”
想到此刻正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父母,老四的心突然
萌生了一种对不住他们的感觉。
去年为了老四和老三去复习,家里已经很缺钱了,母
亲把准备喂到过年的鸡和猪都提前拉去卖了,钱还是不够
数,又叫父亲出门去借。
两兄弟在屋里等呀等呀。
父亲终于回来了,跨上台阶,双手扶在大门旁的石柱上,
张着大嘴直喘气。看见父亲那苍白的面孔,那病恹恹的样子,
兄弟俩知道父亲的肺气肿是越来越严重了,内心又十分难
过起来……
两兄弟马上去扶他老人家到桌边坐下。
老四端来开水,怯生生地说:“爸,你上医院去看病
没有?”
父亲没缓过来气,只是难受地摇手。
一看屋里满目的破烂,老三愁了,这景象跟电影中那
些苦难人的家境一模一样。等了半天,父亲凄怆地说:“我
这病是没法医了。”说罢,便伏在桌上不动了。
这岂不是叫人等死吗?如果有什么不测该怎么办啊?
病和贫困将会早早地夺去父亲的生命啊!
老三、老四知道,父亲过去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
在生产队时,他是担挑推拉、抛粮下种的行家。土地承包后,
坡上的活儿便由父亲一人承担,他还要抽很多时间去帮人
做零工。虽然挣了些钱,但他的衣衫却仍是补丁摞补丁;
每月的旱烟,一直限在三块钱内,后来患了肺病仍无钱治。
因为钱全投进他们两个“祸害”读书的开销里去了。小学
六年,中学六年,兄弟俩又都复读了两年,一年两兄弟花
费数千元。对于一个十分偏僻的山乡农民家庭来说,钱太
稀罕了,这是天上不落,地下不生的东西。一次父亲帮人
去河包镇挑甘蔗,来回四十里路远,挑一百斤给四块钱。
那主人看着父亲没有吃午饭,另给了一块钱叫父亲去吃四
两面条。父亲舍不得,空着肚子挑着担便要上路。半路上,
父亲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最后晕倒在大路旁了。父亲为
的仅是省一块钱,一块钱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又值几何?
然而他老人家却……
父亲在桌上伏了半天,才平稳下来,将那左肩头上有
块大补丁的中山服的扣子解开,里面是件烂了领的白衬衣。
他把白衬衣扎在了裤腰里,再解了两颗衬衣的纽扣,一只
惨白的皮包骨头的手颤抖着伸进去摸了两把钱出来,放在
桌上,一把推给老三,一把推给老四,说:“这是两千,
你们一人一千。”
“找谁借的?”老三、老四惊奇地问。
“唉,找谁借呀?谁都不愿借这东西!”父亲说。
“那怎么来的?”
“全是贷款!”
……
“唉,不知三哥进城拿分数,怎么样了?”老四看着
眼前那铺满黄金一般沉甸甸地等着主人来收割的大片大片
的稻谷,心事重重地又叹了一口气。“好庄稼都是别人家
的……”老四的目光搜索到自己的田里时,目光停住了:
秧苗由于缺肥,跟人缺乏营养一样,长得是稀稀拉拉的。
大家都开始挞谷了,我们家的庄稼秧叶还没淹住水呀!
父母呢,却没在田地里。老四抬眼扫视时,只见母亲
坐在高粱地的田埂上,正朝他挥动着手中的破草帽呢。父
亲坐在母亲的身边,他们好像正在谈论着什么,神色苦闷。
老四走过去,脚上穿着一双用旧凉鞋剪成的拖鞋,发
出一阵阵啪嗒啪嗒的响声,在干燥的田埂上拖起一股股黄
黄的尘土。
“爸、妈,水来喽!你们快喝。我来帮你们割一阵
儿吧!”
“你割啥呀,快回去好好看自己的书。等会儿我回去
就把饭煮好。”
父母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上衣早已湿透,紧紧地贴
在背心上。他们的裤脚高高地卷起,裤管上溅满了星星点
点的泥巴。
母亲接过茶壶,一边举起茶壶倒在嘴里,一边问:“你
三哥回来没?”
问话时母亲的脸色很严肃,父亲却有点慌神,睁着带
血丝的眼睛盯着老四。
老四的心又无端地开始收缩了。他长到二十岁,早已
熟知妈的性情,知道她的内心是很着急的。母亲是一个特
别的女人,村里人都这么说。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县中
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学校三十周年校庆时,墙报上还有她
的名字和简历呢。据说,当时全县女生仅她一人上了县中
学,她还为解放军进镇子剿匪带过路,参加过土地改革运
动,做过县供销联社的总会计,她把数百条的《毛主席语
录》背得烂熟……母亲心里有一样东西,一种与世人不一
样的东西,这个家里的一切都靠这种东西支撑着,老四和
老三的命运也被这种东西支撑着,甚至支配着,丝毫不能
松懈。
“他还没回来呢。”
母亲不再说话,父亲却忍不住望天叹了一口气。母亲
看了父亲一眼,眼光如锥子一般。父亲立刻像犯了错误的
孩子,低下了头。
父亲老是这样,一向忍让母亲。他了解母亲,母亲是
个地道的火炮性格,心直口快,爱走极端,但又是个心地
十分善良的人。老四将目光从父母身上移开,扫向收割了
近一半的寂静无声的田野。正午的太阳正发出灼热的光芒,
威力无穷,不可仰视。劳作的农民都三三两两聚向近旁的
树荫处小憩,以迎接即将开始的又一轮极耗体力的劳作。
“老四,你回家去!你三哥兴许回来了。”老四被母
亲的话叫醒,本来热得发红的脸一下子更红了。老四有些
愧疚地望着父亲那布满皱纹的一脸病态的黑瘦面孔。
“我在家看书头都看昏了。你们好好歇歇,我来割一
会儿。”
“‘祸害’呀!你就保证这次能百分之百考上吗?要
是考不上,还得给我复习,直到考上为止!你想想,你们
都复习两年了,你的好些同学,你扳手指数一数,王立、
蔡文、张超他们,都是来过咱们家的,你的好朋友哪个还
没考上?我看只有你们这两个笨蛋还没考上。看你俩那‘行
李担’准备挑到猴年马月去!我不管,要是不给我考上的
话……哼!”
“是啊是啊,你们俩非给我考上不可!回屋念书去,
我跟你母亲割就行了。”
父亲从来都是这样,总帮衬着母亲说话。
老四往回走,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抬眼看去,哪家的
田间地头没有孩子在帮着干活呢?特别是在这赶时如救火
的收割季节。可偏偏他家,只有两个老人在地头里忙死忙
活的身影。孩子呢?一个到县上的学堂看高考分数去了,
一个则被关在家里念书—害怕考不上。考学是父母给他
们兄弟俩定下的硬性目标。
“老四,你考上了?”邻居的徐大哥路过,手执一根
吆鸭儿的长竹竿问道。
老四板着脸摇头,没说话。
“你们两兄弟,还是要到地里帮着干活呀!你父亲有
病,地又那么多,就靠两个老的在拼死拼活可不行啊。俗
话说,三岁牯牛十八汉,你们这个年龄不来帮着犁地,反
倒耍得像城市的公子哥儿了!”
老四急了起来,说:“他们不让我帮手呀!”
徐大哥叹了口气:“你娘那个性子呀,真是倔强!也
不晓得图个啥?明知那独木桥难过,她还偏让你们去挤。
乡下人本来就这个命,锄头落地才是庄稼呀!不是不支持
你们考这考那,只是我看了,拿那点国家工资还不如我卖
鸭蛋挣得多呢!”
老四低下头,心里又难受起来。在他们兄弟俩念书的
事情上,村里人有羡慕地说:“他们这样念下去,终会考
上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嘛。”也有说风凉话的:“骨头骨
节都没有生正,那考大学,能是随便谁都能考上的吗?想
得美呢!”徐大哥的两个儿子,都只念到小学毕业,家里
人就没让再念了,那两个儿子早就去广州打工挣现钱了。
对于这些议论,母亲一概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这是母
亲身上唯一与这偏僻山村人们格格不入的地方。
母亲是在一次进城办事时见到老四的同学王立的。那
时老四还有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在大街上闲逛,母亲看见
王立时眼睛一亮。王立西装革履,一副学者风范,他太像
他父亲了。在老四喊过“母亲”,另外几个同学依次喊过“阿
姨”之后,母亲指着王立,说:“这同学真俊!叫什么名字?”
王立礼貌地笑着,说:“阿姨,我叫王立。”
老三也站在一边,赶紧补充道:“妈,他就是我们校
长的儿子。”
母亲一愣:“王校长的儿子?”
王立吃惊地看着她:“您认识我父亲?”
母亲笑了:“王校长谁不晓得?他是我们县唯一的南
下干部,大家都知道他。”
以后,母亲总是夸奖王立长得好,懂礼貌,不愧出生
于干部之家。这些话老三、老四却不是很爱听,因为觉得
母亲处处赞赏王立的同时也是在贬低他俩,他俩内心受到
了极大的伤害。
老三、老四知道母亲认识王校长,因为第一年为复习
的事,她曾经到县中学去找过王校长。当时老三、老四为
母亲的行为感到吃惊:他们觉得母亲是一个山乡的农家妇
女,人家是县中学的校长,论级别是县团级,人家会理吗?
可谁知后来,学校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后,将学校的“困难
基金”给了老三、老四,这帮他们家解决了兄弟俩一部分
的上学学费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