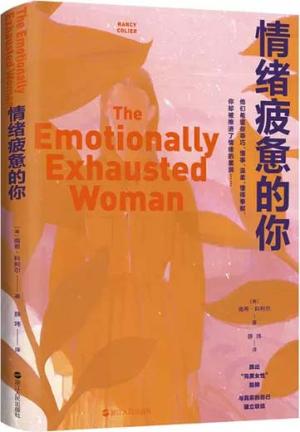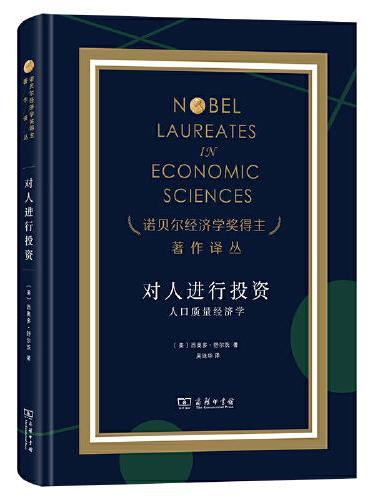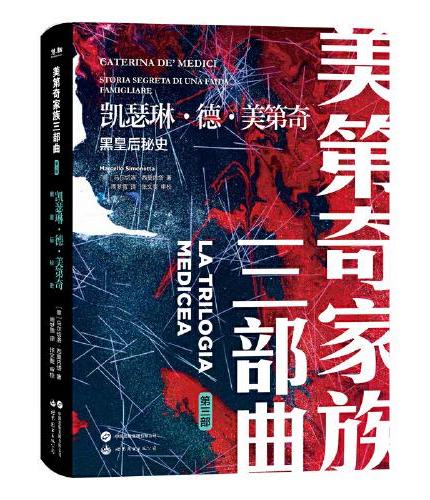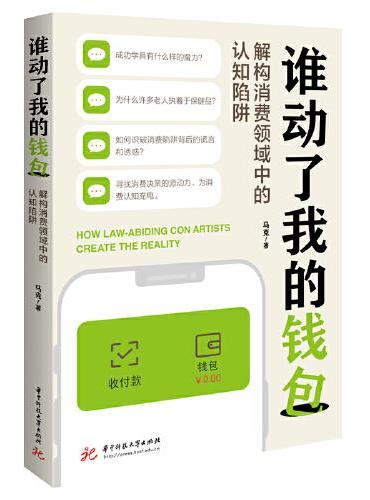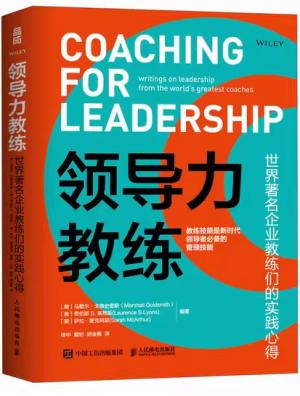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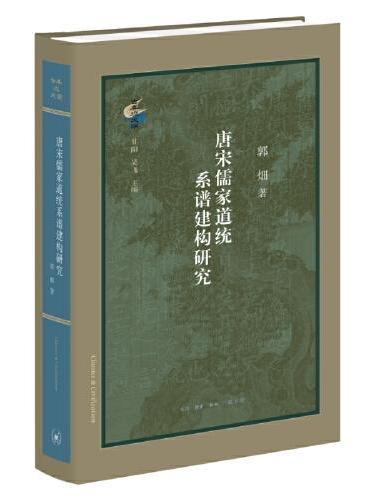
《
古典与文明·唐宋儒家道统系谱建构研究
》
售價:HK$
110.4
![唤醒老虎:启动自我疗愈本能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28/9787111746676.jpg)
《
唤醒老虎:启动自我疗愈本能 [美]彼得·莱文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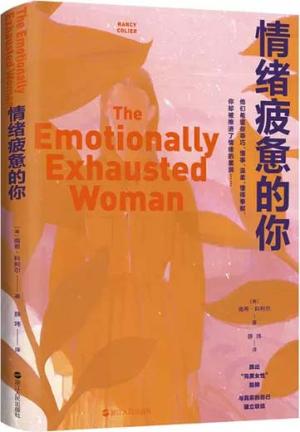
《
心悦读丛书·情绪疲惫的你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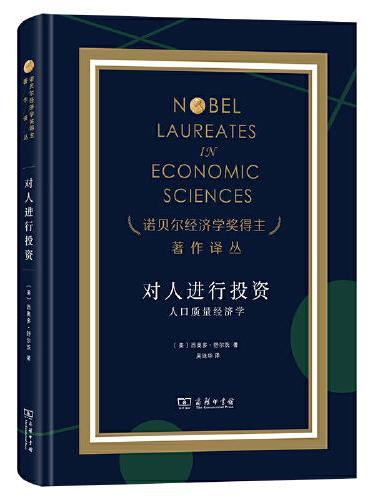
《
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诺奖)
》
售價:HK$
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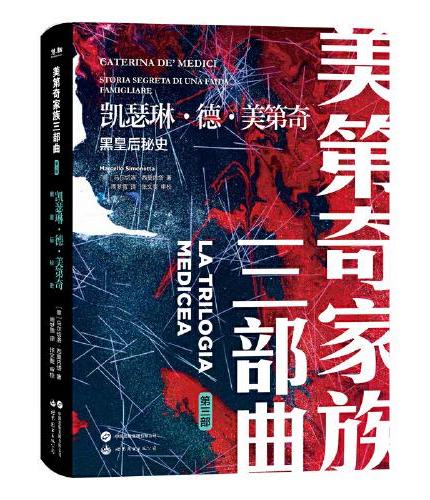
《
美第奇家族三部曲3-凯瑟琳·德·美第奇:黑皇后秘史
》
售價:HK$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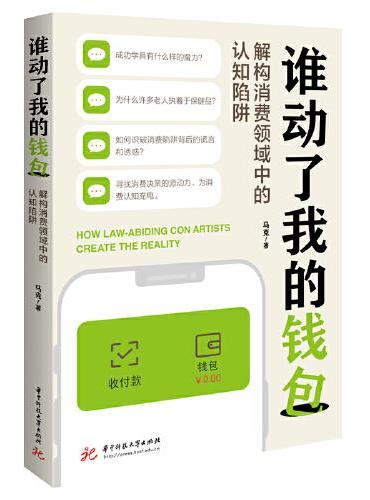
《
谁动了我的钱包——解构消费领域中的认知陷阱
》
售價:HK$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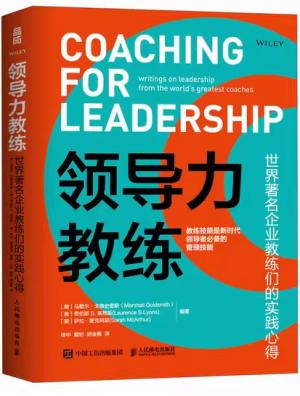
《
领导力教练 世界著名企业教练们的实践心得
》
售價:HK$
80.3

《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2版)(守望者)
》
售價:HK$
113.6
|
| 編輯推薦: |
这是一个天真锋利的女人在世俗中成全自己的故事!步步为营,寸寸惊心!
万历十五年女性传奇,且看明朝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
张艺谋 苏童 毕飞宇 联袂推荐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天真锋利的女人在世俗中成全自己的故事。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商户的女儿令秧十六岁嫁到唐家,不久即意外丧夫。唐氏一族二十九年没出过贞节烈妇,期盼着令秧殉夫,为族人换取一道贞节牌坊,表面上为着光耀门楣,暗地里则觊觎朝廷旌表烈妇的种种好处。他们用尽手段诱导令秧走上死路。为了生存,少女令秧与现实同谋,踏上了艰难而凶险的烈妇之路……《南方有令秧》为百万级畅销青年作家笛安长篇转型之作,她在令秧的身上倾注了自己的体温和当下的悲喜。
小说曾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描绘了万历年间深宅庭院的日常生活,编织密布着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史料信息,全景式地展现明末历史社会风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书写女性在社会逆境中的搏力与挣扎。
|
| 關於作者: |
笛安
作家,代表作:“龙城三部曲”系列小说(《西决》《东霓》《南音》),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景恒街》。其中《南方有令秧》获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景恒街》获得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曾主编杂志《文艺风赏》。
|
| 目錄:
|
章 填房夫人
第二章 元宵花灯
第三章 节妇名册
第四章 旷野戏台
第五章 唐家端午
第六章 百孀宴
第七章 账房先生
第八章 新姑爷
第九章 残臂
第十章 《绣玉阁》
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
第十二章 盛典哀荣
后记 令秧和我
|
| 內容試閱:
|
后记
令秧和我
我知道这个问题必然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一个明朝节妇的故事?我总不能回答说:“我也忘记了。”哪怕事实的确如此。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无比热衷于写后记,甚至自得其乐地认为,我的后记写得怕是比长篇正文还要好。因为那时候生怕别人看不出我想要说什么,生怕被曲解,所以喋喋不休地在后记里跳出来阐释一番,说到底,彼时的创作模式仍然低级,还仅仅局限于“表达”。当我意识到其实写小说有远比“表达”更重要得多的任务的时候,脑子里通常一片空白,干净程度堪比眼前那个命名为“后记”的雪白文档。
任何一个读者都有误读或是曲解一部作品的权力—甚至,即使是作者本人初的思想,也未必能够准确解释它—因为作品里的那个世界一旦确立,便拥有了独立意志一般,遵循着一个不完全契合作者初衷的逻辑,自行运转。所以,我只能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失意男人塑造了一个节妇的故事,这是一个天真锋利的女人在俗世中通过玩弄制度成全了自己的故事,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像战友一般,在漫长岁月荒谬人生中达成了宿命般的友情。所以在写至小说结尾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但我又觉得,这种难过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任何人知道,于是我就写:“他一直怀念她。”
还是要承认,我很中意这个结尾。
没有谁真的见过明朝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建筑在真实记载上的想象,完成一个亦虚亦实的世界。其实我终究也没能做到写一个看起来很“明朝”的女主角,因为终还是在她的骨头里注入了一种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不过写到后我自己也相信了,也许在明朝存在过这样的女人,只不过她从来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然后在时光里留下痕迹。我尽了努力,想要和这个四百年前的女孩或者女人成为朋友,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我发现当我很投入地站在男主角的立场的时候,就能自如并且以一个非常恰当的角度打量并且欣赏令秧—所以,就别再问我令秧是不是我了吧,说不定谢舜珲才更像我。这个故事里,不能说没有爱情,但是谢先生和令秧之间,那种惺惺相惜,那种荣辱与共,那种互相理解—在我眼里,其实这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理想的模式:不必缠绵,相互尊重,一起战斗。
当我开始书写他们之间这样珍贵的情感,我渐渐地忘记了我是在写历史。在那个由我一手虚构出来的四百年的世界里,我的体温,我的悲喜终于找到了存放的地方。我曾经跟一个总问我在写什么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女明星不是艺人,是个节妇。我的朋友显然很开心,微信上传过来一串“哈哈哈哈”,其实我没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还好如今我周围已经没有了问我“这篇小说想要表达什么”的朋友了—曾经有不少,现在,会问这类问题的已渐渐减少了联络—因为我已经到了一个不需要太多朋友的年纪了,这么说可能有点悲哀。
不过若是你们一定要问我想表达什么,我还是要回答的。因为你们是渴望通过我写的故事在另一个时空里寻求朋友的人,我一向都是珍惜自己“灵媒”的身份的。这故事里有一个女人,她热情,她有生命力,她有原始的坚韧—其实我常常塑造这样的女主角,不过这一次,我加重了一些与“残酷”难解难分的天真。这其实也是一种天分,而这故事里的那个男人,便是一个发现这天分的人。恰好这男人冰雪聪明,恰好他落寞失意,恰好他善于嘲讽,于是,他便用这遗世独立的聪明,成全了这女人的天分。他们需要看透制度,利用制度,然后玩弄制度—只是,笼罩他们的,自然还有命运。
这便是我在这个故事里初想要说的话。只不过写到后,想说的话渐渐模糊,原先为了架构故事的那些清晰且有条理的想法,也逐渐混沌于一片苍凉之中。也许这就是我一直痴迷写作的原因,总在某个时刻,明明屋子里只有我,我的电脑,我却是感觉到像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山顶,刚刚目送一群远去的神话人物,我知道他们把整个世界留给了我,还留给我一个有生之年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万籁俱寂,我像个狂喜的孩子那样,静静听着自己的呼吸。
这是我次写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感觉困难的部分并不在于搜集资料,那一部分的工作虽然繁杂琐碎,过程里也总会有些充实的感觉。真正艰难的在于运用所有这些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要在跟我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逻辑里虚构出人物们的困境……可是当这样的想象一旦开始并且能够逐步顺畅地滑行,个中美妙,让我恍惚间回到了十年前次写长篇小说的岁月,似乎写完处女作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再体会过这种由写作带来的畅快的喜悦。这种喜悦来得远远不如当年那么简单直接,因为下笔之前有如此多的功课要做;可是一旦感受到了那种喜悦,随之而来的满心灿烂的感觉跟十年前别无二致。或许,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指的便是这个。
现在我写完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力量,我感谢令秧和谢先生,他们二人让我相信了,我依然可以笃定地写下去,走到一个风景更好也更无人打扰的地方。
再偏爱的小说也终须一别,但是你们又将与她相逢。我的寂寞无足轻重,只盼望你们善待令秧。
谢谢。
可惜她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参加,她是那个仪式上重要的一件瓷器,被搀进来带出去,只看得见眼前那一片红色。所有的鼓乐,嘈杂,贺喜,嬉笑……都似乎与她无关,估计满月酒上的婴儿的处境跟她也差不多。她用力地盯着身上那件真红对襟大衫的衣袖,仔细研究着金线滚出来的边。民间女子,这辈子也只得这一次穿大红色的机会。不过也不可惜—她倒是真不怎么喜欢这颜色。她轻轻地捏紧了凤冠上垂下来的珠子,到后来所有的珠子都温热了,沾上了她的体温。她希望这盖头永远别掀开,她根本不想看见盖头外面发生的所有事。前一天,嫂子和海棠姐姐陪着她度过了绣楼上的后一个夜晚,她们跟令秧嘱咐的那些话她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嫂子说,用不着怕,这家老爷应该是个很好的人—知书达理,也有情有义,婚礼推至三年后,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才算对得住亡妻—这么一个人是不会欺负令秧的。可是令秧没办法跟嫂子讲清楚,她的确是怕,可是她的怕还远远没到老爷是不是个好人那一层上。她知道自己是后悔了,后悔没有在后的时刻告诉海棠姐姐,令秧是多么羡慕她。她想起九岁那年,舅舅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一起去逛正月十五的庙会,她站在吹糖人的摊子前面看得入了迷,一转脸,却发现海棠姐姐和表哥都不见了。他们明明知道长大了以后就可以做夫妻,为什么要现在就那么急着把令秧丢下呢?昨晚她居然没有做梦,她以为娘会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来梦里看她一眼,她以为她必然会在绣楼的后一个夜里梦见些什么不寻常的东西—现在才知道,原来的,长的梦就是此刻,就是眼下这张红盖头,她完全看不见,近在咫尺的那对喜烛已经烧残了,烛泪凝在自己脚下,堆成狰狞的花。
盖头掀起的那一瞬间,她闭上了眼睛。一句不可思议的话轻轻地,怯懦地冲口而出,听见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她被吓到了,可是已经来不及。她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自己抬起脸,对着伫立在她眼前的那个男人说:“海棠姐姐和表哥在哪儿,我得去找他们。”
那个一脸苍老和倦怠的男人犹疑地看着她,突然笑了笑,问她:“你该不会是睡着了吧?”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清瘦的脸,微笑的时候搅出来的细纹让他显得更端正。他好像和爹一样,不知道该跟令秧说什么。他似乎只能耐心地说:“你今天累了。”
“你是老爷?”令秧模糊地勇敢了起来,她知道自己可以迎着他的眼睛看过去。
他反问:“不然又能是谁呢?”他把手轻轻地搭在了她的手背上,她有点打战,不过没有缩回去。
一直到死,他都记得,洞房花烛夜,所有的灯火都熄掉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娘宽衣解带,他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夜晚做什么,他不想这么快地为难这孩子。黑暗中,他听到她在身边小心翼翼地问他:“老爷能给我讲讲,京城是什么样子么?”
唐简淡淡地笑笑,像是在叹息:“上京城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早就忘了。”
“老爷真的看见过皇上长什么样?”他不知道,令秧暗暗地在被子底下拧了一把自己的胳膊,才被逼迫说出这句话来。她听见他说“忘了”,她以为他不愿意和她多说话,但是她还是想努力再试一次,这是有生以来回,令秧想跟身边的人要求些什么东西,想跟什么人真心地示好—尽管她依然不敢贴近他的身体。
“看见过。”唐简伸展了一只手臂,想要把她圈进来—可是她完全不明白男人的胳膊为何突然间悬在了她的头顶。她的身体变得更加僵硬,直往回缩,唐简心里兀自尴尬了一会儿,还是把手臂收回去,心里微微地一颤—你可以抱怨一个女人不解风情,但是不能这样埋怨一个孩子。所以他说:“不过没看得太清楚,谁能抬着头看圣上呢?”
“你家里人叫你令秧?”她听见男人问她。她忘记了他们身处一片漆黑之中。唐简听见她的发丝在枕上轻微地磨出一丝些微的,窸窸窣窣的声响,知道她是在点头。“睡吧。”他在她的被面上拍了拍,“天一亮,还得去拜见娘。”
“老爷?”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陌生。
“嗯?”回答过她之后,他听见她轻轻地朝着他挪动了一下身体,然后她的脸颊贴在了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臂上。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他是夫君;可是她还是心惊肉跳,这毕竟是她有生以来做的的错事。男人的呼吸渐渐均匀和悠长,睡着了吧,这让令秧如释重负。她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胳膊下面,犹豫了片刻,另一只手终于配合了过来,抱住了那只胳膊。她不知道她的姿势就像是把身体拉满了弓,尽力地去够一样遥远的东西。因为这个简陋的拥抱,她的额头和一部分的面颊就贴在了他的手臂上—自然,还隔着那层鼠灰色麻纱的中衣衣袖。她屏息,闭上眼睛。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就在他睡意蒙眬之时,依然会隔着那床缎面的被子,轻轻拍拍她—若不是他这个举动在先,令秧无论如何也不敢这样大胆。她希望自己快点睡着,仿佛睡着了,这一层肌肤之亲就暂时被她丢开,不再恐惧,可是能融进睡梦里,更加坐实了。嫂子告诉过她,洞房应该是什么样的,她知道好像不该是现在这样—可是,也好。
她是被天井或是火巷里传来的杂乱脚步声惊醒的,一瞬间不知道身在何处。夜色已经没那么厚重得不可商量,至少她仰着头看得出帐子顶上隐约的轮廓。有人叩着他们的房门,然后推门进来了。唐简欠起了身,朝着帐外道:“是不是老夫人又不好了?”那个声音答:“回老爷的话,老夫人是又魇住了。喘不上气来,正打发人去叫大夫。老爷要不要过来瞧瞧。”她怀里的那条胳膊抽离出去的时候,她藏在被褥之间,紧闭着眼睛,她听见唐简说:“不必叫醒夫人,我先去看看再说。”—整间屋子沉寂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原来“夫人”指的就是她。她犹疑地坐起来,帐子留出一道缝隙,男人起来匆忙披衣服的时候,点上的灯未来得及吹灭。帐子外面,潦草灯光下,这房间的样貌也看不出个究竟。“夫人,”那是一个听起来甜美的年轻的女孩子的声音,“才四更天,别忙着起来。这个时候夜露是重的,仔细受了寒。”一个穿靛蓝色襦衫,系着水红色布裙的丫鬟垂手站在门旁边,朝着她探脑袋,“我叫云巧,以后专门服侍夫人—老爷到老夫人房里去跟大夫说话,我琢磨着,大喜的日子,夫人是头一天过来,说不定睡得轻,还真让我猜着了。夫人要喝茶么?”她怔怔地看着口齿伶俐的云巧,只是用力摇摇头,随后就什么话也没了—云巧走过来拨了拨灯芯:“夫人还是再睡会儿吧,还早得很,我就住在楼下,夫人有事喊我就好。”—她实在不好意思开口问,这丫鬟叫云什么,她没有记住这个名字—若真有事情,如何喊她。但是一句话不说也太不像话了,于是她只好问:“老夫人生的是什么病?”
云巧蜻蜓点水地笑笑—她长得不算好看,可是微笑起来的时候,眉眼间有种灵动藏着:“我只知道老夫人身子的确不好—半夜三更把大夫找来是家常便饭,好像好几个大夫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平日里也几乎不出屋子—别的就不大清楚了。”
事隔多年,她回想起那个夜晚,头一件记得的事情,便是自己的天真—伶俐如云巧,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比云巧还小几岁的令秧,就不假思索地信了。终于再一次听见关门的声响,是唐简回来了。他重新躺回她身边的时候,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欢喜。这点欢喜让她讲话的语气在转眼间就变得像个妇人,有种沉静像夜露一样滴落在她的喉咙里:“老夫人—是什么病?”唐简回答得异常轻松:“疯病。好多年了。”“老爷的意思是—老夫人是疯子么?”她在心里暗暗气恼着自己为何总是这么没有章法,唐简却还是那副不动声色的神情:“自从我父亲过世以后,她就开始病了,一开始还是清醒的时候多些,这一两年,清楚的时候就越来越少,特别是晚上,总不大安生。不过她是不会伤人的。多胡言乱语地说些疯话而已。不过还是得有人看着她,不然……”她静默着,等着他继续描述老夫人的病情—可是他却问她:“你怕了吗?”寂静煎熬着,唐简似乎有无穷尽的耐心来等待她的沉默结束,她却如临大敌。她知道自己该说“不怕”,该说她日后也会尽心侍奉神志混乱的老夫人,还该说这些本来就是她分内的事情—但是她却隐约觉得,他未必高兴听到这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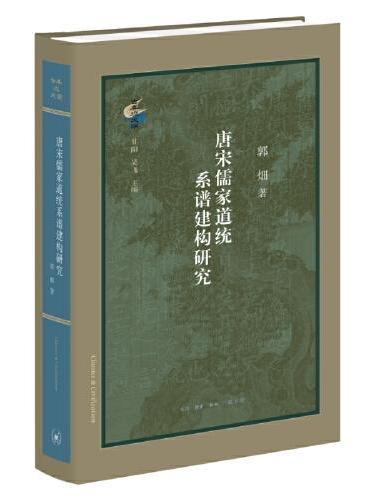
![唤醒老虎:启动自我疗愈本能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28/97871117466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