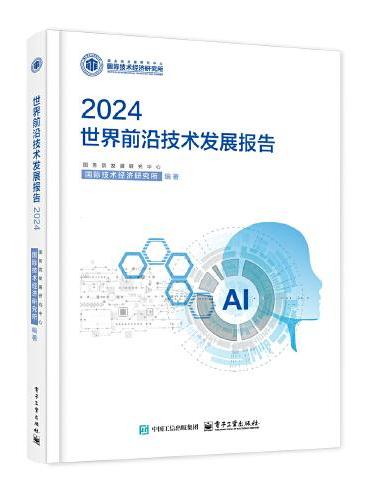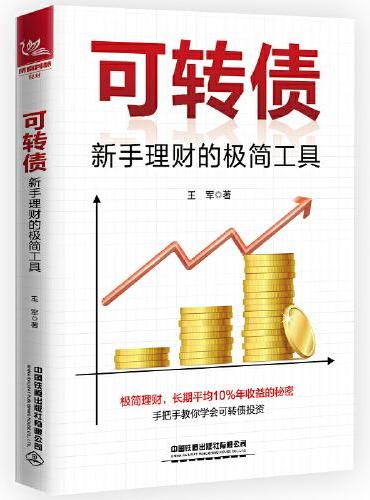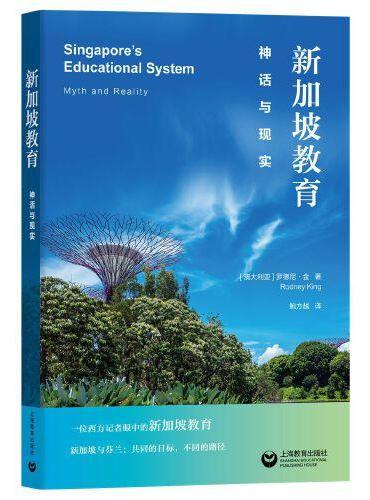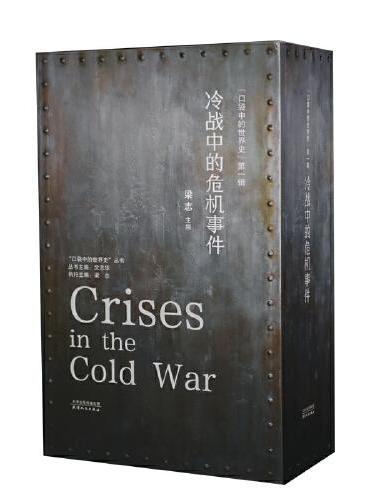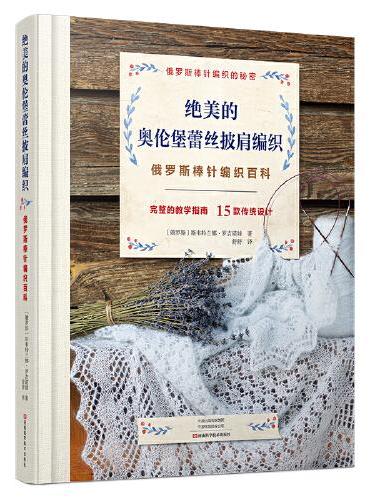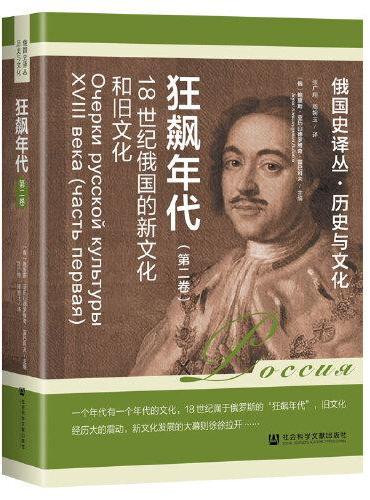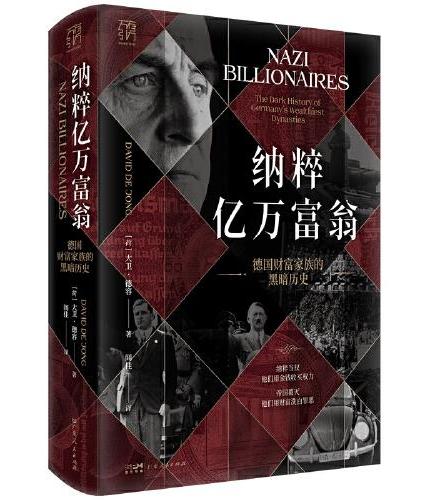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镜中的星期天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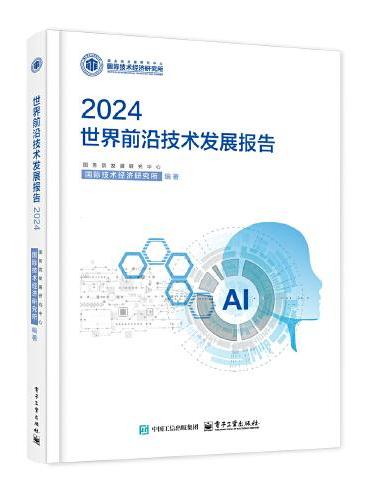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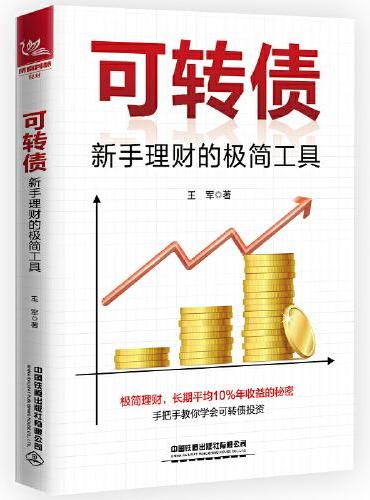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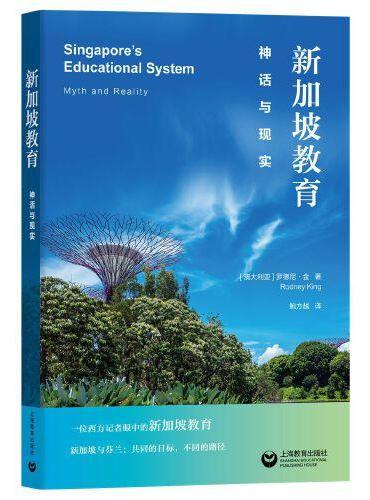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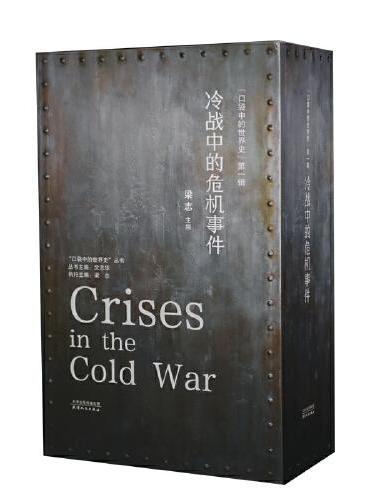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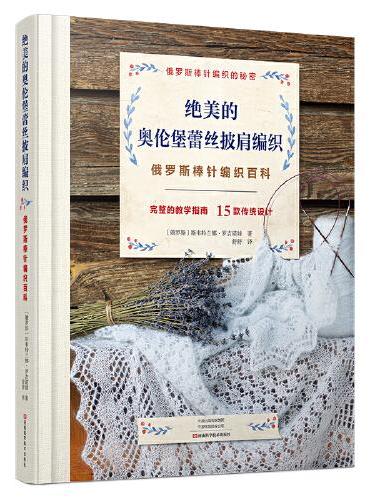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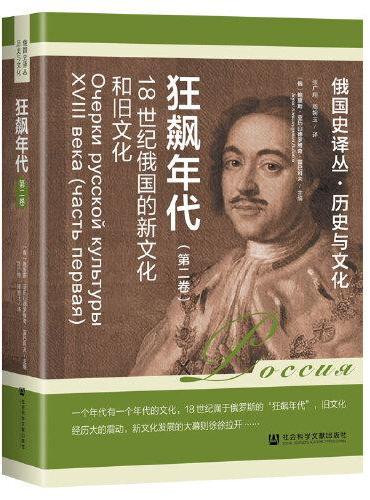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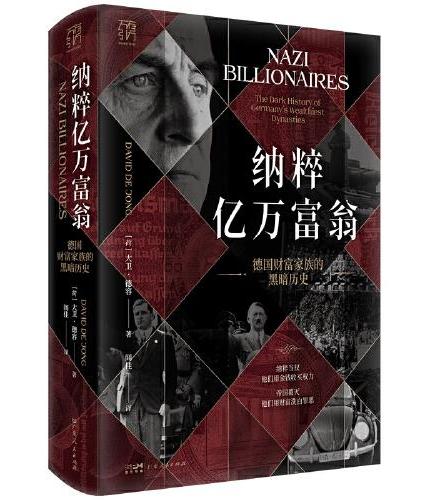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
背后是中国:贯通天文地理,爬梳诗史旧籍,揭示牛郎织女故事及七夕节俗的背后,中华民族万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留下的文明记忆。节庆的中国:将史书笔记、诗文词赋等作品中的吉光片羽,联缀成历代七夕风俗变迁的长卷,勾画出这一传统节庆的昔日繁华。世界在中国:对摩睺罗的身世追寻,揭开了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风情,凝固为中华节庆的祥瑞之物,流风遗韵至今犹存中国南北。
|
| 內容簡介: |
|
七月七是传统的中国节日,哀艳动人的牛郎织女故事千古传诵。而在故事背后,实则是远古闲人观象授时、男耕女织的传统,乞巧、观星等节俗无不与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洞悉与顺应息息相关。本书从牛女故事和七夕节的起源谈起,介绍了七夕的确立与历代七夕的主要节俗。作者以相当笔墨,对宋代七夕风俗及其异域风情和异域渊源进行了描述和探究,更关注到东南沿海的拜魁星风俗,钩沉出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透过民俗学的考察,折射了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
|
| 關於作者: |
|
刘宗迪,出生于1963年,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文化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研究,尤其致力于以比较神话学、口头诗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早期文献,重建上古宗教、知识和历史。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主要著作有《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版)、《古典的草根》《众神的山川:山海经》等。
|
| 目錄:
|
楔 子
第一章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牛郎织女故事以及七夕的起源
第二章 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
——七夕节的确立与七夕乞巧风俗
第三章 古道犹西风,争说泥孩儿
——宋代七夕风俗的异域渊源
第四章 西北望天狼,东海拜魁星
——东南沿海七夕拜魁星风俗与西域
尾 章 渐行渐远云间歌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七夕作为乞巧节,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乞巧的主角是女子,所乞之巧是女红之巧,乞巧节的主角从来就是女性,七夕之神织女其实就是纺织之神。在一些桑蚕纺织业发达的地方,会建有织女庙,庙中供奉织女神,当地的织妇会到织女庙上香、祈愿,七月七日举行织女庙会,如山东沂源县有牛郎庙和织女洞、苏州太仓市有黄姑庙或织女庙。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纺织业,是七夕节和乞巧风俗赖以产生和延续的土壤。近世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布”的入侵和现代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乡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迅速瓦解,“桑柘满阡陌,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缫丝忙”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女性不再专务饲蚕缫织之业,女红针黹之巧也不再是女子最重要的自我期许,以女子乞巧为主要关目的七夕风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因为无所附丽而趋于零落了。
当然,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多样,古语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七夕节虽在整体上没落了,却在某些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还过得红红火火,比如广州的“摆七娘”、潮汕地区的“出花园”、浙江温岭市的“小人节”、台湾嘉义县的“游魁星”、甘肃西和县和礼县的“迎巧娘”,等等。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许多地方过去鲜为外人知晓的七夕风俗被重新“发现”。
这些陆续“发现”的地方七夕风俗,大多已经被命名为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原汁原味的中国乡土传统而大加弘扬。其实,这些地方的七夕风俗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异域影响的印痕。广府的摆七娘和闽台的拜魁星风俗,源于宋代,融合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波斯文化,这一点已见上文,无需赘述。浙江温岭地区的“小人节”,专为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少女举行,当地人在七夕这天供设用竹篾、彩纸扎制的彩亭、彩轿,点缀以各种纸扎的戏曲人物,堪与广州的“摆七娘”相媲美。潮汕的“出花园”仪式,则是为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举行,七夕之日,孩子们要用十二种花瓣泡成的香汤沐浴,穿新衣,踏木屐,祭拜小孩子的保护神“公婆母”。这两个地方的七夕风俗,主角都是少男少女,而非仅为女子,主要活动是成人礼,而不是乞巧。
…………
七夕乞巧节,滥觞于上古,确立于汉末,酝酿于魏晋,定型于盛唐,到了宋代,来自遥远波斯的异域之风,如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奏,使其从原来的清扬哀婉的清商曲,一变而为急管繁弦的胡旋舞,成为中国七夕节历史上最为华彩的一章。宋代之后,随着外来因素逐渐融于本土传统,摩睺罗、种生、谷板等新异之物,或者脱胎换骨,成为七夕传统的一部分,为华夏七夕风俗增添了一抹异彩,或者逐渐消失,泯灭于无形,七夕风俗重新由绚烂至极渐归于平淡。历元、明、清直到如今,宋代的七夕狂欢风俗,除了在极个别的地方还遗风犹存之外,那种罗绮满街、举国若狂的盛况,早已风流云散,元、明、清三代的七夕风俗,大致又恢复了中国传统七夕的婉约基调,不过是秋夕月下,小儿女们穿针引线,拜星乞巧,葡萄架下听私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现如今,尽管牵牛织女会天河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在人间流传,尽管每年七夕人们仍会仰望星空、穿针乞巧,尽管天上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依然在水一方、脉脉相望,但是,无论如何,宋代七夕那般急管繁弦的华彩乐章,早已成为绝响,再也不会时光重现。
近年来,鉴于喜欢赶时髦的青年人对西方情人节的热衷,又因为七夕节的背后原本就有牵牛织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有些忧国忧民之士希望重新复活七夕节,并将之重新界定为“中国的情人节”,借以复兴传统,抗衡西方文化的侵蚀,久经冷落的七夕节似乎又时来运转,迎来了复兴的曙光。实际上,把七夕节重新定义为“情人节”,纯粹是一厢情愿。一个节日的实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故事,而是取决于它的风俗。历史上的七夕节,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风流韵事,尽管历代的文人词客写下了无数情思绵绵的七夕诗、七夕词,民间的七夕,却从来就没有男女交往、恋爱求偶的风俗。七夕节的主题是乞巧,七夕节的主角是女子和儿童,而与两性交往无关。其实,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七夕,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拉开了秋天的序幕,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袅袅秋风乍起,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
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春社、清明、上巳等在内的一系列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时下国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初衷是为了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不过,即使七夕节果真借着“情人节”的摩登招牌梅开二度,那也是一个当代的发明,旧瓶子里装新酒,其底蕴不再是盈盈一水、白首相守的古典爱情,而是另一个需要重新从头说起的欲望都市故事了。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曾经的七夕节,已经成了一曲渐行渐远的骊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