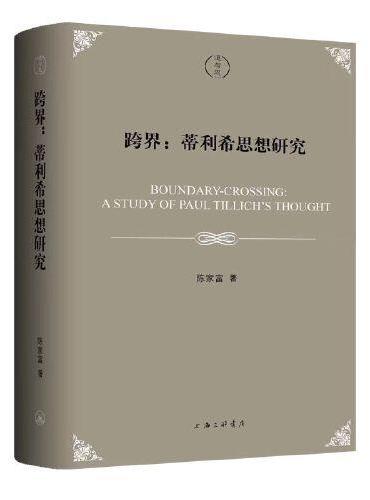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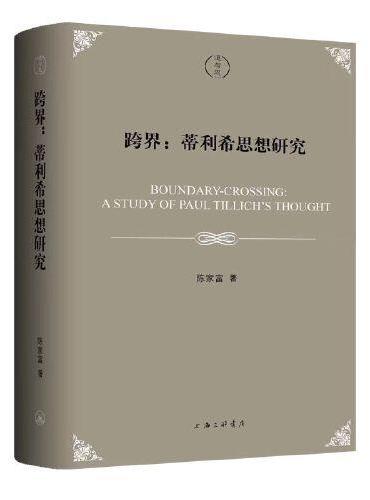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2.0

《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
》
售價:HK$
201.6

《
养育男孩: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
小原流花道技法教程
》
售價:HK$
109.8

《
少女映像室 唯美人像摄影从入门到实战
》
售價:HK$
110.9
|
| 編輯推薦: |
*《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评价陈建功“刻画人物的艺术雕刀,常能有力地突入性格的深处,开掘出性格的、社会的、人生的底蕴。他的叙事手腕,融合了古典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的优秀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格式的短篇小说的意识经验,显示了高强的艺术控驭力。他的文学语言,在老舍京味语言的基础上,博采新时代、新时期北京民众的口语,熔铸成既有旧京韵味又有城市新风的现代京白,很富有艺术表现力。”
*当代京味小说领军人物的代表作
*获国际大奖电影《找乐》的小说原著
|
| 內容簡介: |
本书精选了京味作家陈建功的4部精品中篇小说,《鬈毛》《前科》《找乐》《耍叉》。其中《鬈毛》获《十月》文学奖,根据中篇小说《找乐》改编的同名电影获1993年柏林电影节青年影评大奖、东京电影节金奖、西班牙圣蒂安塞巴电影节奖等。
陈建功描写生活以北京为多,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文风幽默风趣,他的文学语言,在老舍京味语言的基础上,博采新时代、新时期北京民众的口语,熔铸成既有旧京韵味又有城市新风的现代京白,很富有艺术表现力。本集涵盖了作者多年创作的经典篇什,是解读和研究陈建功必须阅读的代表作品。
|
| 關於作者: |
陈建功 1949年11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后移居北京。曾在矿山做工十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后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曾为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出版社社长,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作品主要在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本领域。
出版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丹凤眼》《找乐》《鬈毛》,散文集《我和父亲之间》《嬉笑歌哭》《从实招来》《率性蓬蒿》《岁月拾荒》等。曾多次获得全国性重要小说奖,作品被译为英、法、日、越、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
| 目錄:
|
鬈 毛 1
找 乐 91
耍 叉 134
前 科 204
|
| 內容試閱:
|
鬈 毛
一
这个小妞儿骑着一辆橘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飞快地从我的右边超过去,连个手势也不打,猛地向左一拐,后轱辘一下子横在我的车前。我可没料到这一手,慌忙把车把往左一闪,“咣——”前轱辘狠狠地撞在马路当中的隔离墩儿上。这一下撞得够狠,我都觉出后轱辘掀了一下,大概跟他娘的马失前蹄的感觉差不多。幸亏我还算利索,稳稳站到了地上。不过,车子还是歪倒在两腿中间了。放在车把前杂物筐里的那个微型放音机,被甩到了几米以外。
我拎起了车子,立体声耳机的引线和插头在下巴底下甩打着。那小妞儿回头看了一眼,停车下来了。她挺漂亮,说不定是演电影的,身材也倍儿棒。穿着一条地道的牛仔裤,奶白色的西服敞着扣儿,里面是印着洋文的蓝色套头衫。她尴尬地微笑着,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扬起来,道歉似的挥了挥,推着车走过来。
我他娘的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大概在这么一副脸蛋儿面前想显一显老爷们儿的大方,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向她摆摆手,让她走了。
别以为往下该我走什么桃花运了。是不是我又在哪个舞会上碰到了她,要不就在什么夜大学里与她重逢。我才没心思扯这个淡呢。直到今天我也没再见她一面。之所以要从这儿说起,是因为这一下子太坑人啦,她倒好,脸一红,眼一闪,扬扬手,龇龇牙,骑上车,走了。说不定一路上还为有那么个小痞子向她献了殷勤而扬扬得意。我呢,往下你就知道了,活得那叫窝囊,全他娘的从这儿开始的。
我没想到那个放音机会被摔得那么惨。尽管被甩得挺远,可它好像是顺着地面出溜过去的,我戴的耳机的引线还拽了它一下。它落地的声音也不大,外面还套着皮套。等我把它捡回来打开一看,我傻眼了,机器失灵了还不算,外壳上还裂开了好几个大口子。看来,即便送去修理,也很难恢复原状了。
这玩意儿是我从都都那儿借来的。
“你真土得掉渣儿了!就会听邓丽君、苏小明。听过格什温吗?”这兔崽子考上大学才仨月,居然也要在我面前充高等华人了。
我说,为了领教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格什温,也为了领教同样让他得意扬扬的微型放音机,我得把它们一块儿借走。
“这是我爸爸刚刚送我的。”他显然为自己得意忘形招来的麻烦而后悔。
“放心!弄坏了,赔你!”我在他可怜巴巴的目光下戴上了耳机,又故意把他的宝贝放音机搁在自行车前的杂物筐里。格什温响起来了。“咣咣……咣咣……”破自行车在胡同小路上颤着,铁丝筐哆哆嗦嗦。回头看看这小子忍着心疼,还在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他妈开心。
现在倒好,离我折腾他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格什温的“美国人”还没在巴黎定下神儿来哪。别他妈开心啦,想办法,弄八十块钱,赔吧!
我推起车子,这才发现前轱辘的瓦圈被撞拧了,转起来七扭八歪的像个醉汉。我把它靠在隔离墩儿上,身子站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平伸过一只手去攥着车把,屁股一拧,踹了它一脚。大概这姿势太像芭蕾演员扶着把杆儿练功了,在停车线后面等绿灯的人都笑起来。我看也没看他们,把前轱辘扭过来,打量了一眼,“咣”,又是一脚。这回总算可以推着走了。不过,要想骑上它,还是没门儿。好在离家不远了,就让它这么醉醺醺地在大马路上逛荡逛荡得嘞,这也算他娘的一个乐子呢。
瘸腿老马一样的自行车,在人行道上一扭一扭。西斜的阳光,把人和车的影子推成长长的一条,投到身前的路面上,一耸一耸,一摇一摆,“吱吱……吱吱……”前轱辘蹭在闸皮上,发出耗子似的尖叫。身旁人来车往,急急匆匆。正是下班的时间,北京的马路上,就跟他娘的临下雨之前蚂蚁出洞的架势差不多。
“……就你妈?!就你妈?!”自行车的队伍里,一个娘儿们在训她的爷们儿。蹬辆破车,赔着小心,和她保持着两尺距离的,是一个脸像苦瓜似的男人。
“噢——”等公共汽车的人们兔子一样东奔西窜,在汽车的门口挤成了大疙瘩。售票员故意把车门关关开开,嗞嗞放气,人们越发伸长了胳膊,拥来挤去,好像都淹在了河里,拼命争抢一根即将漂走的木头。
“嘿,瞧一瞧,看一看……”稍稍宽敞点儿的人行道上,“倒儿爷”们开始拿着竹竿,挑起连衣裙,招蜻蜓一样挥舞起来,“瞧一瞧,看一看,坦桑尼亚式鲁梅尼格式大岛茂菲利普娜塔莎玛莉亚花色繁多款式新颖您没到过坦桑尼亚您穿上这坦桑尼亚式您就到了坦桑尼亚啦您当不了大岛茂菲利普玛莉亚您穿上这大岛茂菲利普玛莉亚式您就盖了大岛茂菲利普玛莉亚娜塔莎卡安东尼斯啦——”
……
你要是真的相信我在这中间逛荡能有点儿什么乐儿的话,那才叫冒傻气呢。
实话说吧,我和我们家老爷子干架已经有年头儿了。现在,我们之间简直就是“两伊战争”,停停打打,打打停停。
当然,这不挡吃,也不挡喝。即使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吵得天昏地暗,一个小时之后,我也照样理直气壮地坐到饭桌前,吃他娘,喝他娘。说不定还更得拿出一副大碗筛酒、大块儿吃肉的神气。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管饭行吗?可是,要让我向他开口要八十块钱,那可有点儿丢份儿啦。
唉,这一路我就没断了发这个愁,我怎么能弄出八十块钱来?
“下个月,你想着上电视台报到去。”
中午的时候,我已经“栽”了一回了。
老太太正在厨房里指挥煎炒烹炸,客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句,显然是对我说的。可他既没叫我的小名儿,也不叫我的大号儿,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弓着背,探着身子,坐在沙发的前沿儿,十指交叉,胳膊支在大腿上,脚下那双做工精细的轻便布鞋的前掌一掀一掀。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目光始终停在劈开的双腿中间,好像他吩咐的不是我,而是他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
我正倒在沙发里哗啦哗啦地翻报纸。我才不上赶着搭理他呢。磨磨蹭蹭看完了一段球讯,这才隔着报纸问他:“干吗?”
“去当剧务。先算临时的,以后再转正。”
说真的,没考上大学,真他妈待腻了。我已经考了两次,看来,和那张文凭也绝了缘分,这时候要说这差使不招人动心,那是装孙子哪。大概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没像往常那样儿找碴儿噎他。我没说话,算是认可了。
可紧接着他就来劲儿了。
“不过,得管管自己那张嘴。电视台的人都认识我,别给我丢脸。”
我差点儿没跳起来,把这个临时工给他扔回去。可我还是忍了。细想起来,我也不能算个爷们儿,有种儿——玩儿蛋去!别说一个破临时工了,给个总统也不能受这个!
我不应该把老爷子想得太坏。他再不喜欢我,也是我爸爸。我得相信他是为了我着想的。不过,我敢说,他更为了他给我的“恩泽”而得意扬扬。在他的眼里,我不过是一条等着他“落实政策”的可怜虫。
“爸,给我八十块钱。”
我要是再求他这么一句,我可真成了不折不扣的可怜虫啦!
瘸马似的自行车,一拐,一拐。
太阳已经西沉了,天色还挺亮。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路边的小妞儿净跟她们的相好撒娇使性儿。我已经看见他娘的不下三对儿了。拉她她不走,推她她晃悠。傻小子们一个个束手无策。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偏偏要生出这种管闲事的念头——我几乎想走过去,一人给她一个耳刮子,把兔崽子扇到马路对面去。
过人行横道的时候,我又捅了个娄子。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当然,我敢肯定,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太一门儿心思算计着和老爷子之间的事情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自己犯的是交通管理条例的哪一款、哪一条。
顺着人行横道的斑马线,都快走到马路中心的安全岛了,忽听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交通岗楼顶上的大喇叭里传过来:
“那——辆——破——车——……”
“那——辆——破——车——……”
在北京的十字路口上,你听去吧,岗楼里发出的这种半睡半醒似的声音多啦,我哪儿知道是喊我哪!我又走了几步,那声音突然机关炮一样炸响了:
“说你哪说你哪说你哪……”
我站住了,抬头向四周望去。岂止是我,恐怕这远近百十米的司机、行人都吓了一跳,疑心喊的是自己。我和那些被吓得左顾右盼的人一样,愣头愣脑看了半天,总算明白了,他喊的原来是我。
“你活腻歪了!”他骂了一句,算是总结,那口气像在他们家厨房里训儿子。不过,有这么一句,别人总算踏实了。冤有头,债有主,没冤没仇的各奔前程。
“你才活腻歪了呢!”我都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火儿,梗起脖子回敬了一句。
我敢说,他不会听见我嘟囔了些什么,我们隔着几十米哪。事情大概坏在我的脖子上了——用警察们的说法儿,这叫“犯滋扭”,“滋”,要发第二声。我还没有走到人行横道的那一头,他已经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我了。
“姓名——”黑色的拉锁夹子被打开了。这小子比我大不了多少,不过那模样可真威风,穿着新换装的警服,戴着美式大檐儿帽。关键是颧骨上有不少壮疙瘩。
“姓名——”又问了一遍。
“卢森。”
“哪个‘卢’?”
“呃——”还挺伤脑筋,“卢俊义的‘卢’。”
“哪个‘卢俊义’?”
“水泊梁山的卢俊义呀。”
他翻了我一眼,写上去了。他写成了“炉子”的“炉”。
“在哪儿上班哪?”
“在家。”
“嗬,你这‘班儿’上得够舒坦啊!”他的嘴角撇了撇,“我看你也像在家‘上班’的。”
身后已经围过人来了,呵呵笑着,看耍猴一样。
“家庭住址——”
“柳家铺小区,报社大院儿。”
“噢——”他打量着我,微微点头,“还是个书、香、门、第。”他一定很为找到了这么个词儿而得意,所以要高声大嗓、一字一顿的,演讲一般。他很帅地把夹子合上了,双手捏着,捂在裤裆上,腆起肚子,前后摇晃,“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吗?”
“不知道。”我不由自主地扭脸看了看刚刚走过去的斑马线,苦笑着说,“我……我好像没惹什么事儿吧。”
“照你的意思,是民警叫你叫错了?是吗?!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是吗?!”义正辞严。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那意思。绝对。没那意思,您……叫得很对。”
“那就说说吧,对在哪儿啊?”
这不拿我开涮呢嘛!我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咽了口唾沫,说:“我不该跟您梗那下脖子。”
“哄——”周围的人都笑了。
本来,我才不愿意跟民警废话呢,该认的认,能过关就得了,废话多了有你的好吗?!谁想到他跟我这儿来劲了,我也只好跟他贫一贫啦。还挺管用,这小子不再逼我回答那个混账问题了,他踮起脚后跟,朝人群外看了一眼,好像是想看看马路上是不是还有人应该拉来陪绑。然后,他沉住了气,又捂着裤裆,腆着肚子摇晃起来。
“知道咱们国家什么形势吗?”
“形势大好。”我说。
“北京呢——”“呢”字,一、二、三,拖得足有三拍长。
“形势大好。”我说。
“唔,你还挺明白。”他歪着脑袋,把围观的人扫了一圈,左脚一伸,稍息,“说说吧,你是什么行为?”
“害群之马。”我说。
“啧啧,到底是书、香、门、第!”他又高声大嗓地宣布了一遍。
“我爸在报社大院儿烧锅炉。”
“是吗?”他微笑了,“怪不得,我看你也像个烧锅炉的儿子。”
周围的人又笑起来。说实在的,我要是告诉他我是副总编的儿子,他得再高八度把他娘的“书、香、门、第”说上八遍。不过,我认一个烧锅炉的爸爸也没认出个好来。他算是找着个人把那点儿学问好好抖搂抖搂啦。他由“改革”扯到“打击刑事犯罪”,由“中日青年大联欢”扯到“清除精神污染”。“你他娘的总不会扯到越南进攻柬埔寨吧!”我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暗暗骂起来。
“你笑什么?”
“您挺忙,”我说,“我们报社大院儿里净是报纸,别耽误您的工夫,让我回去自己学得啦。”
“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就好。”他大概也累了,“那你就说说吧,认罚不认罚?”
“认罚。”我说,“您辛苦,收入也不高,罚点儿也是应该的。”
“我一分也落不着!全上缴国库!”他火了,“就你这种态度,还得给你上一课!”
“噢,误会了误会了,那,也好,支援四化。”
“行啦,别贫嘴啦!”看得出来,他有点儿想笑,可还在故意板着脸,“掏钱吧,两块。”
“两块?不瞒您说,一块也没有哇!”我把衣兜裤兜翻给他看,愁眉苦脸地说,“得嘞师傅,我这辆车破点儿,您要不嫌弃,先扣下得啦!”
“得啦得啦,我下了岗还想早点儿回家呢!”他看着我那拧了麻花的前轱辘,忍不住笑了。他这一笑我就明白:两块钱省了。
“走吧走吧,下次再有胆儿犯横,想着带钱!”
“您圣明!”昨天晚上我刚在电视里看了《茶馆》,我觉得这句台词挺棒。
他瞪了我一眼,分开众人,爬回交通岗楼里去了。
我跟在他后面,探着脖子看了看岗楼里的电钟,把车子又支起来。我骗腿儿坐在后货架上,噘起嘴吹了几声“啊朋友再见”。我吹得不响,长这么大了永远也吹不响,这可真让人垂头丧气。
“喂,怎么还不走?!”“壮疙瘩”从岗楼里探出脑袋来,“不是让你走了吗?”
我故意看了看人行横道,苦起脸说:“受了您这半天儿教育,咱们也得长进不是?您得让我在这儿好好总结总结,看看自己到底错在哪儿啦!”
“嗬,倒是没白费我的唾沫啊!”他心满意足地把脑袋缩了回去。
我他娘的倒真有这个瘾!
其实,我是成心要在这儿磨蹭磨蹭。
今天晚上,老爷子好像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宴会。这会儿,说不定还没有走。
二
碰上了我在柳家铺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馄饨侯”,我才忽然明白,这个时候,待在这个路口,实在是一件蠢事。
从这儿往东五百米,就是柳家铺中学。我在那儿上了两年高中,接着又上了一年高考补习班。我的同学全住在附近。沿学校的围墙向南拐,八百米左右,就是报社大院儿了。大院儿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熟人就更多了。正是下班时间,在这儿站着,没个清静,说不定什么时候对面就过来一位,你再腻烦这一套,也得跟他对着龇牙。
“卢森,怎么站在这儿?你爸爸好吗?”
“馄饨侯”骑着车从学校的方向过来,大概是刚刚下班,还是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绸衬衣,哆里哆嗦的凡尔丁长裤。
“弱不胜衣。什么叫‘弱不胜衣’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站在讲台上,用瘦嶙嶙的手指揪起衬衣第三颗纽扣的样子,衬衣里面,仿佛只戳着一根竹竿,“这就叫‘弱不胜衣’,明白了?也可以说‘骨瘦如柴’‘憔悴枯槁’‘病骨支离’,再老点儿,就可以说‘鹤骨鸡肤’啦。当然喽,好听的也有——‘仙风道骨’!……”
他还是那个毛病,老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爸好吗?”要不就是“你爸爸挺好的吧”。
我真替他难过。
三年前,我从城里转学到柳家铺中学,他教我们班语文。当着那么多同学,老远走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好像他跟我爸爸不是哥们儿也是师生。巴结我们家老爷子的嘴脸我见多啦,还没见过这么傻的,我真替他害臊。可是后来,当我们老爷子写了那篇混账文章以后,一听他提起老爷子,我只有替他难过的份儿啦。
“你们呀,一点儿也不知道争气、学好。大米白面吃着,读书呢?一肚子臭大粪!……我读书那会儿怎么读的?我告诉你们……”他从黑板的下槽里抓出一把粉笔末,刷啦刷啦地翻开书每隔几页往页缝儿里撒上一溜,“六一年那会儿,我在师院,饿得我呀,一天到晚凄凄惶惶的。弄了点儿炒面,就这么撒在书缝儿里,看几页,举起书,对着嘴,磕巴磕巴吃一口。有点儿好吃的,都得就着学问吃下去!……”
只要他来上课,课堂上就有笑声。这一段一段的“单口相声”,乐得我们一个个都要抽筋儿。
有一次上作文课。
“九十分钟。照这个题目写吧!我也写。明告诉你们,我搞点儿自搂,给人家写小人儿书的脚本。你们不少人也知道,当老师的嘛,家庭不富裕。有的下了班,老婆孩子齐上阵,糊火柴盒!我不用。作文学好了,至少有这点儿好处。写这一页,一碗馄饨。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就你们中间,比我出息的嘛,当然有。可能吃上这碗馄饨的嘛,也不多。争口气,写吧!……”
他姓侯,“馄饨侯”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班同学里,“能人”多啦。可报社大院儿里的孩子,只有三个,都是报社迁来柳家铺后,转学来的。其余的净是家住柳家铺北里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后代。他们学习不行,嘎七杂八的事可懂得不少。我也就是这一次才知道王府井八面槽那儿有那么一个卖馄饨的老字号,叫“馄饨侯”。这帮王八蛋给我们的老师安上啦!
我长这么大干的顶浑蛋顶浑蛋的事,就是把“馄饨侯”之类的事情告诉了老爷子。那会儿,我还是个少见多怪的“小傻帽儿”,回到家里,没完没了地学舌。
“格调太低了。你们的老师,格调可太低了!”听了这些事情,老爷子非但没露过一次笑脸,反而总是沉着脸,皱着眉,说这一类庄严而伟大的废话。
我从来也不认为我们这位侯老师能当上什么李燕杰。他不过就是一个爱说点儿实话,爱开点儿玩笑,还有点儿可怜巴巴的“馄饨侯”就是了。所以,老爷子根本犯不着这么认真,把这件事写进他的文章。
那篇文章的题目好像叫他娘的什么《“师道”小议》,登在他们报纸的第二版右上角,还用花边儿给框了起来。开头就由“某位老师”的“馄饨故事”说起,然后就“由此想到我们的老师应该……”然后又“由此想到”古代的一个什么鸟人的一句什么“经师人师”的鸟话,然后就“教育事业是关系到育人育才的百年大计”,然后就“是不是值得每一位老师深思呢”?
这篇浑蛋文章整个儿把我给气晕了。老爷子的笔名叫“宋为”,班里的同学没有不知道的。本来,班里那些小痞子们背地里没少了拿我们的“馄饨侯”开心,这会儿,倒全他娘的骂上我啦!
“鬈毛儿!”他们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因为我的头发天生有点儿卷儿,“你丫挺的怎么这么不地道!你们老爷子装他妈什么孙子啊!”
“要是把你平常的胡扯八道整理整理送公安局,也够你狗日的一个反革命了!”
“假模假式的,还‘深思’呢,没劲!”
……
我敢说,这帮兔崽子可逮着一个“臭”我的机会啦。活该,谁让你在大伙儿眼里一直是个牛气哄哄的总编的儿子呢。搬运工的儿子们、抹灰匠的儿子们也该挤对挤对你,撒撒气啦。再说,我们的老爷子也是真他娘的没劲!没劲透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那天下午我又见到了“馄饨侯”。那是个星期一,算算我们倒是有两天没见面了,可我恨不能把脑袋扎裤裆里溜过去。可气的是,他老远就看见了我,还是那么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卢森,星期天上哪儿玩去啦?你爸爸挺好的吧!”
唉,可怜的“馄饨侯”,您饶了我行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