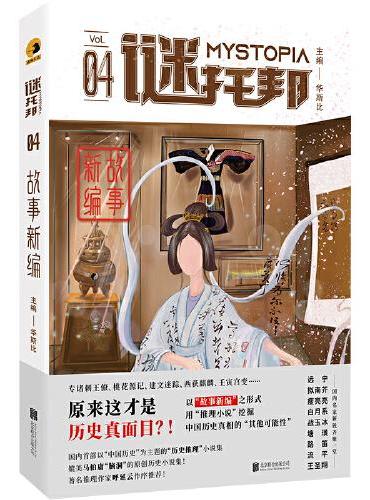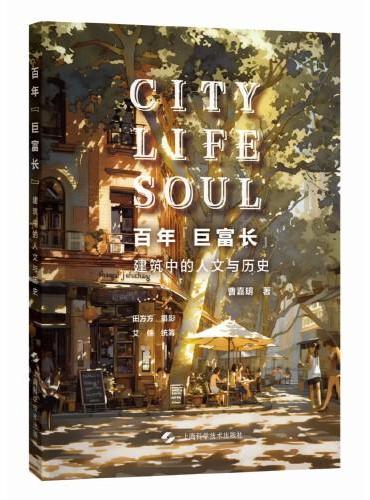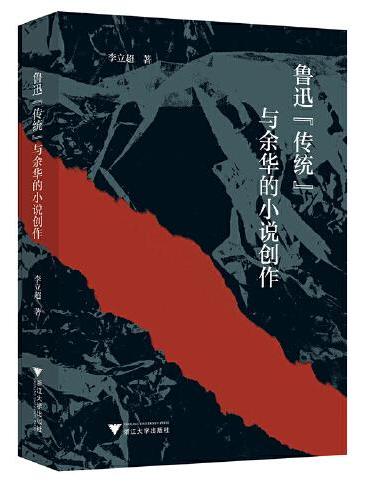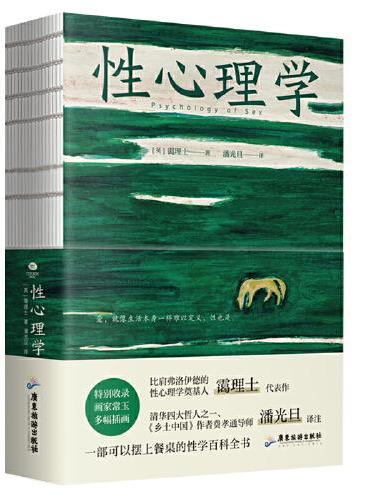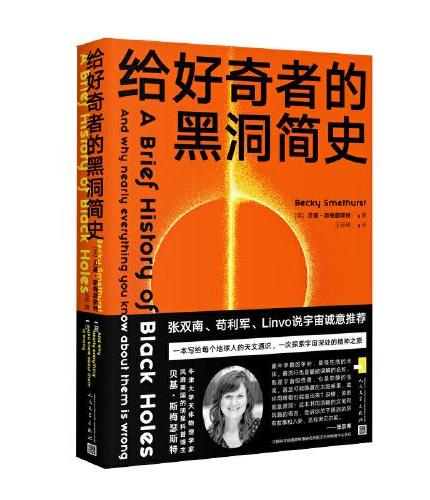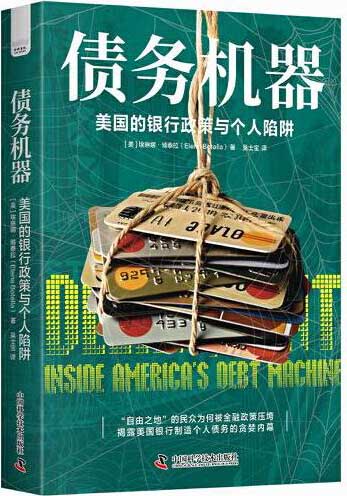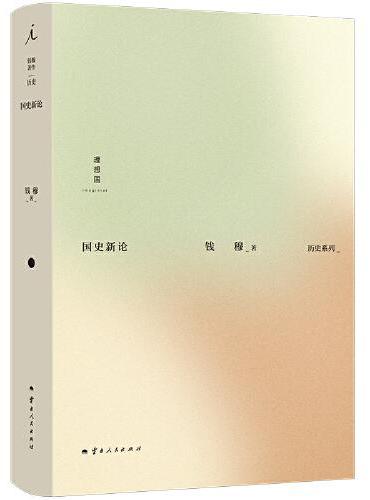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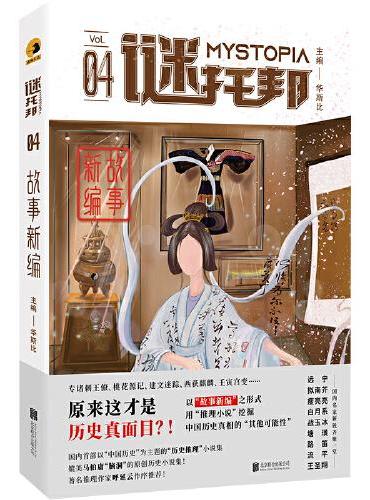
《
谜托邦:故事新编
》
售價:HK$
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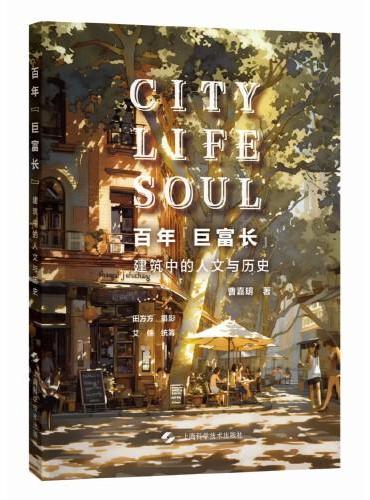
《
百年“巨富长”——建筑中的人文与历史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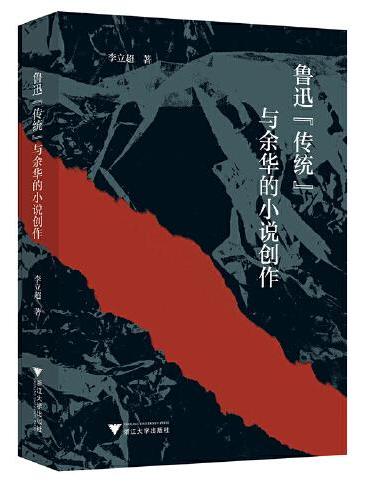
《
鲁迅“传统”与余华的小说创作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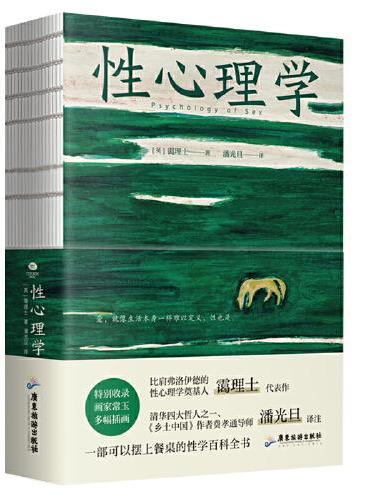
《
性心理学(裸脊锁线装,一部剖析性心理的百科全书,一本好读实用的性学指南)
》
售價:HK$
64.4

《
抢人:数字时代如何快速吸纳精准人才(美国商业图书大奖AXIOM年度图书)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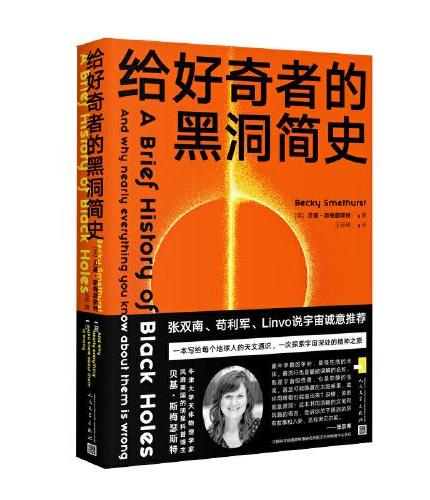
《
给好奇者的黑洞简史
》
售價:HK$
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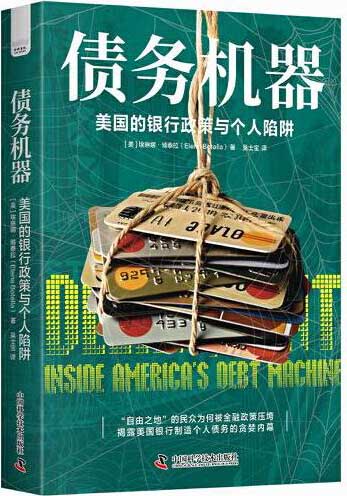
《
债务机器:美国的银行政策与个人陷阱
》
售價:HK$
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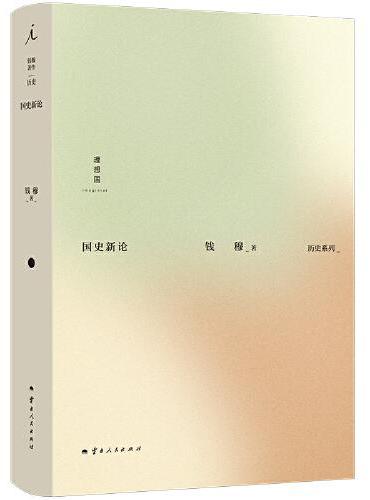
《
钱穆:国史新论
》
售價:HK$
78.2
|
| 編輯推薦: |
|
这是跃动着生命力量的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那些往事也因讲述而不再寂寞
|
| 內容簡介: |
|
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施剑翘、追随司徒雷登44年的傅泾波、亲历过东京大审判的高文彬、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守候敦煌60年的绘画大师常书鸿……这些近现代人物,穿越历史的烟尘,在李菁的笔下复活,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传达着难以言喻的感动。
|
| 關於作者: |
李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历任记者、主笔、副主编。近20年来,采访领域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做了大量一线报道。
2006年,在周刊开设“口述”栏目,采访历史及文化领域有影响的人物不计其数,“口述”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广受欢迎的栏目之一。
先后出版过《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往事不寂寞》《记忆的容颜》《沙盘上的命运》等。
|
| 目錄:
|
序
传奇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施剑翘 : 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
人生长恨水长东——我的父亲张恨水
傅泾波 : 追随司徒雷登 44 年
我的母亲龚澎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李济 : 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一代报人邓季惺 : 被湮没的传奇
解密
1976 年 10 月 6 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赵炜 : 我的西花厅岁月
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
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我所亲历的“9·13”
父亲储安平之死
张志新 :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
名 流
唐德刚 : 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梁漱溟 :逝去的儒者
我的父亲梁实秋
一生的守候——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杨宪益 :破船载酒忆平生
我的父亲罗家伦
吕恩 :往事悠悠
黄宗江 :我的戏剧人生
我的父亲郑君里
往事
毓嶦:我所知道的溥仪
美丽与哀愁——我的母亲浦熙修
我的父亲刘文辉
我的父亲佟麟阁
我的父亲卫立煌
我的公公陈立夫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杨宪益:破船载酒忆平生
天津旧事
我是 1915 年 1 月 10 日在天津出生的,母亲说她在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老虎跳进她肚子里,那一年又是农历虎年,所以有人说我是白虎星,命硬。我小时候身体不好,5 岁那年生病哭个不停,父亲半夜来看我得了风寒,不久就去世了,有人说我把父亲克死了。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这些。
杨家祖籍在安徽,从祖父杨士燮那一代起从安徽搬到天津,祖父最高职位做过淮安知府,与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是上下级关系。据说他性格诙谐,喜欢自嘲。我的父亲杨毓璋是 8 个兄弟中的老大,我的几个叔叔好几个都出国读书,英、法、美等,父亲则去了日本。回国后他先是做了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几年后,又到天津当上了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行长的薪酬比较高,我们家的家产是父亲赚的,不是继承祖父的,我祖父没有很多钱,他请人吃饭还要把皮袄当掉。我的父亲在天津很有名,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关系都不错,因为
他是银行家,能给那些军阀提供钱。我出生后,袁世凯送了个小黄马褂给父亲表示祝贺。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优越,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洋楼里,前后几个院子几个楼,佣人住后面,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有 16 个男佣,16 个女佣;家里就我一个少爷,难免骄纵。我想学自行车,但家里起初怕出危险不让我骑,后来买了一辆,可以骑了,但旁边跟两个人,只能在院子里骑,不能出院子,去北戴河游泳妹妹可以去,但我不能去,家人担心我被淹死。小时候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出去买书,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用钱,每次都是一个佣人跟我去书店,我看什么书就拿,最后是家里每月跟书店结账。
小学阶段是在家里私塾读的,没人敢管我,老师都是很规矩的人,他们教我我还追着老师打,还有个老师教我读《西游记》,我让他学孙猴子,结果把他气走了。这样一连换了好几个老师,直到来了一个姓魏的先生,他喜欢古典诗词,慢慢教我如何对对子。有一次他叫我写一联描写春天景色的句子,我信口诌了一联 :“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柳烟。”先生大为赞赏,说我是个神童,我也免不了沾沾自喜,从此喜欢尝试作诗。
1927 年,我进入了天津一家教会学校——新学书院。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每天早上 10 点做祷告,唱圣歌,但这些都没使我变成一个基督徒。在新学书院我算最激进的学生了,“五卅”惨案后,我还领导学生罢听英国老师的课 ;“九一八”事变后,我想当兵参加抗日,我单独出钱请了一位退伍军人做教练,每天自动组织军训,我一直坚持到最后。老师们对我喜欢又头疼,因为我家里有钱,所以老师也很客气。
那时候刚从英国回来的黄佐临来我们中学做校长,我组织罢课时,他还跟我进行谈话。黄佐临对戏剧很有兴趣,自己编了一个英文话剧《西施》,我被拉去演兵。吴王夫差要自杀,我就说了这辈子唯一的一句台词 :“大王,放下你的剑吧!”解放后他在上海专职做导演,他的女儿黄蜀芹拍的《围城》也很有名。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和黄佐临很熟悉了,但他完全不记得我就是当年带头闹罢课的学生。
因为我要进的教会学校是用英文授课的,母亲怕我听不懂,给我找了一个英文家庭教师。她刚来的时候我还对她很不客气,她叫徐剑生,我对了“快枪毙”——“徐”对“快”,“剑”对“枪”,“生”对“毙”。她比我大 10 岁,先生是位医生,两人关系不是很好。后来我们俩很谈得来,母亲觉察到我们这种微妙的感情以后,很聪明地和她结拜了姐妹,让我拜她为干妈。
1934 年春,我高中毕业。家里原本打算让我在国内读完大学再出国留学,我的意愿是想去清华读文学或历史。但我的英国老师朗曼先生提出要带我去伦敦,母亲可能怕出家庭丑闻,也答应了。到了英国后,徐剑生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给我,我回了一封信,说不要来往了,后来听说她服安眠药自杀了。
牛津往事
刚到伦敦,朗曼先生为我找了一位教希腊文的先生。有一天他问我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这是两所最好的大学。”我问他 :“哪一个更好?”他说,牛津更好,也更难进。“那我就去牛津!”我说。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用功学习,5 个月后,我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顺利通过了希腊文、拉丁文专业笔试。但那年牛津给亚、非学生的名额只有一个,我只好等到第二年秋季入学。暑假,我参加了一个环地中海旅游团,途经直布罗陀海峡、阿尔及尔、里斯本、马耳他、希腊等地玩了一个多月。那时我年轻,也不懂得省钱,为了玩得舒服,我买了个头等舱,每天晚饭时还要打蝴蝶结。坐头等舱的中国人很少,到土耳其时我还被当做日本特务,被拒绝上岸。
在牛津读书的中国学生只有二十几位,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吕叔湘等。留学生大约分为三类 : 一类像我一样自费出来的,不怎么好好念书 ; 第二类是拿庚子赔款出来的,像钱钟书,属于不问政治,只管念书的; 还有一类是国民党派的,他们学习不怎么样,还要担负监视中国留学生的政治任务,认识军阀或高官的就可以得到名额,有些政治任务,我们常喊他们“蓝衣党”,也瞧不太起这些官费生。
牛津管理很严,头一年要住校,晚上有门禁,我经常出去喝酒,晚上 11 点才回来。我所在的墨顿学院在墨顿街上有一条煤道,回来晚了,我就打开街上人行道的盖子,从煤道滑下去。1937 年,我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那年正好赶上“卢沟桥事变”,我就经常在学校演讲,争取英国人的支持。牛津还有一个日本学会,主席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我和他竞争,最后许多日本学会的会员转而参加中国学会的活动,大大超过了日本学会。
我在牛津学了两年希腊、拉丁文学以后,又选学了两年英国文学,1940 年拿到荣誉学士学位,名字上了《泰晤士报》——只有拿到荣誉学位的人才能获此殊荣。
《离骚》是我在牛津上学时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古典作品,当时也是为了好玩。我觉得《离骚》的风格跟英国 18 世纪的诗比较像,翻译时,我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为了好玩也故意模仿那个时代的Dryden 和Pope的风格,那时我才24岁,翻译《离骚》是为了向我的老师、诗人布伦顿表示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也想向老师“显摆”一下自己。后来这个译本50年代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译海生涯
大学一毕业,我就带着我的爱人一起回到中国。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 Gladys Margaret Tayler,“戴乃迭”是我为她取的中文名字,她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取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学生。乃迭是在北京出生的,直到 6 岁左右才回到伦敦。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父亲约翰·伯纳德·泰勒(中文名字为戴乐仁)曾经在我读过的新学书院教过书,后来又到燕京大学任教。最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来到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甘肃省山丹县,发起“工合运动”,收容了许多孤儿,免费对他们进行初级教育,后来还有一些志愿者加入他们的行列,比较有名的像印度的柯棣华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我们认识两年后订的婚。她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预言这场婚姻不会超过 4 年 ; 那时中国正是战乱,条件也很差,我说 : 要不我们算了吧,你留在英国。但她很坚决。那时,我的家境也开始慢慢败落,在伦敦的第三年,家里就不怎么寄钱来,毕业前,我靠卖书度过了最后几个月。
毕业时,我接到两份聘书 : 一个是哈佛,一个是西南联大。哈佛让我去做中文助教,这虽然有吸引力,但是我想回国 ; 那时西南联大想开一门古希腊和拉丁文的课,我从未见过面的沈从文和吴宓向校方推荐了我,我也很想去西南联大。但那时候昆明刚被日本轰炸过,母亲在重庆正好租住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房子里,她认为重庆安全些,哭着要我留在中央大学,我们本来是看不起中央大学的,但听从母亲意见,我去了中央大学英语系。后来我想,我的性情跟闻一多有点像,如果我真去了西南大学,说不定像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呢。
1941 年 2 月,我与戴乃迭的婚礼,和大妹妹杨敏如与罗沛霖的婚礼放在一天举行,张伯苓和罗家伦证的婚 [1]。参加婚礼的,还有一位同样在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贝特兰,他是位传奇人物,曾采访过在延安的毛泽东、“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婚礼上,贝特兰还高唱《松花江上》,现在想起来,在人家的婚礼上唱这样的歌怪怪的,但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气氛。
1943 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见了梁实秋,并受邀到他主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史记》有一部分外国人已经翻译了,所以梁实秋建议我翻译《资治通鉴》。一般我拿着书直接口译成英文,乃迭在那边用打字机打出来,把英文再润色一下。我用 3 年的时间,译完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的 35 卷。还没来得及出版,国立编译馆取消了,这些稿子一直放在柜子里。80 年代,一个澳大利亚朋友对书稿有兴趣,我就全送给他,再没有下落。
梁实秋有点洋派大少爷的味道,比较有才华,人也很随和。可能是因为过去与鲁迅有过激烈的笔战吧,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论文学,他也不喜欢谈政治和时事。我和梁实秋相处得很好,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鲁迅的东西,他骂梁实秋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所以我难免受鲁迅的影响;另外,梁实秋和一些政客来往得比较多,这也是我不喜欢的。
我在重庆时也被复旦大学邀请做兼职教授,在那里认识了梁宗岱,他是我很早就喜欢的诗人,在法国和德国留学 7 年多。梁宗岱是位性情中人,经常跑到我这里来喝白酒。有一次我自己酿了一罐桂圆酒,梁宗岱来了,我从床下特地找出桂圆酒给他喝。他喝了第一口觉得味道不太对,但也没多说什么把那一大碗酒一口喝下。
那时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第二天我到床下找煤油,才发现昨天给梁宗岱喝下的是煤油——因为桂圆腌时间长了也是那种暗黄的颜色,我错把煤油当成酒了。我想,这下他可能中毒死了,结果他竟然没事。梁宗岱后来在“文革”时吃了不少苦,1979 年再见到他时已经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次朋友相见他第一次听说吴宓去世的消息,他一个人走到墙边,大声哭起来,哭得很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那时知识分子都一腔热情地支持新中国,抗美援朝爆发时,像老舍、曹禺等都跑到朝鲜前线慰问了,我没有去前线,跑到火车站去慰问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那时号召捐献,捐 4 万块钱就可以给国家增加一架飞机。我和我爱人也参加捐献,她卖了些我母亲留给她的首饰凑了4万块,等于捐了一架飞机。
1951年春,北京调我和戴乃迭到北京参加毛选翻译工作,当时钱钟书是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时还没有想到什么反对“个人崇拜”,只是更愿意翻译古典文学而不是政治著作,另外我喜欢南京,又在南京刚刚买了房子,所以就拒绝了钱钟书的邀请。第二年,我俩被调到北京来参加亚太会议做短期翻译,在北京时遇见刘尊棋 [1] 被他邀请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和我一样被刘尊棋“拉”进来的还有萧乾、徐迟、冯亦代等。
刘尊棋希望列一个中国古典作品的名单,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清末,选了 150 部古典文学让我翻译 ; 也选一些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现当代文学翻译。翻译鲁迅的作品,选哪一篇去掉哪一篇,都是我和冯雪峰一起商量进行的。两年以内四卷本的《鲁迅选集》就出版了。
可以说从 50 年代初一直到 1955 年我的生活都挺愉快的,那一段也是我翻译的高峰。刘尊棋对我很好,还推荐我去中南海几次。有一次见毛泽东,周恩来介绍我说,“他是翻译《离骚》的”。毛泽东问 :“《离骚》 也能翻译吗?”我说 :“主席,什么都能翻译的。”他想了想,笑一下,要跟我辩论,他可能觉得《离骚》没法翻译。我现在看来,觉得毛主席的怀疑有道理,翻译从技术上来说,是什么都可以的,但是文艺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做到翻译出原来的精神实质。就像你模仿一幅画、雕塑,很难把神韵弄出来。
周扬在做文化部长时,听别人介绍杨宪益念过希腊文,他说《荷马史诗》还没有人翻译,把我从外文局调走,翻译这部作品 ; 结果翻译一半,周扬下台了,外文局的人说,中国也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把我调回来翻译《红楼梦》。那时我们已经组织美国人、英国人翻译了《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只有《红楼梦》是中国人翻译的。我用了一年就翻完前 80 回,正准备翻后 40 回,结果有人来告诉我,你不要再翻了,结果没多久就被抓起来了,一个同事把翻译书稿保存下来。其实我不太喜欢《红楼梦》,那些人,那些事,跟我的旧家庭挺像的,我没什么兴趣,我更喜欢《三国演义》,觉得它好玩一些。
“半步桥边卧醉囚”
1968 年 4 月我们俩被捕之前的两个礼拜,我的邻居、同在外文局工作的爱泼斯坦被抓进去了,我觉得好像很突然,但是我没有把他和我自己联系到一起。
“文革”刚开始时,大喇叭天天喊,“打倒 ××”,我曾经出现短暂的幻听,好像总有一个特务在脑袋里捣乱,耳朵里听见这个“特务”说话,一年以后恢复过来。“文革”让整个中国都陷于狂热,外文局也不例外,发起“书刊检查运动”,把许多名著,把曹禺的《日出》、《雷雨》等译著,都给毁了 ; 在外文局工作的柳亚子的女婿也自杀了。
被抓进去那天晚上我和爱人两个人在家里喝酒,喝了小半瓶——那段时间天天闹运动我心情不太好,晚上常常和乃迭一起喝点酒,她喝了一点酒就去睡觉了。22 点多,有人敲门让我去办公室,然后就被抓了,坐上车被送到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以前鲁迅书里写着,叫“第一模范监狱”。
那天晚上被抓的犯人特别多,那个屋子关了 40 个人。我们就这么竖着,像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躺着。我1948 年,杨宪益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一进去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被旁边一老头捅醒。“你那酒气真好闻,你喝的一定是好酒!”他大概讲错什么话被关了好长时间,好久没闻到这个味儿了。他还关心我被抓时那瓶酒喝完没有。后来苗子写了首诗给我 :“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乃迭的情况,我不知道一个小时后她也被抓起来了,而且就和我在一个监狱里。后来有犯人告诉我,说我们这里面外国人在放风,让我趴在窗户上看,我才知道她也被抓了。我们 4 年没见面。出狱后,我们从来不说监狱的事,她也不知道我曾在不远处看过她。戴乃迭被抓后,她的母亲很担心,在伦敦找了好多人签名,写信给党中央、周恩来,但也无济于事。她母亲不久就去世了。
我在监狱里和狱友们的关系很好,在监狱里很多人还不认字,我们找了会认字的人,每天给他们读,读中央的社论什么的,我还教他们唱英文歌。有一次他们提出想学唐诗,《长恨歌》我记得很清楚,于是一句一句地教他们背,还得一句句解释,他们以前没学过,也觉得很有意思。
那时候也不知道要坐几个月,还是几年。最坏的打算是想也许哪天把我拉出去毙了。遇罗克也在我们这个监狱,在我被抓起来两个星期前被枪毙了,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酒仙桥。结果有一天突然把我拉出去照了一张相,我以为要把我毙了,我想毙了也就毙了吧,狱友们觉得大约我活不了几天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把我放了。
我出来以后就到了北展的老莫餐厅,喝了一杯啤酒。关了我 4 年,放我那天也没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但在出狱时,按一天 4 毛钱的伙食标准,从我工资里扣掉了在监狱里 4 年的伙食费,因为我白住了 4 年的“招待所”。那个时候被枪毙的人,家属还要交 4 毛钱的子弹费。好在没有向我爱人要这笔伙食费,如果向她要钱的话,她肯定比我多,因为生活费比我高。
其实我和乃迭在家里很少谈政治,她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还是中国文化和历史。那时她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儿子杨烨。他上大学时,基本是极左,和家里的人都合不来,我们的唱片,都被他拿去毁掉。在那个年代里,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很大问题,后来他坚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到了英国后仍摆脱不了对自己身份认定的痛苦,在伦敦的寓所里自焚而死。
我们被抓走后,在外文局的住处用封条封上了。回到家时,家里已成了耗子窝了。衣服都被啃烂了,外文书比较厚,它们不喜欢啃,这很幸运。被抓那天喝的白酒竟然还在,只是颜色都是黄的。
在把我放出来之前,他们问我 : 要跟戴乃迭继续在一起,还是离婚?我说,我们还是在一起吧,把家简单收拾了一下。一个星期后,乃迭也被放回来。我从没问过她,是否有人问她类似的话,她又是怎样回答的。我们就这样,还是在一起,直到 1999 年乃迭去世,死亡将我们分开。
(2006 年 5 月 29 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