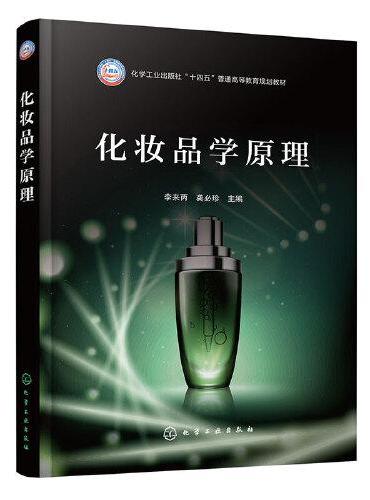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HK$
110.7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HK$
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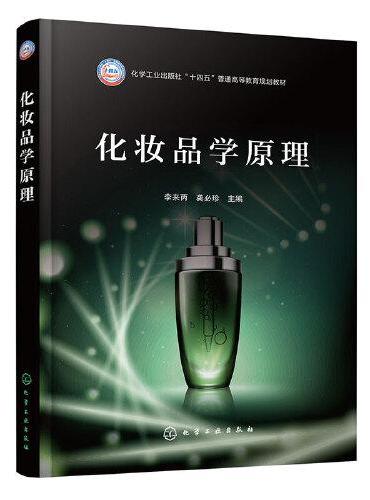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HK$
55.8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HK$
47.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HK$
55.8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HK$
55.8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HK$
109.8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柯南道尔产权会官方特别认可
全景展现福尔摩斯的青少年时代
故事情节巧妙,颇具原著风范,脉络清晰、极具说服力又精彩刺激。
——柯南道尔产权会
《少年福尔摩斯》系列带你领略
大侦探福尔摩斯如何从零开始学
逻辑推理、探案知识、智能谋略
解密大侦探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演绎推理法启蒙自何人?
福尔摩斯的思维殿堂*初是什么模样?
侦缉队贝克街小分队的原型是谁?
福尔摩斯何时何地开始拉小提琴?
福尔摩斯高超的化装技巧从何处习得?
|
| 內容簡介: |
有些时候,群体没有个体明智。看看芸芸众生:一个比一个聪明,但是一旦成为乌合之众,被人煽风点火,往往不堪一击。不过有些时候,群体的行为又比个体明智得多,比如这里的蚂蚁,还有蜂群。
克罗先生的“猎物”之一,当年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布斯仍在人世,并且流亡到了英国。根据克罗先生的推测,“猎物”正在暗中布局,酝酿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好奇地靠近一幢名为“审南多亚”的房子,寻找线索。他发现里面关了个疯子,还有一些珍禽异兽。可他不小心打草惊蛇,导致好友被绑架到美国。这一次,福尔摩斯不得不远赴千里之外,解救好友,同时阻止一群“乌合之众”密谋已久的计划……
|
| 關於作者: |
安德鲁莱恩,英国青少年畅销书作家。莱恩不仅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的骨灰级粉丝,拥有海量相关藏书,还是研读福尔摩斯一系列相关作品的专家,同时,莱恩还是唯一获得柯南道尔产权会授权,创作福尔摩斯青少年小说的作家。
莱恩的代表作还有《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s)等。
|
| 內容試閱:
|
夏洛克垂头丧气,从落地窗进入书房。他觉得脸颊发热,十分尴尬,奇怪的是,还很愤怒——只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为迈克罗夫特抓住他偷听,还是为自己被抓了个现行?
“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他问。
“首先,”迈克罗夫特不动声色地说,“我料到你会在那儿。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年轻人,而且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既有的社会准则对你几乎没什么约束力。其次,之前有一阵微风从打开的落地窗吹进来。你躲在外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你,地上也没有你的影子,但是你的身体挡住了微风。那阵风消失了几秒钟,我推测是被人挡住了。很明显,那个人只能是你。”
“你生气了?”夏洛克问。
“一点儿也没有。”迈克罗夫特回答。
“只有当你粗心大意,让阳光把你的影子投射到阳台上时,”克罗先生和蔼地说,“你哥哥才会生气。”
“的确,”迈克罗夫特赞同道,“那不仅证明你缺乏简单的几何知识,也说明你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意外后果缺乏预判能力。”
“你们在戏弄我。”夏洛克控诉道。
“有一点儿,”迈克罗夫特承认,“不过是出于好意。”他停顿了一下,问夏洛克,“你偷听到多少?”
夏洛克耸耸肩:“有个家伙从美国来到英国,被你们视为威胁之类的。对了,还有什么平克顿家族的事。”
迈克罗夫特瞥了一眼克罗先生,挑起一条眉毛。克罗先生轻笑一声。
“他们不是一个家族,”他说,“虽然听起来很像。平克顿侦探社是一个侦探和安保公司。大约在十二年前,由阿兰·平克顿成立于芝加哥。当时他发觉美国铁路运输公司纷纷成立,但是缺乏必要的安保手段,经常受到抢劫、破坏和工会活动的困扰。于是阿兰趁机雇人成立了一个公司,有些像是超级警察势力。”
“完全独立于政府规则和规章制度之外,”迈克罗夫特嘟哝道,“如你所知,对一个奉行民主并以此为傲的国家来说,设立如此不可理喻的独立机构,真是司空见惯的事。”
“你叫他‘阿兰’,”夏洛克意识到了什么,“你认识他?”
“我们很早以前就打过交道,”克罗先生承认,“七年前,亚伯拉罕·林肯途经巴尔的摩,前往出席总统就职礼时,我和他在暗地里保驾。当时南方各州密谋在巴尔的摩刺杀林肯,平克顿侦探社临危受命,使总统先生化险为夷。从那以后,阿兰时不时地请我帮忙。当然,我从未拿过他们的正式薪水,不过他付过我好几回顾问费。”
“林肯总统?”夏洛克思路有点儿跟不上,“他不是已经——”
“没错,他们最终还是得手了。”克罗先生的脸像花岗岩雕像般沉重肃穆,“巴尔的摩刺杀失败后的第三年,有人在华盛顿朝他开了一枪。他的马受惊,帽子被打掉了。事后,他们找到了帽子,发现上面有个弹孔。就差一点点。”他叹了一口气,“那件事之后,过了一年,也就是三年前,他在华盛顿一家剧院看戏,是当时很流行的《我们美国人的亲戚》,一个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人朝他的后脑勺儿开了一枪,然后跳上舞台逃走了。”
“你不在现场,”迈克罗夫特轻声叹息,“你也无能无力。”
“我本来应该在的,”克罗先生同样叹道,“阿兰·平克顿也该在的。事实是,当晚唯一负责总统人身安全的护卫,是一个名叫约翰·弗雷德里克·帕克的警察。总统遇刺时,他甚至没在剧院里面,而是在隔壁的星星酒馆喝得烂醉如泥。”
“我记得我在父亲的报纸上读过这个新闻,”夏洛克说,他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我还记得父亲谈论过这事,但是我实在无法理解,林肯总统为什么会被害?”
“这就是近来学校教育的问题,”迈克罗夫特抱怨道,“对他们而言,英国历史大概一百年前就停止了,根本没有世界历史这回事。”他扫了一眼克罗先生,这个美国人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猜,你应该知道美国内战吧?”他问夏洛克。
“只看过《泰晤士报》的一些报道。”
“简单说,美国南方十一个州自行宣布独立,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他不屑地说,“就像多塞特、德文或汉普郡突然宣布从大英帝国独立出去,决定另行建立一个国家一样。”
“或者就像爱尔兰脱离英联邦一样。”克罗先生低声说。
“爱尔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迈克罗夫特严肃地说,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夏洛克身上,继续说,“于是,美国有了两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南部联邦的杰斐逊·戴维斯。”
“为什么他们都想独立呢?”夏洛克问。
“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独立自主?”迈克罗夫特解释道,“因为他们不喜欢接受、服从命令。就美国内战而言,是因为存在政见差异。南方各州支持奴隶制,而林肯竞选总统之初就旗帜鲜明地主张解放奴隶。”
“没那么简单。”克罗先生说。
“政治从来不简单,”迈克罗夫特同意,“不过就目前我们讨论的话题来看,确实如此。从1861 年4 月12 日开始,南北双方敌意渐浓。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六十二万美国人死于内战——某些情况下,甚至兄弟反目、父子相残。”他似乎有些发抖,这时,一朵黑云遮蔽了烈日,房间里顿时暗下来。“慢慢地,”他继续说,“北方,亦即美利坚合众国,击溃了南方的军事力量——他们自称美利坚联盟国。南方最举足轻重的将领——罗伯特·李——在1865 年4 月9 日宣布投降。听到这一消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在五天后射杀了林肯总统。当然,这只是惊天阴谋的一角——据说南方还想刺杀国务卿和副总统。庆幸的是,第二个刺客没有得手,第三个刺客吓得落荒而逃。1865 年6 月23 日,最后一位南军将领投降;最后一批散兵游勇——审南多亚号军舰上的官兵,也在当年11 月2 日缴械投降。”说到这里,迈克罗夫特笑了一下,好像记起了什么,“讽刺的是,他们是在利物浦投降的。当时他们为了不向北方投降,横渡大西洋跑到英国。我代表英国政府出席了投降仪式。美国内战自此尘埃落定。”
“其实并没结束。”克罗先生说,“南方依然有人在摇旗呐喊,图谋独立。”
“这就是目前的形势,”迈克罗夫特对夏洛克说,“1865 年7 月,布斯的同伙落网,上了绞刑架。遗憾的是,布斯逃之夭夭,不过据说十二天后被北方军队抓住枪毙了。”
“据说?”夏洛克觉察到了迈克罗夫特话里的语气轻重不同。
迈克罗夫特看了克罗先生一眼:“过去三年里,一直有传言说当时被枪毙的不是布斯,而是一个跟他相貌相似的同伙,布斯本人依然逍遥法外。还说布斯已改名约翰·圣·赫伦,为了保命,已经逃离了美国。他本来就是演员。”
“你们认为他现在在这里?”夏洛克说,“在英国?”
迈克罗夫特点点头:“昨天我接到一封平克顿侦探社的电报。他们的探员打听到一个自称约翰·圣·赫伦、符合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相貌特征的家伙,曾在日本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船。他们让我通知仍在英国的克罗先生。”他又看向克罗先生,“阿兰·平克顿认为,布斯是三年前乘坐审南多亚号抵达英格兰的,待了一阵子,又逃到了海外。现在,他们认为他又回来了。”
“我记得之前跟你提过,”克罗先生对夏洛克说,“我之所以来英国,是为了追捕那些在美国内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漏网之鱼。不是战场上士兵的厮杀,而是屠戮平民、焚毁城镇,以及其他罪不可恕的暴行。既然我还在英国,阿兰希望我来调查这个约翰·圣·赫伦,合情合理。”
“如果我问您,”夏洛克对克罗先生说,“美国内战期间您支持哪一方,您会介意吗?您说过您来自阿尔伯克基。我在伯父的书房里查过美国地图,阿尔伯克基是得克萨斯的一个小城镇,地处美国南部。是不是?”
“没错,”克罗先生承认道,“内战期间,得克萨斯也隶属于南方阵营。但是我出生于得克萨斯,并不意味着我支持南方阵营。每个人都有权基于更高尚的道德准则,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不经意地做了个鬼脸,“我觉得奴隶制……可恶。我不认为,只是因为肤色不同,一个人天生就比另一个人低一等。我宁愿认为,让一个人低人一等的,不是出于肤色这么武断的标准,而是出于其他理由,比如能否理性思考。”
“当然了,南方阵营一定会争辩,”迈克罗夫特不以为然地说,“一个人的肤色,就是他能否理性思考的标志。”
“如果你想判断一个人的智力水准,与他交流就够了,”克罗先生嘲讽道,“根本与肤色无关。我认识一些智力高超的人是黑人,而一些蠢笨至极的人是白人。”
“于是您转投北方阵营?”夏洛克问,他急切地想了解克罗先生不同寻常但又充满魅力的个人历史。
克罗先生看了迈克罗夫特一眼,后者正轻轻摇头。“我虽然身在联盟国,却是为合众国效力的——这么说更合适。”
“间谍?”夏洛克兴奋地问。
“是特工。”迈克罗夫特和缓地纠正他。
“那不是……不道德的吗?”
“现在我们最好不要讨论伦理道德,否则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只要接受一个事实:有史以来,政府一直在使用特工。”
这时夏洛克灵光一闪,想到了迈克罗夫特之前说过的话。“你说,平克顿侦探社要你通知克罗先生有关约翰·圣·赫伦的事。这意味着——”他胸口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你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我,而是为了见他。”
“我来是见你们俩。”迈克罗夫特温和地说,“成人世界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少仅为了某个单一的因素而做决定。成年人会同时为了好几个原因行事。你得理解这个,夏洛克。生活并不简单。”
“它应该那样,”夏洛克叛逆地说,“事情不是对就是错。”
迈克罗夫特笑了笑。“你不必尝试做外交工作了。”他说。
克罗先生则心神不定,夏洛克似乎让他有些不安。“ 这个约翰·圣·赫伦住在哪里?”他问道。
迈克罗夫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查了一下。“他在戈德明的吉尔福德路有一套房子。房子的名字是——”他又查了一下,“审南多亚。不是巧合就是暗示。”他顿了一下,“你准备怎么做?”
“调查,”克罗先生说,“这是我的任务。当然,我得小心行事。像我这样的大个子美国人,很容易被一眼认出来。”
“那就做得隐蔽点儿。”迈克罗夫特提醒他,“另外,千万别自作主张。这个国家有法律,我不希望看到你因谋杀被绞死。”他哼了一声,“我不喜欢反讽,让我反胃。”
“我能帮忙。”夏洛克突然出声,他自己都有些惊讶。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来由地自己蹦了出来。
两个大人惊讶地盯着他。
“在任何情况下……”迈克罗夫特严厉地说。
“绝对不行。”迈克罗夫特话音未落,克罗先生立刻接着喝道。
“我可以悄悄溜到戈德明,询问几个问题,”夏洛克很坚持,“没人会留意我。之前莫佩尔蒂男爵那件事,不是证明我能做一些事情吗?”
“情况不同。”迈克罗夫特辩驳道,“之前你是意外卷进去的,而且好几次情势危急的时候,总是多亏克罗先生帮你化险为夷。”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如果我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父亲永远不会原谅我的,夏洛克。”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听到别人如此描述他和莫佩尔蒂男爵斗智斗勇的事,夏洛克不禁有些沮丧,在好几个事件关键点上,他的努力都被漠视或扭曲了,不过他选择沉默以对。当你面前有更重要的事宜悬而未决时,再去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的往事,没有任何意义。“我一定不会出格,惹祸上身,”他继续抗争,“而且,我看不出到底有什么危险。”
“如果约翰·圣·赫伦真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那么他不仅是职业杀手,还是亡命之徒。”克罗先生分析道,“一旦他回——或被遣返——美国,等待他的将是绞刑架。他就像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一旦认为自己受到威胁,他必定会毫不犹豫消灭自己的踪迹,再次人间蒸发,而我则又要从头再来。我极其不希望你成为他的‘踪迹’之一,被他消灭。”
“还有,”迈克罗夫特盯着克罗先生,低声说,“从平克顿侦探社知会你的事来看,我无法确定他们对形势了解到了什么程度。不过越来越可信的是,在布斯及其同伙幕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当然会有,”克罗先生沉声说,“它被称作‘美国内战’。”
“我的意思是,”迈克罗夫特严肃地说,“据说刺杀林肯总统不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幕后主使至今还没现身。如果布斯现在真的身在英国,那他总要再回美国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来英国的意图是什么?”
克罗先生笑了笑:“如果他还要回美国,我的工作就简单多了。我要做的只是提前通风报信,等他一下船,立刻抓捕。”
“如果我们事先摸清他的意图,不是更好吗?抓住了布斯不一定能阻止那场阴谋。”
“如果真有阴谋……”克罗先生说着,摇了摇头。
夏洛克恍若置身于一场晦涩难懂的哲学辩论。他唯一明确的是:这个在他生活里渐渐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家庭教师遇到了难题,很可能被迫重返故国,或是满世界追捕凶手。如果夏洛克能为这位老师做些什么,他一定不遗余力。只要不告诉迈克罗夫特就好。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他问。
迈克罗夫特不以为意地挥手:“去郊野溜达一圈,或者做点儿别的。我们还要谈一会儿。”
“明天一早去我家,”克罗先生说,甚至都不看夏洛克一眼,“我们继续上课。”
夏洛克溜了出去,房间里的两个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谈话,关于在联邦层面上,英、美两国引渡条约的棘手之处。
屋外仍然艳阳高照。他能闻到烈日下木头被烤焦的味道,以及远处法纳姆酿酒厂麦芽发酵的清香。
戈德明镇应该没那么远,不是吗?既然那里有条吉尔福德路,那应该在吉尔福德附近才对,而吉尔福德离法纳姆很近。马修·阿纳特也许知道路。
马修——也就是马蒂,他喜欢人家这么叫他——最近一两个月与夏洛克相当熟络。他独自一人住在一条窄船上,往来于运河上的城镇之间,迫不得已时做点顺手牵羊的勾当,不过坚决不去济贫院。他在法纳姆待的时间比以往待过的任何城镇都要久,至于为什么,无论是他还是夏洛克,都没说破。
如果夏洛克打算前往戈德明,察看审南多亚那栋房子,以及住在那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杀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家伙,他希望马蒂在他身边。毕竟,马蒂救过他好几回。夏洛克信任他。
他绕过房子后院,经过厨房,到了马厩。几周前,他和马蒂从莫佩尔蒂男爵的庄园带走的两匹马还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吃着一袋干草。男爵的惊天阴谋破产后,夏洛克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那两匹马,于是偷偷塞给马夫一个先令,委托他们照管。似乎没有人发觉家里多出了两匹马。而且,这样一来,他还可以跟弗吉尼亚一起骑马。在接受她的进一步指导后,夏洛克的马术精进不少,这让他十分受用。
夏洛克给他的马上好鞍,骑马走出庄园,他的左手还抓着另一匹马的缰绳。同时照看两匹马让他快不起来,他慢腾腾地走了半小时,还没走出法纳姆的地界。不过他的方向很明确:河边,马蒂的窄船停泊的地方。
马蒂坐在船头,盯着河水出神。一看到夏洛克,他立刻跳了起来。
“你牵着两匹马……”他点明。
“对的,”夏洛克说,“你的观察力真让人震惊。”
“走开,”马蒂冷静地说,“我观察到你想让我陪你去某个地方。如果我没说错,你就不应该那么挖苦我。”
“让你说中了,”夏洛克说,“抱歉,有时候我管不住自己。”
“好了,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也许想骑马去戈德明逛一圈。”夏洛克说。
马蒂眯起双眼:“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路上告诉你。”夏洛克回答。
通往戈德明的路有一片缓坡,绵延好几英里。此处的山头是一座山脉的起点,一直延伸到远方。山脊两旁空荡荡的,郊野一望无际地铺开,消失在远方的雾霭里。
马蒂侧脸看了夏洛克一眼:“我们先沿猪背坡走一阵,然后下山,经过冈歇尔。要走一小时左右。你是想继续走下去,还是停下来歇一会儿?”
“我们歇息一两分钟,欣赏一下美景,”夏洛克说,“顺便也让马喘口气。”
“马没有事,”马蒂点破他,“你是屁股坐疼了吧,是不是?”
剩下的路好走多了,他们经过大片田野和牧地,成群的猪和羊安然地吃着青草。接近戈德明郊外时,出现了一条窄窄的小河,河上有桥,河两岸长满了齐人高的碧绿的芦苇。过了桥,左边又分出一条岔路。
“那应该就是吉尔福德路。”马蒂指着前面说,“走哪边?”
“我们先在城外溜达,”夏洛克答道,“我有预感,我要找的地方还更远,位置应该更偏僻。”
他们揽辔徐行,好让夏洛克仔细端详两旁的房子。马蒂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懒得问夏洛克他们要做什么。
很多房子没有名牌,或者比夏洛克预期的小很多。毕竟,一个称得上“审南多亚”的房子不可能寒酸破败,对不对?名字,尤其是唬人的名字,一般而言,总是与宏伟、壮观的事物相配。
几座房子外面有小孩儿在玩耍,玩陀螺,跳皮带,踢皮球。他们骑马经过时,有一两个还向他们挥手。
终于,他们到了一处宅子。马路在那里拐了个弯,加上周围树木的掩映,那座房子与周围的房子不在一起。站在路上望过去,夏洛克隐约看到门前有一块木牌子,上面刻着一长串名字,可能是以“S”打头的,也可能不是。盛开的紫藤花爬满墙壁,牌子上的字若隐若现,看不真切。
“这里吗?”马蒂问,“我们要不要过去敲门?”
“不,”夏洛克说,“继续往前,走过了房子再停下。”
经过时,夏洛克观察到:房子的门面刷成了白色,墙上有百叶窗,房前的花园被打理得很好。显然,有人住在这里。
一过了房子,两人便缓缓勒马停下。
“看样子,你显然是找对了地方,”马蒂说,“但又不想让住在里面的家伙发现。怎么回事?”
“以后告诉你,”夏洛克保证道,“我得离前门近一些。有什么好主意?”
“走上前去敲门?”
“有意思。”他环顾四周,没有什么能派上用场的东西。“能不能麻烦你再骑马回去,找到刚才那群踢皮球的小孩儿?”他在口袋里摸索半天,掏出一把硬币,“给他们几个便士,问他们愿不愿意把球借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就还回去。”
马蒂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我们大老远来这里踢球?”
“照做就是——拜托。”
马蒂叹口气,接过硬币,掉转方向,同时没忘记回头重重地哼了一声。
夏洛克下马,将马系好,耐心等着,同时靠近房子边上的树木观察。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迹象。这里真是“审南多亚”吗?抑或是别的,比如夏岛居或奇异屋①?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马蒂回来了,胳肢窝夹着皮球。
“任务完成,”他停下来说,“这个皮球没气了。”
“没关系。我们沿路往回走,边走边互相扔球玩。走到房子附近时,不管球在谁手上,都要记着故意失手,扔得越靠近房子前门越好。”
“然后另一个就跑过去捡球。嗯,好。”
“只能是我跑过去捡球。我要看清楚门牌上写了什么,你不识字,对吧?或者说,识字不多。”
于是他们沿路回去,把皮球抛来掷去。有一两次,马蒂故意把球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踢给夏洛克。
走到马路上最靠近那座房子的地方,一条小路岔出去通向房子前门。马蒂特意颠到马路对过,把球举过后脑勺儿,用力往高处抛。皮球从夏洛克头上飞过,落到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弹了一下,朝前门滚去。
夏洛克假装恼怒,在半空中挥了挥拳,然后无奈地耸耸肩,转身沿小路溜到房子前门。弯腰捡球时,他迅速抬眼扫了一眼门旁的标志牌。审南多亚。就是这座房子。现在,他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做。是留下来继续观察,以便回去向迈克罗夫特和克罗先生描述房客的情况,还是斗胆溜进屋里打探一番,如果房客恰好不在家的话?
他还来不及犹豫,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男人从黑暗中现出身影。他又瘦又高,蓄着一缕灰白的山羊胡,不过让夏洛克触目惊心的是他左边的脸颊。他一定被火烧过,而且是被严重烧伤。他脸上被烧伤的皮肤棕红,疤痕狰狞,脸上坑坑洼洼的。他的左眼眶里没有眼球,是空空的一个黑洞。
“小杂种!”他怒骂一声。夏洛克还来不及出声,就被他一把抓住头发,拖进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