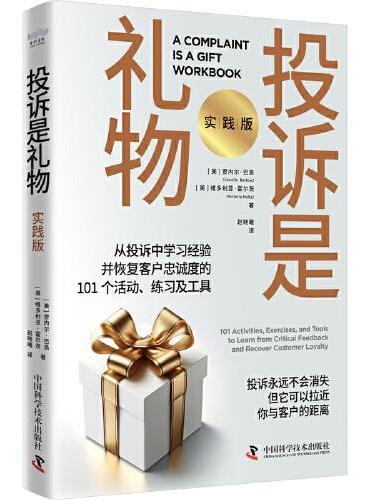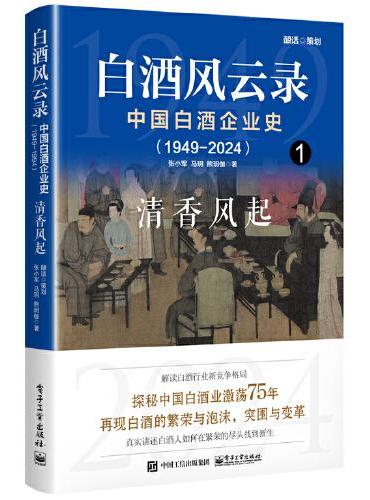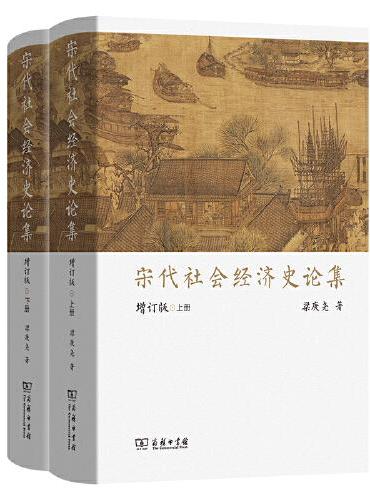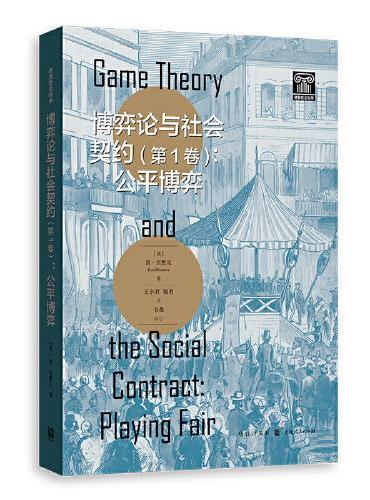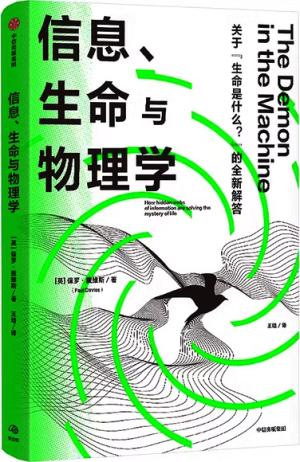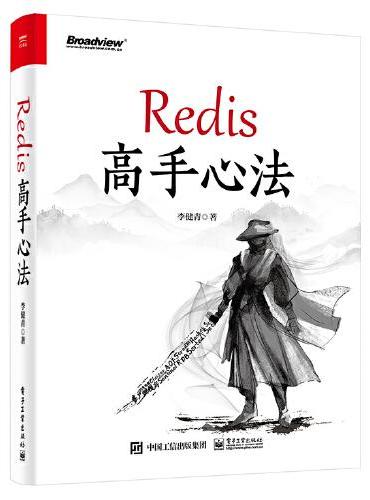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投诉是礼物:从投诉中学习经验并恢复客户忠诚度的101个活动、练习及工具(实践版)
》 售價:HK$
67.9
《
白酒风云录 中国白酒企业史(1949-2024):清香风起
》 售價:HK$
101.2
《
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增订版)(上下册)
》 售價:HK$
331.2
《
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公平博弈
》 售價:HK$
124.2
《
海外中国研究·政治仪式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建构(1911—1929)
》 售價:HK$
101.2
《
信息、生命与物理学
》 售價:HK$
90.9
《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 售價:HK$
78.2
《
Redis 高手心法
》 售價:HK$
115.0
編輯推薦:
诺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一生中不可错过的四本经典文学。本套书由法文原版书直译,并将其拗口的表述方式转化成更贴近当下读者习惯的语言。法语系副教授尹永达为其翻译,保证其准确性与文学性。书中搭配插图,令文字变得生动起来,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爱的荒漠》是作者莫里亚克的代表作。之后三岛由纪夫还写出了《爱的饥渴》致敬本书。《蛇结》被大多数评论家称为是诺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里程碑式作品。对于此书,钱钟书先生特意将阅读此书的感受收录在《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4册中,并摘抄文章且加注了英文评语。《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诺奖作家莫里亚克写作成熟期序幕的佳作。《苔蕾丝·德斯盖鲁》曾一度引起法国舆论界的轰动,并被《法兰西信使报》认为是可媲美《恶之花》作者波德莱尔作品的一部“令人惊叹的杰作”。
內容簡介:
《爱的荒漠》
關於作者:
【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內容試閱
《爱的荒漠》